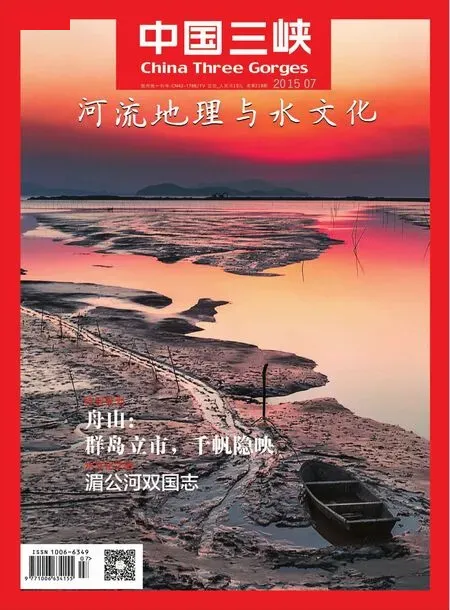記憶中穿越的邊境線
文、圖/喻添舊 編輯/李顏岐
記憶中穿越的邊境線
文、圖/喻添舊編輯/李顏岐
從瑯勃拉邦到昆明的跨國巴士緩慢地蛇行在老撾北部的崇山峻嶺之間,離湄公河的干流越來越遠。蜿蜒的盤山道坑洼顛簸,塵土飛揚。期間除了偶爾幾處標示著中國公司的建筑工地之外,就只有突然出現在半山腰的孤零零的破舊民房了。直到經過城鎮勐賽之后,依然曲折的道路才變得稍微平整,路面開始漸漸被水泥鋪就。那里距離老中邊境只有30多公里了。
在老撾磨丁口岸的邊檢室中,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員企圖索要2萬基普(大約15塊人民幣)的小費,背包客們通常把這稱為賄賂。遭到我的堅定拒絕之后,他不耐煩地揮揮手讓我通過了。接下來我與十幾個中國人一起邁步走進中國,這種感覺很奇妙。他們有去萬象出差歸國的上海工程師,有在唐人街開飯店的四川和廣東老板,也有在數不清的中資橡膠或木材工廠里打工的年輕人,背包客反而沒那么多。看起來更為高大堅固的磨憨口岸大樓中,年輕武警與我搭訕:“你給我講講,老撾那邊是什么樣的?”語氣中絲毫沒有邊檢的嚴肅,隨后又補上一句:“雖然我們離老撾這么近,但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去玩。”
這句話是邊境生活的直觀縮影,我回過頭看向國界的另外一邊,炎熱的蒸汽混雜著灰塵,籠罩在“中間區域”特有的謹小慎微和倉促匆忙之上,透過這層朦朧的迷霧,老撾和柬埔寨的旅行在我腦中似乎第一次開始變得輪廓清晰了。
一星期前柬老邊境的某個傍晚,穿越邊檢的經歷并沒有回國這般令人愉悅,那一次我未能省下同樣沒有依據卻被公開索要的2美金——無論是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還是法國人,每個到達邊境的背包客都被以不予蓋章來威脅對待。之后背包客又開始了由于老撾人毫無守時概念而導致的漫長且不確定的等待。預定下午四點從口岸邊檢站出發的巴士直到七點才到達,更多人已經在這里等待了4個或者6個小時。這種旅行時間的耗費比“區區2美金”的“蓋章費”還令人沮喪,無論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美國人。不過這一次法國人不同了,他們樂天的性格和講笑話的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一位來自巴黎的大廚一邊吐槽老撾人做事效率的低下,一邊喋喋不休地將他的菜譜分享給我以打發時間。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歐洲人都更喜歡到老撾旅行,但他們對祖輩曾在這同一片土地的到達與離開毫不在意,他們只享受今天的一切,甚至享受你永遠不知道將會發生什么的漫長等待,享受在老撾旅行所經歷的所有不確定。
“你‘生氣’嗎?”他突然探過脖子悄悄地問。
“有一點吧,據說接下來到達萬象的交通將十分辛苦。”
“我聽到的說法是恐怖至極,如果可以,我真想替我妻子租一個臨時屁股。但是我才不在乎,法國人在老撾從來沒得到過什么真正享受。事實上——話說回來你覺得我的廚藝怎么樣?你知道,我們法國人說‘Angry’的時候實際上說的是‘Hungry’——那么,我是說,你‘生氣’了嗎?”我承認在邊境無謂等待的時間足夠吃上一頓禮節齊全的法餐了。
“在老撾一切都是未知的!”
夜幕深沉,法國廚子對我說了最后一句話,轉身和妻子坐上塞滿白色臉孔的皮卡(被老撾人充作旅行巴士)絕塵而去——車上的人全是去往四千島的,那里的夕陽和朝霞據說十分慷慨。其他人繼續等待,等待不知何時才會到來的車,去往巴色或萬象。

普西山頂俯視瑯勃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