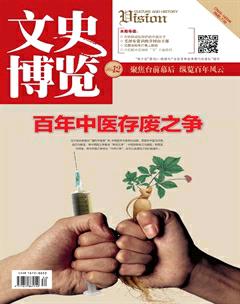蔣介石送父親“五子從戎”匾
李烈鈞小時候非常聰慧,貫通經學,1902 年以武寧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江西武備學堂,1904 年被清王朝選派赴日本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再入士官學校習炮科。1905 年8 月,李烈鈞在東京神田俱樂部聽到孫中山的革命演說并為之傾服,由此開始了革命生涯。
革命黨人不爭功
民國成立后,李烈鈞出任江西都督,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深得民眾擁護。袁世凱曾用200 萬元為李烈鈞祝壽,并提出為他晉勛,想收買他,但都被他拒絕。1913 年,宋教仁被袁世凱刺殺,隨后袁世凱又進行了“善后大借款”。
當國民黨上海總部還在爭論對袁世凱是武力征討還是法律裁決時,李烈鈞于7月12 日在湖口起義,就任討袁軍總司令,打響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槍。有人提醒李烈鈞,無論從哪方面講,國民黨肯定會失敗。李烈鈞答:“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打,這關系到我的人格問題。”他在討袁通電中說:“寧做自由鬼,不做專制奴。”當時,李烈鈞在江西的地位非常穩固,起兵反袁就意味著放棄巨大的既得利益。李贛騮說:“父親的心中只有共和自由的信念,為此堅持了一生。”
在李贛騮幼年的印象中,人們經常會在不同場合問李烈鈞,到底他與蔡鍔、唐繼堯3 人,誰在護國運動中的貢獻最大?“父親總是說作為革命黨人從不爭功,同時父親總是將唐繼堯放在第一位。其實在這次運動中,父親視死如歸的革命氣概,對當時舉棋不定的唐繼堯起了關鍵的作用。”
幼年的李贛騮雖然對這些不能完全理解,但父親那種不居功自傲、為國家民族利益不計個人得失、無私奉獻的精神,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當年,上海大夏大學(1924年因學潮從廈門大學脫離出來的部分師生在上海發起建立的私立大學,1951年與光華大學合并成立華東師范大學)的教授寫了一副挽聯,吊唁孫中山逝世:“二十年革命辛勤,排滿倒袁,百戰相依惟一李;四萬萬人民愿望,興邦建國,千秋遺憾在三陳。”其中的“一李”就是李烈鈞。孫中山生前曾這樣稱贊李烈鈞:“協和(李烈鈞別名)先生上馬能武,下馬能文,誠不可多得之當代儒將。”李贛騮說:“當年父親身體不好,不能遠行,由我二哥李贛駒代表父親去了南京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公祭活動。”
李贛騮幼年時期,李家輾轉到重慶,蔣介石為其安排了住處,卻被李烈鈞謝絕,全家寄宿在歌樂山上的馮玉祥宅。“從我7 歲剛記事起,就感覺到父親與馮玉祥都很反感蔣介石的獨裁。一次在外出的路上,馮玉祥對父親說,他白天去見蔣介石是打著燈籠去的,說重慶太黑暗,看不見世道。父親也預言‘安中國者,必共產黨也!涉世不深的我,那時就對國民黨的腐敗與黑暗有了印象。”
秉父遺志,五子從戎
李贛騮說:“父親是江西人,按輩分是‘烈字輩,我們是‘昆字輩,但為了讓我們不要忘記家鄉,父親把我們的排行都改為‘贛。”李贛騮說,因為父親屬馬,且很喜歡馬,所以兒女中有7 人的名字都以馬命名,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多有“馬”字旁。
李烈鈞晚年中風,半身不遂,不得不淡出政治活動,只掛名國民黨中執委。李贛騮說,“父親對于自己到處呼吁抗日,結果到了抗日的時候,自己卻到云南大后方養病感到慚愧,這違背他的心愿。” 李烈鈞共有10 個子女,盧溝橋事變后,他把身邊到了服兵役年齡的5 個兒子都送到軍隊。在給兒子們的贈詩中,他寫道:“我送兒輩出鄉關,殺盡倭寇方回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蔣介石為了褒揚這一愛國舉動,送了題有“五子從戎”的匾額。但遺憾的是,李烈鈞終因病重,于1946 年2 月病逝。國民黨為李烈鈞舉行了國葬,由蔣介石親自主持追悼會。
直至今日,李贛騮還對中共代表吊唁父親的情景記憶猶新:“當時正值重慶談判,在重慶的毛澤東委托周恩來、董必武、葉挺等前來吊唁,我們兄弟姐妹正身著孝服跪在靈堂行禮。只見董必武手撫棺材說,李老先生,您的‘寧為烈士魂,不做亡國奴的遺言我們銘記在心,將付諸行動。”
李贛騮深有感觸地說:“父輩同仁們身處逆境時所表現出的凜然正氣、愛國義舉和心系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勵我們為早日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加快民族復興偉業盡心盡力。”
李烈鈞相當尊重子女自身的發展意向,子女們有的去了南開大學,有的去了黃埔軍校,有的到了美國留學。1941 年,只有十三四歲的七子李贛骕(音同“肅”)向李烈鈞提出想參加海軍。當時海軍是不受重視的,但李烈鈞聽了以后非常贊同。臨行時,他還讓兒子把一條云南當地的優質火腿掛在身上,以為入伍之禮。抗戰勝利后,李贛骕去英國海軍學校學習,1949 年在海軍起義中被害。
李贛騮說:“二哥李贛駒和七哥李贛骕都在海軍服役;三哥李贛熊擔任遠征軍隨軍翻譯,四哥李贛驥跟著部隊守黃河;五哥李贛驊則從駝峰航線飛赴印度學習坦克技術,開著坦克從印度入境。我從小就立志要像他們一樣。”
李烈鈞平日待人平和有禮,就是對自己的下屬也不例外。有一次,他讓八女兒叫家里的大廚過來談話,女兒很隨意地喊了一聲:“廚師,過來!”李烈鈞立即教訓她:“怎么能這樣沒禮貌!你是要請他過來,必須好好地說一個‘請字! ”隨后讓女兒罰跪了許久,直到快吃午飯了,妻子來為女兒求情,李烈鈞才讓她起來。
李贛騮說:“我的家里軍人多,在這種氛圍里,我耳濡目染,小時候就常常頭戴軍帽,肩佩徽章,腰別手槍。我從小就想當兵,追隨炮兵出身的父親。”李贛騮依次選擇了炮兵、坦克兵、海軍。可遺憾的是,他的視力有100度近視,上前線的夢想就這樣泡了湯。
不過抗美援朝一開始,李贛騮還是告別親人,從江南北上,成為哈爾濱醫科大學代培的俄文醫學系學生,培養目標是戰地醫學翻譯。1955 年1 月,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聽診器坐診的李贛騮,被分配到北京中蘇友好醫院(現友好醫院)給內科專家做翻譯,不到一年又被轉到中直第三醫院(現鼓樓醫院)當婦產科專家譯員。
“文革”中,李贛騮深受迫害。1981 年,他獲得第二次政治生命,步入政壇,當選為邯鄲市副市長,正式成為民革的一員。兩年后,出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不多時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贛騮晚年依舊力所能及地繼續為民革事業、為祖國統一發揮自己的余熱,他多次到臺灣“黨史”館和臺灣“國史”館查閱、復印有關父親李烈鈞的文獻資料,籌備出版李烈鈞的全集。他忘不了李家恪守的原則:“‘官是人民給的信任,‘當官是一種責任,‘官有多大就得負多大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