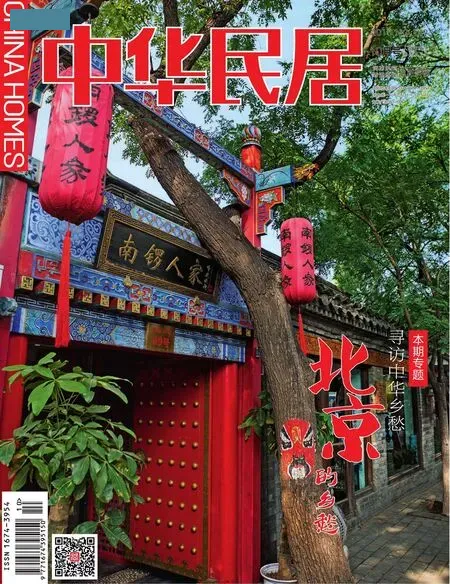延承千年 厚積薄發
延承千年 厚積薄發

顏之推,北齊教育家,其所著的《顏氏家訓》在我國家庭教育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余地也。
——《顏氏家訓》

中國家風之旗,圖騰是日月,但與陰陽無關,寓意為每一個家庭的時光一半用于日間的勞作,一半用于夜間的自省。從家風的歷史沿革,去打撈它的前世今生,沒有誰不被它生生不息的進取之勢折服。它與嚴整莊嚴的宅院共存,卻又比它們多出縝密的邏輯與豐富的內涵;它自儒家治世思想的根基衍生,從那久遠到幾乎以為與天地同歲的 《周易》 而來,傳遞給我們智慧的訊號。
《易·序卦》云:“有天地后有萬物,有萬物后有男女,有男女后有夫婦,有夫婦后有父子,有父子后有君臣,有君臣后有上下,有上下后禮義有所措。”家風乃于禮義之中萌芽,為父權文明的產物,文明高臺加速了它的拔地而起。為了讓社會保有安全感,先民們對家庭關系的規定顯得格外絮絮叨叨——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貞。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無仗遂在中債,貞吉。九三,家人嘀嘀,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從中我們可以讀出一種義正詞嚴的態度:其一,男子司防守家園之職,防內禍除外患;其二,女子無需有抱負,只需承擔持家重任;其三,家庭教育應當威嚴,家人之間不可嬉笑、哀怨,當安分守己,謹小慎微。




《周易》可謂是最早闡釋家庭人倫關系的典籍,它詮釋著家庭和諧的齊家之道、男尊女卑的夫婦關系、趨吉避禍的利害選擇、自強不息的立身原則、知崇禮卑的美德追求。如,“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的軸心關系就是自此而恒定,家長權威的思想也自此深入到華夏大地的每一寸國土里。男主外、女主內,在農耕社會合乎天地之大義。在學校教育尚未形成氣候的時代,父母為一家威嚴教化之長,是育化最早的傳道者。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家道則正;家道得正,則能天下安定;家人和睦,循禮守距,團結一心,便能一世乃至幾世不散不滅。這種家道觀是旗幟的標桿,是頂天立地的主心骨,因為“家道”就是最小單位的“國道”。家道定天下,家風需將這份道傳揚后世,囑托未來。
家風在幾千年的歷史里,也足夠用心。北齊時誕生了“古今家訓之祖”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這本書打開了中華家訓的思想閘門,最先提出了家庭管理需要“風化”(家風教化)。于是,唐朝柳玭的《家訓》,宋朝朱熹的《朱熹家訓》、司馬光的《家范》、陸游的《放翁家訓》,元朝鄭泳的《鄭氏家儀》、鄭濤的《旌義編》,明朝龐尚鵬的《龐氏家訓》、高攀龍的《家訓》、曹端的《家規輯略》,清朝孫奇逢的《孝友堂家規》、朱柏廬的《治家格言》、蔣伊的《蔣氏家訓》等不計其數的家訓著作與篇章,如滔滔江水隨之而來,為那一幢幢紅漆大門后的廳堂樓閣,為那一戶戶同宗同族的世代同堂,為那一天天毗鄰而居的家長里短帶去了法則、制度、約束、信仰。就連帝王之家也不能免俗,唐高宗的《帝范》、明仁孝文皇后的《內訓》、清康熙帝的《圣諭廣訓》等等,不一而足……

顏之推的生平如今已考證得足夠詳細,他的一生無非是生逢亂世的“獨善其身”。那位特殊年代里的“三為亡國人”何其苦,苦到那么恰如其分地孕育出一本名揚千古的《顏氏家訓》。歷史里的苦難總是辯證而生,顏之推自覺人生悲苦,無力于治國平天下,于是將齊家與修身作為頭等大事,殊不知卻無心插柳,家族百年之后誕生了諸多賢能子孫。《顏氏家訓》也讓世人第一次明白,個人的修養可以為家庭更好地服務。
家訓都一致強調,顧家是最基本的善行,任何人必以家為重,這是任何時代都無法改變的家風!我們足可以遐想,千百年來多少個黑沉沉的夜晚,在那些如豆的燭火下、光明如炬的廳堂里,有多少家訓在須眉皓白的老者嘴里娓娓道來。一代又一代人重復著祖先們曾做過的事情——庭訓。兒孫們謙恭地聆聽著教誨,盡管那些早已經耳熟能詳。
“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
“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
是非善惡的點化,將會正式拉開忠誠孝悌、禮義廉恥、謙謹通達、端慎持重的道德差距。家訓將家風具象為文字,家風就可以在更加光明敞亮的青天白日里,代替日漸衰老的長輩,繼續訓育和指導這面旗幟之下長久屹立的人……

《孟母教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