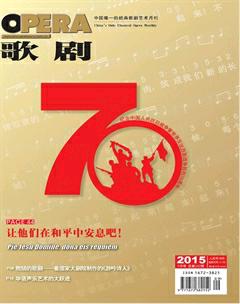田川的歌劇創作論
黃奇石



編者按:劇作家田川作為民族歌劇的又一面旗幟,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歌劇發展的歷史,可謂是了如指掌。本文通過連載的方式,較為全面地梳理田川的歌劇思想,反映出這位歌劇前輩獨到的藝術見解與正確的歌劇史觀,為后人提供一點可資借鑒的經驗。
田川同志一生為人謙和,創作方面,我們只見他總是替別人的作品說好話,很少為自己的作品說什么,包括創作經驗談之類。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歌劇劇作家,對于歌劇創作方面的見解,比某些缺少創作經驗的“空頭”理論家的種種“高論”,一定會切實得多也有用得多。
《歌劇研求錄》
翻檢《田川文集》第三卷“文論集”中,有《歌劇研求錄》一文,是他留下的有關創作心得方面十分罕見的文字。尤為難得的是,這是1962年廣州創作會議之前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的一次小型歌劇座談會的筆記整理稿。時隔50多年,已經具有文獻性質。據田川整理時介紹,此筆記是“文革”中他被抄走的大批劇稿、手稿中后來被退還回來的、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他將其視為“珍寶”,1990年特意加以整理、發表。
《歌劇研求錄》(以下簡稱《研求錄》)是一次會議的筆記,盡管田川說“那些精彩的論點出自何人之口,我仍能記得起”,但他整理成文時并未一一指明發言者是誰,僅列出了一位他稱之為“我的老師和合作者”——馬可同志,說“他發言時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眼前”。筆記中雖也錄有一些不同意見,但田川整理時基本上是正面闡述的居多。因此這份文稿我們可以視為以馬可、田川為主的有關歌劇創作的“談藝錄”。田川題為“研求錄”雖是謙詞——用他的話叫“留作自學之用”——但其中一大部分應是他認同與抱持的見解。至于最后一部分“關于《小二黑結婚》的改編”,是他應邀在會上所做的介紹創作經驗的發言,則完全屬于田川個人的了。
該《研求錄》包括“關于歌劇的形式問題”、“關于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問題”、“關于歌劇題材問題”、“關于劇詩和道白問題”以及最后談改編《小二黑結婚》等五個部分,通篇充滿了藝術辯證法的見解。下面分別略作介紹。
1.“關于歌劇的形式問題”
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是什么?有人說二者是不可分的,如“形象”,算是內容或算是形式?很難分開。有的認為形式和內容,不能合二為一、混為一談,形式還是存在的:“形式與內容,有如一枚錢幣的正、反兩面。”
這本是美學范疇里一對矛盾的概念,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一定的內容要靠一定的形式才能得到表現,反過來,某一特定的形式總是要為某一特定的內容服務的。如戲曲,既有其表現的內容,又有其表現的形式(所謂的“程式”也是形式之一)。沒有內容,形式無從依附;沒有形式,內容無從表現。二者是藝術中既矛盾又統一的兩個方面,是辯證的、發展變化的;而不是機械的、靜止不變的。錢幣正、反面的比喻顯然并不恰當。
內容也好,形式也好,都不可能憑空產生,而是產生于生活,既表現生活而又隨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就新歌劇的產生而言,“也是由于感到戲曲不足以表現新的內容,才產生了新歌劇的形式”。生活變了,內容不能不變;內容變了,形式就不能不變。《白毛女》演喜兒,戲曲的“蘭花手”、“水袖”之類自然就不能用了。
尤其是新歌劇作為表現新的生活、新的內容與形式的新劇種,“還是個年幼的劇種”,一開始是不可能成熟的。“它需要幾十年,甚至一兩個世紀,才能趨于完整和成熟。”而要使它逐漸成熟起來,就必須吸收各種有益的養分,才能生長得好,才能枝繁葉茂、結出碩果。
歌劇是現代的音樂戲劇,它有兩大藝術寶庫可供學習與借鑒:首先是中國的戲曲,其次是外國的歌劇。就歌劇的形式來說,有音樂形式與戲劇形式。舊戲曲的形式如結構的分“出”、分“折”與多“出”、多“折”,很多已不適合新歌劇所表現內容的需要,所以大多改成了像西洋歌劇分幕分場的結構形式。對于這一點,歌劇界幾乎沒有什么爭議。爭論最大的是音樂的形式,也就是當時被稱為“土洋之爭”的那場大論辯。其中較為中肯的意見是:不是討論新歌劇應不應該學習、吸收和借鑒中國戲曲或西洋歌劇的問題,關鍵在于,“我們只能就它吸收、借鑒戲曲或西洋歌劇的經驗來反映生活時,運用得是否得當、是否有生硬的地方,來進行評論。而不能怪罪于學習”。也不要“非消滅了甲種,乙種才能站住。二者似乎是不共戴天,應該可以共戴一天”。
關于音樂的形式,有人認為音調應該更多地從生活中來。“如果在創作中沒有從生活中得來的創作沖動,沒有來自生活的新鮮的音樂語言,不論是搬來貝多芬或是梅蘭芳,都是創作不出來的。《洪湖赤衛隊》的成功,是作者多年在洪湖生活的結果,并不僅僅是從‘三棒鼓的曲調變化而來的。《白毛女》的音樂,也是大家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激動,內心火辣辣的,一邊寫一邊哭鼻子,才創造出來的一種音樂形式,并不是從開始就想到要創造某種什么形式。”歌劇音樂主要是刻畫人物音樂形象、抒發人物內心感情。人物的音樂主題(動機)、旋律性要好,戲劇性要強。音樂的戲劇性與戲劇的音樂性都要結合得好,缺一不可。“有人說《劉三姐》是‘歌舞劇的典,恐怕不符合事實。它在(音樂)戲劇化方面,是很不夠的。民歌本身并不能原原本本地成為戲劇性的東西。民歌,不論它多么深刻完整,但對歌劇音樂來說,仍然只是素材。”
有人提出“創造新程式”,“不應該是關著門脫離內容地另設計一套,而是從生活中或舊有形式中發展出來。”像《白毛女》中喜兒捏窩窩頭的動作,是從生活中來的,用多了不也是新程式嗎?李少春演楊白勞,按了手印后,看著血紅的手指,來個“對眼”,表現昏厥時來個“僵尸倒”,也運用得恰到好處,賦予舊有的程式以新的生命。
對于如何借鑒西洋歌劇的音樂形式,有人認為解決了朗誦調,就解決了中國歌劇的問題,主張把對白中的虛字刪去,譜成朗誦調,或主張盡量取消對白。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西洋歌劇的格式也不盡是“從頭唱到底”。“在德國演出的《卡門》用的是古老的本子,該唱就唱,該說就說。德國音樂家也不認為有說白的就不是歌劇。”據說歌劇《卡門》原是意大利文,傳到德國后,由一位不懂意文的作曲家把道白全譜了曲,他們聽起來也覺得很別扭。
必須指出的是,時至今日,認為“一唱到底”才算是歌劇的偏見,根深蒂固,影響很大。對《白毛女》所謂“話劇加唱”的貶斥就是一例。殊不知中國戲曲行內有“千斤道白四兩唱”的行話,有時“白”比“唱”還要重要。歌劇也是詩劇,劇中的“白”,也應是詩,如《白毛女》中的很多道白。不管是否有韻,歌劇的道白都應講究節奏感與音樂性。有行家認為這就是中國歌劇的“宣敘調”,實在頗有見地。道白式的、說唱式的,都可以寫成中國式的“宣敘調”,完全不必按照西洋歌劇的寫法。總之,關鍵不在于唱多唱少,而在于唱的是不是地方。
2.“關于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問題”
《研求錄》中提到,對于生活與藝術的關系,會上有同志作了個很通俗的比喻:“生活如果是黃豆,歌劇就應該是豆腐,而不能只是豆漿和豆渣的混合物。”從生活到藝術,應該有個提煉加工的過程。但我們的某些創作中,“缺少點豆腐的鹽鹵,豆漿凝結不起來,只好請觀眾喝豆漿吃豆渣了”。這與創作如同將生活的礦石提煉出各種金屬是一個道理。
《研求錄》還寫道:歌劇的形式感是很強的,它的戲劇、音樂、詩歌、舞蹈等要素,都是要講究形式的。因此,它最排斥自然主義。“中國戲曲就最反對自然主義,它總是和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又使你覺得很真實。”例如,古人的宴會,難道只喝酒不吃菜嗎?但戲曲中,多大的宴會,也只是幾個酒杯,喝的還是空氣。觀眾誰也沒提意見。它要表現生活中優美的東西,就必須丟掉一些繁瑣的“豆渣”。我們繼承傳統,就要繼承這些。“某些歌劇,常擺脫不開自然主義的束縛,被生活的原樣限制太死,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還追求自然形態的‘真。……其實臺就是個有限的空間,無論如何求真,也不可能把無限廣闊的世界裝進這斗室之間。舞臺上的一切都是假設的。”
有人舉出袁枚詠《假山》詩:“半倚青松半掩苔,一峰橫豎一峰回。高低曲折隨人意,好處多從‘假字來。”編劇,何嘗不是像布置一座假山呢?從編劇到演出,都是要通過“假”的手段,而取得真的效果。
3.“關于歌劇題材問題”
選材是創作的頭一道關,如同雕刻,選什么材料是先要考慮的事。選材選對了,雕刻起來得心應手;選塊糟石頭,高手也無能為力。
歌劇題材的選擇尤其挑剔,因此也尤為重要。《研求錄》記錄了會上關注的是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是題材“寬與窄”的關系。
新歌劇之所以稱為“新”,是因為它反映新的生活、描寫新的人物、表現新的思想內容。但有人把它弄得很窄,“只能寫當前重大的題材,否則就不是新歌劇。”從真理的全面性看,有主導方面,也應有次要的、破格的方面,不能絕對化。反映現代生活應是新歌劇的主流,但也不要因此而妨礙神話、傳說和歷史題材的歌劇創作。如按新歌劇的特點,來重新處理《牡丹亭》就很有意義。
有人不同意題材分主次,因為一提“主導”,就常常成了“壓倒一切”的了。“但是我們當代的劇作者,總要反映當代生活、創造當代人的形象,專門搞古人,有愧于‘當代兩個字。”
其二是歌劇題材的特點。
有人認為歌劇是有自身的特殊性的。“它的基礎應該是詩。‘大喜大悲、‘有激烈的沖突、‘充滿著激情、‘富于詩情畫意的題材,便適合于寫歌劇。它最忌諱‘說理性強的東西,如開會、打電話、斷官司、作結論之類。”它還忌諱情節性太強的場面,作者忙于介紹情節,就沒有筆墨來描寫人物的內心情感。
歌劇的各種體裁,對題材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例如喜歌劇,如沒有抒情性,就不成其為喜歌劇。抒情的地方才有好唱;最喜劇的地方往往不唱,縱使唱了,也是特型的唱。”
“詩情畫意”從哪里來呢?“歌劇作者,必須具有詩人的眼光,來對待和表現生活。他應該養成這種職業的特長。”歌劇作家在生活中,像蜜蜂一樣,隨時采花,隨時釀蜜。“他觀察生活的著眼點是不同一般的,他腦子里整天想的應該是歌劇舞臺,哪里該唱。”——在生活中發現詩意,詩意最后積累成一個藝術構思,產生了創作沖動。“所以,詩意是不能杜撰的。技巧,只有在來自生活的詩意時才有用處。”
那么,什么題材好寫歌劇?“能發現詩意的題材就能寫。工人生活如有詩意、有藝術的境界,就能出現好的歌詞和音樂。”因此,結論是:“我們的現實生活是豐富的、寬廣的,如果再加上歷史題材和神話傳說,歌劇題材就不會窄了。”
4.“關于劇詩和道白問題”
歌劇是音樂戲劇。這音樂主要是聲樂,是歌唱。因此,它與話劇不同,有大量的唱段,劇本有大量唱詞,既是歌詞也是劇詩。這本來古已有之,戲曲也是音樂戲劇之一種,它的唱詞也是劇詩,而且是極美的劇詩,如《西廂記》《牡丹亭》等。
《研求錄》上記錄了會上有同志說,自從有了字幕后,有些歌劇的唱詞就露餡了一一枯燥無味,干巴巴沒有感情、沒有性格,既不生動,也不優美,只是一些噦嗦的大白話、大“水詞”。有些唱詞寫得很“板”,從頭到尾,總是七字句,整齊劃一,像個“豆腐塊”。作曲家最怕的就是這種“豆腐塊”式的唱詞,旋律、節奏都被框住、被限得很死,無法自由、盡情地發揮。
有的人還認為:“劇詩,是在巨大沖突中產生的一種時代感很強的東西,是和一般的所謂抒情相距很遠的東西。劇詩中高級的境界,不是廉價的花啊草啊之類。面對自然的抒情,是常見的;而面對殘酷的現實遭遇而抒情,才是新鮮的、深刻的。”
歌劇中的人物如何抒情?有觀點認為,人物應該放在斗爭中。最好的戲劇性抒情,是斗爭最尖銳的抒情。有些戲,在毫無沖突的情況下大抒其情,毫無意思。精彩的唱段、抒情的場面,要用戲劇沖突、人物性格發展的場子鋪墊起來。如“洪湖水,浪打浪”,就不是戲劇的抒情:而韓英獄中生死關頭唱“娘的眼淚……,”,就是戲劇性很強的出色唱段。
劇詩的雅與俗的關系。“大雅若俗”,反之亦然,二者是辯證的關系。歌劇是戲劇的一種,是“大眾”而不是“小眾”的藝術。太雅了,容易脫離群眾。昆曲就是因為過于走向“雅”而為“俗”的京劇所取代。有人認為,“真正的戲劇語言,不可能避開粗俗的語言。以為這樣就不抒情了,是不對的。因為抒情詩只取了生活的片段,而劇詩要表現完整的生活面。所以,不能避開這種東西。莎士比亞作品中就有不少粗俗的東西,關漢卿的作品中也有不典雅之處。”
關于唱與白的關系,也同樣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只有“說”沒有唱,就成了“話劇”;而只有“唱”沒有“說”,從頭唱到尾,也會顯得“平”、顯得單調。“文似看山不喜平”,戲也如此。如上面所提到的,有人輕視“道白”,主張刪掉道白,或盡量減少道白,“一唱到底”,都是不明白中國戲曲“千斤‘道白四兩‘唱”的道理,不明白東方音樂戲劇“唱、念、做、打”缺一不可的傳統。道白與唱段,都是歌劇中有機的組成部分。“研求錄”寫道:“當然,在具體的每一部戲中,會有所側重而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側重于唱,有的側重于做…….這是我們的好傳統,應該繼承下來。而問題不在于唱多唱少、說多說少,而在于唱的說的是不是地方、唱詞說白是不是精彩。”
5.“關于《小二黑結婚》的改編”
歌劇《小二黑結婚》改編自趙樹理的同名小說并獲得巨大成功。名著改編,是歌劇成功的一條重要的途徑,古今中外都有實例。中國戲曲名著《西廂記》《長生殿》等、西方歌劇名著《茶花女》《奧賽羅》《卡門》等,就都是名著改編成為經典之作的。因此,歌劇《小二黑結婚》引起與會者熱切的關注,希望作者介紹改編名著成功的經驗。
會上,田川同志談了與改編有關的幾個問題。
其一,改編的必要性。
他認為,歌劇不好寫,“劇本荒”是經常發生的現象。“一個上百人以至更龐大的歌劇表演團體,長時間沒有理想的新劇目上演,很難擺脫嗷嗷待哺、萎靡不振以致離心離德的困境,當然更談不上什么繁榮與發展。”而名著改編是改變“劇本荒”的重要途徑。中外戲劇都有很多改編的劇目,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超過原作的價值和影響,成為膾炙人口、流傳久遠的經典之作。因此,“我們對改編不應有任何歧視,相反,應加以重視和提倡。”“我希望今后有更多改編名著的歌劇問世,以豐富歌劇的上演劇目,讓歌劇事業更加繁榮。”
其二,改編就是創作。
田川認為,創造性的改編就是創作。如果只是機械地按照原著的章節來分幕分場,照抄原著的情節和對話是不行的。“小說與歌劇,到底還是兩種不同的體裁。前者是印成書籍,供人自由閱讀;而后者則要通過舞臺形象,訴諸觀眾的聽覺、視覺,供觀眾在劇場中集中欣賞。”這種區別,決定了同樣內容,要有不同的處理手法。
比如,對題材繁簡、取舍,有很大的不同。小說可以通過敘述來介紹人物,而歌劇則通過人物自身的舞臺動作來刻畫人物,敘述的效果就差得多。如原小說中介紹金旺兄弟的兩段文字,讀來印象頗深,而放在舞臺上效果就差了。
再如,對結構的要求也不同。小說有敘述、有描寫,長短盡可隨意,結構相對自由。“歌劇是以歌唱和音樂作為主要的表現手段的,必須把劇情推到一定的高度,把人物放在富于詩意的情境中,讓人物的心中充滿了詩的激情,才能歌唱得自然……”因此,歌劇的結構,要比小說更加集中和嚴謹。
其三,是如何忠實于原作精神的問題。
首先,“從原著中抽出了基本的故事梗概,即小二黑和小芹這一對年輕人,在爭取婚姻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斗爭中,戰勝了愚昧、落后、迷信的二孔明、三仙姑,戰勝了封建惡霸勢力的代表金旺、興旺,作為歌劇的貫串行動線”。劇作者據此去選擇歌劇所需要的人物和情節,這樣就得刪掉一些東西。如金旺的兄弟興旺這個人物刪掉了,“神仙的忌諱”這一章里所描寫的“不宜栽種”、“米爛了”兩個生動的小故事因和貫串線關聯不大也割舍了。而把小芹與二黑的愛情及其所遭到阻撓等情節,加以強調和渲染,以更集中地表現原著的意圖。
其次,對原小說喜劇風格的理解與把握。
田川認為,要做到準確的理解與把握,是有難度的,且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我想起魯迅先生為悲劇和喜劇所下的定義:把美的東西毀滅了,便是悲劇;而把丑的東西毀滅了,則是喜劇。依此,趙樹理原小說便是喜劇風格,據它改編的歌劇也應是一部喜歌劇。
然而,當田川、馬可他們下去小說故事發生地、山西的左權一帶山區里深入生活時,耳聞目睹了很多男女青年為追求婚姻自由而遭到殘酷迫害的事,有些甚至是駭人聽聞的。即便是小芹與小二黑的生活原型,其命運的結局也十分悲慘:“小二黑”被金旺等人活活打死,吊在他家的驢棚里;而“小芹”則被“三仙姑”逼嫁給一個老商人,遠走牡丹江去了……
所有這些悲慘情況,都激起作者們極大的同情與義憤。他們將這種感情傾注在劇中。“歌劇初次上演時,小芹從家里逃出來和二黑在崖畔相見等段落,舞臺氣氛被處理得相當沉重,帶著濃厚的悲劇情調。這種處理和原作那種熱情、明朗、充滿著輕松幽默的筆調,是很不調和的。”“雖然那段戲的音樂寫得相當委婉動聽,我們在修改時,還是堅決地舍棄了。”趙樹理的高明之處在于“不是照相似的把生活記錄在他的作品中,而是站在更高角度來觀察和處理生活素材,把他同情的人物理想化,賦予他們以勇敢的精神和剛強的性格,在斗爭中獲得了黨的政策的支持,終于戰勝了愚昧落后和封建殘余勢力”。反映生活又高于生活,他把生活中的悲劇轉化成為舞臺上的喜劇,真善美最終戰勝了假惡丑。
最后,田川也沒忘記強調指出,因原作是成熟作家的作品,“它是經過了高度提煉和升華了的生活結晶品,而我們改編者,對農村生活的積累與趙樹理同志相比,卻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增刪修補之間,難免有許多‘削足適履‘佛頭著糞的地方。正如有人指出歌劇改編本的缺陷時所說的那樣,我們缺乏足夠的生活……”這是謙詞,也不全是謙詞。因為任何藝術品,都不可能盡善盡美的。至于田川說該劇的成功主要靠原作的成就和影響,以及馬可等同志在音樂上和演員在表演上的成就,那完全是他的謙讓了。
田川有關歌劇創作較為集中的論述,除了1990年整理的《歌劇研求錄》,還有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那就是他《在1996年全國歌劇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的發言》。發言的前一大半,主要談當前歌劇發展態勢及點評參演劇目,后面則集中談了對今后歌劇創作的若干意見:“關于如何繼續向上攀登,我想談談我的一些粗淺的看法,就教于在座的同行們。”這也可視為田川對未來歌劇發展的一種追求、一種夢想。如今,這己經成為這位一生為歌劇嘔心瀝血的革命老前輩、一位跋涉了幾十年的“過來人”最后的囑托。
田川所談的意見,提綱挈領,簡明扼要:
1.要運用歌劇思維,精心選擇具有時代精神并適于用歌劇形式表現的重大題材。
2.要重視歌劇音樂的整體布局,追求全劇音樂的完整性。這標志著中國歌劇走向成熟。過去最初是小調劇,節格式的,主題有時反復,并不貫穿始終。“洪湖”的牢房一幕比較完整連貫,但前后也不是渾然一體的。
3.要努力追求歌劇的戲劇性和音樂性的有機結合。這是使一部歌劇“好聽,好看”、成為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的關鍵。要改變某些片面強調音樂性而忽視戲劇性的弱點。
4.要增強精品意識,發揮綜合藝術各門類的創造性。良好的劇作,風格獨特而又有強烈戲劇性的音樂,演員出色的表演和演唱、輝煌的合唱,配合默契的樂隊演奏和新穎的舞美制作等,在高明的導演指揮下,有機地構成一部歌劇精品。
5.努力創作反映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生活的歌劇。歌劇如脫離了群眾,就失去了生命力。在創作時要了解群眾在關注什么、喜歡的是什么,使作品內容貼近生活,反映人民的心聲。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又有為群眾喜聞樂見的美好形式。藝術的“孤芳自賞”和庸俗化現象,必須用“雅俗共賞”的作品所代表。雅俗共賞是藝術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