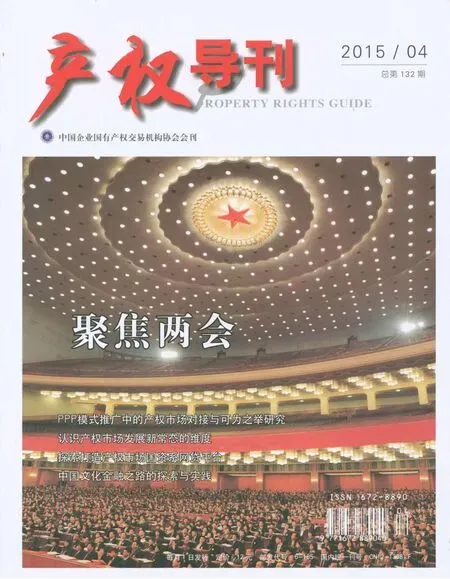觀點集萃
中國經濟GDP轉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長
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1月10日表示——
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兩個特點。一方面,中國經濟GDP增速進入下行通道,轉入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長,今年的趨勢還會繼續;另一方面,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從粗放發展向集約增長轉型。這兩個特征的發展不一樣,前者已是事實,而后者是期望目標,需要經過努力才能實現。如果經濟發展效率沒有提高,那么之前我國經濟粗放增長、數量擴張的矛盾問題就會暴露。此外,原有的經濟發展推動因素弱化了,經濟下行速度會加快,各種矛盾就會激化。當前中國經濟需要在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上。

2015是中國經濟關鍵的調整年
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韜葵1月10日發表專欄文章指出——
2015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調整。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深層次的調整期,其關鍵點是舊的增長點逐步淡出,而新的增長點正在逐步營造出來。這些新增長點并不能像過去那樣在統計數字上得到充分反映。比如各種服務業及新的業態是很難納入統計范疇、進行全口徑計算的。改革是調整的關鍵。如果2015年改革能較順利地深化,改革的力量將會化解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整頓時期的問題,那么中國經濟的調整期將會走得相對順利一些。如果中國經濟的調整期能順利度過,那么中國經濟有望在2016年后再出現相對增長速度比較高,在7.5%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長新時期。
投資者才是股市的根
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1月10日在“新常態下的中國與世界”論壇上表示——
在中國股市里,只有10%的股民在賺錢。而政府的稅費、證券公司以及監管當局等‘陪玩者’拿到的錢是股民分紅的三倍。股市不僅僅是企業融資的場所,更是股民投資的場所,股民應該獲得與生產者同等的待遇,政府監管應立足保護投資者利益,不是要給企業送親,投資者才是股市的根,是魂,是本,是源。所以要“盯住”分紅。
新常態下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前外貿部部長龍永圖1月10日在“新常態下的中國與世界”論壇中表示——
新常態下中國對外開放呈現出高速引進外資和大規模走出去并進的新特點,而大量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營造了好的硬環境。亞太地區共建自由貿易區的提議,將進一步消除各國的貿易壁壘和投資壁壘,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打造更好的軟環境。“軟硬環境”的兼備將會為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
中國企業債務杠桿率全球最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余永定1月10日在“新常態下的中國與世界”論壇中表示——
按照標準普爾數據計算,當前中國企業債務為14萬億美元,美國是13萬億美元,中國已超過美國。而經濟增速下降一般會伴隨著杠桿率的上升,高企的杠桿率只能說明企業負債和還債能力差距過大。因此,必須提高企業的效率,提高整個經濟宏觀配置效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當前經濟增速稍微下降一點,使我們的債務暫時得到緩解,我們可以更大膽加緊結構調整,加緊改革,不要擔心經濟速度下降對我們帶來的損害。
2015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張曉強在1月10日在“新常態下的中國與世界”論壇發言中表示——
2015年中國經濟將面臨比2014年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外部環境看,政治上,日漸復雜化的地緣政治,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不甚理想的發展環境。經濟上,以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反應了全球需求的疲軟。可以說,全球的地緣政治、需求不旺以及金融波動等因素,隨著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都將對中國產生影響。
未來服務業會成為支柱性產業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年會理事長海聞1月9日受邀做客《金融街會客廳》時表示——
我們現在服務業占到GDP的47%,我覺得起碼占到60%至70%的時候,產業結構會比較正常。現在制造業大概每年7%左右增長,服務業每年10%左右增長,這樣,比重會不斷改變,我相信在四五年內,新的產業就會逐漸形成,但長期的產業結構大概需要一二十年,那時候,服務業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股市要完善制度
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1月10日在“新常態下的中國與世界論壇”上表示——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股民的平均持股率只有32天,這說明中國股市是一個完全的投機市場。如果不把投機市場變成投資市場,那么問題是很大的。投資應該變成真正的價值投資,配合穩定的制度建設才能形成穩定的市場。目前中國上市企業多是“包裝上市、捆綁下海”,只是為了圈錢,因此需要完善的制度來保障股民的利益。比如政府不要用過多的行政手段干涉股市,而應該完善一些制度建設,比如完善信息披露、加大對上市公司造假以及揭露證券欺詐等一些擾亂市場和操作市場的行為的懲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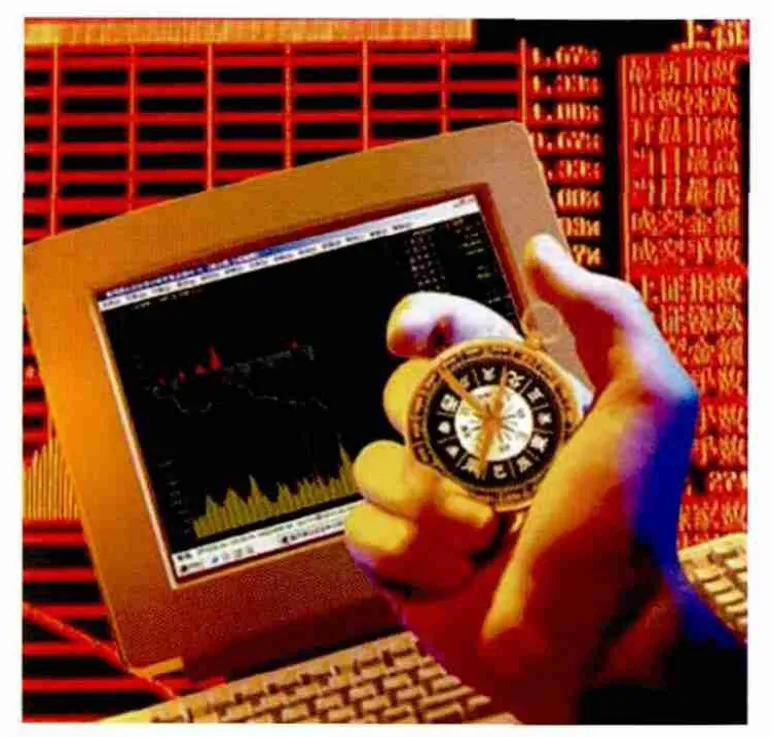
央行貨幣政策隱性超寬松 物價反彈只是時間問題
財經專欄作家肖磊1月9日發微博表示——
隨著大規模投資項目的上馬,以及央行貨幣政策的隱性超寬松,物價的反彈只是時間問題,中國的CPI最低可能是去年11月份創下的1.4%。原油下跌可以拉低全球通脹水平,但對中國CPI的影響有限,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寧愿通脹上行,也不能承受失業壓力,新聞聯播天天鼓勵大學生創業就是希望降低失業率。
中國資本外流已相當嚴重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1月2日發表觀點認為——
中國資本外流實際上已相當嚴重,中國對資本流動的管制主要是對短期跨境資本的限制。“倒逼”并非全無道理,但完全放開的不確定性太大,中國的國內條件和國外環境決定了不應該冒如此大的風險。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前提是先加速國內產權制度、經濟體制和金融體系改革。這些改革并非必須以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化為前提條件,因此,為了中國的經濟安全,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化就應該作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最后一步。
未來穩增長需降低投資對GDP貢獻率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2014年12月28日在財經戰略年會上表示——
增長的兩個來源中,目前資本產出比的增速不可持續,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很慢,令人擔憂。其中,2008年之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大大降低,甚至為負。之所以1978年以后投資這么多,主要來自于非居民建筑與基礎設施,而這部分投資的增長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降低。投資里面投到機器設備的太少了,投到研發的太少了,投到修路、建橋、蓋房子里面太多了,造成一系列問題。投資會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負面影響,未來需要優化投資結構,使投資對GDP增長貢獻率低一些,這樣才能保持比較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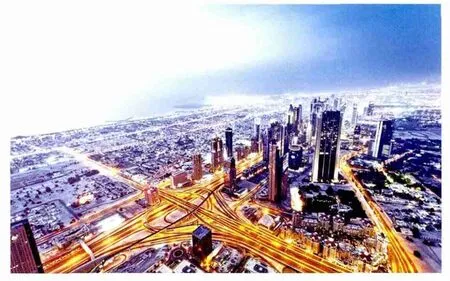
勤打“蒼蠅”讓企業真正輕松前行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2014年12月29日在題為《經濟下行的擠壓性原因》的演講中表示——
目前企業經營環境仍不樂觀。一些行政部門不敢向企業吃拿卡要了,同樣,也不給辦事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在強調清理行政審批權。真正清理的總是一些多年用不著的權力,關鍵性的權力還是不愿清。保護民營企業權益,就是要保持一個健康干凈的營商環境。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門自身涉嫌違法,在嫌疑人未被認定的時候就開始拍賣所有人企業的資產,這種做法只能讓其他民營企業退避三舍。我認為反腐應當從打老虎轉向蒼蠅。企業普遍反映“蒼蠅”太厲害。企業每天面對各個環節的“蒼蠅”騷擾,要嚴厲打擊各種“蒼蠅”對企業的侵害。只有這樣才能讓企業在干凈的環境中健康發展。
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仍有8%的增長潛力
經濟學家林毅夫在2014年12月27日舉辦的“2014年中華工商時報年會”上表示——
判斷未來增速有多高主要看兩個因素:首先是中國目前發展階段的潛在增長率還有多高。其次還要看內部和外部條件怎么樣。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年均9.8%的增長,與我國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差距的后發優勢有關,后發優勢我們已經用了35年。未來判斷一個發展中國家后發優勢還有多高,可看現在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差多少。從這個指標衡量,中國現在相當于日本在50年代初的時候,新加坡在60年代中的時候,臺灣地區和韓國在70年代的情形。所以,我認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還是8%。我們有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借鑒,技術可引進、消化、創新。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技術和產業差距,發揮好后發優勢,她的經濟增長速度可比發達國家高好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