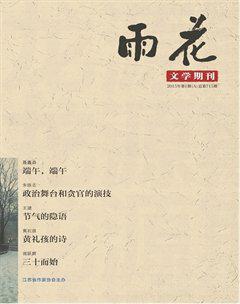月遮半邊虹
■ 德 詠
月遮半邊虹
■ 德 詠
社區要辦花展,鄰居老陳當上了策展人,他幾次三番動員我參加。我想我雖愛賞花養草,但怎能與那些名家高手相比,再說要參展就要有像樣的東西,可我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東西呢?沒想到老陳卻指著那兩盆小姐妹說,可以在那上面挖挖潛力。是嗎?于是我盯著那對小姐妹細看,發現她們像微縮的半座雙拱橋一般橫跨兩只花盆,灑上水后在陽光下晶亮晶亮的,宛如半道彩虹……這時我忽發奇想:以前我曾在為“鴛鴦蝴蝶派”巨子、在上海中西蒔花博覽會上三次奪魁的蘇州盆景專家周瘦鵑寫長篇紀實小說《花夢鵑魂》時,領略過一些栽種知識,何不借鑒周老師當年應邀去京出席梅花學術討論會時,帶去的那兩株小梅樁合栽盆景,標上“雙梅獻瑞”的寓意?我找來一只尺寸相仿的扁竹籃子,拆除拎攀后改編成一個托盤型的盆筐,把那兩只花盆裝進去。因為月光花花大而香、藤葉婀娜,而且它別名為“天茄兒”與“嫦娥奔月”,花語是“永遠的愛”,它的位置又正好把那彎彎的半邊彩虹遮擋住,自然而然地給我提供了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名字:《彩虹醉月》。后來老陳覺得這名字不夠完美,我又把它改為《月遮半邊虹》,交給老陳送到了展覽大廳。
此后我就外出了。沒想到上海喜訊不斷,《月遮半邊虹》第一次參賽就獲了獎。老陳來電、發信祝賀,并說又有新的商業性的大型花展邀請參賽;不久又發短信祝賀獲獎,說又有某某高級別的展覽邀請我參加;再后來索性用以前的短信文字略加修改,不斷報喜不斷更換花展主題,反正連連奪冠,拿獎拿得手都發酸,已經產生榮譽麻痹與審美疲勞了!我就跟老陳說,還是把那些機會讓給其他參賽作品和參賽人吧,再說我那東西也已老掉牙了。誰知老陳笑道:恐怕現在已騎虎難下由不得你了!奇怪,為什么現在我就沒有話語權了呢?等你回來后再詳談吧!老陳說。
一回上海,我就去找老陳。老陳對我說: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勢利”:你越是想要的東西越是得不到,越是不想要的東西卻越往你手里塞!你的東西一獲獎,策展人就會拼命動用媒體大力宣傳自己的政績,花商也瞅準機會不擇手段地炒作,與此同時大量復制第二盆、第三盆……甚至數十盆幾百盆的贗品,冒充獲獎作品,通過明棧暗道,一批批發往各地牟利。說到這里,老陳還誠懇地對我說:“不瞞您講,前兩年我從你家引種的那些翡翠玉,一度瘋狂繁殖,幾乎泛濫成災,差點被我丟進垃圾箱了,可這次卻托你的福,當花商發現它們都出自同一個家族后,立馬三番五次來我家把這些所謂‘具有獲獎家族血統’的后代一盆不剩統統包銷而去。后來才知他們拿去按照你的那盆獲獎花卉如法炮制批量生產,做得像的,直呼原名;不太像的,就改稱邊緣性的模糊的類似之名,旁邊再配上圖片和獲獎詞……吸引那些崇獎迷獎信獎戀獎的忠誠義士粉絲們為它掏心掏肺掏金掏銀。”
老陳看我陷入沉思,便勸慰道:“想不到這種花養花里面還有這么多的‘花頭經’吧!所以我早就對你說,你千萬別為這玩意兒操心,還是回去安安心心地琢磨你的純藝術創作吧。”“不!”我說我忽然對這些“花頭經”感興趣了。因為我似乎發現這里面蘊含著某些值得借鑒和體悟的東西,與影視圈、書畫圈和文學藝術圈以及商業圈里的明星炒作和品牌炒作,有某些相似之處。
那天我去展廳,除了在玻璃櫥窗里的“獲獎花卉名錄”中看到《月遮半邊虹》的圖文外,在整個大廳里卻找來找去也沒找到那兩盆花。我問老陳。老陳說歲月不饒人,它們已到了抱孫弄飴的時候,當年風姿勃發的姿態也青春不再啦!后來,我們終于找到了那兩只并放在一塊的花盆,只見那半邊彩虹已被拗造型拗成了模仿性感女模的“S”體形,粘在盆籃上的標簽寫著《曲線女郎—歷屆花展獲獎名品〈月遮半邊虹〉的姐妹篇》;再看旁邊的那盆月光花已經萎蔫,僅剩幾根枝蔓像冉冉長須牽纏著。她們的周圍、地上又布滿了種子,但這些可憐的兒孫們并沒有擺脫上一代的命運,又大多倒斃在他們的母體的葉蓋下了。當我看見他們那些已移植并嫁接成了幾個圓球形的“頭顱”時,我簡直驚呆了!這些小寶貝怎么形象猥瑣得像一個個怪怪的匪痞畸形兒?黏在盆籃上的標簽果然寫著《壞小子匪痞兒系列—首屆花展獲獎名品〈月遮半邊虹〉的后代》。他們的“發型”,就像在動蕩歲月中受懲罰跪掛牌剃度那樣,但那個“剃度”剃的不光是“陰陽頭”、“馬桶蓋”;甚至還有“西瓜頂”、“刺猬頭”、“雞冠頭”!是誰逼得這些幼崽兒,變成了這副獐頭鼠目的歪棗裂瓜?難道這也算是新一代畢加索那種時髦創新杰作么?
我很不高興地望著那對曾經為我同情、提攜栽培她們的小姐妹,心中不無惋惜地說,難道你們好不容易從當初的逆境中掙扎出來,就是為了走祖輩的老路,繼承老翡翠玉的衣缽,坐上他們凌駕于王的位置?甚至變本加厲地把可說是“曾經有恩于你們”的鄰居—當初同情你們、收留你們在她倆領地中,使你們得以治傷療養的月光花排擠成什么樣子了?她倆看到我不高興,露出了一臉委屈、哀怨的神色,似乎在輕輕地抱怨:瞧瞧我們的家園,這么狹窄,這么逼仄,實在舒展不開身子呀,幾代人擠在一起能不磕磕碰碰么?是的,我想,出于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的確太委屈你們了!……“何止委屈!”她倆似乎在對我說:“沒辦法呀老爺子,這是‘潮’!”“什么‘潮’?”“潮流唄,潮漲潮落,趕不上就會被拋棄被淘汰。”“人家蘭花姐姐不就趕上了么?本來,聽說她們在貧苦的大別山區都是遍地盛開的野花,有人撿到一把送朋友還不要呢!可后來,一炒再炒,身價百倍千倍飛速暴漲……”哦,真是顛覆、瘋狂的追逐,交匯成了一條浮夸、焦躁的物欲橫流的虛無之河。
老陳現在開口講話時口氣也與過去兩樣了!因為他在大花商評獎之后辦班時,及時跟上形勢進了高級培訓班,學習了“染色技術革命”等課程,可以通過花卉根莖吸收天然色素后隨心所欲地使花卉改變顏色。后來他們那些“花卉設計師”已成為當下名師,經常受邀當評委,身價大不同了。凡是同出師門的哥們姐們及其推薦來的作品,一律大開綠燈,不僅由于共同獲益,而且往往鑒賞與審美情趣相投;而對旁門異類,一概排斥。漸漸地變得凡是經他手評出的“杰作”,大都變得一種形狀、一種顏色,很難容忍異性雜交,久而久之,其結果只能是“近親繁殖”,百花凋零……
老陳得意地說,就像你們影視娛樂界,不一樣么?一支歌,一曲舞,一個角色,一次演出……明星不就包裝出來了?驀然間,我想起那年參加戛納電影節時,聽說過評選獲獎杰作的“暗招”中還有一個“道統文藝套路”,這個套路的核心精神是解構,具體藝術表現是頹廢、墮落、怯儒、叛逆……而且歷經渲染,漸成氣候。但是,應該看到,不也有許多奧斯卡的“小金人”頒發給了那些宣揚崇高、英勇、奮發、忠誠、勇于犧牲等撼人心腑的影片創造者么?
怪不得,我們以前一味追求藝術品位與思想內涵、人生哲理的作品,哪怕再勤奮敬業、刻苦求索,到頭來不但收效甚微,有時還常遭貶黜,血本無歸。更別提像某某某某那樣看不入眼的丑陋東西獲這個獎那個獎了。那么,在其他行業里,是否也有類似的“花頭經”呢?
從《月遮半邊虹》到《曲線女郎》和《壞小子匪痞兒系列》,我和老陳似乎發現了隱藏其間的一雙“美麗的無形之手”,她馳騁商海,呼風喚雨,走南闖北,橫行天下。前些年,當她在中國看中了大別山的蘭花,馬上“領養”大炒特炒,價格一路飆升,以至贗品泛濫,但一當發現她“青春期”已過,立即把她當毫不留情地拋棄。之后,這雙“無形之手”到處物色新的有活力的“純情少女”,當做新生取代品來加以“培養”并不惜工本包裝,使她成名。此時往往“鐵面無私”一心追求貨真價實的富有培養前途的“尖端苗子”,任憑天大的面子她也堅守底線,不肯賤賣她的“黃花閨女”,并不惜資本開動各種媒體廣告宣傳機器大肆炒作,使她發展成為“紅得發紫”價值連城的明星。與此同時,這雙“無形之手”還像孫猴子拔根毫毛一般大批制作生產類似的“獲獎作品”,批銷給各地的“第三雙手”、“第四雙手”及其徒子徒孫,狠狠地攬錢、圈錢。過不多久,眼看她那些明星們又韶光已逝,進入了“衰落期”;那雙“無形的手”立刻抓住余熱推出她的“后代”“傳人”,而且為了榨取僅剩的油水,急功近利,來不及也沒耐心再出力費錢去精心培植、撫育,而是加猛藥投猛料,不惜犧牲那些幼輩嫩芽兒畸形發育,催化速成為歪棗裂瓜的“匪痞畸形兒”,卻美其名當做“特色異類”宣傳牟利……
這雙“美麗的無形之手”到底是誰的手?怎么那么長,那么神奇,而且連接著那么多的鏈條環節?
最后,我和老陳終于穎悟:那不就是百十多年前,那位德國的大胡子老爺爺曾在繁華的商業都市中發現的那個隱藏其間的“老妖婆”的手么?她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而且翻云覆雨,上下縱橫,遙控操縱,神通廣大,卻又無跡可尋。
我似乎發現,在我身邊的各種圈子里,似乎也能嗅到那些類似的氣味!面對這種無奈的異化,我們在慨嘆之余,是堅守操節、自尊自律,還是隨波逐流、自甘沉淪?孰是孰非,當自深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