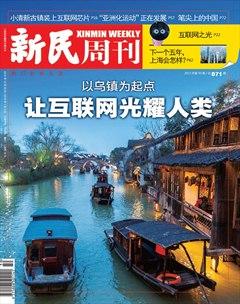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成就房地產鉑金十年
靠農民工去樓市庫存量的傳聞,終于在最近的國家有關會議上落了地。有關會議再次把“化解房地產庫存”作為核心議題之一,凸顯了經濟形勢的嚴峻和部分三四線城市的高庫存風險。這次的招數是把“加快農民工市民化”作為了房地產去庫存的著力點。具體做法可能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進城落戶更容易;通過改革公積金制度,把農民工、個體戶納入其中;通過財政補貼、退稅,或稅收減免方式,幫助農民工在城市里購房。
雖然這則消息迅速刷屏了地產人的朋友圈,但大部分人其實并不是很看好對樓市的實質性利好。原因一部分或在于,把農民工市民化、階層平權這一社會體制改革和房地產去庫存結合起來,難免給人一種怪怪的感覺。誰能想到,農民工多年來享受不到的社會權利,居然是為了消化房地產庫存的目的而促成。更加理性的分析,是對農民工的收入與購買力存在疑問,對他們的信貸消費習慣存在疑問。一個顯然的問題是:農民工如何承受城市高房價呢?
我的看法是,這些質疑不無道理。但我對“農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產庫存”持充分樂觀態度,這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有效化解三四線城市需求不足的問題。并且成為中國房地產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有望成就真正的房地產鉑金十年。

圖為本文作者、著名房地產營銷專家臧建軍先生。
從道義情感的角度,給農民工市民權利,以消化房地產庫存。這個邏輯聽上去著實刺耳,似乎讓人有些對不起農民老大哥的感覺。但要知道,在中國許多改革都是問題導向的,所謂倒逼改革,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無論出于什么目的,平權制度改革總是好事。
從市場需求本身的角度,討論農民工市民化能否擴大住房需求,首先要對“農民工”這一老詞有新的認知。今天的農民工已今非昔比,80、90后的第二代農民工和農民工二代已成為絕對主力。這部分20-35歲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目前的1.5億跨省流動農民工中占80%份額,10年內這部分群體人數將突破2億。如何客觀全面地認知這部分群體,是理解未來中國社會,理解房地產市場變化的重要任務。
第一代農民工注定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根在農村,歸宿也在農村。來城市打工賺錢,最終是為了回老家蓋房,或供子女讀書。但第二代農民工則不同,他們或者中學畢業后就來到城市,或者就是隨農民工父母出生并成長在城市。這部分農民工,國家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新”在年輕,“新”在沒有務農經歷,“新”在對城市生活有著更強烈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負擔。
同時受教育程度相對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承受力低,這一點上他們和城市人群并沒有天壤區別。
剁手黨們每天接觸的快遞小哥,他們的收入可以超過寫字樓里的小白領。更重要的是,這一兩億人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去,在城鎮置業安家是他們必然的歸宿。
所以,被房地產去庫存倒逼出來的農民工市民化,或者新型城鎮化相關的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將進一步掃清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安家置業的障礙,加快他們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步伐,為樓市去庫存,乃至長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當然,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不會改變房地產市場城市分化的格局與趨勢。人口的凈流入或流出,顯然是影響房地產市場最根本的因素。只要有產業支撐,宜居或者宜商的城市,才能吸引到高級人才,吸引到新生代農民工,才能產生房地產需求。中國人口流動包含正反兩個方向的力量。一方面,大城市的吸附能力依然較強,繼續吸引人口向大城市流動。另一方面,農民工的老齡化,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以及中西部的發展,使得人口回流的趨勢明顯。近幾年河南、湖北、湖南、安徽、重慶等省市人口大量回流(估計2008年至今已回流6000萬以上人口),亦是這些省會城市市場活躍的重要原因。從總體而言,在國家新型城鎮化政策引導下,三四線城市的政策應更加靈活、更加有力,也更能享受農民工市民化的紅利。
無論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進展如何,中國房地產總體結構性拐點的趨勢依然不變。農民工市民化會擴容市場需求,但房地產行業最重要的變革還在供給側,也就是房地產企業要主動優化城市布局,要優化產品線,要豐富房地產產品與服務的內涵。
在農民工市民化這一大的政策背景下,我們則更要主動關注和研究這批新生代農民工。尊重他們,讀懂他們,從而服務好他們。誰能抓住這數以億計的市場群體,誰就可能贏得房地產鉑金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