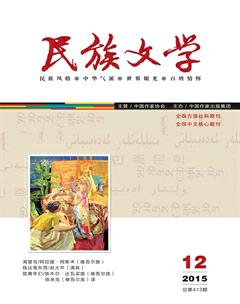武陵史彩筆繪
用文學來描繪中國少數民族歷史,不了解土司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土司制度從宋朝的“羈縻”政策萌其芽,明朝永樂定其制,清“改土歸流”而式微,直到新中國成立止,這一制度在中國存在上千年,而大多數人對此知之不多。
土家族在我國民族大家庭中比較活躍,現有人口800多萬,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川交界的武陵山區。關于土家人族源,學者多認為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也融合了其他族群。潘光旦先生曾說:“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畢茲卡族的祖先,“在漢代屬‘武陵蠻,在南北朝屬‘五溪蠻,在宋代屬‘南北江諸蠻的一種,是可以肯定的。”在封建王朝的“正史”里,將西南諸多少數民族統歸之于“蠻夷”,沒有“畢茲卡”這個名稱。宋代設羈縻州縣制度以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管理,之后,特別是元明,中央政府設立和完善了土司制度,而且經常征調“土兵”幫朝廷打仗,其中最能戰斗的就有“畢茲卡”的先祖們。畢茲卡族將威猛的山之精靈——白虎作為本民族的圖騰予以崇拜。今日的土家人多自稱“畢茲卡”或“貝錦卡”。語言學家認為“比幾”、“畢茲”、“貝錦”等只是同一語詞的方言化,“畢茲”或“貝錦”是名稱本身,“卡”等于“族”“人”。
何謂“土司”?“土”是漢官為了對非直接統治管理地方以示區別而以“土”名之,“司”是官署之意。中國歷史上,凡是設有土司或土官的地區都是少數民族的地區。土司的實質是由封建王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大小首領官職——世襲其官、世長其民、世領其地,這就是土司制度的根本要件。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多建都中原,重內輕外,對交通阻隔的邊遠版圖鞭長莫及,時常難以經略,不得不實行“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統治策略。由羈縻而土司,朱明王朝使土司制度發展到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僅武陵一山,先后得到朝廷放印的大小土司數十家。重慶的石柱、酉陽土司,湘西的保靖、永順、桑植土司,貴州的思南土司,鄂西的容美、唐崖、施南土司等等,都很有影響,何況土司之后數百年間,在這一片熱土上又發生過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武陵山地處西南高地與中原交接帶,是文化交匯之地。相比之下,武陵土司有較強的中央政權依服心理,對漢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善于借鑒和包容。武陵土司制是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成功嘗試。近千年的土司時期是很多少數民族形成和成熟的時期。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國體的進變和民族的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大勢。在民族關系上是多元共存還是強求一統,是封建制還是郡縣制,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影響著歷史的進程。土司是作為朝廷代理人和地方統治者雙重角色存在的,是王朝國家運作的區域化表現,自有其當時的先進性和合理性。土司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一種國家管理制度,對后世也產生著深遠影響。后來,中央王朝和土司的矛盾日益加劇,土官與土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土司制度逐漸僵化,以至難以化解國體的矛盾,中華民族不得不用沉重的代價推動著歷史車輪繼續前行。
武陵圣山,畢茲卡歷史多姿多彩,我們就想用長篇系列小說的方式來描繪這段歷史。《武陵王》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線索,以人物為中心,傳奇演義成書,大的歷史背景、大的情節事件、包括主要人物都未敢編造。作品試圖以廣闊的視角,將土司王的命運放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社會變革狀況中進行描寫,重點展示我國明、清時期武陵土司的社會矛盾和人物命運。突出歷史的包容性與開放性,著墨于當時畢茲卡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妙,著墨艱難的生活景象和向往文明的追求。弘揚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注重史詩性、文學性、可讀性。土家族先民的勇武彪悍、聰穎多才、忠義淳樸、嫉惡如仇等品格亦在作品中多有表現。同時,該作品也想給讀者展示一些生動的民族風景和古邦風俗。試圖營造出一處神秘莫測、瑰麗無比的武陵秘境,誘人進入巫風烈烈、巴俗奇特的時空洞穴之中。
近千年武陵土司歷史為多民族國家治理積累了成功經驗。武陵土司是如何強盛起來?土司制又是如何走向僵化?各土司和中央王朝如何相處?土司王在中國歷史大劇中各自如何伴舞?這些問題也是吸引我們寫作土家族長篇歷史系列小說《武陵王》的動因之一。 “容美”這兩個字是古貝錦卡語的漢字記音,在不同的資料中,有的記為“雍米”,有的記為“雍尼”,有的記為“容米”。從元代始,稱為“容美土司”。據歷史學家研究,“容美”,在貝錦卡語中是“妹妹的住地”之意,由此可以推論:是由遠古一支女性部落衍演而來的。容美部落在族群紛爭、弱肉強食的1600多年里,估計先是融入巴,楚滅巴后,國破而家未亡,“避秦”于武陵山中。元初,羽翼漸豐的“容美”才開始初露鋒芒,向四周頻頻出擊,以證實自己的存在。到至大四年,元朝中央政府在“容美”設立“黃沙寨千戶所”,任命容美峒主田墨施什用為千戶。這是一個相當于縣衙的品級,級別雖然不高,但它標志著容美由“化外之民”從此進入中央王朝的視野,并服從于國家的管轄。
容美土司在武陵土司中持續時間不是最長的,經歷422年,跨元、明、清三朝,歷經15代23位土王。爵位級別在從五品安撫使、從四品宣撫使和從三品的宣慰使上下間升降。欽封的功勛爵位,曾達到正一品太子太傅、驃騎大將軍。這些欽封爵位有爵無祿,有名無實,只是虛榮。容美土司地域最大時包括現在的湖北鶴峰、五峰兩縣和長陽、巴東、建始、宣恩、恩施和湖南石門、桑植諸縣的部分區域。清雍正皇帝曾在一份奏折上批示:“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為富強”。
縱觀有史記載的容美土司23位土王,都有十分生動的故事和愛恨情仇。田墨施什用算是第一任,他憑借自己的實力,第一次將容美峒從無人知曉的后臺,推到群雄紛爭的歷史前臺,之后經過其子田先什用的努力,聯絡“12峒蠻”攻打長陽,再次用武力證實了自己的存在,得到元廷進一步重視。容美峒被確定為相當于州府級別的“四川容美軍民總管府”。而第三任土王田光寶在元、明交替的關鍵時刻,審時度勢,向還是吳王的朱元璋繳納元朝授予的權力印信,受到朱元璋的嘉許,被授予當時土司最高級別:容美等處軍民宣慰司,為從三品銜級。傳說還有“金書鐵券”之賜。以后又經過田勝貴、田潮美、田保富、田鎮、田秀5任土王的經營。給容美帶來巨大災難的是第九任土王百俚俾。他本為第八任土王田秀的庶子,弒父殺弟,血洗王宮,制造梟獍之禍奪得土司政權。后來,他的惡行敗露,被朝廷下獄論死,司主為宣撫同知田世瑛,代理6年,未能有突破性發展。
而將容美土司推向中興的是第十一任土王田世爵。田世爵為田秀幼子,百俚俾謀逆時他6歲,靠奶母覃氏及其丈夫麥文松以子代死,逃到鄰司桑植,在外戚的幫助下,得以長大成人,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3歲時,他回司主政,將一個瀕臨衰亡的容美土司,逐步壯大為受到朝廷高度重視,在武陵眾土司中有很大影響力的強大土司。田世爵為政33年,實際控權39年,其文治武功最突出的有4個方面:其一,他率先將孔孟漢學引進容美,講土語,學漢話,興辦學堂,以詩書“嚴課諸男”。尤其是六子田九齡竟以詩文與當時的“明七子”齊名,開啟土司文學之先河。其二,他關注民生,重視農桑茶藥,發展冶煉工業,與漢地通商,壯大了土司的經濟實力。第三,他發展武備,開疆拓土,吸納招墾外地流民,將容美土司發展成為有民眾數萬人,可調動兵力達到兩萬余人的大土司。第四,他訓練的“鐵塔陣”土兵,勇敢無畏,多次奉朝廷征調,所向克捷。尤其是他親率土軍兩次赴浙江抗倭,“容美精兵悍甲諸部”,立有戰功。最后,終因積勞成疾,田世爵60多歲客死于軍旅之中。
之后,田世爵的兒子田九霄、田九龍先后繼任,繼續發展容美的大好形勢。嗣后九龍的兩個兒子田宗愈、田宗元相承襲。為爭襲司主,又發生了嫡庶內訌,司內發展受到一定影響。傳之田宗愈的兒子田楚產,再傳其子田玄。田玄再度將容美土司推向中興。這時的容美土司實際控制的土地面積達7000余平方公里,土司級別再一次由宣撫司升為宣慰司。田玄死后,他的3個兒子:沛霖、既霖、甘霖先后繼任宣慰使職。此時正值明清政權更迭之時,兵禍連連,形勢復雜,容美土司兩次慘遭李自成敗兵洗劫和南明勢力的勒索,社會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容美土司幾近崩潰。
再一次振興容美的是田甘霖的兒子,容美第21任土王田舜年。他受命于危難之際,奮力撐起搖搖欲墜的容美府衙,撥亂反正,勵精圖治,又一次開辟了容美盛世。他的突出功績也有4方面:第一,他在復雜難辨的政治形勢面前,夾縫求生,審時度勢,毅然投順新的中央政權,從而獲得清廷賞識,被授予正一品的驃騎大將軍,使司主的官階品級名義上超過了行省主官,并且開了武陵土司覲見皇帝的先河。第二,他打開山門,興利除弊,發展經濟,吸納人口,使容美再次出現“出山人少進山多”的局面。第三,他在司內修橋修路修樓宇,煉鐵煉銅煉硫磺,發展手工業生產,開發藥茶貿易,經濟建設活躍繁榮。第四,他最大的功績在于“文治”:他引進人才,興辦學堂,廣推漢學,倡導詩文,崇尚演藝,并且身體力行,傾注了大量心血。此一文治傳統影響深遠,為子孫所稱道。他著述頗豐,親手編輯的田氏6代10位詩人的詩詞大成《田氏一家言》,乃是我國文學史上雖少為外人所知卻十分罕見的土司家族詩集。他引進、傳播被清廷封殺的孔尚任《桃花扇》一劇,顯示其思想開放包容的一面。他是一顆高高升起在武陵上空的閃亮文星。可惜他的應襲長子田昺如乏德乏才,田舜年將司位傳給他之后又反悔,豈料覆水難收。加之自身猛虎秉性,剛直無畏,得罪于行省,又受內外政敵的夾擊,冤殞于武昌獄中。容美盛世遂告終結。
收拾容美殘局的是末代土王田旻如。他是文武全才。青少年時期被其父送往漢地求學,聰明勤奮,出類拔萃,得以入京師國子監就讀。后被選為皇家禁宮侍衛,不久任命為直隸通州同知。此時,上上下下都看好這個精明干練勇武彪悍的漢子。用今天的話說,他是選調上派到中央國家機關重點培養的少數民族干部。然而就在他升遷在即的時候,父王死于冤獄,容美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司主,朝庭令他回容美襲任司職。他在任職的26年里,發揮在京都和通州見識到的先進管理理念,興利除弊,交好四鄰,發展農耕和貿易,使司內一度出現再度振興的局面。盡管他躊躇滿志,卻生不逢時,“改土歸流”的大潮洶涌到來,打破了他的烏托邦理想。他以為自己本屬“流官”序列,拘泥于桃花源中,對多變的國情形勢和封建官場殘酷斗爭估計不足,作出了錯誤的應對抉擇。最后帶著滿腔的遺恨、難了的深情,投環自縊于爵府平山。這“改土歸流”從明朝即有行動,田旻如不會不知,他為何還回司任職?他為什么把最后希望寄托于皇帝?他如果離司赴京結局又會怎樣?這都給文學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想象余地。
隨后,我們開始了解石柱土司、酉陽土司、永順土司、保靖土司的歷史。酉陽土司歷600余年,襲遞20余代,其中不乏經邦治國之才。《武陵王之酉水流香》著重寫了酉陽土司歷史上一個奇女子,寫她從土王千金淪落為舂碓使女,又如何自強不息成長為巾幗英雄的歷程。《蜀錦征袍》則著墨于著名的石柱女土司王秦良玉,她忠君愛國,保境安民,從一個漢家女子成長為南征北戰、威震一方的大將軍。她是唯一一位進入中國封建帝國軍事正史的女都督。湘西畢茲卡剛烈,彭家軍應召抗倭勇立“東南第一戰功”。《虓鎮南疆》生動演義了“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古話,寫保靖土司和永順土司彭氏雙雄共赴國難、抗倭衛國的生動故事。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國體的進變和民族的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大勢。從周天子分封諸侯、戰國時期創立郡縣,封建與郡縣便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史上關于國家結構的兩種理想思潮。在民族關系上是和睦共存還是強求一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影響著歷史的進程。土司是作為朝廷代理人和地方統治者雙重角色存在的,是王朝國家運作的區域化表現,自有其當時的合理性。元明兩朝推行土司制度,確曾對鞏固王朝統治、經濟文化發展,特別是維護邊疆的統一起過重要作用。但是,土司制自身具有濃厚的割據性,少數民族群眾要承受來自于朝廷和土司兩個方面的封建統治和任意剝削。又由于土司間為了爭奪領地、承襲權而導致的仇殺、內訌時有發生。在那個時候,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可是一對矛盾,封建王朝視“少數民族”為“蠻夷”,遑論平等與信任,集權與一統是朝庭的既定方針,“羈”與“縻”只是約束“蠻夷”軟硬兼施的手段。明王朝雖然大力推動“改土歸流”,卻不斷反復。土司和王朝就成了一種若即若離、時叛時順的關系。由于王朝自身的衰落,土司制度的僵化,“羈縻政策”亦少創新。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內憂外患,明王朝已經難以化解國體的僵局。當清王朝入主中原,由小弟做了大哥之后,他不再像前朝那樣猶豫,“改土歸流”得以比較徹底和大規模推行。明清時期,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發展到頂峰,統治者的“改土歸流”是建立在“皇權唯一”基礎上的,“因俗而治”沒有得到好落實,對各少數民族尊重因應不夠,加之高壓與災變,當然遭到抵制,其中尤以西南“苗蠻”的反抗最烈。清廷用武力踏平了云南貴州上百處土司及“苗人”寨府之后,又兵踏廣西,再回過頭來收拾武陵山中的土人苗人。清王朝主導的“改土歸流”便產生了兩個客觀效果:客觀上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客觀上也傷害了“民族”關系。我們今天不可能要求封建統治者“以人為本”,具備馬列主義民族觀,也不能只以階級斗爭一論簡化民族矛盾,但后人確實對其消極面論之不多。封建王朝的兄弟相殘也毀滅了許多精彩的民族文化寶藏,其中包括容美土司數百萬字的詩歌總集《田氏一家言》。
對于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歷史,正史的記載遠不是完整的,基本上是一言堂。土司其地其民曾經占布國家半壁江山,創造和豐富了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燦爛文化。“土人”文化中雖有粗蠻落后的一面,更有純樸剛毅,奮發圖強,勇于求新的一面,特別是創造和保有著許多文化的優異特質,這都是中華民族的無價珍寶。但封建王朝多取“居高臨下”姿態,多采信監控官吏的奏報,多臆斷與歧視,讓后人難以感受到“土人”歷史真實而溫熱的血肉。新中國成立后,開啟了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新篇章,又由于極左的干擾,對“土司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才逐步豐富與深入。但至今,也還未能讀到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專著。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問題關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思想文化安全及社會和諧穩定。愛國主義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所系。武陵土司的興與衰,區域內發生的家國沉浮,愛恨情仇,是文藝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礦藏。誠然,我們的《武陵王》寫作不是歷史考證,不是史論研究,更不是家族史演義。面對沉重的話題,我們以文學賦予其輕松與快樂,注以熱情,涂以色彩。我們想用文學的方式再現一些真實而精彩的短劇,并借助故事和形象進行一些文學的思考。
我退休之后,重拾文學,成立了“李傳鋒民族文學工作室”。 我的兩位合作作家吳燕山、李詩選都是武陵山人,地道土家漢子。我們對文學尤其是對土司題材情有獨鐘。我們結為 “貝錦三夫”,恣意演義土司故事。我們查閱了大量明史清史土司史,研究文獻、文集,積累史料筆記,足跡達及鄂湘渝黔川畢茲卡故地,尋訪古跡,拓抄碑碣,查閱族譜,尋訪老者,拜謁專家,搜索枯腸,數易其稿,遂結構成書。因豐富史事串珠之需,為大眾閱讀的方便,也為影視改編計,我們借用了傳統的章回體及說書藝術,而少用文字機巧恣意妙想時空穿越之術。今年7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會議投票決定老司城、唐崖、海龍屯三處土司遺址為“世界文化遺產”,其中,武陵山土家族就有老司城、唐崖兩處。這讓我們感到無比自豪與欣慰。
責任編輯 郭金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