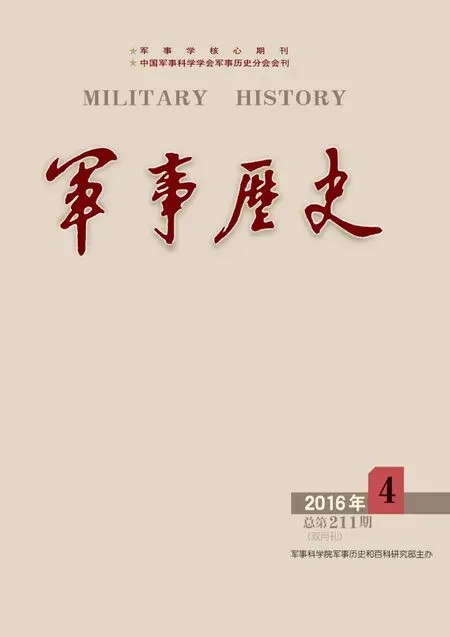《德國克虜伯與中國的近代化》評介
★
晚清軍事近代化道路曲折,進展緩慢,自始至終沒有找到一條真正適合自身發展的清晰道路。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內在制度層面上的阻滯、觀念認知上的欠缺,也有外在國際環境局促等方面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塑了晚清軍事近代化的殘局。對晚清軍事近代化的反思,學術界已有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但相比較而言,大而全的研究成果多,個案研究少,特別是視角獨特、能夠由點及面、專業特征鮮明的研究成果少。
個案研究的學術價值勿庸置疑,但要進行這樣的研究不僅要有嚴謹的治學態度、扎實的史料功夫,更要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還要能發掘出新的史料。相比一般的研究而言,個案研究的難度大,但價值也大。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個案研究成果不足的局面正在逐步得到扭轉,一批年輕有為、視野開闊、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正在從事這樣的研究,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涌現,孫烈的《德國克虜伯與晚清火炮――貿易與仿制模式下的技術轉移》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在晚清70余年歷史中,沒有哪一家西方兵工企業像克虜伯那樣介入晚清軍事近代化如此深入,對晚清軍事近代化的進程影響如此深遠,然而學術界對克虜伯的研究遠算不上完備。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專著僅有《德國克虜伯與中國的近代化》一部,是21世紀初的作品,其他相關的學術成果雖然也有一些,但進一步的研究空間仍然很大。孫烈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發掘的史料,就克虜伯對晚清軍事近代化進程的參與和影響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從而將克虜伯與近代中國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本書的副標題為“貿易與仿制模式下的技術轉移”,所以全書重點考查了克虜伯炮的引進過程,深入研究了克虜伯炮的相關譯著及其影響,對晚清仿制、裝備與使用克虜伯炮相關情況也給予了足夠關注。作者借助新的研究思路,通過研究克虜伯這個點,比較成功地展現晚清軍事近代化這個面。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提到的,寫作此書的目的在于“從個案入手,把握和理解近現代西方工業技術與中國現代化之關系及其特點”。可以說,該書是迄今為止研究克虜伯與晚清軍事近代化之間關系相關成果中最為全面和深入的一部。通讀全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應當給予充分肯定。
一、該書發掘的新史料很好地支撐了新的研究思路,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新史料的出現,必然會提出新的問題,也勢必進一步豐富甚至改變相關的認識”。
第二章是全書的重點之一,以往對克虜伯的研究多以國內史料和德國官方史料為主,而對克虜伯公司留存的原始檔案利用不足。作者在寫作該書期間,利用赴德國留學的機會,想盡一切辦法,搜取了大量克虜伯公司保存的原始資料。通過對這些史料的深入分析和充分利用,廓清了克虜伯公司與清朝政府官員、留學生建立聯系的來龍去脈,澄清了清政府對于克虜伯造炮技術認識的深化過程,并為晚清后來的引進、仿造克虜伯炮張本。而且,新史料的發掘和運用,拓寬了晚清軍事近代化研究的視域,使我們很自然地將晚清的火炮引進過程放在國際大背景下來進行考查,看出克虜伯公司或德國對清政府進行軍事近代化改革的態度,也能比較清楚地反映出清朝官員對西方軍事技術的認知與變化。
二、作者對克虜伯炮相關漢譯書籍的研究著實下了一番工夫,不僅系統地介紹了每部書的主要內容,推測原書的性質和用途,還通過對火炮數據表中數據的逐個比對,發現了由于譯者炮學知識的缺乏導致的翻譯訛誤。
學術界一般認為,以《克虜伯炮說》為代表的這批炮學著作的翻譯對晚清兵器工業,特別是制炮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力地推動了晚清兵器工業造彈、造炮技術的提升。本書作者則通過對漢譯克虜伯著作逐篇、逐段甚至逐字的解讀,做出了比較大膽的推斷,認為在克虜伯公司向清朝的技術轉移過程中,“書本知識的傳播扮演了一個并不重要的角色”,并沒有給晚清兵工業的進步和升級帶來直接的或實質性的變化。這一推斷是基于晚清兵工業實際造炮能力長期停滯不前的事實得出來的。實際上,從晚清留存的各類資料中也能看出,沒有哪一種火炮、彈藥的仿制品是明確受到這批著作的影響而出現的。即便把這批著作當作軍事訓練教材來看待,其指導清軍訓練作用的發揮也極其有限。作者的這一判斷大體是正確的,考慮到晚清政權的統治能力和認識能力,晚清軍事近代化的推進不可能從一開始就采取從科學知識累積到迸發的這種內因式的推進方式,而只會采用簡單的直接引入或模仿。但也必須承認,不管引入的知識是否系統、科學,對人們觀念和思想的改變卻是潛移默化地持續進行的,所以作者也在書中肯定了這批書籍的刊行客觀上促進了相關軍事知識的傳播,“將中國引進和學習的近代西方兵器知識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
三、本書不僅關注技術的橫向轉移,也注意到了晚清對于西方科學知識的吸收問題。
對火藥成分的認識,最能反映晚清兵工企業對火炮制造的科學認知水平。《江南制造局記》對栗色火藥特性的描述直接照搬了明代《火攻挈要》等兵書關于黑火藥的一般說法,絲毫沒有抓住栗色火藥區別于黑火藥的根本點,而且語言表述簡略模糊,幾乎看不出西方科學主義精神的任何影響。盡管到了1893年江南制造局已經能夠仿制栗色火藥,但對于火藥的特性理解仍然停留在很低的層面上。仿制不是創制,不具備近代科學理論的基礎,沒有系統和深入的科學研究方法作指導,無論生產規模有多大都只能徘徊在簡單仿制階段而無法突破。對火藥的認知是這樣的水平,那么對更為復雜的火炮制造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也不會深入到哪里。
不僅技術上存在問題,生產管理上的問題也很多,出現了機器先進和管理落后的怪異格局。管理上的官僚體制導致生產的低效,造成大量資源和人力浪費。書中引用英國上將貝里斯福德在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機器局的見聞很有說服力。他用西方人的標準衡量當時中國的兵工企業的生產和管理能力,認為中國的兵工企業盡管機器先進,但管理落后、浪費嚴重、效率低下,甚至認為當時的中國不可能像晚清政府宣稱的那樣具備了仿造克虜伯炮的能力。貝里斯福德的這些說法不無偏見,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清兵工企業在管理體制、運行方式上存在的問題。正是由于無法從原理上徹底搞清楚火炮制造的內在機理,缺少必要的人才保證,更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理念,所以晚清兵工業對克虜伯火炮的仿制長期停留在簡單模仿上,喊了很多年的“自行造炮”,直到1905年前后才出現具備一定實戰能力的仿品,而質量仍然低劣。更要命的是這種模式的生產效率極低,根本無法滿足裝備保障需求。清朝直到覆亡也沒有建立起規模化的、有可靠質量保障的火炮生產體系。盡管晚清政權內部一直存在外購還是自造的論爭,但實際上,裝備清軍的西式裝備主要還是以外購為主。這就是說,與克虜伯交往了幾十年,技術轉讓了幾十年,清朝始終也沒把外來技術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是很可悲的。
此外,全書配合文字制作了大量的表格和示意圖,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圖表數據的整理與制作非常繁復,費時費力,但卻能讓文字難以說清的東西變得一目了然,增強了說服力和可信度。試舉一例,該書第126-127頁,用兩個中國從德國進口火炮數量統計圖很直觀地說明了中國在1871-1912年期間購炮數量漲落的趨勢。通過這兩張圖,我們也能夠看出中國政治情勢變化對于軍事裝備引進的影響。
總體而言,孫烈的這部新著,定位清晰,結構嚴密,學術見解獨到,是一部不錯的關于晚清軍事近代化的個案研究成果,值得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