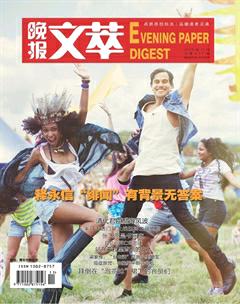農民養老現狀調查
陳墨
“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一個炎熱的夏日,75歲的劉桂花(化名)像往常一樣,站在一棟白色二層樓的門前乘涼。這是她花畢生積蓄蓋起來的,可她現在只享有乘涼的權利。
樓房歸兒子居住,她被“趕”到樓房不遠處一個銹跡斑斑的鐵皮房中。每到夏日,這個10多半方米大小的鐵皮房就像烤箱一樣,劉桂花或許將在此度過余生。
在中國東部某省這個“新農村建設示范村”里,老宅基地被收回,經統一規劃后,重新分配。但只有兒子們擁有入住新居的資格,他們的父母要么搬到統一規劃的“老人之家”社區,要么跟兒子一起居住。
劉桂花無力在“老人之家”蓋房,兒子義不許她同住,只得住進兒子買給她的鐵皮房。
這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村養老案例。
劉桂花一提起兒子就哭。有人告訴她,回答調研學生的問題,會得到20元錢。于是,這名瘦小的老人守在兒子家門口,等著工作人員來找她做問卷調查。
在河南鹿邑,摘一天煙草花能賺10元錢的老人把前來調研的學生團團圍住,爭著要做問卷,有的還與村干部產生了沖突。“真想給他們每人發20元。”課題組成員、帶隊調研的劉長喜說。
《報告》顯示,只有40%的中國農村老人有存款,從東部到西部,有存款的比例下降,均值是35741元。這意味著,農村有60%的老人沒有存款。而在報告中,農村老人一年的支出均值為11303元,其中人情往來的支出位列當下我國農村老人支出第三位,成為較大的經濟負擔。
河北無極縣的一對老夫婦,僅靠種地維持生計,年收入不足2000元,人情往來開銷比收入高出一倍。為了鄰里鄉親關系和諧,老人得病不敢吃藥,只能硬撐。
家庭關系
“現在農村結婚講究萬紫(5元)千紅(100元)一片綠(50元),這就是十幾萬,還得買車呢!”河南農家出身的劉長喜告訴記者,由丁農村男女比例失衡,比起小伙子,農村姑娘更容易在城里成家,農村老年人背負了沉重的競爭壓力。為兒子娶媳婦蓋房子、準備盡可能豐厚的彩禮,成了他們無法回避的一道坎兒。
劉桂花所在村的工作人員為前來調研的帶隊老師算了一筆賬,當地人均年收入6000元,兒子結婚彩禮加酒席10萬元,蓋房子30萬元,兒子成了家,老年人的儲蓄也基本掏空了。
“我給兒子蓋完房子,孫子有時候還來看看我。”坐在用繩子圍成的院墻里,一位老人滿臉輕松地說起自己的最大成就。不過調研的學生卻看出了悲哀。
“婆媳關系怎樣?”調研學生問住在“老人之家”的一名老人。
“好!”老人回答。
“為什么不一起住?”
“自己自由一點。”老人說完,移開了目光。
事實上,這個村子的很多老人和劉桂花一樣,安頓好兒子后,他們多數已無力再為自己蓋房了。“老人之家”土地歸集體所有,以自己小家庭為中心的兒子們也不愿在老人住房上投入過多。這些傾盡所有的老人如同耗盡了最后一滴燃料的火箭助推器,默默地隱沒在“老人之家”黑漆漆的小屋里。
“樂觀”的老人
追隨著房子和企業,大批年輕人擠入城市,留下荒蕪的土地和年邁的父母。空巢老人比例已經超過半數,達到55%。專家們認為,這并不新鮮的話題無疑是養老問題的重中之重。
在調研過程中,常有學生為老人們的“樂觀”“知足”感慨不已——每月領取60元勞保的老人感慨:“從沒想過能過上這么好的日子。”
經歷過戰爭、動亂、饑荒等災難,這些吃上了“好面饃”的老人認為不交租、不冷不餓就是幸福,能吃能喝就是健康。
參加調研的同學們注意到,有的老人嘴上說“滿意”,但臉是苦的,有的笑著說“滿意”,但又加上一句“不滿意還能怎么樣呢”?
廣東一位老人為給孫子騰房子搬到村委會看門,無奈地笑著說“想回家”。即便是住鐵皮房的劉桂花,也沒有大倒苦水,只是用“不好”來回答“子女是否孝順”的詢問。
有七成農村老人希望能與子女同住或住在子女附近,有86.5%的老人對與子女間的關系現狀表示滿意。
去年,張雄在湖南山區某村預調研時見到一名老人。這名老人白己砍樹、刨木板,在幾個親戚的幫助下,在山腰上建成一幢二層小樓,只為讓兒子過年回來時多住幾天。
過年那幾天,走出土地的孩子們“像天兵天將一樣回來了,一個村的生命力在爆竹中得到閃現,老人一年的心酸孤獨在節點上得到平衡”。在每家必備的圓桌邊,失去傳統家長地位的老人們在頗具儀式感的相聚中,尋找著自我尊重的感覺。
“幫幫我們”
劉桂花的兒子不管她,嫁到鄰村去的女兒常來給她送點吃的,即使住在冬如冰窖、夏如烤箱的鐵皮房中,這位老人也不愿走進養老院。
調查顯示,有兒女的老人即便出現兒女不孝等各種原因,6成老人也選擇居家養老,他們多數人對養老院有抵觸情緒。
“我有兒有女,不去養老院!”廣東普寧市一個富裕村子里戴金手鐲的老人說。
當然,還有一部分人則表示沒錢。超過半數的老人認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經濟不能承受、不自由、不光彩、去了怕被子女指責也是重要原因。
據調查,一半以上的鄉鎮擁有養老院,近五分之三的鄉鎮擁有老人活動室。
“擺設!”張雄拍著沙發扶手大聲說,“有擺設比沒有擺設好,因為是進步。”他認為,那些掛著鐵鎖的活動室至少說明了一點,僅有場地還不夠,還需要進行組織。
和“擺設”相比,廣東普寧市一個集體經濟發達村子的狀況就好很多。村里修建了公園,還舉辦過老人投籃比賽,聘請專業教練教授過太極拳。老人們可以在村里的宗祠喝功夫茶,出自該村的企業家還向村聯防隊捐贈了巡邏用的摩托車。
劉長喜說,他認為農村養老的根本出路是以地養老,讓從土地中獲取的收益更多地轉移到農民手中。然而調查發現,盡管半數以上的農村老人依然如老黃牛般在土地上耕種,他們卻難以收獲財富和地位。更多的地方政府從農民手中拿過土地,“種”出了樓房和企業。
問卷以外,劉桂花以為學生是政府派下來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的,為此激動不已。她并不是個例,很多老人搞不清楚學生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區別,一再請求“一定要把我們的情況向上反映給領導,幫幫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