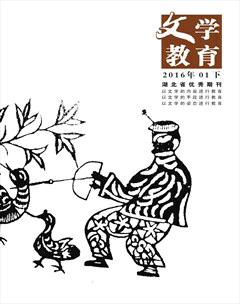重溫現代中國一場關于賽珍珠及其作品的爭議
李冠雄
內容摘要:關于賽珍珠及其作品的爭議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除去新中國成立之后一段特殊時期外,一直持續到現在,其中三四十年代的各家觀點尤為精彩。本文試圖通過回顧這場爭議的歷史背景及其細節,結合文本淺析賽珍珠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探討她對“東方”的認識,以及由此引發的敘事上的取舍。
關鍵詞:真相 東方 民族 自我
賽珍珠于193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大地》三部曲是她的代表作,描寫了農民王龍一家三代人的發家史,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中國人形象,主人公王龍與阿蘭身上勤勞堅韌的品質打動許多美國讀者,《大地》因此長期占據暢銷書榜首的位置。賽珍珠聲稱自己是中國人,熱愛中國文化,她的一生都與中國有著密切聯系。她不停地寫作關于中國的作品,不遺余力地推崇中國文化,為中西方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尼克松譽為“文化人橋”。但《大地》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許多人都認為她沒有寫出中國的真相,同樣也有很多人為她鳴不平,這個爭議直到現在仍在繼續。一個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卻引起這么大這么持久的爭議,這在整個文學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這場爭議究竟在爭論什么?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爭議?我們需要去溫故知新。
一
歷史上從未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像賽珍珠這樣不能服眾。當年與她競爭的作家都是鼎鼎大名的。但是最后名不見經傳的賽珍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結果注定了會引起一場爭議。
許多人都認為賽珍珠的獲獎,與其所處時代的特殊性有很大關系,這不無道理。
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召開。次年,德國便發動了二戰。更重要的一個細節是,諾貝爾委員會在1935年與德國納粹鬧僵。起因是他們將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反法西斯的和平主義者——德國記者卡爾·馮·奧西茨基。希特勒因此在1937年頒布法令,禁止任何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諾貝爾授獎委員會頒獎給宣揚跨種族人性之美的的賽珍珠,會不會是對希特勒及二戰的諷刺?我們只能猜測。但必須承認的是,賽珍珠的成功是有其偶然性的。
1890年到1935年是賽珍珠在中國的時間,也正是中國經歷劇變的時間。這個剛從封建制度中走出來的新國家,所有領域都遭受了劇烈的沖擊。短短幾十年間,它走過了西方數百年的歷程。自鴉片戰爭始,數十年經濟、政治層面的動蕩,終于造成了民國時期整個民族的思想劇變,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學人開始對民族的“自我”進行反思,“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我們應該如何?這些都是當時回響在每一個中國人內心深處的聲音,可以說那是一個從封建殘骸中確立新“自我”的時期。
《大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完成的。《大地》第一部出版于1931年6月,那時美國正遭受“大蕭條”,失業率急劇上升,許多美國人在“王龍”與“阿蘭”身上看到了勤勞堅韌的品質,在精神上獲得了支撐。一經出版,《大地》便登上暢銷書榜首位置,在國內也引起翻譯熱潮。從魯迅這樣的文壇領袖,到普通的素人讀者,都在讀《大地》,一時間賽珍珠蜚聲海內,爭議也隨之而來。
二
賽珍珠對中國的描述影響了世界各地的人。所以,我國學者們對她究竟寫沒寫出中國的真相尤為看重,關于真相的爭議自然也是最多的。
(一)魯迅、江亢虎、祝秀俠、胡風的觀點
魯迅在《與姚克書》中評論《大地》說:“先生要作小說,我極贊成,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究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
中國海外學者江亢虎用英文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抨擊賽珍珠在她的作品《大地》中丑化中國,作品內容失實處不勝枚舉。他認為王龍這樣的農民并不能代表中國,而且《大地》中“官頂子亦不見了”。
在三四十年代眾多文章中,祝秀俠的文章是言語最為激烈的。祝秀俠在他的《勃克夫人的<大地>——一本寫給高等白種人的紳士太太們看的杰作》中言詞十分激烈地批評《大地》,他的結論是:“《大地》是寫給外國的、抽著雪茄煙的紳士們和有慈悲的太太們看的。作品通過‘大地用力地展露中國民眾的丑臉譜,來迎合白種人的驕傲和興趣”。
胡風也撰文批評《大地》,提出了兩個尖銳的問題,“第一,這個在中國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女性作家,對于中國農村是怎樣觀察的?農民的命運和造成這樣命運的條件,在她筆下得到了怎樣程度的真實反映?”。第二個問題是這樣說的:“本書在歐美讀者里面的驚人成功,是由于她的藝術創造的成功呢,還是另有原因?”。胡風認為《大地》并沒有對農民的命運有真實的反映,它所展現出來的異國情調才是它成功的關鍵;而且在藝術創造上,不應該給《大地》過高的評價。
(二)賽珍珠、斯諾、林語堂等人的觀點
對于江亢虎的文章,賽珍珠本人在《紐約時報》上刊文回應,“倘若在任何國家內,居大多數者不能為代表,則誰復能代表?”、“我知道江教授要說什么:還有像他一樣的那些人。他們要求由他們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來代表中國人民。他們要求用已經過去很久的歷史和已失去生命力的畫像(它們是祖宗留下的古典藝術)來代表現在廣大的、豐富的、憂郁的、歡樂的中國人的生活。……為了顯示高傲而藐視沒有文化的農民,完全忽視無產階級的興趣。因此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普通人民遭到過像中國人民那樣多的飽受自己國家的軍閥和知識分子領袖們的折磨與壓迫。在中國,平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裂縫就像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Nora Stirling在《Pearls Buck:Woman in conflict》中描述過,海倫·斯諾初到中國之時,對于當時知識分子對待《大地》的態度感到驚訝:真沒想到年輕中國知識分子對它竟如此切膚痛恨……他們說:“她本不該寫這些可憎的人。干嘛不寫……文明人呢?”。
賽珍珠曾經的好友林語堂也撰文發表過類似看法,他在《白克夫人的偉大》一文中將江亢虎一類的高等華人批判得無地自容,“高等華人所引為羞恥者,我國之‘苦力也。愛國志士所忌外人知道者,亦我國之窮民也。一見外人,即以平民之衣衫襤褸,茅屋湫隘為恥,欲掩飾之不暇。此種淺陋之見,適足以表示吾民族之失自信心,一味以傲效皮毛粉飾門面為能事,而中國之偉大,究竟在何處,無人知道”。
(三)毛如升、黃峰的觀點
毛如升在《勃克夫人的創作生活》一文中有過一個經典的評斷:“莎士比亞的偉大史劇《凱撒》誰也知道里面有多少地方是不符事實的,何況這本《大地》并不是一部歷史小說,風格等忠實與否不是她的責任,她的責任只是把赤裸裸的農民生活,真摯地表現在她所特取的美的風格形式中”。
在戴平萬、葉舟等譯的《愛國者》后記——《賽珍珠和她的<愛國者>》一文中,作者黃峰引用了美國《亞洲雜志》的一封致賽珍珠的公開信,這封信指謫賽珍珠在1937年于該雜志發表的《西方人的武器握在冷酷的東方人手中》一文沒有真正弄懂中國。
信里說:作為一篇詭辯的文藝作品看,你這篇大文或許是聰明的,但一個權威,一個東方的介紹者得更多的審慎,這是人們所期望的。因為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你是一個權威,而且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你是一個中國友人,你必須認識到自己每一句話的重大責任。
三
這場爭議發展到黃峰這里,其實已經觸及到了部分實質。賽珍珠雖然只是自由作家,但她同時也是東方介紹者,應該更多地審慎。那么,她究竟哪里不審慎了呢?
首先,在《大地》中,我們極少看到政府官員的影子。這一點已為江亢虎所提到,也許是江亢虎反動文人的身份讓他這個發現沒有引起回響。賽珍珠在給江亢虎的回應中聲稱“隱去官頂子”是自己有意為之,她的意圖何在?
賽珍珠的丈夫布克是一位農學家,他對中國農業的研究在該領域有極其重大的意義。費正清先生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中,談及中國農業狀況時所引用的資料,大部分來自布克先生。那時候的中國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中國家庭歷來有分家的傳統,土地分配到最后越來越小塊化,基本只夠生存。據記載,那時中國農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佃戶,只有極少數是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擁有上百畝土地的大地主更是鳳毛麟角。脆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其平衡很容易被破壞,隨便一場天災人禍便能將人逼入絕境。但這還不足以令一個王朝垮塌,真正讓清王朝經濟平衡被徹底打破的,是那些不平等條約所列的賠款。據《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田賦占了當時清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有的關稅拿去賠款仍還有絕大部分沒有著落,于是清政府開始增收田賦、厘稅,用雁過拔毛來形容再恰當不過。大部分賠款最終被轉嫁到農民身上。他們認為洋人來了帶來了厄運,并不是空穴來風。
若將“官頂子”展示出來,必然會牽涉到外國侵略的問題,這與主題背道而馳,美國的讀者成了侵略者的共謀,也許就不會那么歡迎《大地》了。所以賽珍珠才將它隱去了。
其次,薩義德的《東方學》出版之后,西方人的“口味”問題被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滲透在了各個領域之中,東方一直被想象為落后的蠻荒之地。這個想象,到了賽珍珠這里發生了變化,她將勤勞善良的品質植入了這個原是“黃禍”的想象架構之中。雖然如此,如果深究本質,則會發現賽珍珠引發的改變仍然是西方話語體系內部的反思。
賽珍珠在《大地》第三部《分家》中的寫作風格與前兩部有了明顯的變化,她更為關注王源個人的內心世界,所以筆觸更為細膩,有時甚至顯得冗長而乏味,直到小說最后,王虎被土匪打敗,王源矛盾的內心才最終在梅林身上找到了歸宿。在這之前,他搖擺不定的內心一方面因祖國歷史的輝煌而自豪,另一方面又為它現實的愚昧與孱弱而自卑。針對這種矛盾心理賽珍珠描寫了三個人物,分別是堂兄王盛,堂弟王孟以及王源。王盛完全西化,整日吟詩作對,對祖國前途命運似乎毫不關心,脫離了自己的根,陷入虛無的生活,他太“新”了,本質上幾乎不再是一個中國人。他的堂弟孟走向了極端的革命,他在人力車夫與洋人的爭吵之中趕走了洋人,然而轉身所面臨的卻是愚昧的車夫,他怒其不爭。隨后不久便背叛了他的司令,投入到一種新的革命中去了。孟否定一切,因此他的革命似乎陷入了無限否定的循環之中,永遠不會結束。孟讓人想起民粹主義,最終走向了極端,是太癡迷于“舊”了。源不一樣,留洋歸來后他接受了現實,舍棄了自己部分的私愿,將父親的債務扛了起來,又投身教育踏踏實實地教書育人,他承載了“舊”,又接受了“新”,成為了賽珍珠理想中的中國人。梅林是被遺棄的孤兒,她有傳統中國女性的美好品質,又有新女性的自我意識,也是一個“不舊也不新”的人。賽珍珠以這兩人的結合作為全書的結尾顯然是大有深意的。
這初看上去并無問題,實際上隱藏著賽珍珠“西方一元論”的歷史進化觀。我們應該注意到,“新”的部分全然來自于西方,西方在《大地》中被視為東方的模版。無論是王孟腦海里的輝煌首都,還是王源理想中的中國未來,都是以美國為模版的。賽珍珠“歐美中心論”是明顯的,她的宇宙進化觀仍然是一元的,是唯西方的,“白人優越感”轉化為一種對弱者的同情,還有一種過來人的淡然心境,希望中國成長為另一個美國。從根本上說,她仍然沒能擺脫“東方主義”的棱鏡,只是對同一個東方的另一種態度罷了。這恐怕是賽珍珠和她的《大地》爭議不斷的根本原因。
四
關于這場爭議,所涉及到的問題很多,本文只是略談了皮毛,賽珍珠及其作品的更大意義還需要時間來發掘。在當代,賽珍珠“文化人橋”的意義更為凸顯,但一味地稱頌會讓我們忽視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她陷入爭議的根本原因。如今的賽珍珠的研究越來越細致,似乎學者們都有意避免對她進行宏觀的評價,究其原因,可能還是爭議太多而無法定義。實際上,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賽珍珠都處在一個尷尬的地位,對于兩國文學史而言,她都沒能被完全地接納。也許正是她跨文化的屬性,讓她處在夾縫之中,同時她還是一名通俗作家,這樣一來連傳統的文學標準似乎也對她失效了,她的意義也許已超出文學之外。通過對這場爭議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或許在文化層面來論述她要輕松許多,她仍然是一個西方人,面對同一個中國,寫出了自己不同的態度。
參考文獻
1.賽珍珠 著,王逢振 等譯:《大地》,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2.[.美]費正清 等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 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985年版
3.[美]費正清 等,章建剛 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
5.[美]齊亞烏丁·薩達爾著,馬雪峰、蘇敏 譯:《東方主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6.[美]巴特·穆爾·吉爾伯特 著,陳仲丹 譯:《后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7.劉龍主編:《賽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郭英劍編:《賽珍珠評論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