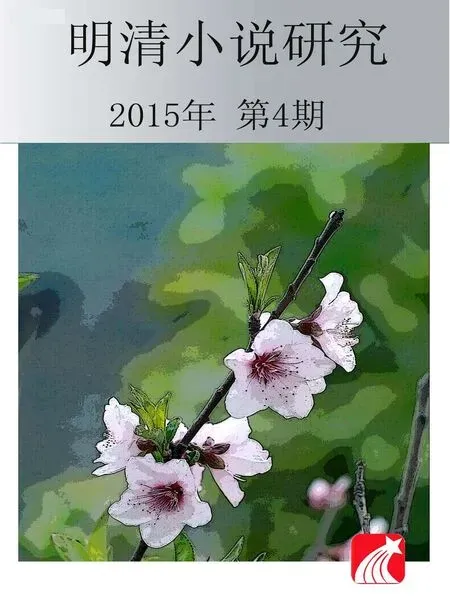《儒林外史》中筵席的敘事
《儒林外史》中筵席的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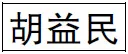
摘要
《儒林外史》中對筵席的描寫很多,構成了該小說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認為書中的筵席描寫蘊含豐富,在表現人物形象、刻畫人物性格以及推動小說敘事等方面都有巨大作用,其具體表現為暗示性、隱喻性、媒介性以及筵席上對話的詼諧矛盾性、整個筵席的狂歡意義等等,這些使得該小說的敘事極其多姿多彩,并體現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現代化”進程。關鍵詞
《儒林外史》筵席敘事魯迅先生評《儒林外史》:“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引,物無遁形……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儒林外史》的寫實性較之以往確有大大增加,體現了近世文學向新文學邁進的過程。它對18世紀江南社會“世相”的寫實,因為“據自所聞見”,筆力又“足以達之”,給人以“如在目前”的逼真感。作者更是“秉持公心”“婉而多諷”,在繼承本民族白話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將古典小說敘事藝術推向高峰,在敘述方式、敘事技巧、描寫深度等在內的形式改革上接近了現代化,這體現在書中各種“世相”的敘述和描寫中。譬如《外史》中作為整個敘事有機組成部分的筵席描寫,就生動體現了以上特點。
論者在論及《儒林外史》的諷刺性藝術時,將書中全部敘事和描寫無一例外地都視為諷刺,然而筵席場面這一生活情景本身并無諷刺性,但作為敘述的有機部分,難于同其他情節割裂開來看,因而有時也確乎存在一定諷刺或寓言的意味。書中看似簡率甚至粗俗雷同的筵席情節描寫,卻因為很多情境明顯吸收了來自民間的喜劇形式,和利用戲劇中的插科打諢等藝術表現形式,蘊含了作者的深意,故而使得《外史》中的筵席敘事與其他諸多小說有著很大的不同,體現了古典小說敘事藝術的較高水平。
假如將《儒林外史》中有關筵席的描寫與《金瓶梅》和《紅樓夢》中宴席的描寫相比較,遠不如后兩部小說讀起來那么精致和令人眼花繚亂,甚至有連篇累牘式的雷同和鮮明的世俗氣。個中原因當然是因為《外史》中所表現的主體并不是貴族富豪而是市井中人,也無意表現奢華的排場與橫流的物欲;此外,還因為小說作者有意婉而多諷,讓所描寫的筵席與一種窮酸氣、腐儒氣以及市儈之氣緊密相連,使得藝術表現更加世俗化、生活化。例如在特定場合有意制造一種滑稽幽默的戲劇矛盾氛圍,來增添諷刺的藝術效果;利用筵席的特殊環境揭示參加筵席者的人性,從而指向知識分子墮落的原因探尋。所以總的說來,吳敬梓并不關注奢豪的筵席場面,沒有像《紅樓夢》不避繁瑣那樣津津有味地細致描寫筵席,更沒出現表現繁文縟節的盛大宴會描寫,而是表面上看似不經意地隨意著筆,實則將豐富的內涵融于樸實的敘述中。
仔細閱讀文本我們發現作者幾乎在小說的每一回都會寫到吃,無論是小說人物在家中日常的請吃、朋友們于酒樓的宴集,還是同道者享用著江南茶點的小聚等,多者數百字,少則三五言,作者借著對筵席、飲食的細節刻畫極大豐富了敘事內容,營造了一種與故事情節水乳交融的氛圍,從而成為整個敘事不可分割的有機部分。
在具體探究各類筵席或飲食的豐富內涵前,不妨對小說中提到的食物做個不完全統計,書中筵席(食物)描寫對象如下:
雞16次,鴨22次,豬肉(包括下水、火腿等)32次,魚蝦(包括蟹)24次,其他(時蔬、瓜果)22次,茶點(各類點心小吃)16次等等,沒有寫具體為何物,只是說飯菜或酒飯的也有好幾次。從以上粗略統計來看,都是普通的飲食,完全是當時市民生活場景的再現,讀起來甚至覺得重復而缺乏創意。但是當每一次普通的聚會和同樣的吃請不斷出現時,因為人物、情節、境遇的不同,這些大大小小、林林總總參與到敘事之中的筵席描寫就有了迥異的內涵和作用。
一、筵席的寓言暗示性
小說里家喻戶曉的一個例子就是蘧公孫與魯編修女兒完婚的宴席上,被一只梁上掉下來的老鼠攪得一團糟,就像傳統的相聲里所描述的場景,書中描寫道:
副末……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膾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然“乒乓”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掉在燕窩碗里,將碗打翻。……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里,嚇了一驚,把碗跳翻,爬起來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副末領單下去。
這段描寫戲中有戲,非常具有喜劇性的場面,在一個本是新婚嫁娶的喜慶日子里卻被一只老鼠攪得一團糟。不光如此,小說接著又寫道“管家因為看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昏了,忘其所以然……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一個烏黑的東西溜溜的滾了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民間節慶儀典上的飲食,是普天同慶……決定著……正面的夸張、隆重而快樂的基調”,但是此時,好端端一場婚宴又變成狼藉一片,成了一只老鼠的獨角戲,誠如臥閑草堂評曰:“吉期飲宴時忽然生出兩件奇事,是埋伏后文編修將病而死,所以點明‘編修自覺此事不甚吉利’。但閱者至此,惟覺峰飛天外,絕倒之不暇,亦不足尋味其中線索之妙。”可見,作者描寫本來孕育新生活的婚慶筵席不僅是為后文埋下伏筆隱藏了線索,也像寓言一樣預示著蘧公孫與魯小姐兩人的婚姻未能善始善終,所謂“不甚吉利”就應該指此,這場由喜劇演變為鬧劇直至悲劇,老鼠的攪局實為“讖緯之言”,這樣的筵席描寫就具有很強的寓言暗示性。
第五回寫到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了一席家宴,與趙氏坐著說話,桌子底下一只瘟貓攪了局,“把床頂上的板跳塌一塊”,打翻了一地黑棗子,下面露出了嚴監生原配王氏畢生積攢的銀兩,然而嚴監生“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后來便叫著心口疼痛,不久一命嗚呼,同樣是通過描寫家宴,準確地說應該是一場具有宗教性的傳統儀典被打擾中斷,作者有意宕出一筆作出一種寓言暗示。《外史》中較為盛大的筵席與民間節慶儀式間都有著重要關聯,對渲染氛圍和推動情節皆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譬如蘧公孫與魯小姐的婚慶儀式、嚴監生除夕的家宴,都是普天同慶,理應以歡樂、隆重為基調的場合,卻出現不和諧音符,從而通過筵席的混亂暗示了不祥的征兆,為后來的故事情節埋下伏筆。筵席敘事的作用不僅如此,在小說中還通過描述筵席的飲食范疇而向讀者傳達隱喻性意義。
二、筵席的隱喻性
《儒林外史》中令人印象深刻、最典型的筵席場景描寫,比如第二回寫周進。一天,前科新中的舉人王惠途經薛家集觀音庵,在此歇腳,并要周進作陪。王惠編造了一大通故事唬弄這個窮苦卑下的私塾先生,“管家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著吃了,收下碗去”。等到次早,丟下一大通“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害得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這是一個以現實主義方法描繪的喜劇場面,兩種進食的對比描寫,略微帶有夸張,不僅寫出新中舉的讀書人可以盛氣凌人、高人一等,也刻畫出未進學的窮楚讀書人的屈辱經歷,無疑是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帶淚的喜劇。為什么會感到一種凄楚與無奈呢?這是因為等級不同直接決定了是否有肉吃,《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將貴族階層比喻為肉食者,換而言之,雞鴨魚肉的渣滓比喻的就是未進仕的寒門,因為未能進入上層階級,便只能啃食貴人的殘羹冷炙。
還是同一回,在上述例子之前,還寫了周進被申祥甫等人邀為孩子的蒙師,請吃飯,“眾人序齒坐下”,端上來的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全是民間盛傳的所謂“發物”,能引起興作的食物,這里似乎也有隱喻之意。不過周進“長齋”,“一箸也不曾下”,天目山樵評曰:“孝子。他日舉人進士之根。”然而其他幾位如梅玖等人也借此機會一番說笑,好好地羞辱了周進,接著又逼迫周進破戒,吃“丁祭肉”(這又是民間流行的儀式,即每年二月、八月第一個丁日祭祀孔子),所以梅玖調侃道:“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眾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吃了素點心就著茶,始終不肯破齋,其心意執著堅定,將未進學而忍受他人之侮辱統統咽進肚里。無論是“豬頭肉、公雞”等發物,還是提供祭祀的“丁祭肉”“胙肉”都是比喻著進學發利,比喻著新的生活開始,而周進的齋戒則似乎寓意為尚未取得功名,乃是“未發”。這里將進學隱喻成集市生意一般,借用俗不可耐的語匯來顛覆八股、科舉在無數士子心中神圣的“光環”,足見吳敬梓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
還有第三回,寫范進岳丈胡屠夫手里拿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則又是另一種隱喻。大腸乃吸納污穢之處,配得上胡屠夫的職業與秉性——粗俗、勢利和無賴的個性,特別是小說著意描寫了胡屠夫在范進進學前后態度劇烈轉變上的種種丑態。事實上,這里讓讀者看到,無論是否闖過科舉這一關,人的本性必然會暴露,庸俗者更庸俗,作惡者更加倍的惡。小說后來的情節印證了這一點,作者用戲劇化的情節揭示了一個事實,就是將人性墮落為更加庸俗卑劣的罪魁禍首是科舉取士制度。
書中也有不同與上文暗含鄙意的隱喻,比如第十六回,匡超人極盡孝心,“買個雞、鴨,或是魚”,“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這里難登大雅之堂的食物恰恰隱喻著一種人性美,“因太公是個痰癥,不十分宜吃太大,所以要買這些東西”。還有像深夜他在父親病榻前大聲朗讀八股文的細節,都看似不經意閑筆的描寫,作者卻不避其贅,用那些普通的食物喻指匡超人的個性與美德,同時這里也暗示了匡超人的未來。接下來作者罕見地用近六回的篇幅描寫了匡超人處于變化成長的未完成過程,同時也刻畫了因為在不可預測的時間流的腐蝕下,新的環境和社交圈子令匡超人誤入歧途,隨之墮落的全過程,其人性的發展變化、周圍環境重塑人之性格和命運等問題令人深思。書中的飲食和筵席除了含有寓言和隱喻性的深意外,還作為一種介質溝通了人與社會。
三、筵席的媒介性
食物可以說是人類與客觀世界構成關系的媒介,因而通過筵席的描寫,深刻展現了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從而生動揭示了隱藏的人性。比如小說開篇寫王冕“烙了一斤面餅,炒了一盤韭菜”接待吳王朱元璋,作者以王冕的“家宴”來呈現其本性,正如閑齋老人《序》曰“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臥評:“原有一種不食煙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通過描寫對象的飲食事實上揭示出了真實人性。
再如小說第十八回:

這里是景蘭江帶著匡超人為了同支劍鋒、蒲墨卿等四位所謂“名士”宴集前做準備的場面描寫,黃小田評景蘭江曰:“慳吝人寫得如畫”;“既如此,何必不做雅人。且分金亦不多,依舊要你包元”。評趙雪齋多給轎夫幾分銀子曰“到底是第一個名士,多出了四分銀子”等等,本是名士間作詩飲酒的聚會,詩情才華才是描寫重點,但是作者不吝筆墨詳寫了筵席的如何備辦,以及為了蠅頭小利而與商販爭執的場景,故意以此沖淡主題,而那些名士不過“分韻已定,又吃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而已。通過此次宴集,作者有意構筑了一個所謂名士“雅集”的真實世界,作詩詞與作八股文看似勢不兩立,卻能在匡超人身上出入自由,這本身就是一種反諷,那些所謂名士又究竟如何作了詩呢?“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語上采下來的幾個字眼。拿自己的詩比比,也是不見得不如他。”黃評語:“不寫諸人之詩如何不通,只從匡超人看出,且曾表明匡超人聰明,故自覺諸人之詩不如他。”這里揭示出假名士的真面目才是作者真正的用意,對假名士宴集前的描寫只是一種媒介,有意在一種世俗的氛圍里深刻表現人性本質,使人的本來面目無處遁形,這是何等的老辣之筆!
還是小說第十八回,文瀚樓店主人邀匡超人出書選考卷文章,“午間又備了四樣菜”,對超人說出了條件:“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著店里吃‘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里供給的。”匡超人大喜,齊評曰:“有小兒得餅之樂。”從字面上意思看,不過是店家滿足出書作者日常生活必需,但是似乎也暗示了選考卷文章就好比平常吃喝拉撒,并無二致,透露了作者對選考卷文章暗寓了諷刺揶揄之情。僅僅“小菜飯”就已經讓匡超人心花怒放,可見即便制舉業在現實世界中并不敵溫飽肚子要緊,人首先要生存才能圖發展,所以糊住嘴是人立足于現實世界的根本,匡超人那時對這個世界的索取僅僅就是能糊嘴的“小菜飯”而已,他與世界多所構成的簡單關系就是以草具之食為媒介。
再例如小說第二十一回寫牛老爹和卜老爹喝酒吃飯,“燙了一壺酒,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筍干、大頭菜”,三言兩語構筑了日常生活中平凡真實的兩位百姓真誠的交往關系,可謂質樸率真,與前文提到的那些假名士對比強烈,事實上,對飲食的不同要求深刻反映了人性的欲望。所以說,作者在借助他筆下所描寫的種種場面,在特定舞臺上展露人物形象,旨在拷問人性,揭橥人的靈魂,譬如在上文例舉的日常筵席和聚會中,逐步揭開人的真實的精神世界,從而塑造了形成鮮明對比的個性形象,而筵席則成了人與周圍客觀世界發生聯系,構成一種聲音交流的媒介,筵席中的語言對話是極富有特定內涵的。
四、筵席上對話的詼諧與矛盾性
“筵席作為對智慧的話語、詼諧的真理的鑲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飯桌上的談話是戲謔的無拘無束的談話,這樣場合的言談,其實同時與其內在的心理活動也是完全相吻合的。在這種氛圍下,人們可能排除任何謹小慎微的想法,袒露心跡。因而作者有意識在特定的筵席環境中通過對話來表現豐富的真實人性。
例如小說第二十五回:

在這場筵席中,通過對話來“追憶”,讓主人公敞開心扉,盡情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對朋友真情流露。作者借倪老爹酒后真言“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批判了讀書致窮而絕無出路,甚至墮落至賣兒鬻女的社會現實。作者不避煩贅具體描寫一次次普通的筵席(絕大多數僅僅是吃飯而已),目的就在于表現普通人的生活,且為塑造人物的形象精心構建一種特殊的氛圍,在每次筵席間讓人們自由的對話,幾杯熱酒下腸后便推心置腹的揭露真心。譬如本來要隨意“吃個便碟罷”但鮑文卿認為“便碟不恭”,于是端上鴨子、肉片,鮑文卿以一句較為詼諧卻含有反諷的問話開了場,“斯文人”如何做了“修補樂器的事”?很顯然,這兩種身份在那時看來水火不容。接下來的一段對白令讀者唏噓不已,倪老爹哭訴了自己的痛苦遭遇,這與讀者閱讀期待的喜劇氛圍形成了反差,從而加強了本段情節敘事的反諷性,也暗含了倪老爹過繼給鮑文卿的兒子與這兩位老者存在著巨大反差,兩種人性對比鮮明(后文第二十六回題為“鮑廷璽喪父娶妻”可佐證)。可見人物的語言描寫極其重要,而在筵席上的種種說話描寫又成為刻畫人性的極其重要的特殊手段。
再舉一例:


五、筵席的民間狂歡意義


泰伯祠大典本身有恢復儒家正宗的意味,在書中被描寫卻成民間難得一見的“狂歡”,對于百姓來說幾十年來未見得這樣的體面禮儀,世風澆薄,傳統禮儀早已蕩然無存。面對群眾的追捧和“扶老攜幼,挨擠著來看,歡聲雷動”,參加典禮儀式的士子們又都歡喜和滿足。筵席的盛大恰恰襯托出人性的貪婪與虛偽,在不明真相的百姓簇擁歡呼聲中,讀書人的欲望得到了極大滿足。當然,在一群祭祀大典中,作者讓我們看到尚還有良心未泯滅的真正的信仰者如虞博士等,他們在作者看來是整個社會希望的種子。在污濁不堪、人心渙散、利欲熏心的黑暗現實中,恢復儒家真正的傳統,以儒家正宗思想解救社會,救贖人的靈魂恐怕是只是作者當時遙不可及的夢想。書中泰伯祠大典對于儒士來說也只是一種恢復禮儀的象征,然而對于尚未覺醒的百姓民眾來說典禮就是盛大筵席,只是一場盛大的“狂歡”而已。
綜觀全書,吳敬梓充分利用書中人物大小各種筵席詳細描述,在有意味的敘述中展開情節和揭示人物內心,塑造人物形象,以婉而多諷,表現世態人情,這些敘事藝術也為后來者提供了借鑒。
注:
①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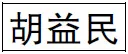
責任編輯:王思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