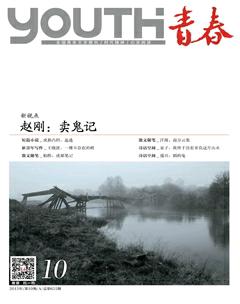南方云集
汗漫
1.一溪惆悵
天姥山下一條小溪名為“惆悵溪”。溪上有古舊石橋一座,乃上山下山者必經之途。
所以,李白、杜甫、孟浩然等等四百余位唐代詩人越過天姥山直抵臺州,必經此溪此橋,必惆悵。當地一書生在十年前研讀《全唐詩》,發現秘密:自杭州錢塘江啟程,經剡溪、天姥山、臨海、天臺山,終結于東海——這是一條唐代詩人密集游走的“浙東唐詩之路”。他們在這條長約一百八十公里的水路山路上乘舟、騎驢或步行,寫下約一千六百余首詩篇。
詩,就是失,就是惆悵。陸地消失、大海浮現,帶來無盡詩意和惆悵,吸引四百多位唐代詩人以及后來無數文人騷客,奔向吳越。
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成為天姥山的廣告詞和旅游說明書。其中,最好的句子并非篇首關于浙東山水盛景的夢中幻象,而在于結尾處的痛心疾首:“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一個惆悵之人、詩人,走過惆悵溪,看溪水如古往今來的人與事,明滅不定,東流入海。一群群惆悵之人,結隊走過惆悵溪、班竹村、東晉山水詩人謝靈運伐木鑿巖開辟的小路,登上天姥山,望洋興嘆。一代又一代惆悵之人,走過惆悵溪,然后像溪水里的葉子、花朵、光線、魚,消失于時間、詩……
一個深秋的下午,我自上海而來,自紅塵和權貴們中來,直腰,站在惆悵溪邊,想起不開心的李白。當年,李白在此,想起的應該是惆悵溪下游的剡溪,以及在一個雪夜里訪問戴安道的行為藝術家王子猷。王子猷這個《世說新語》里頻頻出現的人物,在剡溪的雪夜里應該想起埋在剡溪岸邊山中的父親王羲之。王羲之在惆悵溪、剡溪以北的山陰蘭亭,以人工引來清流激湍作為流觴之曲水小溪,與友人列坐溪水兩側一觴一詠、暢敘幽情,嘆曰:“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一個古人想起他以前的古人,想起他之后的我、我們……
一溪惆悵。
水,流逝,時間的隱喻。萬水歸海,海就是時間的集合,如墓,如藍色屋頂、卷宗無際的偉大圖書館——美國現代詩人肯寧翰的一首兩行詩:“生流向死就像溪水流向海,生是新鮮的而死對于我卻是鹽。”這句子,像是在剡溪、惆悵溪、山陰蘭亭曲水小溪邊寫的,像是在向李白的“古來萬事東流水”這一名句致敬。肯寧翰像李白一樣在夢中登上天姥山眺望東海和死亡?一個絕望的人,一個書生,只能在語言里自救、尋找鹽?
在上海,環堵蕭然。在天姥山,四面蔥蘢。豹隱青山龍歸海。我非豹非龍,獨自登上天姥山頂峰眺望一番,然后下山,在斑竹村里晃蕩。卵石鋪筑的古驛道依舊,驛鋪、客棧、飲食店、貨棧、百貨店依舊,官員、公差、隱士、俠客等等古人不再,往來者皆為當代村民或游客。在一茶館內喝茶,老板講了惆悵溪的傳說:很久以前,劉晨、阮肇二人入天姥山采藥,在這溪邊遇兩位仙女,各自相戀,并在此筑房成家;一日劉、阮下山賣藥,歸來,兩位仙女已渺無影蹤,徘徊溪畔,惆悵不已,附近竹葉也因兩個男人的淚水而斑斑點點——溪名、村名由此而來。關于美的惆悵,同樣是關于時間的惆悵:怎樣才能使時間克服美的虛幻和短暫……
班竹村粉刷過的舊土墻上題滿詩句,署名為謝靈運、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朱慶余、王勃、賀知章、許渾、宋之問、杜牧、蘇東坡、陸經、林逋、李漁、郁達夫……歷代詩人打破時間的界限,歡聚一壁。那些枯寂如古宣的墻壁,因這些名字、墨跡而美好。我已經沒有了毛筆,只能掏出小鋼筆,抄錄墻壁上幾首關于惆悵溪的句子:“只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中。細草香飄雨,垂楊閑臥風。卻尋樵徑去,惆悵綠溪東。”(劉長卿)“我生南北本殊津,邂逅相逢若聚蘋。送客溪邊一惆悵,新歡過眼又前塵。”(王洋)“桃溪惆悵不能過,紅艷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韓愈)……
夢游天姥吟留別。吟誦,留給友人后人,以便小別或永別。
沿惆悵溪下行,經過沃洲湖和沃洲山禪院。禪院安靜,墻壁鐫刻白居易所寫的《沃洲山禪院記》,其中最好的一句為“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這座古寺,應該是眉目之間的一粒長壽的痣?我是這眉目之間的一粒塵埃?禪院內竟設有一戲臺,逢陰歷節日有越劇演出以娛神。越劇,就產生于剡溪所一越而過的嵊州——剡溪,像越劇中女子凌風飛揚的水袖情懷,剡溪兩岸的云團,如同越劇中的念白……
尤其喜歡于是抄錄禪院戲臺兩邊木柱上所刻的一幅對聯:“白頭夫妻三更月,碧血英雄一局棋。”人生大戲,也無非“愛”“恨”“情”“仇”四字。月落棋罷,萬千夫妻英雄,一概煙消云散——
惆悵。語言在緩解還是加重著惆悵?詩、文、念白,是在淡水中加鹽,還是在傷痕上撒鹽?
捏一支鋼筆,捏一溪墨水和惆悵,我的手指像惆悵溪上的那座石橋,爬滿皺紋般的青苔……
2.片石山房的月亮
揚州慢,時間在揚州園林里終于慢了下來,
敘事和沉思在繁復的細節里才會減速,半日可抵百年——
何園,何芷舠的園子,一個晚清重臣的園子。
從快退隱到慢,從廟堂退隱到片石山房,
亂石模擬山川,池塘隱喻江湖,用石頭間一處孔穴和光,
合作完成池面上一輪白晝的月亮——
一個隱者、一個歸人的心臟病?
這是我游蕩揚州兩日之后寫下的詩作《揚州慢》中的一節。
何園,晚清湖北按察使、江漢關監督何芷舠(1835—1909)在49歲時急流勇退、購入片石山房、用十多年時間建成的私家園林,如今成為與個園齊名的“晚清第一園林”。
中國園林,南北有別。北方園林格局擴大,喜紅黃二色,似官服,似官方報紙套紅標題的社論,平鋪直敘。南方園林大都因占地面積有限,必須疊石、筑樓、曲廊,方能移步換景、搖曳多姿,像用不多的詞匯、不長的篇幅來寫詩——讓語言在不斷的轉折中凸顯深意。白墻黑瓦,如同園林主人知白守黑的信條——知白晝之繁囂,守黑夜之靜幽。何芷舠,就是這樣一個厭倦了晚清宦海,把何園當成一個春夜、一個春夢的智人。
“舠”,刀子一樣的小船,停泊在何園一角用瓦片鋪就的地面“浪花”上,成為“船廳”,何芷舠與小妾曾斜臥其中,喝茶、聽雨、讀書,想想李鴻章、左宗棠們正乘風破浪或逆水行舟,嘴角就微微露出一絲嘲諷?但他并非一個徹底熄滅了人間煙火氣的隱者雅士,天井地磚上用卵石鋪就的圖案,泄露了主人的隱秘內心:鳳凰在梅花鹿脊背飛翔,暗示“俸祿”;花瓶中插著三把劍戟,兆示“平升三級”。善于使用隱喻,是何芷舠們的一大特點,無論從政、退隱,都需要歪打正著一般的修辭能力。何園,是何芷舠的一闕《揚州慢》?
但它更像一種復調敘事:結構、語言、內涵,都矛盾而多元,眾聲喧嘩,而非單一旋律的奏鳴——何園中央懸空的兩層復式回廊,被建筑界譽為“城市立交橋”的雛形和模型,可供主人、來賓、女眷、仆從等分層次、分區域流動,有效提升了空間利用效率、維護了各群體的私密性。房間內的佛像、香爐、日式拉門、法式壁爐、油畫架、百葉窗、西洋歌劇唱片、太師椅、沙發、山水畫、黃酒作坊……敘述著晚清時期中西雜糅的一種生活方式。多年后,何芷舠移居上海,耗盡全部財力辦持志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前身),培養翻譯家、外交家——這是一種出人意料而又合乎邏輯的復式小說的結局。
但我更喜歡把這個園子稱為片石山房,因它與苦瓜和尚、清初畫家石濤(1630—1724)有關。
石濤也是一個復調的人:原名朱若極,生于明末皇族世家,十歲時明亡、家人罹難,成為孤兒,被一太監帶著逃出華麗宮闕,剃發修行,改名石濤。在寺院里開始習禪、畫畫,尤愛在敬亭山、黃山一帶漫游,手摩心追,“搜盡奇峰打草稿”,創造出一種濕墨筆法:將一張空白宣紙弄濕,再行筆墨,如同春雨后的一片曠野才能有奇山異水呈現。成為與八大山人齊名的同代畫家。受到兩下江南的康熙的接見,跪拜于揚州運河邊的碼頭,呈上 《海清河晏圖》。還俗,娶妻生子,賣畫養家,定居揚州。死后葬于瘦西湖邊的蜀岡,成為奇峰之上的一地青草……矛盾,多元,一言難盡。
在揚州,石濤安頓自己的身體和內心,用畫卷和石頭。片石山房,是石濤用一片片石頭作為筆墨層層堆就的立體山水畫卷:一道白墻,如同宣紙,白墻前一方池塘,“池上筑太湖石山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清人錢泳《履園叢話》)。細細端詳這一脈蜿蜒僅百余丈、石頭頂端舊色如積雪的“寒山”,山峰形勢與石頭紋理相一致,大約也在實踐著石濤的筆墨理念:“峰與皴合,皴自峰生”“一峰突起,連岡斷塹,變幻頃刻,似續不續”。想象石濤,大約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觀察、選擇、搬動、疊放,如同把種種塊壘、積郁一一搬出內心,來接受雨水澆灌、風雪淘洗,成為山水自然的一部分……
片石山房,一件傳世之作,成為一個人的化身。至于這一帶“寒山”之巔有意構造的一個圓形縫隙,則幫助天光穿過,合作完成池面上一輪白晝的月亮——沿池塘,慢慢走,隨著角度的轉移,可以看到這輪虛擬的月亮在變幻盈缺,從新月、滿月,到殘月——像石濤的心、何芷舠的心,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安詳、顫栗甚至梗塞。
復調的月亮。復調的片石山房。
山房一側矮墻,開設一個方形空口如同一面鏡子,透漏出矮墻那邊的梅花、芍藥、桂花、牡丹、槐花等等依序開放而后凋敗的花朵——鏡中的花。依然是一種隱喻。
石濤與曹雪芹的祖父、江寧織造曹寅關系密切。清廷在南京、蘇州設置的多個織造府,負責向紫禁城輸送絲綢布匹,又暗自作為皇帝的情報機構,搜集江南一帶資訊和動態,防范統治風險。所以,曹寅與石濤的話題就可能比較復雜,不僅僅是琴棋書畫、蜜桃苦瓜。揚州,這樣一個在宋元、明清改朝換代之際屢屢蒙難的烈女般的城市,是曹寅、石濤的一個重要話題吧?談“春風十里揚州路”(杜牧),回避“烽火揚州路”(辛棄疾)?
曹雪芹或許追隨著曹寅來過揚州,在揚州詩局看祖父監督校刻、印制《全唐詩》,在片石山房看那一帶“寒山”和白日之月。《紅樓夢》中多處寫到疊石假山構成的園子,酷似片石山房。《紅樓夢》或許也可看成一部中國最早的復調小說,由人物、敘事者和隱含作者之間的矛盾構成的復調,由主旨的多元而構成的復調——像片石山房和以片石山房作為核心的何園。
清末民初,畫家黃賓虹作為何芷舠的親戚而屢屢居住于何園,以片石山房為師,揣摩石濤水墨筆意,但卻以自己收藏的石濤真跡換來張大千摹仿石濤的偽作。張大千癡迷于石濤,大量仿作已借石濤之名存世。但片石山房唯一,白晝的月亮唯一,不可摹仿、流通、私藏。
片石山房建于清初,何園擴建于晚清。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的紅色政治風暴中成為一座廢園。重修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游客如云。
三百多年來,園子的主人次第浮現而后消失。但畢竟留下一個園子,作為他人追憶、懷想一段舊光陰的路標。而我早年出生的那個清寒院落,今已成為田野。我現在所居的上海市內的一個小房子,某一天也會寫上“拆”字。
或許,鏡中花、水中月,才是這紅塵俗世的真實主人。你、我、他,皆為過客、游客。
忽想起杜甫所寫過的三個字:無家別。
3.在南京遇到梅花
無意中與南京梅花山的梅花相遇。
二月,陪母親、妻子在南京游蕩,計劃中的目的地有四:中山陵、明孝陵、總統府、夫子廟。但卻在明孝陵前的梅花山,推翻原定行程,消磨一個下午——這座燦爛、香氣襲人的山丘!火紅、粉紅、玉白、雪白、暗綠、鮮綠、金黃、蠟黃……如此大面積、多種類的梅花,平生初次相遇,在萎靡中年,在花期正盛的陰歷早春。
數年前,曾與妻子、兒子來南京,游明孝陵時最感興趣于陵前甬道兩側的一系列石雕:武士操劍、文人握筆、馬、麒麟、羊……漢代石雕的粗拙風格,與我的粗服亂發很協調。舊石頭,與我皺紋重重的老身體很協調。當時,沒有意識到甬道旁邊這一座名為“梅花山”的山丘的存在。因為,當時五月,梅花匿跡于樹根,等待雪和寒意。梅花與熾熱的生活沒有關系,像低溫、安靜的女子,不認識高燒、熱鬧的荷花、牡丹。一萬種花朵,隱喻一萬種人生和態度。
日本能樂藝人家族內部秘傳四百余年才公開出版的談藝錄《風姿花傳》,書名意思是“藝人的風姿,須像花朵那樣傳揚”。作者、能樂藝術大師世阿彌,在書中叮囑后輩,要了解十種藝術類型,“更要牢記年年來去之花”。
目前,二月,在南京,我終于認識并將牢記這年年來去之梅花。
與母親和妻子一起在山丘上下流連。周圍,游人表情一概癡迷,紛紛以手機、相機留影于梅花與梅花之間——攝影術是一種悲傷的藝術,任何攝影者都能意識到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喪失。母親對我吩咐:“給我再照一張,與這棵梅樹——誰知道還能不能再來看梅花了……”她已越過古稀之年。她名字中就有一個“梅”字。我外祖父、中原鄉村里的一個著名中醫王恩恵,應該也是喜歡梅花的人。后來,我父親接著喜歡梅花。但外祖父、父親都已經去世。母親常常夢見他們,像一棵梅樹,夢見樹下走遠了的人?
清代伊秉綬有名句:“梅花百樹鼻功德,茅屋三間心太平。”我的鼻子功德就很高,對女人脂粉香和這滿山的梅花香,敏感。但我體內有茅屋三間,來安放一顆漸漸蒼老的中年心臟嗎?梅花山頂,有亭翼然。坐下來,四望,可見山丘下的明孝陵及兩公里外的中山陵一派蒼綠、游人如云。孫文,朱元璋,一個推翻了帝制的人,一個熱愛帝制的人,分別睡在了兩處山脈之巔,似斷實連。游人們不知道這兩個人睡姿的區別,兩座陵的區別。但我知道,這兩個人都是內心不平靜之人、胸懷廣廈萬間的人。
我是小人物,中年之后漸漸放棄雄心壯志。幫母親、妻子背旅行包、提茶壺、照相,就很有幸福感。她們在梅樹下動情、動心、動身。妻名字中有“石”字,性格中就含了堅毅的部分,但遇到這些云霞般的花朵就柔軟得像山丘上的春泥。她和我母親的關系,在滿山梅花面前達到新高度:評價兩棵樹的差異,商量穿過山丘的路線,協調合影時的立場,指導我仰拍、俯拍時的角度……南京的梅花,參與到一個家庭的生活中來了。
妻子要為我和梅花拍照,我疑慮:“男人在花叢里拍照,有女性氣吧?”她說:“梅花不是別的花。你站那一棵干枝梅前吧——枝條硬的梅,像英俊男人!”以一棵英俊的梅樹為鏡子,我看到了自己的臃腫、塵俗、軟弱。
在中國,關于梅花,有許多名詩、名篇、名畫。或許與漢民族長期處于低溫的生活有關——堅持讓人性在低溫中保持光彩和暗香。顯然,在南京,這樣一個充滿失敗感、創傷感、遺址感的六朝古都,荷花、牡丹都不宜大規模生長。在南京遇到梅花、牢記梅花,合適,必須。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滿了南山。”這是詩人張棗的名句。梅花與后悔有關,這是他的發現。穿過梅花山,幾朵梅花落在頭上,我就成了一個后悔中的人?
在秦淮河附近的一家旅館的便簽上寫了以下句子:
梅花山的梅花開了:
粉紅、朱紅、淡黃、金黃、綠、淺綠、白……
一棵梅樹的花期是另一棵梅樹的花期,
像一個人的人性,是所有人的人性。
在滿山花香里聞到自身的狐臭氣——
我內心藏著一只、兩三只狐貍?
山坡上成群結隊的游人和悲傷,加強著春意和失意……
4.甪直,未厭
甪直,蘇州附近一個古鎮。歷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春秋時期。比周莊老1600歲,比同里老1500歲。所以,它也被稱為“古都”——吳王闔閭的離宮,曾在此。“臥薪嘗膽”“聞雞起舞”“十年生聚”“退避三舍”“紙上談兵”等成語,亦產生于此。全鎮由六條溪流、一條吳淞江構成一個“甪”字。甪,一種吉祥的獸——六條溪流構成了它的身體,吳淞江在獸角的位置上一掠而過——在下游成為蘇州河,成為上海的一部分。
甪直與同里、周莊的景色大致相似:隱喻財富的流水,鎖住財富的密集石橋,烏篷船,頭頂綠頭帕像肩上長出荷葉的搖船女人,搖船小調,精雕細琢、軼事繁多的古宅,收藏錢幣、紐扣、繡花鞋、硯臺、性用品等等舊物的小型博物館,石頭或青磚鋪就的魚鱗一樣的小街,春陰中的管弦柳絲,南腔北調的游客,用河流做枕頭的小旅館,為水聲、燈火和叫賣聲收稅的稅務官,旅游集散中心……人散后,一鉤新月,也是相似的。但小鎮一角的現代作家、教育家、出版人葉圣陶墓地鐫刻的“未厭”二字,使我內心一振:甪直有新意、有深意——
未厭。晚唐,陸龜蒙屢試不第,在湖州刺史、蘇州刺史身后的帷幕里當幕僚,興味不大。后,轉身來到甪直蓋房耕田,扔了四書五經,寫《耒耜經》。其中,記載了陸龜蒙在甪直將犁由直轅改為曲轅以節省人力、畜力這一唐代最重要的農具發明。我懷疑,甪直曲折的流水啟示了這一發明。“鄰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稔年”(陸龜蒙)。顯然,這是一個關心稼穡和天氣陰晴的農人,類似于有理工科色彩的現代知識分子,從心靈到四肢都在自我解放。他自名為“散人”:“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像是在談論散文寫作秘訣。這個散人、散文般的人,拒絕做公文般的人——長慶年間,朝廷以高士之名贊譽并征召入京,陸龜蒙堅辭。再征召,陸龜蒙干脆提前死掉了,埋在甪直。厭與未厭,長安與甪直。
未厭。晚清,甪直人王韜來到上海,成為墨海書館的一名編輯,修改、潤色西方科技書刊,把英語中的“物理”“天文”一類名詞翻譯為“格致”。格物致知,這是中國傳統知識體系所匱乏的理念和能力,導致了王韜耳邊鴉片戰爭的炮聲隆隆。王韜,在搖頭晃腦之乎者也的儒生一族中是異類,和徐光啟一樣成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國人。后因反清,逃亡香港,創辦了中國第一份華人報紙《循環日報》,由此成為“中國記者之父”,每天一篇文章,縱論強國之策,文風銳利痛快,“五四”以后白話雜文這一文體,即濫觴于此。晚年,鄉愁深深的王韜得李鴻章默許,回故鄉,甲午戰爭爆發前,病故,用骨頭感知鄉土冷暖和草根綠意。
未厭。民國,五四時代,葉圣陶來到甪直,在保圣寺內所辦的吳縣第五高等小學教書,開始了他實踐“教育救國”這一理想的生涯。講佛念經之地,回蕩童聲,這只能是民國、五四時代、甪直才能發生的事情。葉圣陶在保圣寺內編寫的《國文》教材篇目如下:《最后一課》(都德),《項鏈》(莫泊桑),《娜拉》(易卜生),《史記》(司馬遷),《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鑄一柄合用的斧頭而不是繡花針”,葉圣陶舉著自己編寫的教材、舉著這一柄合用的斧頭,帶領學生們在校園里辦起了農場、手工室、圖書館,編印民國時代第一本詩刊《詩》。他想造就一代新人,在現實中,在小說里。保圣寺的一盞油燈下,葉圣陶寫出了長篇小說《倪煥之》、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等等。多年之后,去世,葉圣陶長眠在保圣寺一角的四棵千年銀杏樹下,墓前有他墨跡“未厭”二字……
從陸龜蒙、王韜、葉圣陶,到今天的游人、我,對甪直、江南,未厭。憫農、憂國、啟蒙這一傳統,在甪直暗滋黙揚,使其區別于其他古鎮。《多收了三五斗》這篇小說中的“萬盛米行”,目前落實為甪直的一個景點,陳列著現今江南已經消失了各種農具:曲轅犁、水車、木锨、鐮、耬、斗、秤……但沒有米。我站在這里,像一個因米賤而傷心的戴舊氈帽的稻農,還是像一個從眼鏡上方投出鄙夷眼神的賬房先生?坐上米行前的一條游船,我穿過甪直,像一粒干凈的米,還是像一枚圓滑的、發臭的銅錢?
搖櫓的船娘在唱情歌:“打一個金人來換,也不換你那人。就是金人也是有限的金兒,你那人有無限的風流景。”結尾一句,出人意料地媚、好。明清交替之際的蘇州人馮夢龍,熱衷于收集江南一帶民歌(亦稱吳歌、江南小調、掛枝兒),編纂出《民歌時調集》,其中一首《金不換》與這位船娘的歌詞基本相似。馮夢龍應該來過甪直,認識這位船娘的祖先。這情歌,陸龜蒙、王韜、葉圣陶或許也在甪直的船上聽過,甚至參與了歌詞的加工創作。
所以,未厭。
5.沙溪,一座廢園
沙溪,上海以北六十公里、蘇州以東約三十公里處的一座水鄉小鎮。
我被“沙溪”二字的美感吸引而來,但沒有見到想象中的沙堤清溪。
穿鎮而過一條大河“七浦塘”,兩端聯系古運河、長江。貨船往來,載水泥、鋼材、糧食、船工、女人、狗、灶臺、炊煙、收音機里的昆曲……這條河與明代戚繼光乘船出海抗倭有關。河水渾濁。
與戚浦塘大致平行的一條小溪穿過古鎮區,明清房舍、廊橋、茶館、米店、煤球店、書店、診所、古石橋……溪水渾濁。若干游船破舊龜縮于水邊。江南一帶才子如袁枚、李漁、金圣嘆,應該都曾到此一游,那時,溪水應該清晰可見沙粒。
游客寥寥。我就在鎮上人的眼中顯得醒目。他們過自己的日子,我看他們怎么過日子。一堵舊墻貼著沙溪鎮衛生院打印的《婦女體檢通知》,有“臨檢前四十八小時內不要發生性關系,可喝水以使膀胱澎湃便于檢查”等字眼——他們過自己的日子,不考慮異鄉人的觀感。但“膀胱澎湃”四字,好,只有水鄉的人能夠這樣寫。
中午時分,一個回收并販賣古舊文物的小店才剛剛摘下門板。店老板從鄉下擺攤收貨回來:“今天早晨收了一個銀茶壺,乾隆的;收了一個碗,光緒的;十一個毛主席像章,文革的。”他貨架上擺著粉盒、煙壺、茶碗、硯臺、花瓶、耳環、佛像、硯臺……依稀指向舊時代里的江南生活。小店生意清淡。老板抱怨:“周圍的千燈、同里、周莊,以前都沒有沙溪好——這里是交通要道,通江達海呵。現在,沙溪沒有門票也沒有人來呵——你為什么來?”我笑笑。我不敢說因為沙溪名字好才來的,那太顯得矯情。
我嚼著新出爐的燒餅,在街上亂走,看到一座廢園:兩層住宅,一棵桂花樹濃香滿覆庭院,壓水井鐵質出水口上長出青苔像嘴巴上蕪雜的胡須,一地野草,一輛舊自行車在墻角萎靡不振,窗簾泛出舊色,紗門內正間里的沙發依稀可辨……我站在鐵柵欄制成的大門外窺視這一切。這個廢園的主人不拒絕一個過客的偷窺和猜測。他去了哪里?他有著像這座廢園一樣荒涼的命運?
我汽車上的GSP無意指示出沙溪鎮旁的一片稻田和小溪流:項脊涇!想到戚繼光的同代人歸有光的《項脊軒志》!開車直奔這一地址——歸有光就出生在這片稻田和小溪流的位置上。他家族建立在昆山的一個小庭院,被命名為“項脊軒”,紀念這片田野,遂有《項脊軒志》。我曾經在昆山游蕩,在傳說就是項脊軒所在位置上建起的一個飯館里吃了一碗面,以致敬意。
喜歡歸有光這一名篇結尾處的閑筆:“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也。”沉痛。沙溪鎮上的那座廢園內,桂花樹亦亭亭如蓋,有無名的哀涼和歡喜?不知。
萬物終將廢棄,例如,一個人的身體、一輛在暮色中奔回上海的老款帕薩塔車。
但沙溪、沙堤清溪,曾經在歸有光、我、這個廢園的主人等等身體內,反復涌現……
6.穿過杭嘉湖平原
杭州、嘉興、湖州三點之間的平原——杭嘉湖平原。
杭、嘉、湖三座城市像三塊鎮紙,使這一紙絢爛美景不至于被風吹亂——太湖是巨大的硯臺?誰的手點染出這一片中國最美最重要的平原。集鎮500余,面積6400多平方公里,由長江、錢塘江泥沙和湖水積聚而成。地勢低平,除零星孤丘,一般海拔僅3~7米,湖泊眾多,河流縱橫,水域面積約占十分之一。
此地光、熱、水資源能促使稻類作物一年三熟。糧、油、蠶、絲、魚、湖羊……使杭嘉湖平原馳名中外。明清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就暗藏在這片平原。那些被開發成旅游區的名門大宅,在杭嘉湖平原上比比皆是,證明著這一地區的富庶和神奇。它們有著大致相似的格局:一進、二進、三進、四進……幽深曲折——
一進,正堂,舉行家族婚喪、迎賓、節慶、祭祀等重大儀式之地,氣氛森嚴;二進,男主人喝茶、議事、閑談之地,雕花的扶手椅、茶幾、古瓷器;三進,女主人與女賓聚會、處理家務的地方,椅子尺寸已經縮小,且沒有了扶手,須垂手直坐,房間陳設簡單,表明男女地位的差異;四進、五進則是臥室、書房、庫房一類地方,玻璃柜里陳列著黑白照片、名人之間的信札;丫鬟、仆人的房間則在不顯眼的角落;四面高墻圍攏而成的天井,種植玉蘭、竹子,筆直向上,似乎想看見墻外的世界;地面,石子精心鋪設出各種圖案;后花園,在“才子佳人相見歡,私定終身后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完婚大團圓”的傳統戲劇中是重要空間;小池塘,養有蓮花、鯉魚……
這些宅邸的第一代主人有著大致相似的發家史,或從船工開始經營起航運業,或從商店學徒起步成為了資本家,或從蠶農遞變成了絲綢商、從鹽商變成了官僚……家族后代的命運、歸宿大致相似:或壯大如繁密的樹枝,或凋零,或移居各地、隨風四散,隨時代之風而四散。什么樣的庭院,就有什么樣的主人、結局。
現在,這些江南私宅最終成了公共景點,被游客羨慕、流連、猜想、感慨。宋、明、清以至民國的江南秘史,大部分章節書寫在這些宅邸內的陰影處、空白里,隨風,四散。從這些宅邸里穿過,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落難的公子、情人、別有用心的身份不明者、海外來賓、革命者、背著一麻袋糧食的長工……
一個傍晚,我走進杭嘉湖平原邊緣的朱家角鎮,去“課植園”看“情景昆曲”《牡丹亭》。課植園又叫“馬家花園”,一個熱愛讀書種地的清末鄉紳馬文卿的私家莊園。課植園正廳懸有對聯:“課經書學千悟萬,植稻麥耕九余三”。讀,學習一千就能悟出一萬種道理;耕,勞作九個月就可以休息三個月。一個懂得生活的智者。用十五年時間建成的中西風格合璧的課植園,面積一百公頃,劈有稻類實驗區、手工作坊、藏書樓,馬文卿在園內讀書、學英文、實驗稻種、修理家具、談情說愛……
現在,馬文卿已經消失。馬家后人去海外留學、經商、繁衍。此地被藝術家們青睞,讓穿古代戲裝的才子佳人在樓臺溪水邊,詠唱青春和愛情。我隔著一條溪水來聽、看、想,月亮就漸漸浮現樹梢了。演員們提著燈籠揮動溪水一樣的水袖,唱腔像水聲。我隔著一條溪水打量他們,像沒有臺詞和力量的仆人,惆悵。
移居上海已近二十年,比鄰杭嘉湖平原,我漸漸開始熱愛速度緩慢的南方劇種,如昆曲、滬劇、評彈、越劇,水袖飄逸,唱腔逶迤,充滿散意、古意。緩慢的唱腔,讓時間減速?熱愛緩慢,是一個人加速趨入晚年的標志吧。朱家角的夜晚漸漸深了,馬文卿體驗過的夜晚深了,半彎新月,明媚如同美人頭上的銀簪……
反復穿過杭嘉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地圖一片湖藍。高速公路穿過陰性的水鄉,如同公牛,必須被圍在公路兩側漫長水泥圍欄構成的牛圈里,約束荷爾蒙。高速公路之外,平原,小路隱約閃爍,像女孩喜歡拐彎,喜歡藏到樹林、草地里去被人呼喊、尋找……
我,一個正逐步進入晚年的人,在江南生活,像杭嘉湖平原這頁水墨上的一個墨點——
杭州、嘉興、湖州……
一輛載重卡車穿過王國維徐志摩穆旦金庸們的
墨汁凝成的黑夜一一擦肩而過的紛繁故居
這些名人們化為破空而去的鳴蟬
所褪下的紛繁空殼,盛滿江南平原的星光燈火
這繡滿了星光燈火的一卷絲綢!遼闊!
被小名為杭、嘉、湖的三姐妹刺繡、雙面刺繡——
在杭嘉湖平原的另一面,反向對稱映現另外一種景象?
比如,王國維徐志摩穆旦金庸豐子愷們的立場
關于塵世、愛情、文風的立場,將會發生微妙逆轉?
至于我乘坐的這輛卡車以及它急速掠過的浩蕩太湖,
則反面繡成四足怪鳥以及它急速飛過的浩蕩云團?
被蚯蚓、蛐蛐們觀察和吟唱
從它們的角度,打量卡車以及
我隱隱約約的面影、明滅不定的煙頭——
或許也可看作是一個南方幽靈,
騎著一點熒火虛妄地奔馳——
在奔馳中回想來路和前途?尋覓曾經居住的肉體和姓名?
我,一個南方幽靈?在杭嘉湖雙面刺繡出的夜色里
迷失于自身和吳越的真相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