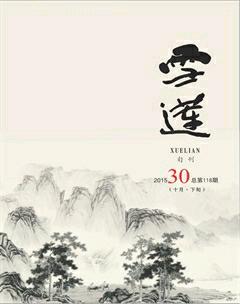情深理切 至情至性
王怡
[摘要]李密的《陳情表》根據晉朝“以孝治天下”的原則而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既照料了年邁有病的祖母,又保全了自己看重的名節,更贏得了觀望新朝的機會。從而使得晉武帝對他無從責罰,而只得“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養”。表文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陳情于事,寓理于情。
[關鍵詞]以情動人;悲苦身世;自表心跡;諄諄孝情
千百年來,人們常以“忠則《出師》,孝則《陳情》”相提并論,被譽為千古美文的《陳情表》,是李密因祖母年老多病,須由自己侍奉,暫不能應征做官,而向晉武帝陳述衷情的表。一邊是情深似海的祖母,一邊是恩重如山的圣上,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李密巧妙化解矛盾,變被動為主動,最終達到欲先盡孝而后盡忠的目的。文章寫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首先,情感轟炸,以情動人。李密很善于揣摩對方的心理,開篇便痛陳自己悲苦不幸的家世與祖孫二人相依為命、情深似海的處境,為后文提出“愿乞終養”的請求預作鋪墊。悲苦與不幸最容易引起別人的同情,所以本文開篇用“臣以險釁,夙遭閔兇”八個字以凄楚悲苦的筆調分別闡述了自己人生的“四大不幸”:第一,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第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第三,少多疾病,九歲不行;第四,門衰祚薄,晚有兒息。作者直陳其事,運用白描手法,“零丁孤苦”“煢煢獨立”“形影相吊”等寥寥數語把自己形單影只、孤獨寂寥的情狀極為形象地表現出來,營造了自己生存的“悲慘世界”。失去父愛母愛的孤兒本已令人同情,人生的種種不幸更是雪上加霜,惹人悲泣!早年的他有幸存活到現在,多虧了祖母劉氏的悉心照顧,可如今就連撫養自己長大成人的祖母已風燭殘年,常在床褥,“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這種相依為命的祖孫情感非同一般,正如他所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余年”。在這層層悲情的渲染之下,晉武帝又怎能不被感染,不被打動?
其次,自表心跡,排除疑慮。悲愴凄楚的家庭身世或許能激起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可也會很快從搞政治的陰險多疑的晉武帝心中迅速溜走。因為李密曾入仕“偽朝”的特殊身份又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也是晉武帝內心最大的憂慮!李密多次“辭不赴命”,最擔心的就是會被晉武帝認為自己有懷念舊朝、矜憐名節、不事二主之心,所以他“實話實說、不避嫌疑、直陳宦歷”,加之他又在表章中一再恭頌“圣朝”:“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舉國上下,不計前仇,舉賢任能,政治清明,皇恩浩蕩。自己一個“亡國賤俘”,至微至陋,榮恩加身,惶恐不已,感激涕零,怎會不滿?怎敢不滿?他一面對新朝稱頌不已,反復表達對晉武帝的感恩戴德之情,滿足晉武帝的權威欲與虛榮心,另一面又對偽朝表示遺棄,表明自己“本圖宦達,不矜名節”的做官志向,這正是最初掌握政權的晉武帝愿意看到的態度和聽到的聲音,讓晉武帝確信自己已經完成“政治立場”的徹底轉變,也是向晉武帝做出了最有力的表態,打消晉武帝的疑慮。
最后,以孝為名,名正言順。李密抓住晉武帝“以孝治國”的政治綱領,寓事于理,寓情于法。李密在文中反復強調祖母的病:第一段的“夙嬰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劉病日篤”,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真是“祖母無臣,無以終余年”,如今的自己如果一旦離開,就是不仁不孝,所以自己這種不離祖母盡孝的做法,既是在盡孝也是實踐當時晉武帝提出的?“以孝治國”綱領,恰好為自己孝敬祖母找到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將自己納入晉武帝的治國體系中,符合晉國的國策,順應當時的潮流。同時也為晉武帝毫不費力地找到一個“以孝治國”的典范,雖是個人私事,實則一定也令晉武帝歡欣不已。然而精明的李密還不放心,在提出先盡孝后盡忠的方法后,才恰到好處地提出“烏鳥私情,愿乞終養”的請求,使晉武帝不得不恩準。
李密在表章中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斗膽向皇帝陳情,陳“情”是這篇奏章的核心所在,而作者要表達的感情又是很復雜的。我認為既有照顧自己年事已高,把自己一手拉扯長大的祖母的諄諄孝情,也有對蜀漢王朝的懷舊忠情,還有對新王朝步步緊逼,殷切征召的惶恐與畏懼之情。這些復雜的情感交織在一起,使李密進退維谷,無所適從。這正是《陳情表》表達感情的多重性。當然,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李密緊緊抓住了中國人最強調的感恩:“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知恩不報非君子”大做文章,以孝報親恩,所以“以情動人”既真實又感人,情真意切,水到渠成。同時也保全了古代儒生講究的“忠臣不仕二主”的名節,這對于他而言或許是災禍,但是李密卻巧妙地化險為夷,一次次“矮化自我,抬高他人”,一次次忠實的表態,一次次對晉武帝的感恩戴德,為自己取得對篡奪了正統地位的晉王朝的觀望機會,不必在蜀國剛剛滅亡不久就為新王朝效忠,還沒有將自己在新朝為官的仕途之路封死。真可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終,李密成功地將事、情、理巧妙融合,使晉武帝看了這篇表文,深受感動,不僅同意了李密的請求,還“賜其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還感嘆說:“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可見這篇奏表寫得多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