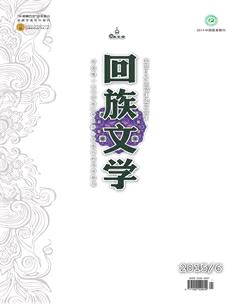孤獨的凝視
蘇濤(回族)
雖然之前已經聽說蘇本理哈吉身體不行了,但在得知哈吉歸真的消息后,還是無法接受老人離開頓亞的事實。在北京上學的時候,我就隱隱感到韋州老一輩文化人的珍貴。因而在心中暗暗舉意,要對這些老人做口述采訪的工作,將老人們的人生記憶留傳后代,當時腦海中第一個想要見到的老人便是蘇本理哈吉。遺憾和愧疚的是,我家與哈吉家雖是多年的鄰居,我卻對哈吉的文化功績所知甚少。于是那個假期便叫了同伴拜勇坐客車去哈吉女兒的家。由于是第一次做口述采訪的工作,我和拜勇事先都沒有做基本的功課準備,兩人扛著相機就突兀地出現在了哈吉的家里。整個采訪過程磕磕絆絆,遺漏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此別三年,我雖從學校畢業并走上工作崗位,卻在聒噪的城市里拖延著、迷失著,在渾然不覺中失去了最后見到哈吉的機會。未曾想到,在三年不負責任的耽擱后,聽到的竟是哈吉歸真的消息!這個為韋州的民族教育、民族文化奔走呼號了一生的老人,終于安靜地躺在了韋州西墳寺的墳院里。
失去了蘇本理哈吉的韋州,好像沒有缺少什么,其實并非如此。他帶走的東西,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可是一旦失去,韋州就失去了分量。韋州鎮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同心縣東部,可韋州人很少說“韋州鎮”,韋州人習慣說“韋州城”,這一方面源于韋州被四面矗立的城墻包圍的地理存在。據說古時韋州古城四周建有護城河,看上去韋州城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船只一樣,因而有“韋州古城像只船”的說法;另外,“韋州城”三個字更能說明韋州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
早在北宋年間,韋州就是李元昊西夏國的政治軍事重鎮。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庶十六子朱旃被封為慶王,第三年就藩韋州。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慶王開始在韋州修建王府、避暑勝地等,韋州達到了空前的鼎盛。在整個清代,韋州稱韋州堡,其重要性一直延續到民國。實際上,對于韋州人而言,真正讓他們為之驕傲的是韋州的教門,特別是韋州的經堂教育歷史。和很多回族聚居地一樣,韋州也享有“小麥加”的美譽,坊間更有“寧夏的教門看韋州”的說法。伊斯蘭教在元滅西夏后就傳入韋州,但讓韋州成為中國伊斯蘭教重鎮的標志性事件,則是海太師(海東陽)于明萬歷十七年(1589年)秋遷到韋州并在韋州設帳講學。作為中國經堂教育創始者胡登洲的嫡傳弟子,海太師落戶韋州使得韋州成為中國經堂教育歷史脈絡中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將歷史拉近,甘肅河州馬萬福阿訇于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由麥加回國,拉開了伊赫瓦尼尊經革俗的歷史序幕。當相對先進的觀念在彼時的回族聚居區遇到巨大阻力之時,韋州是最早接受伊赫瓦尼思想的地區之一。據現有資料,大概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馬登海阿訇便已經開始在韋州傳播伊赫瓦尼了。正是這樣顯赫的傳統,讓韋州城的信仰表現出了和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氣質。這種氣質流淌在祖祖輩輩韋州人的血脈中,使得韋州雖然身居一隅,看似微不足道,但卻巍然屹立,處世不凡。而正是這樣的歷史文化傳統孕育了蘇本理哈吉,同時哈吉也將他的一生緊緊與韋州聯系在了一起。
蘇本理哈吉于1928年生于韋州一個家學豐厚的家庭,其父蘇盛華是韋州城第一個大學生,且考取的是北京大學。2013年寧夏高考理科狀元韋州小伙兒王偉,當時被各路媒體爭相報道。大家關注的焦點不是王偉本人,而是吃驚于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回族小鎮怎么能和狀元聯系在一起。但倘若他們了解韋州的歷史,便會發現狀元的出現絕非偶然。在一個世紀以前,韋州人便已經求學于北大!蘇盛華的才華展露于北大的一次演講,當時被馬鴻逵發現。畢業后,馬鴻逵便將他接回寧夏,其后便開始了其豐富的人生履歷。新中國成立前,蘇盛華先生曾任鎮戎縣教育局長、靈武縣吳南鄉清真完小校長、韋州中阿女子師范學校校長、內蒙古磴口縣縣長、中寧縣縣長等職。晚年曾任吳忠市政協委員、同心縣政協委員、自治區伊協委員等。在現存關于蘇盛華先生的史料中,他的諸多頭銜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著名回族教育家”。如1934年成立的寧夏省私立中阿學校,日常校務工作原本由馬鴻逵的參謀長馬光田負責,馬光田離開后就由總務主任蘇盛華擔任。當時學校的阿文課程主要由副校長虎嵩山阿訇負責,而漢文課程則由蘇盛華講授。可以說,蘇盛華是民國時期寧夏地區中阿學校最重要的倡導者和推行者。到1940年左右,寧夏地區的中阿教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遍布寧夏各地的中阿學校共達到二十四所。
蘇盛華在北大求學期間就對中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學習之余他閱讀了大量的中醫書籍。北大時期的醫學儲備使晚年的蘇盛華先生長期在吳忠及同心地區行醫。蘇本理哈吉治病救人、辦教育、興教門的人生軌跡無疑來源于早期豐富的家學啟蒙,家父蘇盛華先生強烈的民族情懷和文化復興的意識深深地植入到了他的心中。
蘇本理哈吉最主要的社會身份是醫生,這自然得力于他父親的影響,但同時離不開他本人對醫學深入的學習和鉆研。哈吉在針灸、肝病以及皮膚病等醫學領域有著極高的水準,同時哈吉的很多中醫偏方治療了不少患者的疑難雜癥。不但韋州人找哈吉看病,很多外地人也慕名前來韋州問診把脈。哈吉晚年雖然住在位于同心的女兒家,但依然有很多外地人到韋州打聽哈吉在同心的住處。在2012年的那次采訪中,我注意到哈吉的書桌上除了與醫學有關的書籍外,還有《儒林外史》《聊齋志異》《三國演義》這些古典文學名著以及魯迅、蕭紅、郁達夫等現代作家的小說集。與哈吉的交談中我得知,哈吉早年求學于國立隴東師范學校和蘭州大學的時候,在業余時間還進行小說和詩歌的創作,可惜后來所有手稿都在文革時期被丟棄了。正是這樣的情懷和視野,讓哈吉在救死扶傷、替人消除肉體痛苦的同時,和他父親蘇盛華一樣走上了一條長途漫漫的信仰之途。
文革結束后,民族教育正是百廢待興之時,教門復興可謂迫在眉睫。但清真寺里對滿拉的培養卻依然固守于傳統的經堂教育模式:不但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沒有固定畢業期限,同時在課程設置上,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文法和宗教經典教義為主,其他自然社會科學則很少涉及。這種與外界隔膜的傳統教育方式在新時代下日益顯示出其不足之處,新式教育的歷史使命呼之欲出;與此同時,中國社會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于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使得社會上涌動著一股下海經商的熱潮。對物質利益的格外看重和對精神追求的日益漠視,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嗅覺靈敏的韋州人自然也感受到了時代的躁動,一些年輕人呼吸到了空氣中的金錢味道,便紛紛南下廣州和云南,部分人誤入歧途走上了販賣毒品的道路。正是鑒于清真寺內傳統教育模式的弊端和挽救韋州青年免入歧途的舉意,蘇本理哈吉于1993年在韋州老墳寺創辦了寧夏第一個由民間發起建立的中阿阿校。可以說,韋州中阿阿校是寧夏地區民間阿拉伯語新式教育的開端,見證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寧夏民間創建阿拉伯語學校的時代風潮。蘇本理哈吉對韋州中阿阿校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學校創辦伊始,由于韋州人對于這種新型教育模式并不認同,因而學校的生源極少。哈吉便親自到學生家中動員,當時阿校清真寺的開學阿訇正是后來名滿西北的馬陸阿訇。依托于韋州中阿阿校,哈吉開創性地運用了新式的教學模式,并破天荒地使用了當時極少人聽說過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阿拉伯語教材。在師資方面,哈吉專門從外地請專業教師到阿校授課,并邀請了很多具有新觀念的韋州年輕教員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不僅如此,哈吉還親自授課,講授與中醫有關的知識。很難想象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中國,一所小鎮的民間阿校竟有如此豐富的課程設置。在我看來,那是屬于韋州民族教育的黃金時代,而這一切的締造者正是蘇本理哈吉。他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了其父蘇盛華在民國時期的教育理念:即強大和振興一個民族必須從教育開始!事實上,哈吉的教育改革更大意義上而言是完成了與海太師的歷史對接,韋州傳統的經堂教育模式在蘇本理哈吉的中阿阿校以更具現代意識的新形態復興了!隨著韋州中阿阿校的逐步發展,學校的知名度也日益提高,更多的家庭愿意將孩子送到學校來。伴隨著學校生源的日益增多,學生的就業途徑也變得寬廣。有留校當老師的,有去外地繼續求學的,有出國深造的,還有去義烏、廣州等地當翻譯的,這些韋州青年從韋州阿校畢業后都踏上了一條積極健康的人生之路。
這其中讓人頗感意外甚至連蘇本理哈吉本人也沒有想到的是,1993年他創辦的韋州阿校竟造就了中國民間阿拉伯語翻譯的一個奇跡。1998年左右,畢業于韋州阿校的年輕學子在廣州和浙江義烏等地接觸到了阿拉伯商人。他們便用在學校習得的語言知識與阿拉伯商人建立起了聯系,這些最初的個體翻譯行為在日后逐漸成長為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商貿往來的重要力量。 隨著翻譯行業的日益興盛,竟直接帶動了中國民間阿拉伯語學校的歷史轉型:即由培養傳統的阿訇滿拉到培養新型翻譯人才的轉身。毫不夸張地說,由蘇本理哈吉創辦的韋州中阿阿校引領了中國民間的阿拉伯語翻譯事業,并將之推向全國。誰也不敢想象,1993年那一個個扛著母親縫制的被褥進入阿校學習的毛頭小子,日后竟在義烏、廣州等地建立起了連接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商業共同體。而這條繩索的源頭就在韋州城,在蘇本理哈吉建立的韋州中阿阿校!如果說韋州阿校的創辦是蘇本理哈吉留給世人的一個硬件工程的話,那么在歷經三年,幾易其稿完成的《韋州回族》則是哈吉留給韋州,乃至回族穆斯林的一件精神寶藏。
真知是無言的,而求知者也從來是孤獨的沉默者。關鍵在于,是否有高貴的舉意,是否具備一種正義的立場、一種有溫度的情感。在主流文化領域的研究方法中,口述歷史可以說是近些年才逐漸興起的。1997年,一位韋州老人在操勞于阿校工作的同時,以將近七十歲的高齡開始了對韋州歷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和時下所謂學科組或調研組不同的是,哈吉是孤身一人騎著自行車在韋州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戶地進行走訪搜集和挖掘整理的工作。回族沒有把歷史付之于筆端的書寫傳統,有的只是口耳相傳的歷史沿襲。現有的實物也在文革期間被大面積損壞,這些都使得哈吉的口述歷史工作有著常人無法想象的艱難。在歷經了三年夜以繼日的辛勞后,十萬余字的《韋州回族》終于誕生。全書共分八章,分別從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經濟、習俗等角度對韋州歷史文化做了詳細的介紹。這不但填補了韋州回族沒有書寫自我的歷史空白,更為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和寶貴的史料。可以說,《韋州回族》是了解韋州歷史的必讀書目,更是了解回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百科全書。
如果說創辦中阿阿校由蘇本理哈吉開創,而后參與者眾多,一時蔚然成風;那么書寫《韋州回族》,則是他一個人的孤獨行走。更讓人嘆服的是,哈吉在完成《韋州回族》后并沒有停下他文化搶救的腳步。在印制了一百本《韋州回族》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后,哈吉又歷經四載完成了《韋州回族》的第二版。相較于第一版,第二版的《韋州回族》增加了近一半的內容。令人遺憾的是,其手稿在幾經輾轉,托人出版的過程中丟失了。如果說,我們把寧夏地區最大、最古老的韋州清真大寺拆毀,尚可歸咎于文革年代,那么在歷史車輪已然駛進了教門光明的今日,把《韋州回族》第二版手稿“弄丟”的人,可能不曾知道,他丟失的不僅僅是一部手稿,而是一本受得起任何溢美之詞、凝結了哈吉畢生心血的民族地方志。哈吉在《韋州回族》的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盛世修志是我國的一項優良傳統,值此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大好時機,我們這一代人如不及時搶救整理出這些將會被永遠湮沒的歷史資料,不僅有愧前代,且有罪于后人。”今天讀到這段文字,敬佩和愧疚感滿心而生。手捧哈吉字字書寫的《韋州回族》,再追想起孤獨穿行于韋州古城之下敲響一戶戶家門的那個老人,不禁眼眶濕潤。文化不會沉默,蘇本理哈吉這樣一位來自民間的求知者,以腳踏實地的真實平衡著時下不義的學術研究。
我們這個民族,自明代以降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這樣的歷史塑造了我們,也限制了我們;而地處西北深處的地理空間放逐了我們,卻又制約著我們。于是大家偏安一隅,度過余生。但是,這樣的個人修行對于這個民族更高遠的發展意義何在呢?從這個角度而言,蘇本理哈吉的文化整理和搶救工作就顯得非常重要。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滿懷著一腔熱血,要為民族、為信仰奉獻一生、戰斗一生,卻在庸常的俗世中碌碌無為。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陷入了真正的惶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到晚年看著鏡子中滿頭白發的自己,黯然神傷。蘇本理哈吉用他那種對待本民族的熱情和情懷,以及為民族的文化事業竭盡心力的行動提醒我們,人的一生中最大的事業乃是虔誠的舉意以及為之奮斗的過程。毫無疑問,蘇本理哈吉做到了。
韋州現在似乎不缺少話題,也不缺少有錢人和大阿訇,缺少的是讓外界眼睛一亮的文化尊嚴。而正是蘇本理哈吉創建韋州中阿學校和書寫《韋州回族》的行動本身,使像韋州這些已經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回族聚居區,在當代有了可以言說的資本和資格。
在2013年采訪哈吉的過程中,一個細節特別讓我注意。采訪時,哈吉總是不時中斷自己的談話,眼睛盯著空氣中不知名的所在,沉思著、凝視著。我分明看到了哈吉眼神中的孤獨和蒼涼,那是獨屬于他的氣質。他經歷了韋州教門的黃金時代,他以一人之力力挽狂瀾保住了中阿學校,他孤身一人歷經七載完成了無法估量的《韋州回族》;但同時,他也經歷了家庭變故,看到了今日教門中的虛偽和浮華。這如何能讓他不孤獨,在衰弱之中,在生命行將終結之時,他保持著傾聽,保持著思考,更體驗著那灼人的孤獨。真主在齋月里全美了哈吉,浙江義烏清真大寺更是破天荒地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為埋葬于千里之外韋州西墳寺的蘇本理哈吉站了異地者那則,這幾乎象征了穆斯林無常后的最高榮譽。但我更希望,韋州人不要忘記了那荒蕪落寞的墳場里埋葬著的這位老人。每一個回族聚居區都有像蘇本理哈吉這樣的老人在消逝著,他們中的每一位所帶走的都是這個民族無形的精神財富。而我們對這些老人往往熟視無睹,忽視了他們給這個民族帶來的尊嚴。這正是蘇本理哈吉孤獨的癥結所在,也是我們真正的悲哀所在。我們應該保護和敬重這樣的老人,因為保護他們就是保護我們自己,敬重他們就是敬重我們這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