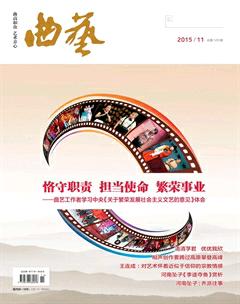王連成:對藝術懷著近似于信仰的宗教情感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帶有鼻音的參與,說起來的音色就不會這么美妙,更無法流傳。鼻腔有時候有弱音器的功能,它讓聲音有懸起來的美感,砸在你的耳膜上不疼。鼻音音節讓干澀、冰冷變得溫潤、濕潤,讓稀薄變得濃郁,讓噪音變成樂音。鼻音音節是離生命最近的音節,它時刻吮吸著生命的氣息。構音器官有鼻的參與,讓你仿佛嗅到山川、江河、大自然的清新,鳥語伴著花香的音色美。”
拋開上下文,難以想象以上這段情感豐沛的文字來自一篇專業性極強的學術論文。干澀、冰冷與溫潤、濕潤;稀薄與濃郁,這些與感官緊密相連的詞匯能輕易喚醒讀者曾經有過或者似曾相識的生動體驗。這種將極端抽象幻化為親切熟悉的本領來源于一位年屆六旬的山東快書藝術研究員和表演藝術家,王連成。與俱可稱為資深的年紀與閱歷形成鮮明對比:不論在聽者眾多的講學課堂上,還是在無甚特別的日常里,他不時流露出的率真態度昭示著童心未泯。文藝志愿服務項目曲藝培訓班的授課中,甚至有不少青年學員有感于他的活潑熱情,而調侃他是“老頑童”。而他本人似乎也自然而然地認可了這個稱呼,甚至比旁人尊稱他為研究員、藝術家更加受用。在他的世界里,研究員被解讀為“搞研究的人員”,而藝術家則是“搞藝術的家伙”,本就沒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資本。
也許藝術于他本就不是什么獲取功利的敲門磚,他才能如此坦然而誠摯地說上一句,“我對藝術懷著近似于信仰的宗教情感”。他說這話時,語氣平淡,好像在敘述再正常不過的客觀事實,卻足以令聞者感受到他對曲藝藝術的摯愛。他反對認為國人沒有信仰的論斷,在他看來,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具體的神化了的偶像,而是概念崇拜。雖然具體認識千差萬別,但無一不指向對真、善、美的追求。對藝術懷有摯愛的人,他們的信仰就是即使默默無聞也值得為之奮斗一生的藝術。
記者:用把事物系統化梳理的思維來做曲藝研究,其意義和價值是什么?
王連成:以往的曲藝研究范疇多是歷史的和經驗類的,現在曲藝要成為一個學科,進行基礎理論的研究是必要的。基礎理論是什么樣呢?用一句話來概括,將來我們要告訴學生什么是曲藝。但什么是曲藝只給出一個定義不行,需要提供立體的、有維度的感受。我們為什么要立體地、有維度地研究曲藝?我覺得是為了對更多的年輕人進行傳承。曲藝成為學科,學科必須科學。科學是什么?科學都是應用邏輯。試問,假如了解了定義,就能等同于了解曲藝嗎?我覺得恐怕不行,我們研究者既要從整體上觀察曲藝,又要像一根鋼針一樣,扎到曲藝的內部,找到它的核心部分,逐層剖析,尋找規律。很多目前普遍接受的知識體系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漢語拼音方案》和現行的高校現代漢語語音訓練系統,都是以語音學的現象精細描述為依據,把音節分成多個音素,進行拼讀。對比之下,而我們的曲藝大師向來沒有任何一位是把音節分開來念的,曲藝有一套整體認讀的方法,字是整個讀出來的。那么建立曲藝的整體認讀體系之后,語音學還有什么用?我想它們可以作為“修理工具”,我們先用整體認讀的方法讀出音節,用“修理工具”的知識進行更細致地分析,從而使知識更加準確。語言學家王力曾經有過這樣的論述:普通語音學是適應全人類的,是把語音當做物理現象和生理現象來研究的。可僅有物理描述是遠遠不夠的,每一個漢字都是有生命的。一出聲音就有動作,聲、情、形、韻、律相生相依,每一個曲種都因此而有一個具體的形狀,其共同構成的大曲藝家族也有了更加宏觀的形狀。搭起這個大形狀,以便于曲藝人在不同的空間位點上進行研究,手、眼、身、法、步是形狀,跳進跳出也是形狀,僅僅有形不行,還要有情。曲藝的核心是說,說不夠過癮,打著拍子說就出現了快板這樣的曲種;仍然不過癮,還想要再美,半說半唱,于是出現了像單弦這樣的曲種;藝術在視聽上還想要再突破一層,就需要體現方言的音樂性了,于是起初并不記譜的藝人們開始記譜……曲藝依照聲、情、形、韻、律的系統軌跡繁衍發展,蔚為大觀。
曲藝是說的藝術,而唱是曲藝最美麗的衣裳。曲藝是“說”和“唱著說”的藝術,這么說,比起講曲藝是語言藝術似乎更加準確。“說”具有對象感,是具有主動性的藝術,是“我要告訴你,你知道了嗎?不知道不行,我還要繼續想辦法告訴你,說到你的心里去”……形象地說,曲藝是“頂”著觀眾說、唱。
視聽是曲藝藝術的載體,因此站在曲藝的內部研究它的聲、形、情、韻、律很重要。
打個比方,找邊界的研究方法好像告訴別人饅頭是什么面做的,而我們現在研究的方法是告訴別人怎么做饅頭。
記者:不少曲種依聲腔形成特色,方言的音樂性在創作中如何體現?比如山東話與普通話聲調不同,那么創作山東快書時如何充分認識山東話的特色從而為創作服務,創作出從內容到音律都很好的作品?
王連成:我不會說陜北話,但是聽了幾段陜北說書作品之后,我感到創作的規律是共通的。我假如寫一段陜北說書,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印象來寫,因為我只了解山東話,并不了解陜北方言。但是作品到了陜北說書藝人手里,他們要按照當地方言特點進行二次創作。我們現在創作一段曲藝作品,了解曲藝大的創作規律就有可能實現,即把握曲藝創作最基本的要領——結構的意識(結構學)、包袱的組織等這些共性的東西。《黃帝內經》有句話說得好:智者求同,愚者求異。我們進行分類一定不是“劃邊界”,而是找系統中共性的東西。研究曲藝這個系統必須了解曲藝內部的基本原理。系統論基本原理的第一條“整體觀察”,沒有這個理念就別談系統;第二條“找出關聯”,各個部分間的有機關聯;第三條“層次清晰”。這幾點是重中之重,一定要把它找到。尤其是找到有機關聯,這對于內部求同是很重要的。另外,曲藝系統滿足“整體性”“動態性”“有機關聯性”“秩序性”這四條基本規律,是個動態系統。
如果講體系呢,網絡是個體系,由多臺接入的電腦組成,共同作用才能產生效果。所有事物具有萬物同源性,人、天體、系統,是一樣的道理。曲藝不是物質的,是意識上的系統,千萬不要忽視了意識上的系統和物質上的系統是相通的。大致相通,什么相通?只要是規律就是相通的。一些專家也帶著善意質疑:說你是個研究山東快書的,你研究山東快書怎么就能夠講了解了整個曲藝的體系呢?這就是一點含全。“一粒沙子窺世界,一朵野花觀天穹,一只手掌托無限,一個時辰含永恒。”在中醫的理念中,人的耳朵像一個倒過來的嬰兒,耳朵上的穴位與人體各個部分的機能一一對應。為什么拿來山東快書這個曲種能夠研究整個曲藝體系呢?山東快書是打著板半說半唱,“唱”它能夠得著,“說”它也能夠得著,居于中間,便于觀察兩端,所以用這一曲種來研究曲藝體系我認為是適合的。此外,山東話貼近普通話,所有音節跟我們所說的普通話幾乎一致,只是聲調錯位,這對于“聲、形、情、韻、律”的曲藝體系研究,無疑是一大優勢,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系統論的觀點認為:“一旦了解了組成整體的小單元性質,就算掌握了整體。”(霍紹周·《系統論》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記者:基于地方方言和文化產生發展的曲種想要“走出去”,需要進行哪些努力?
王連成:曲種被認可的意義,有時候不只是曲藝本身的意義。我們聽過陜北說書認為它很有陜北的文化底蘊,認可了它,但是假如因此我們在北京開個陜北說書的場子現實么,效果又會怎么樣呢?因此我認為地方曲種“走出去”的意義不在于此,而是讓更多人通過陜北說書了解到我們的民族情感、民族性格。曲藝“走出去”的更大意義在于此。“出去”的目的不是在外國建立書場,那不是常態的東西,“走出去”是讓外界認識這塊土地,認識我們的藝術,而回去以后我們還要更好地服務于百姓。在服務當地的同時,各個曲種之間加強聯系,加強在動態中的有機關聯,互相學習借鑒,又衍生出更多新的曲種,讓曲藝得到發展。高元鈞為什么是大師?他當年不僅僅局限在自己的地域上,甚至曾經前往十里洋場上海演出,眼界很寬闊。他是河南人,而他唱山東快書用山東話,個別的字往普通話靠一些,讓觀眾聽得懂并且順耳好聽。在推廣普通話的背景下,我覺得地方曲藝表演可以使用帶著自己方言味道的普通話,“多元”讓大家聽起來有意思,反而比都用標準的普通話表演更有意思。
記者:藝術審美主體間的互動關系很重要,曲藝表演不能僅僅是“對你說”,而是一種相互吸引、相互刺激的交互作用。那么從受眾審美接受的層面考量,我們在創作上應當注意些什么?
王連成:創作的時候僅僅是為了表演很不夠,要有為了受眾寫曲本的意識。想要形成良性發展,生產者、表演者、受眾、環境幾要素缺一不可。抓創作,抓表演很重要,但培養受眾,為了受眾而寫同樣重要。老百姓心靈深處最柔軟的部分,最歡樂的部分,你要觸摸到,找到它,運用我們曲藝創作的技巧表現出來。此外還要考慮環境,只在小劇場當中演是不夠的,同樣一個節目在縣城演出和拿到春節晚會的舞臺是截然不同的,環境換了,創作的要求自然也要適應性地作出調整。
記者:結合自身談談創作和表演兩方面體驗集于一身對一個曲藝人的重要性。目前這兩者在很多時候是割裂的,寫是寫,演是演。如何能將二者很好結合,使之相互促進?
王連成:我們提倡用“三條腿”走路。現在我們倡導的學科建設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我想應該是能演、能寫,能研究的人。過去我們的曲藝家哪個不是學問家呢?16世紀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把人的知識分為三類:一類是感性知識,一類是理性知識,還有一類是直覺知識。我們曲藝大師的知識大多是來源于直覺知識,千萬不要說他們沒有文化,因為他們掌握的大多是直覺知識。而我們理論工作者應當把直覺的知識進行理性的描述,落實到文字,寫成文章時候又要運用感性的語言,這樣文章才好看,有藝術含量。有些觀點不接受我們感性的描述,認為這些是廢話,主張用些生澀的語言說話。但正是這些所謂“廢話”才體現了語言的立體維度,我認為不會寫廢話論文最可能成為廢紙。這是常有事。看行文生澀的論文生不如死,從傳播的意義上來講,這樣的論文就已經失敗了。是塊黃金沉到泥里不為人所知沒意義,要想辦法使它漂起來,讓世人看到它的金光閃閃。曲藝家感性的知識是一種思維方式,不是說感到就感到的。比方說我描述語音系統中的鼻音時,就能想到鼻韻母的美妙和多情,進而聯想到女孩的撒嬌。這些東西你在音韻學里面找不到,在目前的大學教學中也找不到,這是我們一輩子搞藝術的那個家伙(藝術家)經過長時間實踐以后體會出來的東西。什么叫藝術家?就是搞藝術的那個家伙;什么叫研究員?就是快書研究會里的那個成員,它不僅僅是職稱。能證明藝術家價值的只有一點,靠他的作品和成果。我們看成果這個詞,很形象,就是研究成了的東西像一個果實。我們思考一個問題,更形象的詞是思路。這就是中國語言的形象色彩。喇叭褲和喇叭沒關系,形似喇叭;獼猴桃和獼猴沒關系,是長得像獼猴的水果。大鍋飯和大鍋沒關系,雞冠花和雞冠沒關系,只是像它,好似它。甲骨文中大象的“象”,老虎的“虎”字,并不是絕對的象形,而是像神,神似。但是我們再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鳥就是鳥,鴿子就是鴿子,是很形象的圖畫。中國的曲藝、戲曲、繪畫等藝術門類崇尚一個主義——寫意主義。把意思寫通了,點到為止,讓觀者產生聯想,使之有一個立體的維度概念和形象的把握。概括起來這樣的體驗是:直覺知識,理性描述,感性成文,如此強強聯合的傳承才是最有力的。
研究曲藝要弄明白系統論,要了解語言學美學(視聽效果),要知道簡單邏輯學,還要明白哲學的一些道理。什么是哲學?哲學說透了就是內部的規律。另外還要了解我們中國人最傳統、最基礎的情感。現在對于曲藝更重要的一點,是要了解我們的國家和國情。誰說中國人沒有信仰?我不贊成,其實我們的信仰是一種概念崇拜,是大的概念,而不是具體偶像。中國人的思想是自由的,我們崇拜真善美。不了解國家,不了解人民,創作上就如同無源之水。創作以大善為底色作支撐,出來的作品必定是暖暖的。即使諷刺也是溫暖的、善意諷刺,而不是惡意的。諷刺是為了讓諷刺對象聽到,感到疼痛,反省自己,然后改過,向好的方向發展。如果一個作家的內心不善良,他就會缺乏發現真善美的眼光和心智,會無視掉很多有價值東西。
記者:您現在所做研究是一種共性提取式的工作,曲藝是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傳承的。甲傳給乙的過程中很強調傳授雙方的個性。那么您認為曲藝傳統的強調個性的傳承方式和您現在正在努力建構的強調共性規律的傳承方式,兩者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
王連成: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矛盾。如果你把共性的、基礎性的東西做好了,在這個基礎上會出現更多的個性,出現更多的態度。每一個曲種和演員都是個性的,我想問一下什么叫個性?個性就是一個人自己的態度。沒有自己的獨特態度就沒有個性。共性的研究恰恰是為了培養各種各樣的態度打基礎。學習完基礎課程,具備形成態度的能力了,再跟著老師學習但是不像老師了,你就是你自己了。齊白石說過,學我者生,像我者亡。
基礎理論研究最后的結果和最終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培養一個學生具備樹立自己獨特態度能力:確立對待藝術的態度,對待社會的態度,對待生活的態度,對待人的態度,對待事的態度。說書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傳情達意,表達我們的態度,這個態度的核心是棄惡揚善。曲藝演員應該有“找鏡子”的能力。創作上,善良是一面鏡子,邪惡是一面鏡子,貪腐是鏡子,優秀是鏡子,先進是鏡子,落后是鏡子,請客送禮是鏡子,兩袖清風是鏡子……找到了鏡子,就無異于找到了創作的選題。確定選題之后,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用曲藝的手段,把用意變成詩意,把實情變成詩情,完成創作的升華。
記者:評價好的曲藝作品的標準是什么?
王連成:好的曲藝作品讓觀眾有娛樂感,起碼讓人看了開心,帶來視聽上的沖擊,具備藝術性;同時,還要有思想性。一定不能讓人傻樂,在樂的同時,或叫人思考,或叫人反省,傳遞一種溫暖和正能量。一個好的曲藝作品從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別人的行為處事。最后,好的曲藝作品要有流傳的能力。一笑了之的作品不叫好作品,好的作品應是可以反復欣賞,并且令人樂意反復欣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