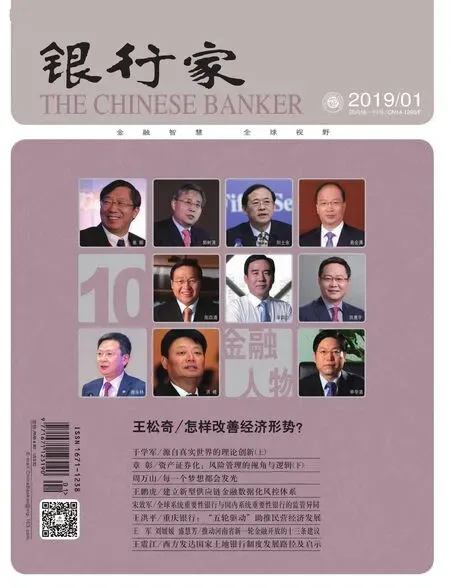通縮時期的宏觀政策抉擇
梁紅

隨著2015年全年GDP平減指數(shù)降為負值,市場開始爭論中國是否進入了新一輪通縮周期。我們認為,本輪增長下滑、物價通縮的歷程與1998~2002年期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首先,通縮的前奏均是信貸的無序擴張之后帶來長時間的去杠桿過程,以及固定資產(chǎn)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持續(xù)多年下滑。其次,外部需求環(huán)境不確定性較高,增加了總需求增長的脆弱性。最后,投資回報率的下降需要政府實施逆周期寬松政策并采取結構性改革措施,以達到重振經(jīng)濟,提高投資回報率,并實現(xiàn)經(jīng)濟轉(zhuǎn)型和促生新的經(jīng)濟增長引擎的目的。
歷史重現(xiàn)
兩輪物價通縮的前奏均是信貸的無序擴張之后帶來長時間的去杠桿化過程。1992~1993年中國經(jīng)歷了信貸的大幅擴張(1993年一季度高峰時M2同比增速達43%),固定資產(chǎn)投資增長過快。隨后,投資回報率開始下降,通脹大幅上升。1993年PPI高達24%,1994年4季度CPI高達27%,房地產(chǎn)價格也隨之大幅上漲。之后的貨幣緊縮政策和企業(yè)部門去杠桿化導致貨幣擴張速度迅速放緩,通脹水平快速回落——M2同比增速隨后連續(xù)8年下降,PPI在短短4年的時間由高通脹轉(zhuǎn)為通縮。更引人注目的是,名義GDP同比增速從1994年4季度高峰時的37.4%快速下滑至1999年三季度的僅5.8%。時至2015年,距M2同比增速在2009年三季度達到高峰的30%已過去了6年,而PPI已經(jīng)連續(xù)44個月為負。由于2008~2009年的無序投資熱潮,2009年以來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開始超過實際GDP增速,表明邊際投資回報率下降,類似于1995~1999年期間的情形。
與當前的情形類似,1998~2002年動蕩的外部需求環(huán)境動蕩令復蘇之路變得曲折。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外部環(huán)境快速惡化,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大幅升值20%以上,短短一年多時間內(nèi),出口同比增速從30%以上劇降至-8%。2000年,在信貸周期性見底后不久,經(jīng)濟還處于大病初愈的虛弱狀態(tài),互聯(lián)網(wǎng)泡沫的破滅再次把出口同比增速從將近40%打壓至3%左右,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再度升值15%,經(jīng)濟復蘇再一次受到擾動。有意思的是,盡管外部需求環(huán)境欠佳,1997~2003年中國年均經(jīng)常賬戶順差仍達到GDP的2.1%,表明當時內(nèi)需疲弱對經(jīng)濟增長的拖累更大,結論似曾相識。在本輪總需求增長減速過程中也伴隨著出口增長持續(xù)下降,而2012年以來美元走強也導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了近30%。然而,這次情況有所不同的是,除了美元流動性收縮和歐元區(qū)動蕩等因素的影響之外,中國自身的經(jīng)濟放緩成為本輪外需下滑的重要原因 。
借鑒與啟示
1998~2002年間,投資回報率下滑導致的內(nèi)需疲弱以及外部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促使政府采取果斷的逆周期政策應對。此外,彼時中國經(jīng)濟迫切需要通過更有效的財政和金融資源配置降低企業(yè)部門負擔、提高效率、實現(xiàn)轉(zhuǎn)型、并發(fā)現(xiàn)新的增長引擎。中國是如何成功扭轉(zhuǎn)下行周期并走上持續(xù)多年的復蘇之路的?我們認為,當時采取的宏觀對策包括兩方面:通過逆周期政策來緩沖需求的放緩,以及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打破供給端的掣肘。
貨幣和財政政策大幅寬松
貨幣政策顯著寬松以降低財務成本。1997~2002年期間,央行累計下調(diào)基準利率675個基點,累計下調(diào)存款準備金率700個基點。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大幅下調(diào),加上窗口指導和債務重組的努力,有效地降低了財務成本,有助于修復企業(yè)部門的盈利能力。因此,工業(yè)企業(yè)利息支出占營業(yè)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3.5%下降至2003年的1.3%。對比如今,雖然目前基準利率已經(jīng)處于歷史低位,但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仍高達17.5%,存款準備金率仍有充足的下調(diào)空間。
財政政策顯著擴張,以減輕稅負和提振總體需求。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0.7%擴大至2002年的2.5%,而國債余額凈增量達GDP的10%左右(按如今的GDP規(guī)模計算,相當于6.8萬億元)。此外,政策性銀行債券的發(fā)行力度也顯著上升——政策性銀行債券余額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3.2%增加至2002年的8.1%,4年的凈增量達GDP的近5%(按現(xiàn)今的GDP規(guī)模計算,相當于3.4萬億元)。因此,盡管目前國家發(fā)改委和財政部計劃未來3年發(fā)行1.2萬億~1.5萬億元的政策性銀行債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但考慮到2015年短短4個月內(nèi)已完成了近6000億元的專項債發(fā)行,我們認為這一發(fā)行的總額度仍有進一步擴大的空間(表1)。
盡管面對較大的周期性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仍保持穩(wěn)定。由于中國貿(mào)易伙伴的貨幣,尤其是亞洲鄰國的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1997~1998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升值了20%左右。當時中國經(jīng)濟的周期性走弱也加大了人民幣匯率的下行壓力,但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和互聯(lián)網(wǎng)泡沫破滅期間成功保持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穩(wěn)定。值得注意的是,1998~2002年期間中國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遠遠小于當前——1998年外匯儲備僅為1,45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4%,而當前的外匯儲備為3.5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32%。另一方面,當時所需的相對價格調(diào)整是通過國內(nèi)價格通縮與效率提高來實現(xiàn)的。2002年后,隨著中國經(jīng)濟增長動能的回升,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很快消退甚至逆轉(zhuǎn)。1998~2002年的經(jīng)驗表明,隨著經(jīng)濟基本面的好轉(zhuǎn),匯率貶值的壓力可能會迅速下降甚至轉(zhuǎn)向。
供給端改革釋放經(jīng)濟增長潛力
除了采取逆周期措施緩沖需求增長的放緩,1998~2002年期間中國在4個領域?qū)嵭辛擞绊懮钸h的供給端改革。這些改革不僅幫助中國經(jīng)濟走出通縮,也提升了中國隨后十年的潛在增長率。
國有企業(yè)改革極大地提高了企業(yè)部門的效率。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yè)運營效率低下。國有企業(yè)部門因為銀行過度放貸而背負著高杠桿率,同時盈利能力極低。1998~2002年期間的國有企業(yè)改革成功淘汰了制造業(yè)的過時和過剩產(chǎn)能,并在國有和私營企業(yè)之間引入了更多競爭。1998~2002年間,共約3100萬名國有企業(yè)員工下崗,而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數(shù)量減少了一半以上。而正是得益于國有企業(yè)的重組,工業(yè)部門的生產(chǎn)效率和盈利能力從1999年開始逐年改善,杠桿率顯著下降,在5年時間內(nèi),虧損的國有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量減少了將近60%。 采取措施對銀行資產(chǎn)負債表進行了重組。當時新成立的四大國有資產(chǎn)管理公司共發(fā)行了1.06萬億元的專項金融債,以購買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chǎn)。此外,1998~2008年中國通過財政部特別國債、財政部借款以及央行專項票據(jù)的形式向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和國開行注資約1.8萬億元,幫助清理了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積聚的不良貸款。這些舉措有效地修復了銀行系統(tǒng)的放貸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nèi)信貸增長跟隨總體需求回升,銀行在1998~2002年間清理不良貸款所形成的負債在資產(chǎn)負債表中的占比逐年消減。如今,銀行系統(tǒng)再度面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但嚴峻程度或不及上次。銀行資產(chǎn)負債表的重組或?qū)⑼ㄟ^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以及銀行利潤增長來有序消化不良貸款的方式來實現(xiàn)。
實行了以放松管制、擴大私有部門準入等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放開眾多行業(yè)的私營企業(yè)準入不僅幫助吸收了大量國有企業(yè)改革帶來的下崗員工,同時也有效促進了經(jīng)濟整體效率的提高。1998~2002年的改革使得我們現(xiàn)在享受到的大量多元化產(chǎn)品和服務成為可能。如今,中國面臨對更多行業(yè)放松管制和擴大私有部門準入的機遇,特別是效率仍然低下和/或仍面臨供給瓶頸的生活服務業(yè),如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電信等等。我們認為,政府或?qū)⒏袆恿υ试S私營企業(yè)進入與提高民生和生產(chǎn)效率(科技創(chuàng)新、電訊基礎設施等)相關的行業(yè),因為提高相關行業(yè)的效率較為符合政府的長期發(fā)展目標。
城鎮(zhèn)住房改革建立起了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的新市場。城鎮(zhèn)住房改革帶來了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持續(xù)繁榮,為城市地產(chǎn)這一重要的生產(chǎn)要素創(chuàng)造了市場、并通過市場力量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了潛在增長率。如今,農(nóng)村土地確權和戶籍政策改革的機遇或?qū)⒋俪梢粋€更加有效的農(nóng)村產(chǎn)權交易體系的建立,并對經(jīng)濟產(chǎn)生類似的推動作用。同時,農(nóng)村土地改革的進展有望為戶籍改革掃清障礙,促進本屆政府所提倡的“人的城鎮(zhèn)化”。一方面,“人的城鎮(zhèn)化”或?qū)⒋龠M人力資源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的轉(zhuǎn)移,促進經(jīng)濟整體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釋放農(nóng)村土地資產(chǎn)的價值也有望在中長期帶來投資和消費的持續(xù)增長。
促進了可貿(mào)易部門與全球的加速融合,并顯著提升了制造業(yè)的效率。制造業(yè)的對外開放以及和全球供應鏈的對接推動了中國向生產(chǎn)前沿躍進,并在隨后多年內(nèi)提升了中國可貿(mào)易部門的增長速度和效率。雖然加入世貿(mào)組織之前,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在1999年下半年已出現(xiàn)見底跡象,但我們認為,加入世貿(mào)組織仍對中國經(jīng)濟隨后十年潛在增長率的提高做出了十分積極的貢獻。對比當下,中國的金融業(yè)或?qū)⑦M一步對全球競爭者和資產(chǎn)配置者開放。盡管坐擁全球最大的儲蓄池,但中國的金融體系的發(fā)展還比較落后,未來發(fā)展多元金融產(chǎn)品、提升金融資產(chǎn)配置效率的空間依然很大。例如,中國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chǎn)(50%為現(xiàn)金)僅為GDP的1.5倍,而美國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chǎn)(現(xiàn)金僅占14%)達GDP的4.3倍。正如當初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加入世貿(mào)組織對中國可貿(mào)易部門的發(fā)展和整體效率改善的巨大影響,如今金融業(yè)的全球化或許也將對中國金融業(yè)以及經(jīng)濟增長產(chǎn)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思考與展望
經(jīng)過1998~2002年期間多年的需求端政策支持和供給端改革,中國經(jīng)濟進入了持續(xù)復蘇的軌道。2002年后新一輪的經(jīng)濟增長受益于房地產(chǎn)投資、消費升級和出口需求的帶動。經(jīng)濟在1998~2002年通縮階段之后的復蘇力度和持續(xù)性均遠遠超過當時大多數(shù)經(jīng)濟學家的想象。回顧歷史,這是由于1998~2002年期間的市場化改革通過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提升了潛在增長率。
如今,中國經(jīng)濟可能面臨著與1998~2002年類似的挑戰(zhàn)。我們認為,本輪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放緩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因素,因為單純的結構性變化不應伴隨著如此巨大的相對價格變動。因此,中國政府可能會采取與1998~2002年相似的宏觀政策來應對,包括更加堅決的逆周期宏觀政策和供給端改革。中國經(jīng)濟的下一個增長引擎將是什么?雖然新的增長動力可能在經(jīng)濟增長下行階段被周期性疲弱的趨勢掩蓋,但鑒于目前我國人均GDP僅為7800美元,中國經(jīng)濟無疑仍有充足的增長空間。
積極的逆周期政策和市場化的結構性改革將有望繼續(xù)降低企業(yè)部門各項成本、提高效率、并為新興產(chǎn)業(yè)的形成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宏觀環(huán)境。面對大量的過剩產(chǎn)能和嚴峻的外部需求環(huán)境,本輪中國經(jīng)濟的復蘇之路可能也將較為曲折。對比上次,短期內(nèi)政府仍有空間來加大逆周期調(diào)控的力度。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正面臨著與1998~2002年類似的推行供給端改革的機遇。政府定下了雄心勃勃的增長目標——到2020年,我國GDP要達到17萬億美元、人均GDP要達到12000美元,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勢將有令人振奮的增長機遇。雖然中國經(jīng)濟下階段的增長動力尚未明朗,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隨著國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廣義的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將在中國經(jīng)濟的下一發(fā)展階段迎來蓬勃的機遇。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