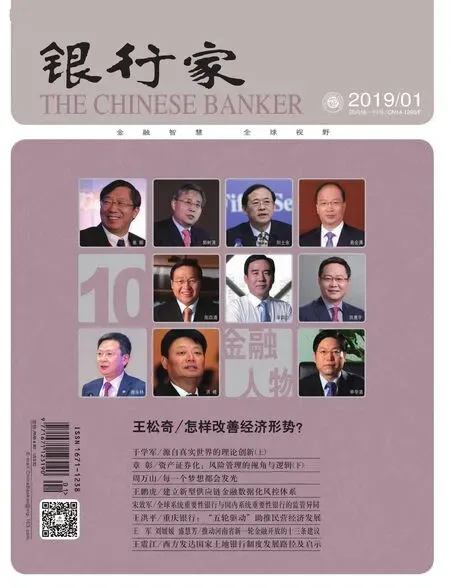人民幣加入SDR會給中國帶來什么?
謝亞軒 劉亞欣 張一平

2015年11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IMF工作人員今天向執董會提交的特別提款權(SDR)審議文件評估認為,人民幣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要求,建議執行董事會認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并將其作為除英鎊、歐元、日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種貨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工作人員還認為,對于工作人員2015年7月向執董會提交的初步分析中指出的所有懸而未決的操作性問題,中國當局也均已解決。雖然IMF將在11月30日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和投票,但從目前信息來看,人民幣加入SDR幾成定局。
SDR的前世今生
IMF于1969年10月第24屆年會上通過了設立SDR(特別提款權)的決議。之所以得名特別提款權,是為了與成員國按照基金份額所確定的普通提款權相區別。
SDR是一種人造貨幣,因此它面臨著定價的問題。SDR最初的定價原則是作為單位美元所包含的黃金的等價物,即SDR與美元的兌換比例是1∶1,它能夠替代黃金進行國際收支的結算,因此也被稱作紙黃金。隨著美元與黃金的脫鉤,SDR的定值也轉向了一籃子貨幣。1974年,SDR改由當時占全球出口額1%以上的16種國家的貨幣組成的籃子定值。但是這個龐大的貨幣籃子在計算上過于復雜,不利于SDR的推廣和發展。最終在1980年,IMF決定將SDR的貨幣籃子減少為五種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美元、英鎊、法國法郎、德國馬克和日元,并且每隔五年討論一次SDR籃子貨幣的權重問題。1980年以后,這些貨幣的權重分配上,美元始終居于第一位,常年來約占40%以上。比較引人矚目的是歐元比重在這十年間上升了5%,但這是由于英鎊和日元比重下降造成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經濟的強大和美元的領導地位并未因歐盟的建立和歐元的投入使用而受到影響。2011,SDR中美元的比重下降到41.9%,這與金融危機后貨幣體系和儲備貨幣多元化的趨勢相符。
SDR的分配與用途
SDR的分配就是SDR的創造和供給,其實質是IMF向其成員國提供無條件和無成本的信用額度,是按照成員國在IMF中的份額比例進行分配的,份額越大所獲得的SDR數量越多。SDR本質是一種信用資產。
SDR的分配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一般性分配:IMF根據世界經濟的發展情況和對儲備資產的需求狀況,定期決定是否分配SDR。通常情況下,IMF每隔五年開會討論這一問題,到目前為止IMF已進行過三次一般性分配,分別是1970~1972年分配了約93億SDR、1979~1981年分配了121億SDR,以及在2009年分配了1612億SDR。
另一種方式是特別分配,這種分配主要是IMF為了某一特殊目的所進行的分配,分配數量、對象都不一定。最近的一次特殊分配是2009年IMF根據1997年的決議所進行的分配。主要分配對象是那些在1981年之后加入IMF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未能像從前兩次一般性分配中獲得SDR。這次特殊分配的數量為214億SDR,目的是保證成員國的SDR分配數量與其在IMF中的份額相一致。
當前SDR總規模較低,作為儲備資產的吸引力較小。1970年至今,IMF共分配了約2040億SDR,約合3180億美元,不足全球非黃金外匯儲備的5%,對比來看,僅是中國的外儲規模便超過3萬億,可見SDR的規模很小,這主要是由于SDR的吸引力不高造成的。IMF規定每隔五年討論一次SDR的分配問題,但發達國家使用SDR的積極性和緊迫性不高,并且認為過多的分配SDR會造成流動性過剩,引起通貨膨脹,因而發達國家不愿意多分配SDR。再加上發達國家在投票權上的優勢,發展中國家認為SDR實際用處不大,既不能滿足本國清償國際收支赤字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其對發展資金的需求,因此發展中國家對SDR的興趣也不高。
特別提款權的用途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會員國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動用特別提款權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償付逆差;第二,會員國與其它會員國可通過達成協議,用SDR換回對方持有的本國貨幣;第三,會員國還可用SDR歸還向基金組織的貸款,和支付應付基金組織的利息費用。但是,SDR只是會員國在基金組織“特別提款賬戶”上的一種賬面資產,不能直接作為國際支付手段,用于貿易或非貿易支付。不過,SDR既無須償還,又代表著無條件支配可兌換貨幣的權力,確實可以作為一種額外的資金來源或儲備資產的補充。
推動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的原因
在實際應用中,SDR產生的實際交易并不多,SDR僅為賬面資產,意味著人民幣加入SDR并不會強制使得各國增加人民幣儲備,加入SDR也并不能夠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伯南克在一定程度上說的對,中國推動人民幣成為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的強烈愿望來自于“榮耀感和國家形象”,“如果人民幣成為SDR 貨幣,對普通中國人沒有絲毫影響。主要是象征性意義。”
那么,為何要推動人民幣加入SDR?
人民幣加入SDR實際上是為成為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鋪平道路。成為儲備貨幣隱含的重要條件便是“國際認可”,因為只有將這樣的貨幣作為儲備才能夠保證緊急用途下貨幣能夠被對方接受,SDR貨幣籃子由權威的國際組織IMF評定,實際上是“國際認可”這一概念的實體化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構建對于一國貨幣的共同信心與公信力,而這種信心對于貨幣國際化顯然是至關重要的。更為現實的意義,則是希望這樣的信心可使各國增持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從而增加對中國金融資產的配置,為國內帶來增量資金。
更長遠看,中國目的在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無論是金融危機時還是當下,由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都給全球經濟帶來了諸多不穩定因素,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不受外界約束卻廣泛影響全球,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多極化與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也并不匹配,這尤其會干擾和制約像中國這樣后崛起的新興市場發展。
周小川行長在2009年提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倡議,采用IMF的特別提款權方案作為改革的第一步,而提升SDR貨幣籃子的代表性又是SDR自身改革的第一步。可見,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在根本上是改革現行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起點,這也是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有助于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預估人民幣在SDR中的比重
IMF認為,貨幣在SDR籃子中的比重應該綜合考慮該國的出口情況以及這種貨幣在其他國家儲備資產中的份額,從而充分反映這種貨幣在全球貿易和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的重要性,目前采用的兩者比重分別占60%和40%。
對人民幣而言,從出口角度考慮,2010~2014年中國出口在全球占比11.0%,低于歐元區和美國,排名第三,但所調查到的全球官方儲備中人民幣僅占1.1%左右。若嚴格按照上述方法和以上數據計算,人民幣的權重約為13%;而在IMF8月的評估報告中曾指出,IMF估算的人民幣作為第五種貨幣的權重可能為14%;而IMF在過去假設的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方案中,2011~2015年人民幣的權重均高于英鎊、日元。綜合以上幾點考量,我們預計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為13%~14%,可能略高于日元、英鎊,但仍遠低于美元與歐元。
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會給國內資本市場帶來多少新增資金?
如前所述,納入SDR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意味著國際社會逐步認可人民幣具備國際貨幣的資格。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初期,價值儲備職能將率先影響境外貨幣當局在外匯儲備幣種配置的調整。換言之,人民幣納入SDR將在中期刺激外國央行將人民幣納入其儲備資產,進而增加人民幣債券的配置需求。再者,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的接受度提高,離岸人民幣清算行持有的離岸人民幣存量也將上升,這類銀行配置人民幣債券的需求也會相應提升。
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的份額可能與日元或英鎊較為接近,若對應日元英鎊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即3.4%或4.1%。但人民幣還存在一個不利因素,即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程度遠低于日元或英鎊,雖然中國正不斷加大資本項目開放步伐,但在維持經濟、金融穩定和開放中始終要取得平衡,短期很難達到日本、英國的開放程度,而人民幣貨幣和資產可得性可能會限制外國央行增加人民幣資產配置的熱情,因此,我們預計中期內,4%是人民幣資產占比的上限,3%是一個中性的預測,2%可能是較為悲觀的預測。換言之,外國央行持有的人民幣資產目前看最多將達到4600億美元,較之目前1000億美元左右的人民幣資產存量,增長3600億美元。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測算主要針對外國央行增持人民幣資產的預測,正如其他國家央行拿到美元儲備后投資于美國國債一樣,外國央行增加了人民幣儲備資產后,也會將人民幣投資與國內銀行間債券市場。顯然,境外私人部門也會增持債券、股票等資產。
(作者單位: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