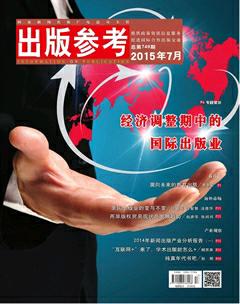美國出版業現狀分析
管丹

美國出版商協會近日發布的數據表明,美國圖書出版產業2014年整體銷售同比增長4.6%。其中K-12教材板塊增幅最大,為9.9%;專業出版領域銷售增長4.6%;大眾出版領域銷售增長4.2%。大眾出版仍然是最大板塊,2014年總收益為154.3億美元。2014年,全美圖書總銷量增長3.7%,達27億冊,其中大眾板塊增長4.1%(包含宗教出版),達24.2億冊。
美國出版商協會注冊會員1200余家,下轄的國際委員會有9個成員,代表著美國 400多個版權代理和書探。當人們說起美國的電子書成熟并接近飽和時,所指是小說,占小說圖書的70%。美國出版市場的翻譯類作品較少,占其全部圖書產品的3%,而這3%的翻譯產品中僅有3%來自中國(含港臺地區)。本文主要對美國圖書的銷售渠道及數字出版概貌做以介紹和分析。
一、美國主流實體和數字渠道
我用以下圖表來直觀、系統闡述,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人為割裂紙書與電子書,實體渠道與數字渠道。因為當前美國市場,大眾圖書基本上是紙電同步銷售,各主要發行商大多也兼營實體渠道和數字渠道。
表1 美國主要發行商概況(全國和地區性發行商1000多家)
表2 美國各圖書銷售渠道占比(大眾圖書)
二、美國數字出版情況
本文中涉及更多的是美國五大大眾出版社(包括企鵝蘭登、哈珀·柯林斯、西蒙&舒斯特、麥克米倫、阿歇特),他們目前的紙書與數字書的銷售比例,穩定在7:3。從他們的實踐看,數字出版并沒有擠壓紙書空間,而是給出版社帶來了30%的銷售增長。美國電子書中最暢銷的品種是愛情、科幻、偵探小說,還有財經勵志等。2014年美國數字圖書中增長最大的是兒童讀物,但這個增長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小說而不是圖畫書。
這里我需要強調,上述數據都是指大眾出版。而我們國內各家出版社目前的產品線、自身定位以及大眾圖書在各社占比,都是我們面對諸多國內外數據時要注意的前提。
本次我將個人研究范圍限定在美國的藝術出版,是尊重業界對文學、大眾、科技及少兒等圖書期刊如火如荼的數字化趨勢判斷而做的獨立分析,我更關注藝術出版在數字語境下或失聲或審慎的一些案例。
三、美國出版公司個案
以DOVER出版社為例,該公司創立于1941年,以出版各種有價值的圖畫書、圖文書,出版讓讀者能用最實惠的價錢買到的書為己任。他們的定價原則是DOVER自己人愿意出這個價錢買這個書。職業道德和策略的另一想法是他們不要一下給讀者太多同類書,造成讀者選擇痛苦。他們的電子書單品種銷量高,雖然定價低,但跟紙質書一樣也能形成高額利潤。他們的定價策略是這樣的:如紙電單獨銷售,電子書訂價為紙書的80%;如紙電捆綁銷售,捆綁后價格為紙書定價的1.1倍。本質上是用電子書的形式來激勵和帶動紙書銷售,是策略,是回饋。需要說明的是,美國目前紙質書的稅收在3%以下,而電子書的稅收卻高達15%到25%。
美國的藝術類圖書,尤其是大型藝術畫冊很少有被認為適合做電子版的。一是因為圖片數字版權取得難度大、成本高;二是因為電子版閱讀的視覺體驗不如紙本畫冊大、易翻閱、看得細、色差小。具體講,美國ABRAM出版社(1949年成立的美國國際藝術圖書出版社)的600多部電子書中,84種為藝術類圖書,多為技法和專著等文字及說明類圖書。MOMA目前僅做了90種電子書,由于電子畫冊品質不高、屏幕呈現小、銷售市場小等原因使其數字出版的成本收益比率不堪忍受。RIZZOLI上線的47種電子書在其集團整體圖書品種處于嘗試階段,沒有藝術畫冊而大多是兒童及大眾圖書。
ABRAM、RIZZOLI以及阿歇特(Hachette),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有自身強大的發行渠道和網絡,作為出版品牌的同時,也都是發行品牌,不僅發行本公司產品,還為其他同類出版機構代理發行。這種做法既豐富了自己的產品,又強化或統一規范了某一區域同類產品的市場定位與秩序。而我國大部分出版集團在國際上,目前大多是作為一個巨大的出版管理機構出現,暫時還不是巨大的出版和經營品牌。但是我想我們應該是有信心,因為阿歇特最早是法國公司,RIZZOLI最早是意大利公司,他們都不是英語母語國家,今天卻都在美國及全世界堅強存在,自信十足,是我們中國出版企業的榜樣。
四、對美國出版業的幾點思考
第一,數字語境下的現象與本質
數字出版本質上遠不是圖書形式的問題,是思維方式,是技術應用。數字出版的最高境界是出版大數據的應用。它的最終指向應該是讀者或客戶的最大化。美國的愛思唯爾(Elsevier)對內容資源深度加工整合,形成功能強大的細分領域數據庫,向全球大學和研究性圖書館提供產品。這是他們數字產品收入的最重要來源。為閱讀而閱讀的人是少的,而為研究、為特定目的選擇性地閱讀將是主要需求,而能精確檢索是滿足這個需求最需要做的工作。
第二,不能忽視的中美出版業所處的生態環境差別。
首先是著作權規范方面。談到數字出版,不能忽視的第一重要問題是著作權。相比美國著作權生態環境,我國從作者到出版社到社會都還是不成熟,沒有建立起信用體系。數字產品一旦上到互聯網上,便無國界。仍以MOMA為例,他們為了出版一本《畢加索》畫冊,不惜花費95000美元圖片費,耗時一年半去取得300幅圖片的授權許可。而國內,現在作者跟出版社簽訂的《出版合同》一律打勾或劃掉,根本不在意細節上彼此的約束和法律責任,這和國外用一張圖都得有授權,缺一個授權都不能出書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不精細分析某一單品的特有情況,打包一攬子地兜售給外方我們帶有法律瑕疵的圖書產品,輕則暴露我們的非職業性,影響品牌聲譽,重則會招致法律訴訟。
其次是出版商競爭心態方面。培訓班的專家談及新媒體和數字出版時,能更多地將它放入到出版歷史和著作權本質上去分析,就版權法的崇高理想功能與實際商業應用間尋找它們的平衡。這是相對于國內傳統出版社的更為理性客觀的角度。
第三,出版企業運行管理機制方面。
中美兩國的出版業所處的生態環境與社會心態是不同的,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它直接影響雙邊合作的艱難與否和成敗得失。美國出版透出技術融入的輕快感,中國出版顯出體制附帶的沉重感。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反思我們的企業和行業對新辦公技術和制作技術的應用,似乎更多的是通過設計師和印廠的推動實現的。然而差距不只在技術、機制、企業心態和組織協調的精力與成本上,更在做事、做項目的精準度和執行力上。中國出版業數字與版權和印刷制作等分屬不同部門和領導,交接處銜接不力,受主觀和人為影響較大。美國數字出版的用人經驗是新技術和新業務招錄新人來做,盡量避免讓老人學新技術。
一位了解中國、希望與中國合作的電子書商不無沮喪地告訴我們:他在亞馬遜網站上所見4000種中國數字圖書,元數據缺失和混亂令他們苦惱不堪,而這些基本元數據和營銷元數據恰恰是營銷和資源再利用的關鍵。從美國書展期間我們進一步接觸中,他也透露出對于有些中國公司熱衷于簽署戰略協議,簽署那種后面帶著長長圖書清單的一攬子合同的做法,感到無力和無奈。
最后是政府和社會層面的推波助瀾。中國的一些平臺與技術公司熱熱鬧鬧地張羅著數字出版,不排除有文化理想者和創新求變者,但是中國政府在此領域的各種資助和投資,客觀上也可能成為他們的動力或動機,如投資動漫產業一樣,每一次導向型政策下都會誕生一些所謂的大公司大項目,但是多年以后,我們能夠看到的景象并不真正繁榮。中版集團作為傳統出版基地,產品以社科、學術、專業等不同于大眾圖書的品相和功用呈現,具有相對冷靜的反應,我個人認為是正常的。由于中國與美國出版行業所身處的大的生態環境不一樣,因此不能簡單地就兩種出版業所呈現的表象來比對參照。
行文至此,我用美國《出版視角》雜志主編愛德華提出的“五個不要”作為結語并與同道共勉:
一不要過度高估版權的價值,在不同的市場、不同的時間,人們的取向是不斷變化的,片面強調自己手里的版權多有價值是不可取的;
二不要聽信所有的數據,數據很多、變化很快,一定要考慮數據的來源,來源可靠的數據才可信;
三不要過度設計你的流程、人為地讓事情很復雜,包括傳統印刷程序等在內,要讓流程越簡單越好;
四不要輕易放棄現在還行之有效的做法,不要因為出現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概念、新的技術就對原有的體系持懷疑態度,在沒有評估的情況下,輕易放棄目前還有效的做法是不值得的;
五不要低估“中國品牌”的價值,不要低估中國自己的能量,成功取決于中國自己。 (作者單位系中國美術出版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