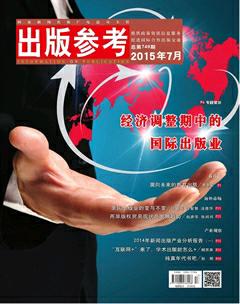尋書記
鄭利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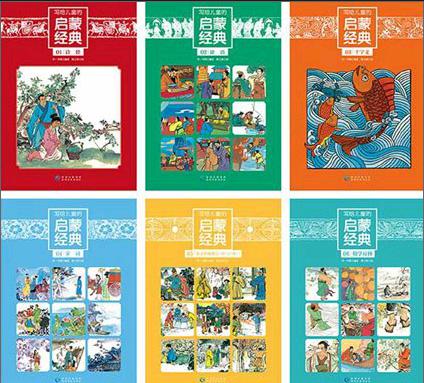

步印童書館是北京步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旗下的童書品牌,目前已出版小牛頓系列、小小牛頓等暢銷品牌圖書,2015年4月又新推出《寫給兒童的啟蒙經典》系列圖書,新穎的寫作手法及親切典雅的文本吸引了眾多讀者。
茉莉書店巧遇
2013年10月,簽下《幼獅少年》400多期選編權之后,意興闌珊之際,前往臺大附近著名的茉莉二手書店,書店在一條幽靜的小巷里,與旁邊繁華的羅斯福路形成強烈的對比,似乎是這家書店讓這條小巷沉靜下來。書店有一個小角落專門陳列二手童書,我席地坐下,一本一本細細看來,如同尋寶者一件件清點發現的寶物,不愿漏掉一絲一毫。就是在這個角落里,偶遇一本由華一書局編寫的《兒童啟蒙文學》(步印簡體版改名為《寫給兒童的啟蒙經典》)中的一本:《論語》。步印從沒有觸碰“國學”這個時下的顯學。或許純粹是好奇心的驅使——想看看臺灣的出版前輩們如何去給孩子講國學——我翻開了這本品相陳舊、其貌不揚的書。照例先讀序言:中國第一位老師。單看這一標題就覺立意不凡,一口氣讀下來,總共六七百字的文章,竟然將封建解體導致貴族平民化的大背景、論語成書過程、為何《論語》里多只言片語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娓娓道來,絲毫不覺枯燥。心下不禁暗暗稀奇。展讀內文,“吾日三省吾身”一句,在注解翻譯之余,輔以“曾子的三面鏡子”一文,將忠誠、信實和學習喻為三面鏡子,形象而易于理解;“君子食無求飽”一段的故事以“孔子為什么教我們吃不飽呢,餓肚子的滋味可真難受”開篇,再講了一個“子夏變胖子”的小故事說明求學和欲望之間的關系。語言輕松活潑,故事有趣生動,完全是孩子的視角,孩子感興趣的語言!讀來讓人拍案叫絕。如此國學讀本多有意思,我讀起來都津津有味。一時間,闌珊遁消,斗志方興。如此好書,當立拿下。
按圖索驥
茉莉二手書店只有一本《論語》,得先想辦法拿到全套書。遂決定雙管齊下:一方面請臺灣出版界朋友幫忙找全套書;一方面了解華一書局的情況。出版界的朋友一向都很給力,那份熱情和效率總能給我帶來驚喜和感動。第二天,差不多30年前的出版物就出現在了我的眼前。一本本地翻閱,一本本的感動。文本皆精品。與此同時,朋友打聽到的消息則有點讓人失望:華一書局早就停業了,如同曾經在臺灣出版界叱咤風云的錦繡、光復書局、小牛頓一樣,銷聲匿跡了。連神通廣大的臺灣出版發行協進會理事長盧欽政先生都為難了:要想短時間找到版權方似乎不大可能了,只有回北京后再慢慢等消息了。
回到賓館,32本厚厚的大書擺在眼前,在此時我的眼中,它們如同可望不可及的一座座寶庫,我時刻感受到它們散發出來的誘惑,卻無法靠近她、擁有她!此時此刻,情何以堪!
出版方不能直接找,轉換思路,那就找作者看看。全套書的作者署名華一編輯群,這一署名在大陸不多見,而在臺灣童書的黃金時代卻很常見,充分開放的市場導致了生產環節的細分,出現了專門的編輯團隊和設計團隊。只是為此團隊里的成員一個個谷歌下來,信息都非常少,無法查找。此路不通,只有再找插畫家,《啟蒙文學》共32本,其中27本的插畫家署名皆為陳士侯。谷歌一下得知,陳士侯先生已為臺灣首屈一指的工筆畫大師了,且在臺灣藝術大學執教。恰好認識一位對臺灣藝術圈很熟悉的朋友,經他周旋,很快就聯絡上了陳先生,并約定第二天見面的時間和地點。轉機顯現。
拜會陳士侯
與陳先生見面的地方在敦煌畫廊,為一日式園林小院,幽靜雅致,在寸土寸金的大安區,實在不多見。陳先生的畫作大多委托這家畫廊處理。見陳先生前,心中略有忐忑,陳先生的畫作在臺灣每平尺已達20萬-30萬臺幣了,如此大拿會不會好溝通呢?
見面之后,疑慮頓消。陳先生真誠而質樸,十分健談。談及這套書,陳先生感觸良多。開始為這套書插畫時,他只是兼職在做——白天在漢聲出版社上班,晚上才有空為《啟蒙文學》畫插畫。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陳先生為《啟蒙文學》畫的第一本《論語》與漢聲的扛鼎之作《中國童話》風格很接近。
后來,陳先生辭去漢聲的工作,專心為《啟蒙文學》畫插畫,一畫就是兩年多。為了跟上圖書出版進度,基本上是每天兩幅的節奏,期間不能中斷,陳先生笑言,當時病都不敢生!
兩年多的時間,陳先生全身心投入在書的插圖中,當時兩岸關系緊張,臺灣關于古代服飾、器具的資料甚少,大陸的連環畫給了陳先生不少幫助。其時臺灣禁售簡體字圖書,陳先生想了一個絕妙的辦法:趁去香港的機會購買大量連環畫,在酒店將每頁的簡體字部分剪掉帶回臺灣。為了查找方便,陳先生將連環畫一張張貼在墻上,當時其工作間貼滿連環畫的殘片。
這套書的畫酬也十分豐厚,陳先生因此有了房有了家,再加上兩年多高強度的工作學習,讓陳先生的藝術之路百尺竿頭,從此淡出出版業,潛心作畫,終成一代大家。也因此,陳先生對華一的老板——從物質和精神方面都給予大力支持的紀先生不勝感激!所以陳先生說,這套書的插圖版權是屬于華一書局的,即便華一書局不再經營了,也應當屬于紀先生的后人。
可惜的是,陳先生與紀家太長時間沒有聯絡,也沒有他們的聯系方式了。
初會紀氏雙雄
因緣際會,曾永義教授幫我們找到了華一老板紀斌雄先生兒子的聯絡方式。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豪不猶豫地撥通了紀先生的電話,順利地約好見面地點,似乎一切皆水到渠成。我們志在必得。
見面約在中山路捷運站附近的一家日式餐廳。除了我聯系的紀先生之外,還有一位他的雙胞胎哥哥。這對兄弟搭配很絕,哥哥沉著冷靜,寡言少語;弟弟開朗大方,是營銷好手。兩兄弟個個高大英俊,我稱之為“紀氏雙雄”。紀氏雙雄對步印兩位急切而不時秀肌肉的介紹一直保持謹慎的友好。會談在紀氏雙雄“我們認真考慮考慮”的禮貌性表態中結束了,這是我們事后得出的結論,當時我們可不這樣想。因為手握《吳姐姐講歷史有事》《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小牛頓科學館》等臺灣當年的重量級產品,我們大有志在必得、舍我其誰之氣勢。
焦急的等待
會見紀氏雙雄是在我們回北京的前三天晚上,我特意給他們透露了行程,希望能在回北京前確定此事。我們自信地認為第二天就會接到他們同意授權的電話。事實證明我們的自信是盲目的,一直到下午5點都沒有收到任何消息。我有點沉不住了。于是只有再向臺灣出版業的朋友咨詢了。從一個朋友那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華一創辦者紀斌雄先生很早就和大陸有合作關系,上世紀90年代初,紀老板去山東收一筆數量頗大的版稅,晚上在酒店暴病身亡,官方的說法是飲酒過度引發疾病,但對他的去世一直有各種傳言。得此信息,頓時有不祥之感,臺灣人大多對新認識的大陸人懷有謹慎的懷疑,何況紀家還有如此沉痛的記憶。這下如何是好?一時不知所措。
“出門靠朋友”這句話再次得到了驗證。在與另一位朋友聊及此事的窘況時,熱心的朋友說,我不妨給你找一下一位以前發行界的元老再去打聽一下。晚上我們與這位羅總一起在一家臺菜館吃飯。混發行的果然豪邁,羅總得知我們的困難后馬上說,我認識紀氏兄弟的叔叔,紀老板意外去世后,有一段時間華一是由他叔叔掌管的。遂立刻撥通了電話,這一電話后來起了關鍵性作用。第二天我們就接到了紀氏兄弟的電話,他們提議在我們回北京之前再見面商討版權之事。
如愿以償
與紀氏兄弟的第二次見面,局面有了實質性的改變,謹慎的友好變成了其樂融融的坦誠。紀氏兄弟坦言,第一次見面后,原本無意出售版權,他們生活富足,并不缺錢,平時最大的愛好是出海釣魚,并邀我們有機會一同前往。
關于合同的談判意想不到的順利,很快達成意向。回到酒店,長期緊繃的弦終于松了下來,是一種愉悅的疲憊,感覺好極了。
接下來就是緊張而有條不紊的編輯制作工作,其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事情,以后有機會可以接著給大家說說。
(作者系北京步印文化創始人,策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