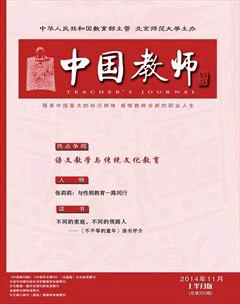黎松齡:語文學科承擔著對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任務

《中國教師》:根據教育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有關內容,今后我國將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您認為這有何意義與價值?
黎松齡:文化的傳承,本來就是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無論對民族還是個人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現今,面對各種文化交雜的現狀和一些心態失衡、道德失范的言行,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尤其具有現實意義。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之夢,需要培養富有民族自信心和愛國主義精神的青年,需要具有家國情懷、社會關愛和人格修養的國家公民。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這里的“德”包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是人文精神的底蘊,從教育育人的目的到現實和未來的需要,我們都必須將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使命來完成。
《中國教師》: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教師節時提到,對語文課程,他“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黎松齡:現在語文教材雖有多個版本,但選文內容絕大多數還是一些傳統經典名篇。新中國成立之后,伴隨政治運動和教學觀念的改變,語文課本幾經變革,但有個爭論卻一直不斷,那就是古代詩文到底應當在語文教材中占多少比例。
把古代經典詩文從語文課本中去掉,這當然不可以,習總書記不贊成,我們語文教師也不會贊成。但如果因此就將語文課本變成古代經典詩文集,顯然也是不可取的。語文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綜合性與實踐性的特點,決定了語文學科的性質,使得語文課本的選擇與教學具有明顯的“示例”性。語文學科承擔著對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任務,承擔著作為基礎工具在現實生活的交流、溝通、理解與運用等任務。雖然語文學科和理科類學科相比,在知識科學體系上不如它們,但作為一門學科,它也有著自身的規律與學科特點。
當然,現行語文教材確實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一些傳統名篇被去掉或者刪減的現象也確實存在。但這又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只恢復或增加古代經典詩文是否就可以達成我們所期待的對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我認為,要完成這一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只靠語文學科,只靠語文課本,或只靠語文教師,是遠遠不夠的。如有可能,我希望能夠專門開設一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
《中國教師》:您認為語文學科在傳統文化教育中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黎松齡:語言文字、民族文學與傳統文化是構成語文教學的最重要的三個有機部分。語文本身就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直接體現,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語文學科的性質與特點、語文教學的內容與目的,決定了語文教育與傳統文化密不可分,決定了語文學科在傳統文化教育中獨特的重要作用。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從先秦諸子散文,到歷代史傳政論,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具體感知和認識,主要是通過語文教材的相關課文學習到的。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人生態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處世原則,等等。從漢字中感受我們民族的智慧,從古詩文中了解我們民族的傳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貫穿于語文學習的始終,對學生的傳統文化浸潤,無疑是所有學科中最為持久與濃重的。
《中國教師》:在當前語文學科課程與教材設計中,您覺得它涉及傳統文化內容的比重如何,這一比重對學科教學產生了哪些影響?
黎松齡:我們學校現在使用的是京版教材,古詩文的比重約占1/3。在古詩文內容方面,除了教材上的,我們在課堂上也會適當補充一些人教版語文教材中選用的經典名篇。在必修模塊教學中,古代詩歌的安排相對較為集中,但從整體安排上看,是文言文與白話文混搭,交叉在一起。在選修模塊教學中,史傳文學和先秦諸子散文的安排較為集中,其他內容基本上也是混搭。從教學效果看,這種混搭與集中各有自己的優勢,但集中的時間與內容不宜過長和過重,否則會讓學生感覺吃不消。畢竟古詩文還有一個語言障礙的問題,疏通文字、了解相關背景等需要占用相當的教學時間;而且語文學習還要致力于實踐應用,文質優美的時文也是語文教材不可缺少的。至于比重問題,不同單元或專題可以根據內容有不同的安排,一篇或兩篇現代文都可以。
《中國教師》:就教材的編寫而言,您認為在設計教材內容時要注意哪些問題,才有利于傳統文化教育,或者說傳統文化教育的效果會更好?
黎松齡:僅就語文教材的編寫來說,我認為要選擇傳統經典名篇。一方面,這些文本內容經過時間和教學實踐的考驗,具有經典示范性;另一方面,這可以使教材相對穩定,有利于教學與考查。而且,在精選古詩文的同時,我希望能夠在單元或專題里加入一兩篇與之相關的現代文論,既可以幫助師生深入理解,又可以實現語文的現代交際工具的功能示范。因為古詩文學習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解決古代語言文字帶來的障礙問題,如果教材的安排過于集中,學生的閱讀會因此感到疲憊,興趣也就難以長時間保持。中間適當穿插一些現代詩論或文學評論,對學生來說是一種調劑,對所學內容與認識來說也是一種延伸。
京版教材中關于孔孟專題的部分是古今都有,文言與現代文合編,既有《論語》、《孟子》選文,也有《孔孟》和《淺談〈論語〉》。教學可以靈活安排,比如以《孔孟》作為專題導讀,學習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和《齊桓晉文之事》后,再閱讀《淺談〈論語〉》,甚至可以鼓勵學生嘗試對《孟子》進行研究性學習,仿寫《淺談〈孟子〉》。從教學效果來說,文白混編,對學習的廣度和深度、閱讀與寫作、繼承與創新,都有好處。
《中國教師》:現在許多學校都為學生提供選修課或校本課程,您認為在學校自主開發的這些課程中應如何進行傳統文化教育?
黎松齡:我非常贊成通過選修課或校本課程來加強民族優秀傳統教育。不論是專題性的,還是文選性的;不管是研究性學習,還是傳統講授交流,甚至是主題活動或專項講座,這些都可以說是很好的形式。比如可以圍繞“忠孝禮義廉恥”選擇史傳文學選讀,也可以集中先秦諸子散文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文段進行比較閱讀。最好是與傳統文化的教學研究結合,以減少隨意性,增強科學性。
我校作為中國教育學會“十一五”科研規劃重點課——中華傳統文化與青少年素質教育研究的實驗校,曾重點對《論語》、《孟子》、《弟子規》、《孝經》、《莊子》進行篩選,整合出適合中學生身心特點的內容并進行研究學習,篩選出古代文學史綱要和與中學課本密切相關的重點作家,普及文學史知識和對學生進行知識分子人格教育。此外,我校還成立了謙沖國學社,通過社團活動交流平臺,對學生進行傳統文化興趣培養,將中華傳統文化與學生的課外活動有機結合,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該課題研究成果在全國獲一等獎。
《中國教師》:您認為教師在學科教學中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可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黎松齡:我認為要針對不同階段學生的特點進行教學,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滲透傳統文化。以《游俠列傳》這一課文的教學為例。對高一新生來說,這篇文言文在文字、內容、思想上都具有較大難度。對此,教師通常會有幾個選擇:側重“工具性”,梳理文本,積累文言詞匯和用法;側重“人文性”,在粗通大意的基礎上,理解和拓展“俠”的文化;側重實踐或綜合方面,帶領學生通過工具書和相關資料解決閱讀中的問題。但我會將關注點放在“過程和方法”上,帶領學生粗通文本后,針對學習過程中學生生成的問題和爭論,將他們帶到圖書館,引導他們查閱資料,并根據興趣與所持觀點自行組成若干研究性學習小組。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可能會生成如下研究性學習課題:從郭解的興亡看“俠”存在的社會環境,“俠”的概念及其演變,“俠義精神”的產生、影響,俠士行為與精神古今之比較,從《游俠列傳》的詳略安排看司馬遷“知識分子的良心”,從“刺客”與“游俠”看《史記》的人民性,“俠”與“儒”之比較,我們現在是否還需要俠義精神,等等。由于問題與課題是在學生學習過程中自然生成的,學生學習與研究的積極性會變得異常高漲,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過程中,不僅可以加深對司馬遷寫作《游俠列傳》的目的與中國“俠”文化的理解,而且還會有所拓展;在合作、探究的綜合實踐中,學生的主體地位會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還會幫助學生在初高中的銜接過渡中實現自我激勵、自我成長。
另外,我們還會結合教學相關內容開展一些主題活動,如在學完先秦諸子散文后開設形式多樣的“諸子講談”,結合史傳文學探討漢代的英雄崇尚,配合戲劇和詩歌教學設立“戲劇節”和詩歌創作誦讀比賽等。此外,我們也會開設眾多的選修課,如《論語》選講、《莊子》選讀、唐詩鑒賞、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等。同時,借助中校區的有利條件,營造中華傳統文化與校園文化整合的硬環境。
(責任編輯:孫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