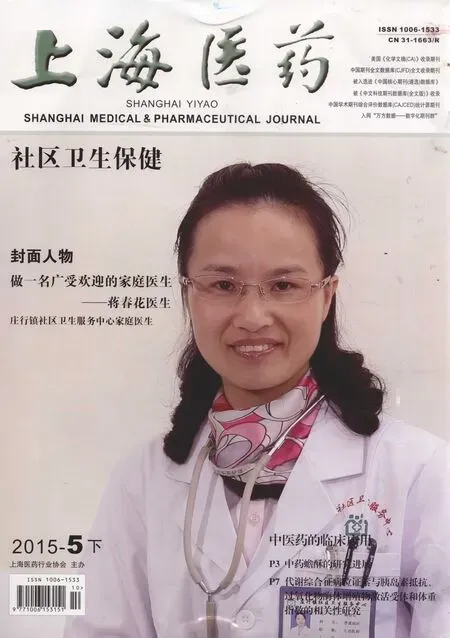代謝綜合征病位證素與胰島素抵抗、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和體重指數的相關性研究*
周一心韓振翔祁麗麗蔡偉青周宇豪宋紅普黃靜怡張慧琰(.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 上海 007;.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上海 007;.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上海 0006;.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 0000)
代謝綜合征病位證素與胰島素抵抗、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和體重指數的相關性研究*
周一心1**韓振翔1祁麗麗2蔡偉青3周宇豪1宋紅普4黃靜怡3張慧琰3
(1.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 上海 200137;2.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上海 200437;3.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上海 200062;4.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 200030)
摘 要目的:研究代謝綜合征的病位證素與胰島素抵抗(IR)、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PPAR)-γ及體重指數(BMI)的相關性。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納入曹楊社區代謝綜合征患者206例,檢測IR、PPAR-γ和BMI,分析病位證素與這些指標的相關性。結果:代謝綜合征病位證素為腎、肝、脾,與IR、PPAR-γ和BMI相關。結論:IR、PPAR和BMI可為臨床代謝綜合征中醫辨證的指標。
關鍵詞代謝綜合征 病位證素 胰島素抵抗 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 體重指數
*基金項目:上海市衛計委青年資金資助(2010Y130),上海市醫學重點專科資助(ZK2012A25)
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lic syndro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factors of insulin resistance, PPAR-γ and BMI
ZHOU Yixin1, HAN Zhenxiang1, QI Lili2, CAI Weiqing3, ZHOU Yuhao1, SONG Hongpu4, HUANG JingYi3, ZHANG Huiyan3
(1.Shanghai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0137, China; 2.Yueyang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437, China; 3. Caoya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Pudou District, Shanghai 200062, China; 4.Shangha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lic syndro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factors of insulin resistance, peroxisome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PPAR)-γand body mass index (BMI). Methods: Two hundres and six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in the Caoyang Community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 The level of the PPAR-γwas examined,the insulin resistance and the BMI of 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olic syndrome of TCM and three factor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metabolic syndrome of TCM inferred kidney, liver and spleen,and was related to insulin resistance, PPAR-γ and BMI. Conclusion: The three factors can be used as the objective indexes for clinical metabolic syndrome of TCM.
KEY WORDSmetabolic syndrome; metabolic syndro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sulin resistance; peroxisome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γ; body mass index
代謝綜合征是以糖和脂肪代謝紊亂為核心的一組癥候群,是心血管疾病和多種代謝危險因素在個體內聚集的狀態,其很多征候、相關疾病可見于“消渴”、“肥胖”、“眩暈”、“胸痹”等病。本研究在既往研究基礎上辨證成人代謝綜合征病位證素結構,研究每例患者病位證素與臨床指標的關系,篩選出每一證素相對的特異敏感指標,從而為中醫治未病、中醫藥社區干預奠定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對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街道常住居民進行糖尿病高危人群調查,由居委會工作人員根據納入標準進行初篩,然后由曹楊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通過體格檢查和相關生化檢查進一步篩查,最后確定糖尿病高危患者206例,入選者均有戶籍并居住1年以上,其中男性67例,女性139例,年齡36~89歲,平均(66.12±10.20)歲。
納入標準:根據2004年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CDS)代謝綜合征診斷標準[1],凡具備以下4個組成成份中的3項或全部者可診斷為代謝綜合征:①超重和(或)肥胖:體質指數(BMI)≥25.0 kg/m2。②高血糖:空腹血糖≥6.1 mmol/L和(或)負荷后2 h血糖≥7.8 mmol/ L,或已確診為糖尿病并治療者。③高血壓:收縮壓/舒張壓≥140/90 mmHg和(或)已確診為高血壓并治療者。④血脂紊亂:空腹血三酰甘油(TG)>1.7 mmol/L,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男性<0.9 mmol/L,女性<1.0 mmol/L。腹圍男性>90 cm,女性>85 cm。
排除標準:①繼發性肥胖如繼發于下丘腦、垂體炎癥、腫瘤、創傷、Cushing綜合征、性腺功能減退癥等;②繼發性高血壓如嗜鉻細胞瘤、腎性高血壓、腎素分泌瘤、醛固酮增多癥;③血脂異常是繼發于甲狀腺功能減退癥、腎病綜合征、膽道阻塞、口服避孕藥、胰腺炎等;④除外1型糖尿病、其他特殊類型糖尿病及妊娠期糖尿病、糖尿病伴有嚴重并發癥;⑤合并嚴重肝腎臟器病變或并發冠心病、腦卒中;⑥惡性腫瘤、肝炎及肺結核等傳染病、精神系統疾病患者;⑦合并風濕或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炎癥性疾病;⑧不能配合證候信息采集者或不同意參加本研究者。
1.2 方法
根據朱文鋒等[2]的“證素辨證”方法制定臨床觀察表,以各癥狀要素積分和閾值法確定證候及各個辨證要素的權重。辨證時,先分別將患者癥狀按提示的辨證要素進行累加,取超過100閾值的項目作為辨證診斷。當某一要素70≤貢獻度積分<100時,雖然該證素的診斷不能確立,但說明存在相應的病理變化。病理積分和分級判斷:當積分<70,歸為0級,為基本無該證素病理;70≤積分<100,歸為1級,為存在輕度病理變化;100≤積分<150,歸為2級,為存在中度病理變化;積分≥150,歸為3級,為存在嚴重病理變化。對納入患者進行證素辨證,根據證素>100閾值的標準,篩選出病位證素。
對所有患者進行人體測量,包括身高、體重、腰圍、計算BMI,并抽取空腹靜脈血測定空腹胰島素(FINS)和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PPAR)-γ水平,按模型評估法(HOMA)計算胰島素抵抗(IR)指數,即HOMA-IR=FPG×FINS/22.5。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AS 9.1.3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x± s表示,計數資料用均值(Q25, Q75)表示,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相關性。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表1 206例患者的基線證素分布

表2 三項指標與臟腑證素的相關性
2 結果
從表1可見,代謝綜合證基本證素為腎、肝和脾。
3 討論
代謝綜合征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密切相關,是由IR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和代謝紊亂。研究表明代謝綜合征患者患心血管病的風險增高3倍,患糖尿病風險增高5倍,心血管死亡率增高2倍[3]。
辨證論治是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證素辨證理論通過對辨證要素的提取,將復雜的證候系統分解為病位和病性的證候要素。本研究通過對納入病例進行證素辨證,根據證素>100閾值的標準,篩選出基本病位證素。本研究表明,代謝綜合征病位證素與脾、肝、腎有關,與文獻報道一致[4],脾的運化失常,肝失疏泄,腎失其正常主水液功能是代謝綜合征發生的基本病機,其中脾虛失運,痰濕內蘊是代謝綜合征的病機關鍵[5]。
IR是指正常劑量的胰島素產生低于正常生物學效應的一種狀態,表明胰島素作用的靶器官對胰島素作用的敏感性下降。有研究表明代謝綜合征中醫各證型存在不同程度IR的現象[6],代謝綜合征各中醫證型與IR密切相關[7],而氣陰兩虛者顯著高于痰濕瘀滯者和胃熱脾滯者[8]。
PPAR是一類由配體激活的轉錄因子,屬于核受體超家族成員,主要存在于脂肪組織,調節脂肪細胞分化,并促進脂質和能量儲存,與脂類代謝關系密切,與脂代謝紊亂相關性疾病緊密相關。PPAR-γ能不同程度的被脂肪酸及其衍生物激活,參與調節脂質水平。PPAR-γ調節、活性或表達的改變可能參與IR發生的分子機制[9]。
腹型肥胖構成了代謝綜合征的主要成分,邵繼紅等[10]報道BMI、腰圍、腰臀比與代謝綜合征關系密切,BMI和腰圍均可用于肥胖的判斷以及作為代謝綜合征診斷標準的組分。
綜上所述,IR、PPAR、BMI與中醫證素脾、肝、腎相關,可為臨床代謝綜合征中醫辨證提供一定參考。
致謝:本文數據的統計處理由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周宇豪完成,在此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代謝綜合征研究協作組. 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關于代謝綜合征的建議[J]. 中華糖尿病雜志, 2004, 12(3): 156-161.
[2] 朱文鋒. 證素辨證學[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8: 6.
[3] Eckle RH, Grundy SM, Zimmet PZ. The metabolic syndrome[J]. Lancet, 2005, 365(9468): 1415-1428.
[4] 孫曉波, 石巖, 連捷, 等. 近5年來中醫藥治療代謝綜合征研究進展[J]. 遼寧中醫雜志, 2014, 41(1): 179-181.
[5] 冀天威, 石巖, 楊宇峰. 從脾論治代謝綜合征[J]. 遼寧中醫雜志, 2012, 39(7): 1280-1281.
[6] 李樂愚, 梁振鐘, 朱曉華. 代謝綜合征胰島素抵抗與中醫證候辨證分型關系研究[J]. 實用心腦肺血管病雜志, 2008, 16(11): 13-14.
[7] 蘇潤澤, 麻莉, 董惠潔, 等. 代謝綜合征中醫證型與胰島素抵抗及腫瘤壞死因子-α、瘦素的相關性研究[J]. 遼寧中醫雜志, 2013, 40(8): 1517-1519.
[8] 王坤玲, 王魁亮, 郭軍. 代謝綜合征中醫證型與胰島素抵抗的關系[J]. 新疆中醫藥, 2006, 24(5): 25-28.
[9] 葉林秀, 徐焱成, 朱宜蓮. 核轉錄因子PPARs與代謝綜合征[J]. 國外醫學?遺傳學分冊, 2002, 25(4): 232-234.
[10] 邵繼紅, 沈霞, 潘林, 等. 不同體質指標在不同MS診斷標準中應用比較[J]. 中國公共衛生, 2009, 25(3): 261-262.
收稿日期:(2014-11-11)
作者簡介:**周一心,女,碩士,副主任醫師。研究方向:中西醫結合神經系統疾病研究。E-mail:hanxiang798007@163.com
文章編號:1006-1533(2015)10-0007-03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R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