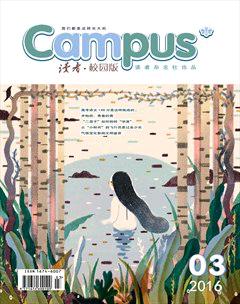等來草木青青的繁盛
彭君睿,土家族,“90后”專欄作家。
我7歲時離開村子里的小學堂轉學去了城里。
進入新學校的第一天,數學課上有點禿頭的老師點名要新同學背一遍乘法口訣表。我戰戰兢兢地站起來,倒是零失誤地背完了。接下來等待我的卻是全班同學的哄堂大笑,更有淘氣的男同學笑到用拍桌子來助興,我原本就憋紅的臉這下更紅了。
“咳,上課回答問題要用普通話的。”老師終于開了口。
“我們寨子小學堂的老師從來都不講普通話,我也不會講。”我的話音剛落,更大一波的哄笑聲襲來。
這就是我啟蒙階段的真實模樣,好在那個年紀里守住一點上進心就能護住那點脆弱的自尊,名次上靠前的幾位就能得到全部的快樂。之后便是很多個一個人認真學習的日夜,我從練習每一段課文的普通話的正確發音開始,從每一個陌生英文單詞的拼寫著力,對著一道雞兔同籠的奧數題下著那個年紀最誠懇的決心。
既然我的眼前是一塊大大的黑板,我的手邊是厚厚的課本,我的身邊是把《紅樓夢》講得跟童話故事一樣好聽的老師,那么我就學習吧。好好上學總是沒錯的吧。
在進入省重點高中之前,一路都很順利,靠態度能搞定的事情都不是難事。我在吊腳樓的木屋子里長大,堂屋里貼滿了大大小小被暴雨天漏進屋子里的雨水沖得發白的獎狀。如果說十幾歲之前的求學之路是一個家庭共同的大事,那么在我高中之后,這件大事唯一收尾的人便是我自己了。
高中之后面臨的是密密麻麻把每一天都撐得滿滿的試卷以及內心那股被班主任不斷撩撥起來的對大學生活的憧憬。我是想考所好學校的。從來沒有想象過這條路上會有岔子出現,還是我擺不平的。上高二身體開始變得不好,時常在教室聽見同學們沙沙沙地演算理科題目的晚自習課,我頭疼得快要跟所有夢想告饒。
我病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沒有服輸,每天在醫院和學校之間穿梭,在膠囊跟試題間不停地切換。我想,還是要跟著熟悉的同學一起進考場,還是希望早設想好的未來能如約而至。
但是沒辦法了,一定要先治病。
在休學之后將近一年的時間里,媽媽炒菜的油香味和藥渣味每天一起鉆入鼻腔,我也顧不得擔心會不會倒了旁人的胃口。
內心是消沉的,可還是不想讓父母心里太為難,我開始勻出更多的時間做些別的事情。看書、寫日記、賞夕陽,在那個還是高中生的年紀,很多苦難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個僥幸就繞開了。可我撞上了繞不開的,看起來敞開的、坦蕩的生活開始變得有阻礙,逼仄不已。
后來我學會了按時吃藥,好好睡覺,認真讀書,一筆一畫地做史鐵生每一本書的讀書筆記。
這樣的小孩肯定是能順利過關的。
一年后重返高中課堂,做題備考。爸媽為了減輕我的心理負擔,再三囑咐我身體最重要,考上專科學校也是好的,最后我考取了一所剛過一本線的熱門學校,在上海。親人們的喜出望外,倒像是這個結果是老天對一個大病初愈、急急忙忙考大學的孩子的眷顧,是求之不得的運氣,哪里還能討價還價呢?
我規規矩矩地去上了半年多時間的大學,在離下一次的高考還剩4個月的時間,拎著行李箱轉了轉陸家嘴就踏上了回老家的路途——我退學了。這是個不大輕松的決定,是不被理解、不被鼓勵、阻礙重重的一條路。
在高三課堂第一輪復習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重返周考、月考、模擬考連番轟炸的備考生活里,四個月的時間里我吞下了許多的非議跟不解,生硬地把很多那時候還不很懂的道理銘記在心,不去計較風險、不去焦慮失敗。
這一次,我又考到了上海,學校小有名氣,專業是自己退學時選好的。雖是不完美的結果,但依然算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整個中學時代的夢想。
在我年幼天真的時日里,放羊、種地、收糧食,這些重而煩瑣的事情都躲得遠遠的,從不與我糾纏。除了觀察嬉笑怒罵的活人,我還琢磨過嚴寒酷暑里始終撒著歡的牲口,看過雨水漫過田埂,盯過莊稼的長勢,送過一次又一次的花草枯榮。
回想過去在我身上留下的記憶,我曾無數次雙手縮在袖筒里,遠遠看著大人們裝滿自家的糧倉,看著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看著日落時分縈繞在村子上空的裊裊炊煙,我對這背后所隱匿的大自然的平衡與規律保有虔誠的敬畏。直到有一天,我學著爸爸媽媽在田地里春耕播種的樣子悄悄地在屋子旁松了一塊土,撒了兩行苞谷種,蓋上泥土,那個夏天它們竟然綠油油地長起來了。在對一切不可撼動的敬畏之中得到了讓我感到興趣盎然的東西,我讓一塊土地長出了玉米而不是雜草,我借著陽光雨露選擇了一種植物,我能改變這片大地上的局部長勢。這使我的勇氣隨著身體一起成長。
如今我走出了大山,結束了中學生活,跨入另一個嶄新的環境。依舊偏愛在清晨早起四處看看,這是整個大地最有希望的時刻,也是我在中學時代最難熬的一段時光里最愛思忖的時刻。
世界在日落時分最開闊,陽光在橫掃之時最沉重。那些攥緊拳頭、咬緊牙關、獨自拼搏的歲月是勵志格言跟窘迫現實無法講和的多幕劇場,于我而言這是一段深埋在記憶里勝過大肆抒懷的歲月。
剩下的人生,我會住舊一幢房屋,吃完很多碗米飯,吞下無數句怨言。席地而坐之處,皆是青草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