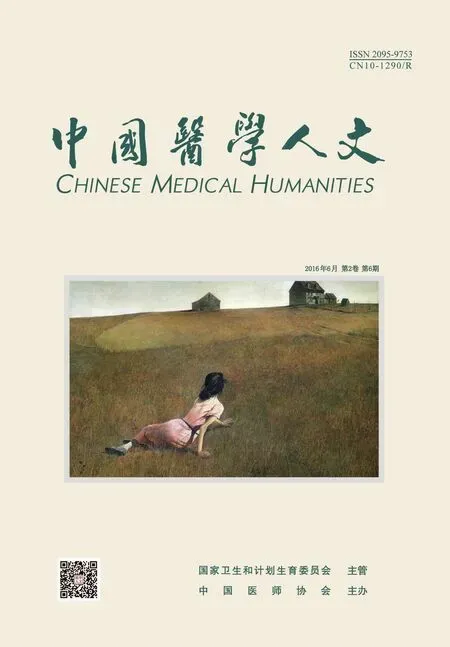小“親戚”
文/鄒 垚
?
小“親戚”
文/鄒 垚
這是一個來到我們這里僅僅50個小時的孩子,而我見到他也不過是幾面而已。他卻與我們都“沾親帶故”,有著不多卻是一絲絲的聯系。
白班快要下班了,值班醫生從產科打電話回來,說要收一個低血糖的孩子。這對于我們來說并不覺得會是一個危重的情況,做好前期準備就等著孩子被抱下來了。晚上7點,一個男娃娃被抱了下來,白白胖胖的。
怎么形容那個白色呢?蒼白?青白?反正不是粉白。那是一種透著不健康的白色,好似那皮膚之下隱藏著什么蠢蠢欲動的東西,在白熾燈的照射下蟄伏著,伺機而動。他全身的肌張力很高,胳膊僵硬地彎曲著,薄薄的兩片唇瓣緊緊地閉著,沒有特別的哭鬧,雙眼緊閉,好像在拒絕我們,拒絕看,拒絕表達。
在我交完班臨走的時候,聽到醫生說,“他的BE是-17.8……肯定是感染了……”第二天白天一睜眼,便看到朋友圈里同事說搶救了一宿,插管里都是血。具體情況我沒有細問,卻已開始擔心他的情況。
進入到這一個夜班,因為忙碌,在接班以后并沒有來得及去看看他,只聽得呼吸機高頻震蕩的聲音響徹整個房間,同時看到、聽到同事在不停地處理執行新的醫囑。
當我終于忙完手頭的工作以后,我進到了他所在的房間。他躺在開放輻射暖臺上,全身依舊青白,雙手被軟布“捆綁”固定在身體兩側,皺著眉頭,從插著插管的喉嚨里竭力試圖發出哭聲,表達自己的痛苦、不滿,證明生命體存活的信息。
過了沒多久,當我再次進到屋子看他的時候,插管里、嘴里、胃管里已經又開始出血了。暗紅的血液半凝狀態地掛在嘴邊,染紅了固定插管的白色膠布。高頻震蕩百分之百的氧濃度,卻也僅僅維持著七八十的氧飽和度。插著尿管,給了幾次速尿,卻仍舊只有不到五毫升的尿,在連接的注射器里停留著不見增多。血壓偏低,多巴胺泵入也沒有好轉,擴容、腎上腺素,無效,反復給予,無效。
一夜的忙碌和努力,換來的是生命極為勉強維持的狀態。下了班在休息室補覺,中午醒來便聽到了孩子離去的消息。雖說心有準備,但生命的消逝仍是令人難過。
當孩子剛來的時候,同事告訴我:他的媽媽是本院護士,也是我的學姐。這好像是一下子多了個“小親戚”似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便好像加重了他在我們心中的分量。我的同學和孩子媽媽在同一個科室,后來向我詢問孩子的情況,告訴我孩子媽媽好像不太知道孩子怎么樣了。當孩子逝去后,同學聽到消息表示很震驚。
聊天的過程當中,我越來越為我的學姐感到難過。曾經與孩子只是一面之緣的同學,曾經只是與孩子共同度過一輪班次的我們,在這個時刻都難過和遺憾,那與他共同生活整個孕期、辛苦生出他、愛他、見到他、還未享受母子情深便失去孩子的母親呢?我無法想象那是怎樣的痛苦,或者說我的想象在這樣的痛苦面前蒼白無力,就像那嬌小慘白的身軀一樣。
仍是一個夜班,同樣是足月兒,來的時候是同一種菌感染,有著類似的不好的臨床表現,剛剛忙碌完了搶救的準備和預防措施。結束了這篇文字,卻絕不希望這個孩子有著相同的結束。
努力仍在繼續,希望也是。
作者單位/北京協和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