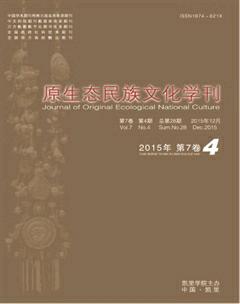主持人語:法律,民間與官方的二元敘事
一直以來,法律的敘事被國家所無可爭辯地領有。無論在西方世界影響甚大的分析實證法學的所謂“主權者命令說”,還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維辛斯基的“國家意志”或“統治階級意志論”,都把法律作為國家專有的外部裝飾和統治工具,從而法律不過是作為外在于人們生活日用的來自國家的必要強制。至于民間,則對于法律只能仆從和接受,而不能在任何意義上創生、支配、甚至解釋之,更不能自作主張,建立所謂脫離官方法的民間“法律秩序”。對法律的這種理解和界定,自然形成在法律敘事上的官方無限霸權和獨斷解釋。民間有關法律的需要也罷,有關自發交往中的秩序構造方式也罷,都沒有、也不可能被官方認真地納八考察視野。盡管人們的日常生活、交往行為以及秩序構造,未必一定亦步亦趨于官方法的約定,甚至在更多時候,民間秩序的構造,主要是民問自發規范作用的結果,可在理念上,這些實踐似乎無關緊要,人們寧可對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樣,法律就只能被定位于官方的安排,至于官方安排的規范是否符合民間需要,是否符合日常生活,是否對社會秩序的構造必然起到促進作用,而不是因為此種規則,反而破壞了既有的民間秩序,攪亂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論者們卻在所不問。
但是,人類秩序構建的實踐卻并非總是按照官方法律的秩序路線圖而亦步亦趨、循規蹈矩。反之,我們常見的人間交往秩序,即便與當下法律完全合轍或者并不反對,但其直接規范來源并不總是依照官方法,更多時候所依賴的乃是一個地方、一個族群、一個組織一直以來所奉行的民間規則。因此,把民間規則及其秩序功能納八社會治理——社會自治、公共互治和國家(政府)他治的范圍,是現代治理體系必須關注的話題。官方法的使命,不是刻意去改造民間規則,而讓其屈服于官方法的頤指氣使,毋寧說官方法必須回應民間規則的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升對民間規則的表達方式,即以更為正式的、或符合法言法語的方式,升華民間規則的表現方式,磨搓民間規則的區域差異,推廣民間規則的應用范圍……這才預示著官方法生成的合乎邏輯的進路,也預示著官方法的合法性——盡管即使如此,仍會不可避免地存在或新生完全異于官方法要求的規范及社會秩序。
這事實上引出了有關法律的兩種不同的視角或敘事方式,即法律的民問敘事和法律的官方敘事。法律的官方敘事前已述及,這里繼續就法律的民問敘事略加管陳。所謂法律的民問敘事,乃是指以民間立場來理解和認識法律,處理人們交往行為和規范秩序的思維視角。這一思維所垂注的問題大致可作如下二分:其一,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締造交往秩序的規則作為理解和認識法律的重要入口,從而尋找法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社會基礎;其二,以人們日常對官方法的態度和選擇為參照,發現民間視角的官方法究竟是什么。這兩個方面,如果借用埃利希的“活法”概念,不妨將其共同稱為民間“活的”法律思維或敘事。民間的法律敘事這一命題的提出,自然不是要否定官方法律敘事的價值,更不是否定在法治進程中官方法和法言法語對社會應有的,有時甚至是決定的作用,而是強調經由對民間法律敘事的認真對待,修正或改進官方法可能存在的形式機械、內容呆板、對社會生活的涵攝能力有限以及其不可避免地借用官方的權勢對社會帶來的壓制效果等。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法律的民間敘事,既有助于社會主體自治地參與、組織和維護臺法秩序,以資官方法的實踐因應;也有助于通過民間規則和民問需要而補充或矯正官方法可能存在的種種不足,實現民問與官方的法律溝通、秩序溝通和意義溝通。
本期刊出的3篇論文分別是謝暉的《法律的民問敘事(上)》、許娟的《傈僳族社會變遷中的非正式懲罰——以臘村為例》和麻勇恒、范生姣兩位作者的《神判與“村治”——基于貴州村共有資源開發利用權喪失的案例分析》。廣義說來,這3篇論文都以法律的民間敘事作為探討的基本方向。其中前者專門以《法律的民間敘事》為題,可以認為是作者對近些年民問法研究的范式進行總結的一種嘗試和努力。本期刊出是該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只能候明年擇機刊出。十多年來,作者雖然分別在《山東大學學報》、《甘肅政法學院學報》和《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主持了多個民間法、民族習慣法和法文化研究的欄目,但盡量堅持不刊發自己的文章,以便騰出版面,刊發更多同仁、特別是相關領域的青年學者的文章。此次應吳平教授邀約和催促,算是第二回破例,也可作為作者對其多年來關注的民間法這一領域相關問題的初步總結。另2篇論文更在實證視角詮釋了法律的民問敘事,開闊了讀者對法律的民問敘事之觀察視野。
[責任編輯: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