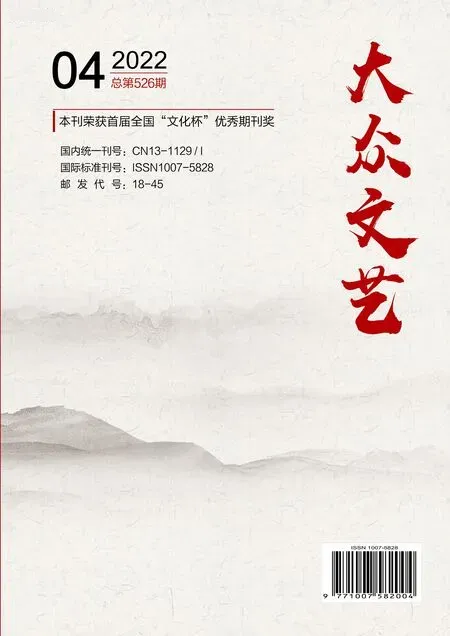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紅樓夢》的悲劇美學
夏翩翩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570228)
?
《紅樓夢》的悲劇美學
夏翩翩(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570228)
摘要:悲劇性是《紅樓夢》最突出的美學效果,它在“見—生—入—悟”四個階段的循環(huán)往復中,完成了美學上的悲劇效果。本文從文本細讀的角度來分析《紅樓夢》的悲劇過程,從而體悟曹雪芹筆下“萬境歸空”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美學境界。
關鍵詞:紅樓夢;悲劇性;儒;道;佛;美學境界
悲劇有一種攝人心魂的魄力。叔本華曾提出三種悲劇類型,王國維認為《紅樓夢》屬于第三種悲劇。它的悲劇非偶然因素,而是那幾乎無事的悲劇:馮淵對英蓮的一見鐘情卻奏響了他的死亡之曲;王熙鳳忌憚賈瑞便毒設相思局,使他命喪黃泉;尤三姐愛慕柳湘蓮,他卻僅憑流言蜚語拒絕婚事,最后落得一個揮劍自刎,一個冷入空門。
俞平伯在《紅樓夢簡論》中提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他強調了“色”與“空”的重要性,卻忽略了“情”,有失偏頗。其實“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是一個循環(huán)的過程,是不可分割的。起初人從萬物皆空看見世間萬態(tài),這是“見”;其次人在世間萬態(tài)中萌生了情,以此來維系世間萬態(tài)的和諧,這是“生”:再次人把情賦予世間萬態(tài),一切便都有了情,這是“入”:最后透過有情的世間萬態(tài)悟得萬物皆空,這便是“悟”。而這一空通過色的呈現和情的維系,得到空的飛躍。《紅樓夢》悲劇美學的最高境界是“空”,而要達到“空”的境界,必少不了“情”的維系。小說正是通過見-生-入-悟四個完整的過程的循環(huán)與歸元,它的悲劇美學才躍然于紙上。
一、見:從頑石到玉石
賈寶玉是女媧氏煉石補天多出的頑石,在天上,他被造物主女媧氏拋棄,聽說紅塵中的榮華富貴,便乞求一僧一道攜他去瞧瞧。劉再復曾說:“這是他經歷的第一番‘空’,有了這次空,才想到人間來見色—女媧用五色土構造的色世界。這一經歷便是‘因空見色’。”后來通過冷子興與賈雨村的閑談,作者道明了頑石的歸宿:天上的頑石到人間變成玉石后,與賈寶玉合二為一,并記錄下了他的紅塵往事。再看賈寶玉,他是美玉的化身,又是曹雪芹理想的寄托,主要體現為第一,容貌的絕美。他“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曉之花”,有如傾城佳人。第二,行動的叛逆。長到七八歲便說起了孩子話:“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第三,思想的乖僻。對于情感,他更傾心于木石前盟;對于人生,他不走經濟仕途之路,把官吏譏為祿蠹;對于世俗觀念,他不僅顛覆了男尊女卑的理念,還以身踐行,但最終還是被末世湮沒。
因此,從頑石到通靈寶玉,一個天上,一個人間;一個無才補天,一個不容于世;一個凡心蠢動,一個偏僻乖張;一個出世,一個入世;一個因空,一個見色。
二、生:從木石前盟到金玉良姻
王國維曾說《紅樓夢》“壯美多于優(yōu)美”,這里的壯美指各種悲劇美的總稱。而小說的壯美則最集中地體現在從木石前盟到金玉良姻的演變過程中。林黛玉的前身是絳珠仙草,賈寶玉則是神瑛侍者,木石前盟的湮沒是小說最為悲戚的毀滅,由寶黛的三世情緣逐步完成。
小說開篇講述了林黛玉與賈寶玉的第一世情緣。他們一個是神仙,一個是仙草,因灌溉之情結緣。后來絳珠草脫換成絳珠仙子,對神瑛侍者郁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此為第二世情緣。正是這段情緣,才有了還淚之說的第三世情緣。有了前世姻緣的牽引,他們自然心息相通。不想薛寶釵出現了,但黛玉要的是與寶玉惺惺相惜的“情”,寶釵要的是芳齡永繼的“姻”。寶黛的超脫世俗的愛情不為家族、社會、時代所容,相反,寶釵的合理之情才得到眾人的擁護。初發(fā)美好的木石前盟,成了賈寶玉夢中的追求,而金玉良姻卻成了禁錮他的枷鎖。
從木石前盟的主動萌發(fā)到金玉良姻的被動接受,賈寶玉在這兩種感情的轉變中,由色生情,以大悲劇收場:黛玉淚盡而逝,寶玉空自悲戚,寶釵獨守空閨。曹雪芹想讓這塊無才補天的頑石來末世補情,但他失敗了,因為封建的末世容納不了心心相惜的愛情。
三、入;從夢魘到無夢
《紅樓夢》中專寫夢的地方很多,有詩意的夢,也有讓人措手不及的噩夢。據統(tǒng)計,全本小說大大小小的夢總共有三十二處。無論是太虛幻境還是人間的大觀園,都可以納入曹雪芹的大夢之中。“到頭一夢,萬境歸空”是經歷了一番人情世故后,了悟了色,抵達空的大夢。而大夢由眾多小夢構成。所謂“傳情入色”,便是入夢,在大大小小的夢中,人世的聚散離合紛呈上演。
甄士隱是小說中第一個登場的人物,他一生經歷了骨肉分離、家離子散,最后遁入空門。曹雪芹利用甄士隱的小夢,同樣隱射了大夢。小說最后一夢,也暗示了大夢的結束。小說以甄士隱的夢為開端,復以賈雨村的夢為結尾。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是很重要的一個夢。正是在夢里,他了解了林黛玉、薛寶釵、賈元春、賈探春、史湘云、妙玉等金陵女子的悲劇命運。
《紅樓夢》的夢是沉重的,然而無夢的悲劇才最可怕。夢的結束,就是悲劇的結束。黛玉淚盡而逝之后,寶玉沒有見到她最后一面,想在夢里找尋她,卻再無夢了。在賈府分崩離析之后,該去的去了,該離的離了,最后連做夢的寄托也沒有了。正是這無夢的凄涼,為寶黛的愛情悲劇收了場,也完成了傳情入色。
四、悟:到頭一夢,萬境歸空
荷爾德林說人類應該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曹雪芹寄希望于書中人物,想要為他找到生生死死的現實生活之上的詩意棲居的“空”,經歷了世俗生活里的食、睡、愛的綿延不息,超脫生與死的困境,走向澄明之境,詩意地棲居在人世間。
《紅樓夢》中的主人公賈寶玉與林黛玉有世俗的一面,也有超脫志趣的一面。在大觀園里,他們結詩社、作詩詞、猜燈謎,一起談禪悟道,便有了《葬花吟》的千古絕唱,有了《芙蓉女兒誄》的哀婉悼念,也有了“無立足境,是方干靜”的了悟。世俗的生活被他們過得有滋有味,這不正是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嗎?
但是這種詩意棲居的大夢在封建末世是曇花一現的,魯迅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在《紅樓夢》這部“悲劇中的悲劇”里,父權、皇權、族權像無形的利爪,扼殺了每一個自由的靈魂。曹雪芹建造的臨時天堂——大觀園,為眾兒女提供了短暫的詩意棲居,然而,當繡春囊事件一出現,那些四面而來的利爪便乘機拽住了欲(玉)的把柄,賈府這個顯赫百年的大族,一層一層地被褪去浮華的表層,最后剩下一顆空心。
曹雪芹以儒理,窺視著世態(tài)炎涼、人情冷暖;以佛眼,勘破了世間繁華、過眼云煙;又以道心超越了俗世糾紛、生生死死。《紅樓夢》全書彌漫在悲涼之霧之中,在一個又一個美好生命被淹沒之后,我們看到了生的無奈,還有死的超脫。這便是了悟了生死之后,歷經了“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悲劇體驗,抵達了“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最高悲劇境界。《紅樓夢》的美是詩意的,又是毀滅的,“見—生—入—悟”既是詩意美的始發(fā)因子,也是悲劇美的誕生結果。在這個完整的循環(huán)過程中,《紅樓夢》完成了它在美學上的悲劇效果。
參考文獻:
[1]王國維.紅樓夢評論[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2]劉再復.紅樓夢哲學筆記[M].中信出版社,2010.
[3](清)曹雪芹.紅樓夢[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夏翩翩,碩士研究生,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專業(yè):文藝學,研究方向:性別詩學。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