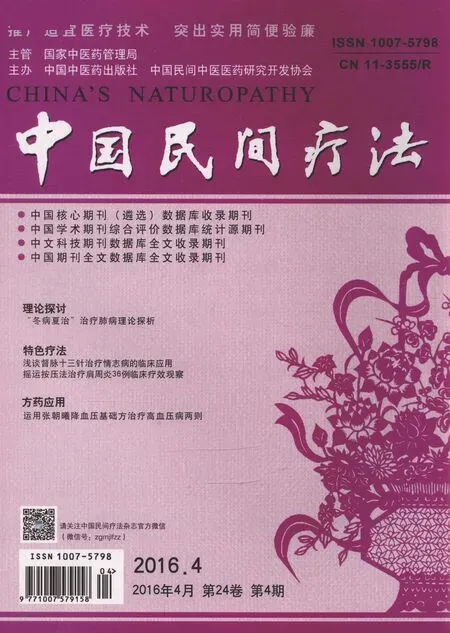淺談督脈十三針治療情志病的臨床應用
閆松濤
(北京朝陽國醫之家中醫醫院,北京 100015)
?
淺談督脈十三針治療情志病的臨床應用
閆松濤
(北京朝陽國醫之家中醫醫院,北京 100015)
“督脈十三針”是已故金針大師王樂亭教授在臨床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針法。它具有疏通督脈、調和陰陽、補腦益髓、鎮驚安神的功效。筆者在臨床治療焦慮抑郁癥、失眠、癲癇等情志疾病中應用“督脈十三針”的刺法,取得較為理想的治療效果,還能減少西藥帶來的不良反應和依賴性,提高生活質量。但目前“督脈十三針”的臨床應用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局限性。現將“督脈十三針”治療情志病的體會介紹如下,以供廣大同仁參考。
情志病的病因病機
現代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工作壓力、生活節奏、飲食習慣的改變,導致了大量情志疾病的發生。情志即“七情”,指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變化,是機體的精神狀態。七情是人體對客觀事物的不同反映,正常情況下是不會致病的。但若長期經受精神刺激或突然受到劇烈的神經創傷,超出正常人體生理活動所能調節的范疇,則會導致氣機逆亂不暢,臟腑經絡氣血陰陽失調,由此引起的疾病稱為情志病[1]。宋代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指出:“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郁發,外形于肢體。”“夫五臟六腑……情動則亂,故有喜怒憂思悲恐驚,七者不同,各隨其本臟所生所傷而為病。”即七情內傷,直接影響相應的內臟,臟腑氣機逆亂,氣血失調,導致各種病變的發生。
心主血藏神;肝藏血主疏泄;脾主運化而位于中焦,是氣機升降的樞紐,又為氣血生化之源。故情志所傷的病證,以心、肝、脾和氣血失調為多見[2]。如心神失養或邪擾心神所致不寐;憂思郁怒,肝郁氣結所致郁證;脾虛失運,痰涎上擾,或痰火相搏,蒙蔽清竅所致癲狂。
“督脈十三針”治療情志病的理論依據
“督脈十三針”是王樂亭教授本著“精簡、實用、穩效”的原則,在督脈28個穴位中精選了百會、風府、大椎、陶道、身柱、神道、至陽、筋縮、脊中、懸樞、命門、腰陽關、長強13個穴位,共同組成“督脈十三針”。這套針法于1958年初正式確立。臨床適應證包括腦和脊髓病變或損傷引起的各種癱瘓;神經官能癥、抑郁癥、更年期綜合征;癲癇、角弓反張;脊柱強痛、腰背酸痛、風寒濕痹。
《素問·骨空論》闡述了督脈的循行:“督脈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后,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后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系兩目之下中央。”從督脈循行路線可以發現,手足三陽經會于大椎穴,陽維脈會于啞門,督脈是手足三陽七脈之會,故督脈為“陽脈之海”,具有調節和振奮人體陽氣的作用。中醫學認為腦為元神之府,主神明,與人的精神、意識、思維、運動功能有關。腦為諸陽之首,“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竅”[3]。而督脈“上額交巔,上入絡腦”,故督脈與腦關系最為密切。《靈樞·口問》說:“心者,五臟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說明心與各種情志刺激有關,心神受損可涉及其他臟腑。而督脈“上貫心”,對于情志活動有重要的調節作用。《素問·五臟生成論》提及“諸髓者皆屬于腦”,腦為髓之海,髓為腎生,督脈“通髓貫脊”,溝通了大腦與脊髓的聯系。督脈“絡腎入腦貫心”,如果督脈經氣發生錯亂,則可發生多種情志疾病。由此可見,針刺“督脈十三針”可起到補腦益髓、鎮驚安神、醒神開竅的功效。
“督脈十三針”刺法
1.穴位定位:正確定位是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治療效果,在臨床定位過程中充分利用體表骨性標志來確定和檢查穴位位置,如第7頸椎棘突、肩胛岡、肩胛骨下角、髂嵴。
2.針具:最好采用0.35 mm×40 mm的不銹鋼針。太細的針具容易彎針,且穿透性不夠。
3.針刺深度:百會穴為仰刺,深度為1~2分;風府穴進針深度0.5~1寸;大椎至腰陽關各穴進針深度為1~1.5寸,以毫針剛刺透棘間韌帶為佳;長強可進針1.5~3寸,以患者在毫針刺入后不自主喊“啊”為佳。
4.針刺順序:從針刺百會開始向下至長強。
5.補瀉手法:采用捻轉補瀉手法,順督脈循行方向,向右捻,大指向前,食指向后為補法[4]。反之為瀉法。
典型病例
例1.患者,男,64歲。初診時間:2015年5月21日。主訴:不能入眠2周。患者失眠十余年,每因情緒影響而發作,服用舒樂安定后即可正常睡眠。2周前因家庭矛盾再次失眠,白天夜晚均無睡意,整日不能入睡,服用舒樂安定后仍無效,遂前來我院欲中醫治療。刻下癥:神疲乏力,胸悶,心煩易怒,整日不能入睡,咽干,納差,大便不成形,小便可,舌紅苔白,脈沉滑。既往史:高血壓、高脂血癥,2014年因心肌梗死行心臟支架手術。西醫診斷:頑固性失眠。中醫辨證:心脾兩虛、肝郁氣滯。治法:養心健脾、疏肝解郁。針灸處方:督脈十三針。隔日1次,每次30 min,補法。患者初診時不欲中藥治療,只想針灸治療。針灸3次后已可1 h內入睡,針灸8次后已可在半小時內入睡,睡眠基本恢復正常,結束治療。1月后隨訪未反復。
例2.患者,女,57歲。初診時間:2014年4月22日。主訴:抑郁癥五年余。患者因丈夫5年前去世,心情一直郁悶不舒,2年前獨女結婚后抑郁加重,終日悶悶不樂,性格孤僻,不愿與人交談,對事物無興趣,煩躁易激動,時時欲哭,女兒女婿探望時情緒極易失控。醫院診斷為抑郁癥,長期服用帕羅西汀,癥狀可得到一定改善,但停藥后癥狀反復,再服帕羅西汀效果不顯著,欲中醫治療而前來就診。刻下癥:精神呆滯,面色晦暗,善太息,乏力,失眠,與醫生交流中因情緒波動而落淚,二便正常,舌紅苔白,脈沉細。既往體健。西醫診斷:抑郁癥。中醫辨證:肝郁脾虛證。治法:疏肝健脾。方藥予以甘麥大棗湯合柴胡疏肝散加減:浮小麥45 g,大棗10 g,甘草10 g,柴胡10 g,郁金10 g,白芍10 g,青皮10 g,陳皮10 g,香附10 g,烏藥10 g,炒棗仁30 g,遠志10 g,菖蒲10 g,牡丹皮10 g,羚羊角粉1.2 g。水煎服,7劑,每日2次。針灸處方:督脈十三針。隔日1次,每次30 min,補法。患者每次就診和治療筆者均要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而方藥則隨癥加減。二診時病情有所緩解,五診時已可由女兒女婿陪同前來,諸癥明顯改善。經過2個月治療,患者女兒反映她母親的情緒在向積極方面改變,睡眠基本正常,可以和女兒女婿平和的交流,并參加了社區的老年合唱團。為了鞏固療效,囑患者繼續治療1個月,于2014年7月底結束治療。1月后隨訪未反復。數月后偶遇該患者,見其精神飽滿,已無懨懨之狀。
例3.患者,女,55歲。初診時間:2014年7月7日。主訴:小腦萎縮伴癲癇發作三十余年。患者家屬告之該患者三十余年前患腦炎,因醫院誤治而影響治療,后出現走路不穩、肢體搖擺、語言不清、智力減退,各種癥狀進行性加重,并經常出現癲癇小發作。刻下癥:神情呆滯,對外界刺激無反應,共濟失調步態,震顫,語言障礙,智力低下,體胖,下肢無力麻木,進診室時需母親攙扶,每一步都要其母以自己的腳推動患者的腳前行。為控制癲癇發作,長期服用苯妥英鈉,但每日癲癇仍發作5次以上,每次持續數分鐘可自行緩解。二便正常,舌紅苔白厚有齒痕,脈沉。西醫診斷:小腦萎縮,癲癇。中醫辨證:脾腎兩虛、痰迷心竅。治法:健脾益腎、化痰開竅。針灸處方:督脈十三針。隔日1次,每次30 min,補法。治療時本欲針藥結合,但患者拒藥,只能施以針灸治療。最初針灸過程中患者不能配合,需3人全力按于針灸床方可操作。治療1個月后其父母反映患者走路較前有力。3個月后每日癲癇發作次數降到了3次左右。患者在針灸時躁動減輕,2人已可輕松應對。患者父母自行給患者停服苯妥英鈉,患者癲癇發作反復,每日5次左右。恢復服用苯妥英鈉并繼續針灸后,每日癲癇發作再次降到3次左右。針刺6個月后癲癇發作逐漸降到每日1~2次,可以在母親攙扶下自己緩慢行走(仍是共濟失調步態),在其父訓斥時可以用哭來表達情緒。但因其父母均已近80歲,已無力堅持長期帶其前來針灸而停止治療。2月后電話隨訪其病情已退步至治療前的水平,甚是可惜!
總結
失眠、焦慮抑郁癥、躁狂癥、癲癇疾病具有治療見效緩慢、容易復發的特點,尤其是在西醫臨床中藥物不良反應和嚴重依賴性是難以克服的。而中醫對于情志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悠久歷史,“督脈十三針”自王樂亭教授創立以來已有近60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無論是王樂亭教授,還是本人的恩師鈕韻鐸教授,或是其他金針前輩同仁都積累了許多使用“督脈十三針”的臨床經驗。在吸取前輩寶貴經驗的基礎上,筆者在臨床實踐中大量應用“督脈十三針”治療包括情志病在內的各種疾病,深刻體會到這套針法對于情志病治療不僅在臨床上可取得較好療效,更可使患者減少或擺脫因長期服用西藥所帶來的藥物不良反應和依賴性,提高其生活質量。作為較成熟的一套治療方法,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督脈十三針”的功效以及將“督脈十三針”與中藥更好地結合運用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摸索實踐。
參考文獻
[1]段盈竹,魏紅.論情志病[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17(5):193-195.
[2]印會河.中醫基礎理論[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98.
[3]鈕雪松.金針大師——王樂亭[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297.
[4]鈕韻鐸.金針再傳——跟師王樂亭臨證隨筆及經驗選穴[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4:203.
(收稿日期2015-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