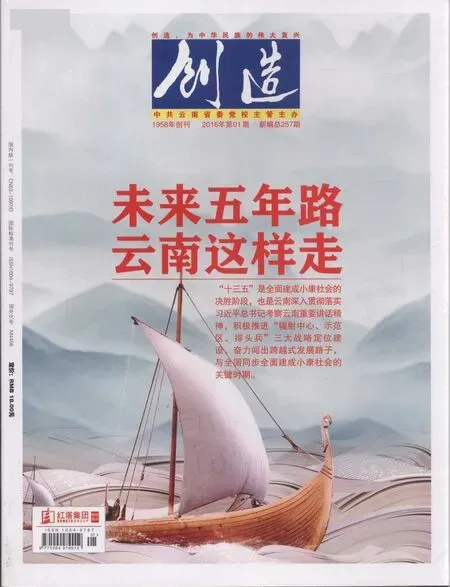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治理——傳統文化助推中國式治理探微
文/魏崇輝 王聰會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治理——傳統文化助推中國式治理探微
文/魏崇輝 王聰會
中國式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須立足于我國的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展開。
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過分強調各種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倡導權力多元化但有著過度削弱國家主權和主權政府權威的風險。盡管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它也不可能代替國家和市場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還有“治理失效”的可能。中國式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須立足于我國的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展開。
一、為何要轉向治理:現代“治理”的緣起與適用
1989年世界銀行概括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此后“治理”便廣泛地被應用于政治發展的研究中,成為一個流行詞。治理一詞的適用范圍很廣,可用于社會、公司、政府等各種組織或團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重大決定》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被首次提上新一輪的改革日程,受到廣泛關注。從全球發展來看,治理是當今社會謀求發展的趨勢,基于我國目前社會現狀,治理確實為我國社會轉型階段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
“治理”一詞提出后,很多學者對其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理論層面上對治理這一概念的界定各有不同。英國學者羅伯特·羅茨曾經從不同的視角給予治理以不同的內涵:作為最小國家的管理活動的治理,指的是國家削減開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作為善治的治理,指的是強調效率、法治、責任的公共服務體系;作為社會控制體系的治理,指的是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作為自治網絡的治理,指的是建立在信任與互利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絡。全球治理委員會發布的《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報告對“治理”作出了較為權威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基本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
質言之,我們所探討的“治理”,是要創造一種新的方式或者是說秩序,從政府權力獨掌到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合作,社會多元主體協同合作;從權力集中到權威弱化、權力分散,使得責任共擔。“治理是一種內涵更豐富的現象。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隨著治理范圍的擴大,各色人等和各類組織得以借助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并實現各自的愿望。”治理是相較于以往行政模式的進步,是基于民主平等的基本內涵,尋求更好地實現公共利益的運行機制。這一機制中,通過多元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能夠更加有效地表達各方訴求,為公共利益的實現保駕護航,同時也是在更好地實現政治生活中的“善”和“正義”。一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政治學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但是,不僅僅我國提出治理所面臨的當前社會現狀與西方國家大不相同,同時,中西方對于對“正義”的理解也存有差異。中國人理解“正義”需要顧及“人的全部與整體”。因此,如果要適用治理于中國社會,必須考察中國傳統文化在治理中的生存空間。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治理中的生存空間:基于禮治的精英治理為例
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進程中創造了豐富的治理文化,這些治理文化以自身特有的結構形式出現,奠定了當下塑造中國式治理的基礎。長期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傳統文化隱含著人與人之間以至整個社會運行中處理問題的規則、理念、秩序乃至人們遵循的信仰。傳統文化在中國獨特的生存狀態成為了當代中國治理的重要因子,也將繼續影響未來中國的治理文化與治理結構、治理秩序。一方面,傳統的治理模式可為我國當前創新治理提供原始基礎和啟示借鑒;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包含的包容和諧等理念是現代治理過程中所需的重要理念支撐。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中的這些生存空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同時也是我們向前邁進探索新道路可資利用的重要資源。固然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革,文化也要求緊跟時代符合改革潮流,尤其是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被不斷批判以致不再有以往的獨尊地位,但長期以來的傳統文化并沒有被完全割裂。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中,傳統文化并沒有整體衰亡,它以碎片化的形態分散于社會生活中,在社會自治領域中,其所包含的人際準則、家庭和宗教文化等習俗在城鄉都生存了下來,并以零散的方式鑲嵌在社會自治體系中,與法治治理體系等形成一個相互支撐的關系,在法律所不及的地方,傳統文化仍然是調整人們關系、處理社會問題的重要力量。
具體而言,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禮是社會公認合適的行為規范。合于禮就是說這些行為規范是做得對的,合適的意思。如果單從行為規范一點來說,本和法律無異,法律也是行為規范。禮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維系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而禮卻不需要這樣有形的權力機構,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在當今農村偏遠地區,很多問題的解決方法基本上都是習慣習俗爭端以溫和方式加以解決,降低了處理糾紛的成本。凡是在中國本土經驗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都能為我們所接受,而且能夠開花結果,因而本土經驗非常重要。禮治是長期以來基層治理的本土經驗,現代化治理過程中應對這樣的社會自治做出積極回應。禮治為治理提供了一種規則規范,有助于搭建一種公眾認同的治理秩序。
中國文化的語境下,禮治起了重要作用。而禮治發揮重要的基本渠道是精英治理。基層鄉土社會中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文化精英長期以來影響與引導基層的治理手段與治理結構。此處的所謂“精英”更多指稱的是一種或多種資源的占用者。當前,基層社會中這種精英治理依然存在并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鄰里家族之間出現糾紛時通常會找這些有威望的人出面調解;涉及整個村莊集體利益的問題也會在這些人的帶領引導下共商對策。這實際上體現出一種社會結構力量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農村治理運行過程中的外在表現。它和現代化治理并不違背,相反,精英治理方式為現代化治理提供了范式基礎。可以在這種人們普遍認同的治理方式的基礎上加以引導,降低治理的成本,減少了引入治理機制的阻力。基層精英作為傳統社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載體如何在當代多元參與型治理中傳承與發展,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類似于鄉紳這樣的治理角色,也值得探索,集聚在城市的社會精英退休后回鄉或者到社區,將是很寶貴的現代治理資源。如今農村居民自治中仍有這樣的傳統,一方面,治理規范和原則方面,在不觸碰法律底線的范圍內,人們習慣于以傳統的“禮”為規范和標準解決爭端;另一方面,治理結構方面,一個村莊中年長名望高的人或是資源占有量大的人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治理過程中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鄉土社會中“禮治”和“卡里斯瑪”型精英治理普遍存在。另外,在城市或者城郊發達的農村地區,傳統文化中的習俗碎片依然鑲嵌在人們身上,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人們處理問題的選擇依然是以常理常識作為行為準則。
三、傳統文化助推中國式治理的可能著力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傳統文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傳統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同樣地,治理方式也無法復制。在西方范式和中國經驗的緊張關系之間,如何建成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是一個重要問題。西方國家的治理理論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傳統文化助推中國式治理的可能路徑。
首先,從傳統文化出發,樹立文化自信,以“中國話語”構建治理體系。依托傳統文化,從現實出發,構建一個共同的“中國話語”,將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民間治理傳統及其表達方式與現代治理結合起來,給予其合法身份和地位,發揮其應有作用。傳統文化的主要價值在于其所具有的解釋能力,它可以填補法律之外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空缺部分,給人們一種“合理”向“善”的價值解釋。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核是一套價值系統,其中需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位于傳統和當代語境的關節點上,需要為中國的政治選擇和治理體系設計及提供理論闡釋和價值基礎,以“中國話語”吸納治理中的傳統文化。
其次,基于禮治的精英治理是我國長期傳統文化中保留并延續下來的治理手段,挖掘傳統文化中類似的可資利用的資源,加強其與現代治理模式構建的契合,是我們所面對的重要問題。中國文明在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一度遭受普遍懷疑和嚴重抨擊。但是,歷史證明中華文明有極強的兼容包容能力和強大的生命力。歷史證明但凡反叛過去數典忘祖,一味地要推倒重來的行為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當下塑造中國式治理也是如此。任何外來治理資源只有與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社會轉型、全球化、信息網絡化迅猛發展的當下,實現傳統資源、本土經驗和民間習俗等等治理資源的現代轉型,是形塑基于傳統文化的中國式治理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