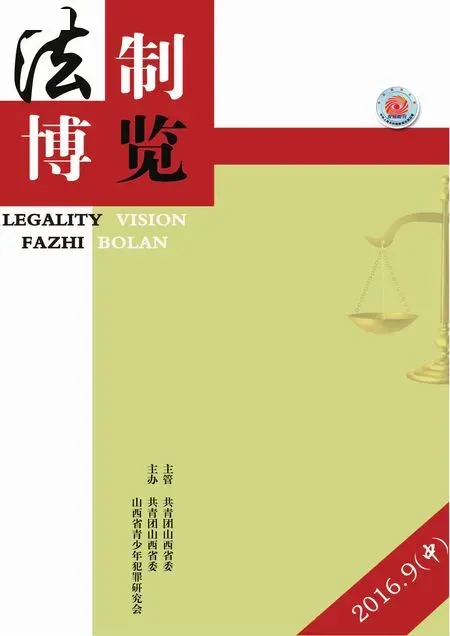從高級法的變遷看西方法治的發生與發展
陳旭仰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 200063
?
從高級法的變遷看西方法治的發生與發展
陳旭仰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200063
高級法的變遷體現了西方法治發生與發展的規律。在中世紀,高級法的作用是限制權力,法治生發于教權與王權的競爭。而資產階級革命高舉了天賦人權的旗幟,將權利保護納入了法治的范圍。最終,民主立法觀念代替了高級法觀念,維系著法治的發展。西方法治發展從限制權力出發,達至權力與權利的協調。
高級法;限制權力;西方法治的發生與發展
現代西方法治是如何發生的?回答這一問題的目的,不僅在于澄清歷史史實,更要總結出西方法治的發生與發展規律,為我國法治提供借鑒。長期以來,對于法治的發展規律存在著一種爭議,法治究竟是起源于對權力的限制,抑或是對權利的保護?通過回顧中世紀以來西方漫長的法治發生史,探明法治萌芽于對權力的限制,可以得知:在西方法治生成的初期,將權力納入法治的軌道是主旋律,至于權利的保護則應當位居次席,然而法治發展的長期目標則是以權利保護為目的。
一、中世紀高級法的作用是限制權力
(一)高級法協調了教權與王權的關系
在西方中世紀,高級法是與《圣經》、教會的教義、《國法大全》等結合在一起的。將《圣經》作為高級法限制主權者權力的經典案例,是主教貝克特與亨利二世的并行管轄權之爭。貝克特援引《圣經·那鴻書》中“上帝不對同一罪行處罰兩次”的條文,否定亨利二世《克拉倫登憲章》第三條“犯有重罪的教士須由教會法院審判,若確認有罪,須送回王室法院判處”的效力。兩人的沖突引致貝克特遇刺。伯爾曼指出:“貝克特是為這樣一個原則而死的,即王室的司法管轄權不能不受限制,而且世俗權威不能自行決定其應有的界限。”[1]該原則包含了主權者應受高級法制約的思想。所謂的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并非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而是防止本只受輕罰的教士在世俗法院受到重罰,進一步維護教會對于某些宗教事務的管轄權。
在中世紀,與限制世俗王權相對應的是對教權的限制,通過若干個世紀,由地方宗教會議、全基督教宗教會議、一些主教所頒布的教規、格里高利改革的教令以及羅馬國法大全經格拉提安整理為《歧異教規之協調》,由此教會開始了漸漸轉變為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教會內部教皇與樞機主教、主教與教士會的橫向權力劃分,教皇和主教、主教與教區教士之間的橫向權力劃分,以及世俗政治體對教會管轄權的限制,構成了復雜的權力制約關系。教會內部培育出了某種依法而治的東西。[2]教會內部的權力劃分以與權利保護并無關系。
(二)《大憲章》是貴族階層與王權斗爭的產物
離開教會與王權的斗爭,轉向英國直至今日還保持著權威、被視為英國法治之源的《大憲章》。眾所周知,在《大憲章》第二十九條“凡自由民……不得被剝奪其自由權……”中的“凡自由民”,在當時所指的都是貴族階層。在英國,法治在最初的含義上并沒有與普遍的自由結合起來;但是由于《大憲章》及普通法所具有的向前發展能力,通過對于“自由民”的不斷重新闡釋,最終使其與現代的普遍自由觀念相契合。[3]盡管,《大憲章》是一種實證法,但是其具有不同于普通法律的崇高地位,被視為英國的高級法。但是,《大憲章》所指向的仍然是獨斷專行的王權。
二、資產階級革命將權利保護納入了法治的范疇
在中世紀的西歐,法治的含義主要集中在限制權力。那么,權利保護與法治的結合究竟在何時發生?這與英、法兩國資產階級革命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一)保護個人權利是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成果
在法國,《拿破侖法典》反映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兩條戒律:物的戒律,即所有權不受侵犯;以及個人戒律,即人人都應照管自己的事情。在英國,經歷了都鐸王朝的絕對專制之后,資產階級經過斗爭獲得了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在法律實踐中則具體表現為:臭名昭著的星室法庭和高級調查團等君權法庭被廢除,普通法法官、普通法律師發展出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陪審團審理制度的正式確立以及對傳聞證據的否定。
(二)高級法觀念聯接了權利保護與法治
必須指出,權利保護與法治的耦合是由高級法的概念帶來的。《拿破侖法典》的起草者聲稱他們繼承了萬民法中的自然理性——契約自由和所有權自由——觀念,他們從以下學者那里汲取了高級法的意識:多瑪在《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所建立的以自然法為依據的資產階級法律原則,以及孟德斯鳩所贊美的貿易背后所蘊含的精神,即勤儉、節約、節制、勞動、智慧、寧靜、法律和秩序。[4]而在英國思想源流應歸于福蒂丘斯、柯克、洛克這三位學者,他們都極力倡導高級法思想,如柯克大法官在博納姆案中提出的“議會法令有悖與共同權利和理性,普通法將對其予以審查并裁定該法令無效”的附論。美國憲法也由此發源,其司法審查理念即來源于博納姆案,加之柯克對《大憲章》的推崇,以及法律之下的議會至上觀念,三者一起構成了作為美國憲法的重要歷史淵源。
三、限制權力與保護權利的結合標志著民主立法取代了高級法觀念
中世紀的法治著力于對權力的限制,這是法治發展的萌芽階段。到了近代,以保護個人自由為核心的高級法觀念出現,并且進一步在實證法之中得到體現。在現代,限制權力與保護權利進一步結合起來,不再依靠無法得到確證的高級法來說明權利,而是以民主立法來保障個人權利。
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權利要能夠生效和實施,只有通過那些做出對集體有約束力的決定的組織。反過來說,這些決定的集體約束力,又來源于它們所具有的法律形式。”[5]一方面,公民權利不可能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得到實現,但另一方面,政治力量應當受到法律的調節,以確保各種決策不至于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政治力量受到法律限制的最重要的形式在于民主立法。而民主立法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私權利,其產生方式又在于公民行使政治權利。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都落實在法律文件中,不再需要以高級法來加以論證。
由此,現代國家既具備了應有的行動能力,而能夠在實現政治目標的同時充分尊重人的獨立與自主。在確保權力運轉的同時,強調對于權力的限制以保護權利,不再從虛無縹緲的高級法層面出發去探討法治,轉而從民主立法中尋求正當性。
四、結語
從西方高級法的變遷史可以發現,中世紀對權力的限制是法治發生的邏輯起點。進一步的,高級法觀念與個人權利相結合,成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最終高級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法治的正當性轉換到民主立法之上,以此達成權力與權利的平衡。這一歷史變遷啟示我們,法治發展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必須準確把握時代的脈搏,認清當下法治的主要目標,以取得較完滿的法治成就。
[1][2][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312-325+250-259.
[3][美]愛德華·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M]強世功譯.北京:三聯書社,1996:27.
[4][美]泰格 利維.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M].紀琨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14.
[5][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童世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165.
D62
A
2095-4379-(2016)26-0166-02
陳旭仰(1990-),男,上海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2014級法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