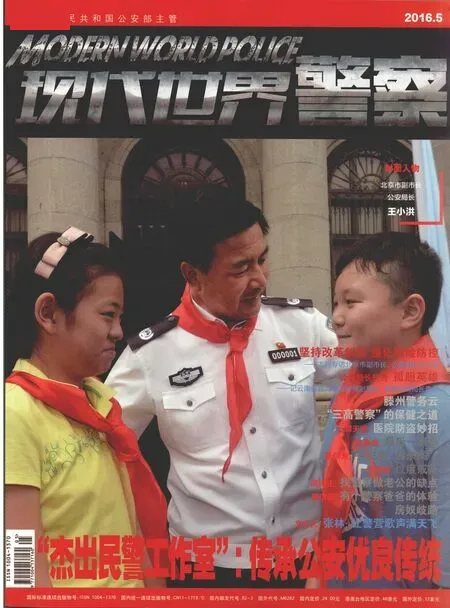生的思考
文/ 張寧
生的思考
文/ 張寧
長(zhǎng)久以來,學(xué)習(xí)東西方不同的文明,腦子里總有一個(gè)揮之不去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在早期西方文明中人們關(guān)心的問題極為細(xì)微,細(xì)微到生活中人與人交往的各種瑣事,而我們?nèi)A夏的先民與哲人卻把目光投射在了浩瀚無邊的宇宙天地?孰優(yōu)孰劣恐怕無法一言以定論,然而對(duì)這種反差進(jìn)行一番比較,或可發(fā)現(xiàn)些許深長(zhǎng)之意味。
“文明”的主題似乎太大了,一篇短文實(shí)在無從下筆,我們就從三部法典說起吧——《哥爾琴法典》《十二表法》和《法經(jīng)》。
1863年至1884年間,一部《哥爾琴法典》在近四千年前古希臘文明誕生之地克里特島被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容相當(dāng)完備,涉及家庭婚姻、養(yǎng)子、奴隸、擔(dān)保、財(cái)產(chǎn)、贈(zèng)予、抵押、訴訟等70條法律規(guī)定。這部法典是公元前5世紀(jì)由古希臘的阿提卡地區(qū)立法者創(chuàng)制的。幾乎在同一時(shí)期,也就是公元前450年,在平民的強(qiáng)烈要求下,改組后的羅馬共和國(guó)十人委員會(huì)在法律十表的基礎(chǔ)上新增兩表,正式頒布《十二表法》。這是羅馬第一部成文法,共105條,涉及土地占有、債務(wù)、家庭、繼承和訴訟等諸多方面的法規(guī),非常詳細(xì)具體。
此時(shí)的東方法律界發(fā)生了什么呢?戰(zhàn)國(guó)初期,魏國(guó)的李悝著成《法經(jīng)》。其原文早已散失,但在其他文獻(xiàn)中可了解其大致內(nèi)容。如《晉書·刑法志》指出,《法經(jīng)》由《盜》《賊》《囚》《捕》《雜律》《具律》六篇組成,且開宗名義道,“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盜”“賊”并不是現(xiàn)代漢語意義上的盜賊。“盜”是指危害統(tǒng)治者財(cái)產(chǎn)的行為,“賊”是指危害統(tǒng)治者政權(quán)和人身安全的行為。顯然,《法經(jīng)》是“王政”的產(chǎn)物,其鋒芒所指乃廣大勞動(dòng)人民。《法經(jīng)》并非個(gè)案,稍晚一點(diǎn)的“商鞅變法”具有更加鮮明的統(tǒng)治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色彩,因其廣為人知在此不贅述。這一點(diǎn),與《哥爾琴法典》和《十二表法》有著相當(dāng)大的區(qū)別。
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xiāng)”,《哥爾琴法典》從內(nèi)容上也不難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現(xiàn)實(shí)需求,盡管這里的民眾還不能包括奴隸,而它也只是當(dāng)時(shí)眾多古希臘城邦成文法典的一個(gè)代表。《十二表法》本就是在平民的反復(fù)斗爭(zhēng)中誕生的,其制定最早發(fā)端于平民保民官特蘭梯留在民眾大會(huì)上的提議,此后的一系列法案更使平民具有了擔(dān)任執(zhí)政官和其他高級(jí)官職的權(quán)利,平民會(huì)議則成了具有完全立法權(quán)的機(jī)構(gòu)。由此不難看出,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民眾包括時(shí)代的精英關(guān)注的都是非常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財(cái)產(chǎn)、人身關(guān)系等私權(quán)和利益,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和自由,表現(xiàn)出鮮明的契約精神,這些都是“人”的問題。
那么公元前5世紀(jì)前后,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先人們?cè)谒^上層建筑領(lǐng)域關(guān)注的是什么呢?這個(gè)問題其實(shí)很好回答。公元前5世紀(jì)其實(shí)是中國(guó)的“第一個(gè)大黃金時(shí)代”,柏楊先生在《中國(guó)人史綱》中稱這個(gè)世紀(jì)“思想學(xué)術(shù)界呈現(xiàn)出百花怒放的奇觀”,世襲貴族千余年對(duì)知識(shí)的壟斷瓦解了,平民階級(jí),包括奴隸,都可以獲得各種知識(shí)和技能,于是“中華人的思想學(xué)術(shù),進(jìn)入空前的輝煌時(shí)代”。看看諸子,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們所關(guān)注的恰恰是與“人”的問題相對(duì)的“天”的問題,以及“王”“圣”之道,是形上之思和宏大敘事。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合一。”孔子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說:“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yīng)之以治則吉,應(yīng)之以亂則兇。”墨子說,“兼愛”“非攻”,“義人在上,天下必治”。李悝和商鞅的主張更是王圣之道的一種具體闡釋,即君主如何統(tǒng)治國(guó)家。
概括起來說,盡管都是關(guān)乎“生的思考”,但在這個(gè)問題上,東西方文化的明顯區(qū)別就是:一個(gè)抬頭看天,一個(gè)低頭走路。“天”,既包括頭頂?shù)暮泼S钪妗⑷f物的運(yùn)行法則,也包括高高在上的圣和王如何統(tǒng)御世界;“路”,則是邁開腿就要遇到的問題,關(guān)乎人如何才能更好地生存。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差別,用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簡(jiǎn)單分析,無非是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然而,有些問題一旦具體化又似乎不那么簡(jiǎn)單。諸如,單從法律文本上看,《十二表法》對(duì)平民權(quán)利的肯定,顯然比李悝和商鞅維護(hù)專制的法律更具積極和進(jìn)步意義,可問題是當(dāng)時(shí)的羅馬尚處奴隸社會(huì),而戰(zhàn)國(guó)魏已經(jīng)進(jìn)入了封建時(shí)代,更不用說后來統(tǒng)一天下的秦帝國(guó)了。
誠(chéng)然,同樣的問題又有不一樣的觀察角度。如果閉上法律之眼,僅從哲學(xué)角度看,是我們關(guān)于“天”“圣”“王”的想法高了一點(diǎn)點(diǎn),還是他們關(guān)于“人”的思考實(shí)際了一點(diǎn)點(diǎn)呢?更為重要的是,兩種文化所泛起的漣漪似乎依然震蕩著今天的時(sh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