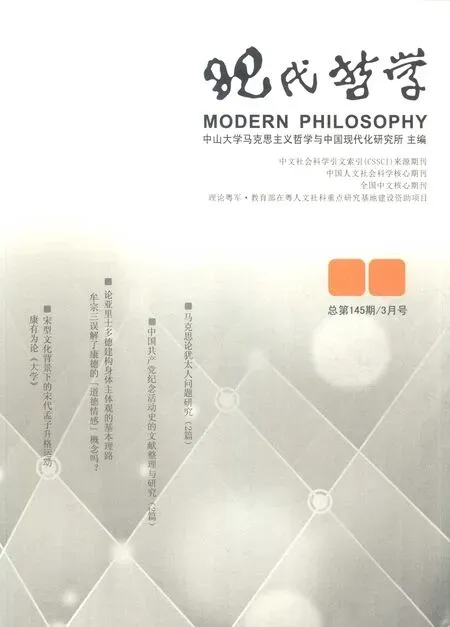喬姆斯基方案的笛卡爾貢獻*
劉小濤
?
喬姆斯基方案的笛卡爾貢獻*
劉小濤**
【摘要】笛卡爾究竟為喬姆斯基語言研究方案作出了何種貢獻?這個問題對于喬姆斯基語言哲學研究和理性主義思想史研究有重要意義。著眼于歷史和學理兩個方面,本文從麥吉利夫雷提供的答案入手討論,致力于論證兩個觀點:(1)否定性的論點:語言的創造性算不上是喬姆斯基方案的笛卡爾貢獻;(2)肯定性的論點:喬姆斯基方案真正的笛卡爾貢獻是一種理智化的解釋人類認知能力(特別是語言能力)的思路。
【關鍵詞】語言能力;語言知識;理智主義;笛卡爾;喬姆斯基
一
自《笛卡爾語言學》(1966)出版以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喬姆斯基稱自己的語言研究綱領是“理性主義的(rationalistic)”;甚至,按照詹姆士·麥吉利夫雷(James McGilvray)的判斷,喬姆斯基晚些時候的“生物語言學”旗號也不過是“笛卡爾語言學”的“升級”而已*James McGilvray,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Edition, inCartesian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以歷史的眼光看,不管是就語言研究這一特殊領域來說,還是就一般性的哲學傾向而言,喬姆斯基都已成為二十世紀理性主義發展史的重要環節。眾多理性主義哲學家里,笛卡爾或許是影響喬姆斯基最深的一位。因此,出于語言哲學研究的動機(特別是如何評價喬姆斯基方案對語言能力和語言知識作出的解釋),抑或出于哲學史或語言學探究的興趣,笛卡爾究竟在哪些方面影響了喬姆斯基都是一個有點意思的問題。
討論這個問題,需要預先作出一個限制。
一方面,喬姆斯基強調當代語言研究(指生成語法研究)有其現代理性主義哲學的根源,或者說,它跟一種特定的心靈理論有關聯。更明確地說,他指的是當代語言研究和現代理性主義哲學都特別重視語言的創造性特征,后者曾是促使笛卡爾發展一種區別于機械論的心靈哲學的重要原因。*按照笛卡爾的意見,動物(以及機器)的行為都可以按照機械論的方式給出解釋,然而,因為人有心靈,人類的行為(包括語言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根據機械論的方式來解釋。正因此,《笛卡爾語言學》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語言的創造性,喬姆斯基將發現語言這一特征對于語言研究的重要性歸功于笛卡爾;*喬姆斯基在多種著述里闡發了笛卡爾式的理性主義觀念對語言研究和心靈研究的重要性,比如《笛卡爾語言學》(1966)、《語言與心靈》(1968)、《語言知識:它的本質,來源,與使用》(1986),等等。就語言和心靈研究之關系而言,這些文獻的核心理念非常一致;不過,根據麥吉利夫雷的意見:“《笛卡爾語言學》比任何喬姆斯基的其它著述都更關注語言的創造性這一事實,并就它對心靈科學和行為解釋的重要性做了探究。”(James McGilvray,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Edition, inCartesian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在他的語言哲學著述里,在提到“理性主義”的語言研究時,喬姆斯基想著的也往往是笛卡爾,其它理性主義者的相關理念常常起了佐證或強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哲學文獻里,“Cartesian”這一語詞標記的觀念常常并不單單來自笛卡爾,有些觀念甚至與笛卡爾本人的想法相抵牾。比如,賴爾就特別聲明過,他要攻擊的笛卡爾神話(或者說“官方理論”)并不僅僅是來自笛卡爾的理論(《心的概念》,第19頁)。確實,無論是“Cartesian Linguistics”這一書名,還是它的副標題——“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都意味著喬姆斯基討論的范圍不限于笛卡爾。實際上,喬氏在赫爾德(J.G.Herder)、施萊格爾(A.W.Schlegel)、洪堡特(W.von Humboldt)等人那里都找到了同“語言的創造性”相聯系的觀念,并且收獲了其它一些概念資源,比如洪堡特所說的“語言形式(form of language)”。
“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一樣)這個詞可以容納繁雜的東西,要作出準確而不貧乏的討論過于困難。這里,我打算讓自己的目標更有節制些,僅僅關心喬姆斯基方案的笛卡爾貢獻(Descartes’s contribution),換言之,不以笛卡爾作為理性主義的代表來探究喬姆斯基方案中的“笛卡爾式的貢獻(Cartesian contribution)”。
接下來,我們先分析麥吉利夫雷提供的一種答案;然后,著眼于歷史和學理兩個方面,我要嘗試論證兩個核心觀點:(1)否定性的論點:語言的創造性算不上是喬姆斯基方案的笛卡爾貢獻;(2)肯定性的論點:喬姆斯基方案真正的笛卡爾貢獻是一種理智化的解釋人類認知能力的思路。
二
以上述基本問題為導向,如果在笛卡爾和喬姆斯基之間作個比較的話,根據他們之間一般哲學傾向的差異,可以獲得一些否定性的判斷,即笛卡爾哲學中的哪些內容并沒有對喬姆斯基構成實質性影響。有些論題易于識別,比如:(1)不是笛卡爾式的心身二元論。因為喬姆斯基從來沒有假定一個不依賴于身體的心靈(笛卡爾式的心靈跟一個自然化的語言理論方案天然地不相容)。(2)不是笛卡爾式的以普遍懷疑為特征的方法論。喬姆斯基從沒有懷疑過某些語言經驗的真實性,反而一門心思要給語言經驗提供充分描述和解釋。語言習得的刺激貧乏和語言的創造性特征,如果它們是真實的語言現象的話,都不過是經驗觀察。(3)不是笛卡爾式的基礎主義知識論。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并不是以笛卡爾式的方式從某個第一原則通過演繹逐步建立起來的,因為笛卡爾的知識論和其心靈哲學之間的關聯,我們也可以合理地懷疑,喬姆斯基式的天賦語言知識是否能夠承擔笛卡爾式的辯護功能。(4)不是笛卡爾式的天賦觀念論。典型的笛卡爾式天賦觀念是諸如“上帝”、“三角形”之類的東西。作為一個社會政治領域里的左翼精神領袖,上帝的觀念在喬姆斯基的理論里沒有任何位置;而生成語法的原則(喬姆斯基確實認為它們是天賦的)跟“三角形”之類的觀念有著方方面面的差異。一個顯然的差異是,笛卡爾式的天賦觀念是意識可及(accessible)的,而喬姆斯基式的語法規則是一種“隱知識(unconscious knowledge);進而,它們的認識論作用也因此有重要差異。
這些判斷的某些方面仍然讓人心存疑慮。拿喬姆斯基的語言知識論來說。因為假定語法規則有天賦來源(普遍語法的原則和參數),這些天賦的語法規則是人們獲得語言能力的基礎,并且在解釋和描述人的語言行為中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按照喬姆斯基的意思,它們要能為說話者的特定語言表達式提供結構描述(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以確定表達式的語音和語義解釋。在這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它們具有一種近似于“基礎”的知識論地位。然而,因為笛卡爾式的天賦觀念是意識可及(accessible)的(或者用Zenon Pylyshyn的術語說,是“認知可穿透的(cognitive penetrable)”),而喬姆斯基式的語法規則是一種“隱知識(unconscious knowledge; tacit knowledge)”,這使得說話者和語言學家獲得這些知識(以及語言知識系統)的方式都不可能是笛卡爾式的演繹。
這些否定性的判斷,或許都還有些討論的空間。不過,即便這樣,它們仍然能刺激人進一步思考,究竟笛卡爾在哪些方面影響了喬姆斯基,進而影響了當代的語言研究?
就我們對文獻的了解,這個問題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根據阿彌陀佛·達斯·古普塔(Amitabha Das Gupta)的判斷,喬姆斯基主要受惠于笛卡爾的兩個觀點:“首先,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媒介;其次,存在天賦觀念。根據喬姆斯基的解釋,這兩個論題對于語言研究都有深遠的意義。第一個論題解釋語言的創造性,喬姆斯基將它刻畫為語言學中的笛卡爾問題;第二個是一個認識論論題,喬姆斯基利用它來解釋說話者的語言知識的本性。”*Das Gupta, “Descartes and Chomsky: An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Mind”, inIndianPhilosophicalQuarterly, Vol. XXVI No.1, 1999, pp.125-147.
在《笛卡爾語言學》(第三版;2009年)的《序言》里,詹姆士·麥吉利夫雷表達了同樣的探究興趣,并且也給出了一個正面答案。按照他的意見,笛卡爾對于語言科學以及喬姆斯基方案的貢獻是間接的,并且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1)笛卡爾促進了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建立,包括運用形式方法(主要是數學)研究自然現象、為待解釋的現象建立操控實驗、建立理想化模型、追求描述和解釋的充分性,等等。(2)語言的創造性,主要因為笛卡爾在《談談方法》(第五部分)里指出的人和動物、自動機的兩個根本區別:其一,人能創造性地使用語言;其二,人依靠理性行事,這樣一種能力可以適合于一切場合。(3)一個計算主義的心靈理論;特別是開啟了一種計算主義的視覺理論。*James McGilvray,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Edition, inCartesianLinguistics, pp. 36-48.
古普塔的判斷有諸多可爭辯之處。詹姆士·麥吉利夫雷的答案經過喬姆斯基本人審定*Ibid., p.6.,它值得我們嚴肅對待。
三
從態度上講,麥吉利夫雷對于喬姆斯基的工作極其贊賞,他甚至稱《笛卡爾語言學》是“前無古人,迄今無匹的一項關于語言創造性以及產生語言的心靈的本質的語言-哲學研究”*Ibid., p.1.。同樣作為理論工作者,他對于喬姆斯基方案也抱有十足的信心,換言之,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喬姆斯基追隨者;當然,是根據他詮釋后的喬姆斯基(以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天賦論、內部論等為特征)。
有可能,喬姆斯基會對麥吉利夫雷解說的某些判斷不以為然。比如后者強烈的自然主義論調,“要將人類語言和概念帶到自然主義研究的領域之外,這是一種非理性的執著”*Ibid., p.23.;實際上,喬姆斯基堅持方法論的自然主義,但對形而上學自然主義有自覺的抵制。以及麥吉利夫雷對理性的解釋——“我們認知能力的運用”*Ibid., p.34.;喬姆斯基的“理性”概念跟笛卡爾的“理性”概念有非常近的親緣關系,至少,就根據理性解釋理智行動這一點而言。然而,麥吉利夫雷的“理性”概念無論如何都不同于笛卡爾式的“理性”概念,因為笛卡爾承認動物的認知能力,但不會認為動物也有理性。
考慮到喬姆斯基方案引起的眾多非議*除了學術觀點上的爭議外,我特別注意到,有些學者——他們曾是喬姆斯基的同事并且是早期生成語法研究的重要成員——曾批評喬姆斯基犯有某些學術不端,比如,有意欺騙(在明知道論點錯誤的情況下,仍然選擇發表自己的論文);采納了別人的成果但不注明出處,等等。甚至,他們嚴厲地指責喬姆斯基“漠視、蔑視真理;鄙視探究的標準;持續、無恥地自我推銷和拔高;顯然的不融貫;以及對異見者口誅筆伐的癖好”。(cf. Robert D. Levine & Paul M. Postal, “A Corrupted Linguistics”, inTheAnti-ChomskyReader, Lanham, Md.: Encounter Books, 2004, p. 204.),一種批判性的眼光對于獲得更客觀的評價就非常必要;對于麥吉利夫雷的評論,我們同樣需要一種批判性的眼光。相比于他對喬姆斯基語言科學方案的說明,麥吉利夫雷對喬姆斯基的笛卡爾影響的說明顯得不那么讓人信服。有許多理由讓人懷疑上述判斷的基調是否準確,以及上述三個方面是否切中要害。
首先,喬姆斯基稱自己是一個理性主義者,“笛卡爾語言學”的旗號更是直接紋上了笛卡爾的名頭,這看起來總意味著某些比“間接影響”更重要的東西。其次,就麥吉利夫雷所說的三個方面而言:第一,沒有理由認為喬姆斯基是等到閱讀笛卡爾的著作時才領會到現代意義的科學方法。誠然,笛卡爾為現代科學方法做出了貢獻,但是,就像說亞里士多德因為其邏輯研究而間接地影響了當代任何一個學者,說笛卡爾對現代科學方法的貢獻間接地影響了喬姆斯基這實在過于貧乏。第二,認知科學的許多爭議使得我們尚不清楚戴維·馬爾(David Marr)式的計算主義視覺理論會不會是視覺理論的正確方向。即便是的話,說笛卡爾預示或開啟了這一正確方向,并因此預示了一種計算主義的心靈理論,從而至少間接地影響了喬姆斯基對待心靈的態度,這個推斷的每一步都非常可疑。第三,關于語言的創造性特征,問題因為幾個原因顯得稍微復雜些。一個原因是,語言向來不是笛卡爾關心的直接主題,即便在其著述的某幾個段落里論及語言,也僅僅寥寥數語,而且是服務于別的目的;對這些相對簡單的論述,看起來可以發展出多種不同的解讀。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還并不真正清楚笛卡爾、語言的創造性、以及喬姆斯基的語言學方案之間真實的關聯是怎樣的。這兩方面都需要作更深入的討論。
四
以下是《談談方法》中那個因喬姆斯基而更為出名的段落:
如果有那么一些機器,其部件的外形跟猴子或某種無理性動物一模一樣……我們還是有兩條非常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判明它們并不因此就是真正的人。第一條是:它們決不能像我們這樣使用語詞,或者使用其他由語言構成的訊號,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思想。因為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臺機器,構造得能夠吐出幾個字來,甚至能夠吐出某些字來回答我們扳動它的某些部件的身體動作,例如在某處一按它就說出我們要它說的要求,在另一處一按它就喊疼之類,可是它決不能把這些字排成別的樣式適當地回答人家向它說的意思,而這是最愚蠢的人都能辦到的。第二條是:這些機器雖然可以做許多事情,做得跟我們每個人一樣好,甚至更好,卻決不能做別的事情。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它們的活動所依靠的并不是知識,而只是它們的部件結構;因為理性是萬能的工具,可以用于一切場合……依靠這兩條標準我們還可以認識人跟禽獸的區別。因為我們不能不密切注意到:人不管多么魯鈍、多么愚笨,連白癡也不例外,總能把不同的字眼排在一起編成一些話,用來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思想;可是其它的動物相反,不管多么完滿,多么得天獨厚,全都不能這樣做。*[法]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44—45頁。
喬姆斯基在談及語言的創造性的時候,常常直接或間接地引用笛卡爾的這段論述,特別是其中加了著重號的文字(著重號是我加的)。在《笛卡爾語言學》一書里,喬姆斯基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語言的創造性;并且,很明確地講,他用“語言的創造性方面”這個短語指的是“(日常的語言使用)沒有范圍限制和不受刺激決定的性質”*Noam Chomsky,Cartesian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0.。正是根據這些論述,麥吉利夫雷將語言的創造性概括為三個特征:(1)非決定性:指的是語言行為并不是由環境因素以因果的方式決定的;(2)無限性或創新性:指人們能說出的語句的數量(以及長度)特別大,且不受制于既有知識或環境;(3)恰當性:指在各種環境里,人們總能作出恰當的言語反應。*James McGilvray,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Edition, inCartesianLinguistics, pp. 41-44.
我本人不太能從笛卡爾的評論里讀出喬姆斯基所理解的“語言的創造性”,也不太認為笛卡爾心里想著的是喬姆斯基意義上的“創新性”;尤其是考慮到,有些時候,喬姆斯基用“語言的創造性”指的是人們能理解或生產以前沒有聽到過的無限數量的語句(甚至潛在無窮長的語句)的能力,笛卡爾的評論里完全沒有提及這一點。自然,語言行為的非刺激決定性和應對環境的恰當性都是笛卡爾的評論里包含了的東西。但是,這兩個特征都并非語言所獨有,毋寧說,它是一切人類理智行動都體現了的特征。對笛卡爾來說,使得人類的行動體現這兩個特征的原因在于人有心靈和理性(它們都可以普遍地應用于一切場合),而不是因為有語言,言語行為不過是人類智能行為的一種類型罷了。
喬姆斯基關于語言創造性的討論依賴于他從笛卡爾的評論里引出的一個重要判斷——“(語言)是一項特有的人類能力,它不依賴于智能”*Noam Chomsky,CartesianLinguistics, p.59.。自然,語言能力對于一般智能的獨立性是獲得語言機能假設(language faculty hypothesis)的一個重要基礎,然而,將“語言能力不依賴于智能”的判斷歸屬給笛卡爾,這特別可疑。雖然笛卡爾提示說,即便一個愚拙(dullest)的人,也能將語詞組織成語句來表達思想,但是,這個理由并不能推出語言能力是一項不依賴于一般智能的能力。首先,沒有特別有力的理由認為,笛卡爾在心靈的理性能力之外還假定了一種作為語言行為基礎的語言能力;根據喬納森·雷(Jonathan Rée)的解讀,笛卡爾反對那種認為心靈由多種不可還原的心智能力(如感覺、理智、意志、記憶、想象等)構成的多元主義,并認為所有的心智操作都可以還原為思想(thinking)。*Jonathan Rée,Descartes, Allen Lane, 1974, p.92.其次,如果假定在具備智能的人和不具備智能的人之間存在嚴格且明晰的分界,那么,從文獻上看,笛卡爾所說的愚拙的人或者白癡應當落入于“具備智能的人”這一概念之下而不是相反。再次,喬姆斯基們曾區分了語言能力的兩種意義——實際使用語言的能力以及一般性的理解和生產語言表達式的能力;*喬姆斯基有時候分別稱它們為一階能力和二階能力。以完全同樣的運思,我們也可以區分理智能力的兩種意義——智能的實踐運用和一般性的運用智能進行理智活動的能力。關于語言能力的哲學思考(為語言能力提供解釋)并不關心如何把話說得風趣幽默;關于一般智能的哲學思考也不關心如何運用理智能力來發現自然或人類社會的某些真相。在區分智能和智能的實際運用之后,一個很顯然的觀察是,要獲得語言能力不依賴于一般智能的結論,必須要證明一個缺乏智能的人也能表現出語言能力;一個具有語言能力的愚拙的人卻不能作為恰當的例證,因為他雖然在智能的實際運用上糟糕些,但他并不缺乏智能。
如果不過度解釋的話,看起來,笛卡爾說的不過是,我們不可能設想有一臺如此復雜的機器,它在任何環境里都能像人一樣好地作出恰當的言語反應,而這歸根結底是因為機器不具備理性能力,或者說沒有心靈。對笛卡爾而言,這自然意味著,要解釋人類的語言行為,我們需要引入心靈(笛卡爾式的);純粹機械論的解釋是行不通的,它只能解釋我們身體的動作。但是,笛卡爾的評論絕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假定一個人類獨有的語言機能(模塊化的)來解釋語言行為(我們知道,笛卡爾的心靈是不可分的,而且其唯一的本質就是思想),甚至,如果要用某種方式來刻畫語言機能的話,它就需要一種能進行遞歸構造的結構。
在喬姆斯基賦予了語言的創造性以特別的重要性之后,圍繞這個議題,產生了一些有趣的討論。比如,瑪格麗特·德拉克(Margaret Drach)指出,喬姆斯基第一次在論文里引入“語言的創造性”的時候,指的是“產生和理解以前從未聽到過的語句的能力”*Margaret Drach, “The Creative Aspects of Chomsky’s Use of the Notion of Creativity”, inThePhilosophicalReview, XC, No.1, 1981, p.49.。特別有意思的是,瑪格麗特·德拉克發現:如果考慮到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語言行為之區分的話,那么,喬姆斯基眾多討論語言創造性的論述并沒有一種前后清晰一致的用法;有時候,文獻上的依據讓我們認為語言的創造性在于語言的使用,有時候,他的論述又試圖告訴我們,語言的創造性指的是語言能力*Ibid., pp.44-65.。對于當前目的而言,瑪格麗特·德拉克的重要教誨在于,從笛卡爾的評論,怎么樣也不能說他是在討論“產生和理解以前從未聽到過的語句的能力”;自然,笛卡爾也不會有類似喬姆斯基似的麻煩,即究竟創造性是語言能力的內在性質,還是語言使用中體現出來的特征。我本人也留意到,《笛卡爾語言學》初版于1966年,據麥吉利夫雷云,此書的早期形式完成于1964年。然而,在喬姆斯基1966年的另一篇論文里,當喬姆斯基為語言的創造性援引學術史資源的時候,他確實只講到了洪堡特和葉斯泊森*[美]喬姆斯基:《喬姆斯基語言哲學文選》,徐烈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頁。。
既然從笛卡爾的評論看不出喬姆斯基所描繪的語言的創造性特征,而且,喬姆斯基首次使用“語言的創造性”這個短語時也沒有特別強的笛卡爾關聯,這些理由就極有可能表明,語言的創造性以及這一特征在喬姆斯基理論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都是喬姆斯基自己勾勒出來的,盡管他在笛卡爾那里找到了些模糊的影子。然而,這還夠不上說是笛卡爾為喬姆斯基語言方案所作的貢獻;要說有的話,也只是為“笛卡爾語言學”的旗號提供了一個可依附扳援之處。確實,笛卡爾和喬姆斯基都認定語言是人類這一物種獨有的東西。然而,雖然笛卡爾強調了語言的某些特異方面(笛卡爾也許不會反對用“創造性”來概括這些方面),不過,很顯然的是,區別于笛卡爾,喬姆斯基訴諸完全不同的理論術語和運作機制來解釋這一現象。就解釋語言的創造性這一現象而言,笛卡爾的運思并沒有對喬姆斯基方案產生特別實質性的影響(雖然他們都意識到語言現象對于解釋心靈的重要性)。我想,這些理由已足夠讓我們懷疑,對于喬姆斯基方案,語言的創造性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笛卡爾貢獻。
五
雖然語言的創造性經過官方認定,但仔細想來會發現它有些似是而非之處,那么,較之語言的創造性(以及麥吉利夫雷所說的其它兩方面),對于喬姆斯基的語言研究方案而言,是不是還有別的更稱得上是笛卡爾貢獻的東西呢?
對這個問題,我以為,有另一個值得考慮的替選答案:一種理智化的解釋人類認知能力的思路,即我們可以通過闡明具有某種認知能力的人的特定領域的知識,來表征(或刻畫)人的特定認知能力。對于喬姆斯基而言,這里所說的特定的認知能力和特定領域的知識就分別是語言能力和語言知識。顯然,這一思路體現了一種更一般性的看待心靈的態度,以及心靈和行動之間關聯的方式(更準確地說,可以根據行動者的知識來解釋其智能行動);依據喬姆斯基的方案,我們應該把生成語法看作是一個生成機制,它根據特定的刺激輸入產生特定的語言行為輸出,因此,輔以必要的補充(特別是可以通過說明機制來說明行為這一運思),認知能力的理智化解釋思路也就是行為的理智化解釋思路。按照我的判斷,對于喬姆斯基的語言研究方案,這才是特別重要的笛卡爾貢獻;意識到這一點,容易獲得一種發現奧秘的喜悅,當然,心理體驗還不能為這一發現的確切性辯護。
因為缺少像麥吉利夫雷般可以依賴的文本依據,我的意見,看起來像是一個心理的或者學理上的假設。它的優點是不太好證偽,它的缺點是不太好證實。不過,我希望,至少能給出些說得過去的理由。
提出這一假設的消極理由在于:一方面,我一直不太能理解喬姆斯基語言研究方案和笛卡爾之間的真正關聯;特別是,當意識到笛卡爾式的心身二元論,天賦觀念論,以及他對待經驗和理性的方式都并沒有在喬姆斯基身上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時候(任何認真想過這問題的人都應該會同意我的判斷),我的困惑就變得愈加強烈。另一方面,我們不太滿意于已有的解釋;如果以麥吉利夫雷的解釋為典型代表的話,我想我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從正面講,提出這一假說主要基于以下考慮。
首先,在對“能力(capacity)”這個概念作分類和解釋的時候,喬姆斯基斷言:“能夠做某事和知道如何做某事是有區別的;特別是,知道如何做某事包含重要的理智成分”*Noam Chomsky,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喬姆斯基援引了喬納森·雷關于笛卡爾的評論,“(Jonathan Rée)敏銳地注意到笛卡爾那更寬泛的思想(thinking)概念的后果,笛卡爾提出了‘這一特別重要的論題:人類的行動和知覺比它們看起來要更理智些,因為它們總是包含了思想,觀念或心靈;并且因此它們是奠基于這樣一些結構,這些結構跟柏拉圖式理論所稱作的理智知識并無不同’”*Ibid., p.255.。
如果暫時不考慮知覺是否一定包含概念性內容的話,喬納森·雷的這一評論里所概括的笛卡爾論題包含兩個主論點:其一,人類的行動總是包含思想以及心靈的運作,從而都是理智行動;其二,理智行動奠基于知識(這里自然指的是命題知識)。看起來,喬姆斯基所認可的東西(以及他的語言研究方案所假定的東西)以喬納森·雷的解讀為橋梁與笛卡爾發生了真正和諧的共鳴;如果對比笛卡爾二元論或者是天賦觀念論的命運,這個印象會愈發鮮活。
其次,像其他一些以研究喬姆斯基著稱的學者一樣,我留意到,在許多語境里,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語言知識(knowledge of language)”概念常常是可以互換的。要獲得更清晰的理解,不妨考慮他的這樣兩個觀點:(1)生成語法是說話者知道的語言知識;(2)生成語法表征說話者的語言能力。看起來,“語言知識”是一個心理學和認識論的概念,而“語言能力”是一個飽含生物學意味的概念,僅當在假定了理智化的解釋思路之后,喬姆斯基才能忽略這兩個概念面貌上的差異而在某些語境中互相替用。
再次,從理解的角度說,即便喬姆斯基從未明確表達說從笛卡爾那里繼承了這樣一種理智化的解釋思路,我們仍然可以發現,賴爾勾勒的理智主義神話可以作為理解喬姆斯基關于語言能力和語言知識的解釋的有效模型(也許,需要改動某些細節以適應不同年齡階段的喬姆斯基)。
根據賴爾的勾勒,理智主義傳奇(intellectualist legend)主張如此區分智能行動和非智能行動,“主體的任何一個智能行動都有一個在先的內在驅動行動,即對一個適合于解決問題的調節性命題的考慮”*G. Ryle,TheConceptof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p.31.。
對于當前討論,可以獲得的啟發是,如果用“語言行為”替換上述表達中的“智能行動”,用“生成語法知識(或者普遍語法的原則)”替換其中的“調節性命題”,理智主義傳奇就可以獲得一種喬姆斯基版本。我想,這就為我們根據賴爾勾勒的理智主義傳奇來理解喬姆斯基的語言方案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著迷于最佳解釋推理的讀者也可以這樣想,因為理智主義模型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喬姆斯基方案,因此后者實際上很可能就是這樣的。
另外,說喬姆斯基假定了一種理智化的解釋人類智能的方式,這一點在認知科學和心靈哲學的討論里能得到些旁證,喬姆斯基處理語言能力的方式是崇尚符號主義認知模擬和計算主義心靈哲學的學者們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目前,他們已普遍感受到一種需要面對賴爾無窮后退論證的壓力,如上述,賴爾的論證針對的就是一種理智主義的解釋人類理智能力和智能行動的方式。*Avrum Stroll曾費力解釋一個現象,即為什么《心的概念》在出版后的頭十年里引起了熱烈討論,但之后便被大多數人忽視了(Avrum Stroll, Gilbert Ryle, inACompaniontoAnalyticPhilosophy, Edited by A. P. Martinich and David So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 121)。Avrum Stroll沒有預見到,《心的概念》(特別是Knowing-how和knowing-that的區分)會在21世紀的頭十年再次引起熱烈討論。
六
醫生對病情的診斷,常常不依賴于病人自己的判斷;對喬姆斯基語言研究方案的笛卡爾貢獻的診斷,也許并不必然依賴于喬姆斯基本人的判斷。基于前述理由,看起來,相比于天賦觀念、或者是語言的創造性,認知能力的理智化解釋思路更值得稱作是喬姆斯基方案的笛卡爾貢獻。在另一些地方,我力圖論證,語言機能假設對于解釋語言能力既不充分,又不必要*劉小濤:《喬姆斯基的“學習理論論證”和模塊性假設》,《哲學研究》2008年第10期。;而且,對于解釋語言能力和描述語言行為而言,生成語法規則不可能是充分的語言知識*劉小濤:《作為語言知識的句法規則系統?》,《自然辯證法研究》2009年第11期。。如果訴諸語言知識來說明語言能力會遇到種種困難,這或許意味著,一般性地講,認知能力的理智化解釋思路還有待更進一步的審察。
(責任編輯任之)
**作者簡介:劉小濤,哲學博士,(上海 200444)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中圖分類號:B712.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6)03-0098-07
*本文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于虛擬現實的實驗研究對實驗哲學的超越”(15ZDB01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用主義研究”(14ZDB022)的資助。
本文曾先后在復旦大學分析哲學讀書會(2014年5月)、第九屆全國分析哲學大會(2014年8月)宣讀。一些尊敬的師友以及一位匿名審稿人曾先后提出若干修改意見,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