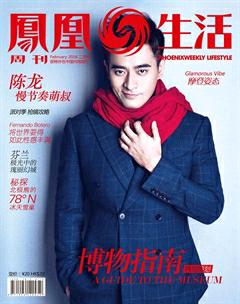一個博物館管理者,他關心什么
白瑜彥

與城市中大多匆匆其行的人相比,博物館的管理者,大概會被認為是在從事著一份絕對清閑、與長年固態的文物古跡相看兩厭的工作。可深圳博物館的葉楊館長說,雖然棲身在沉默的歷史塵埃中,但他們相當忙碌,特別在這個被強調為社會服務的時代,收藏早已不是唯一要務,考研文物臻品、展覽和輸出其文化價值,都成為管理者肩上的重要擔子。這些博物館中人,就像秉持一盞莊嚴的燭燈,夜夜游走在一條靜止的時光隧道中,或許微弱,但那些照亮古跡的螢火之光,一定會被敬仰。
珍藏 ?延緩文物的衰老
博物館并不是由一個個玻璃柜簡單搭建的展臺,它代表著國家在收藏歷史長河中遺留下來的珍貴寶藏,因此不管是考古隊辛苦挖掘出土的,還是通過社會愛心人士捐贈的,一旦確認其價值,就會把它悉心保護起來。鑒于萬事萬物都有一個自然風化的損耗過程,歷史越悠久的文物,它的軀體就越脆弱,這是永恒的真理,而博物館可以做的,就是讓這個過程變慢。
“一張宋代的畫,如果放在某個人家里,不被特別保護的話,根本無法保持原本的樣貌,可能現在已經永別于世了。你們只看到文物殘存的靜止模樣,但不知道我們付出的心血。”館長說。保護文物的第一關,就是要摸清收藏的道兒,要用很多辦法來延緩它衰敗,運用自然科學中的學問來對抗時間。這實際上有很繁重的工作,博物館有專門收藏保護的部門,研究怎么防濕、防霉、防塵、防蟲,讓它衰敗的過程變得微乎其微。這都是博物館的職責與功勞,目的只有一個——讓文物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深圳博物館的舊館,于2015年8月起開始閉門整修,因為三十年前的設備設施早已達不到條件,安防、消防可能也達不到標準,比如在不能恒濕恒溫的環境下,一會冷,一會熱,文物就會隨之一會漲,一會縮,這對于全人類的寶藏而言是巨大的傷害。因此在硬件上,博物館要用盡一切方式來避免文物的損壞,力求“一件都不能少”。
細考 歷史背后的真貌
葉館長曾擔任深圳多年的考古隊長,許多重要遺址的發現他都參與其中。于考古人員而言,他們并不獵奇,也從沒碰到過像電影《尋龍訣》中的漫天幻象和神乎其神的事件,更不會一頭栽在一個像“彼岸花”這種傳說的靈異寶藏當中。他們關注的,反而恰恰是那些出土文物不多、文獻記載稀缺的地方。“我們要看到的是一個全國的面貌,而不僅僅是西安古城是啥模樣,洛陽古都是啥模樣。”商代之前沒有任何文字資料,而人什么時候可以稱為人,而不是猿人,那都是一個個考古發現的,它為人們了解過去打通了死灰下的時間通道。
因此在文物出土之后,除了好好珍藏,工作人員還要開始卯足勁考研。這是博物館的另一重要職務,考古的目的就是把整個歷史狀況復原出來,這是一門綜合的科學,需要用到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自然科學等等,檢測它的成分,判斷斷代的歷史,分析龐大的體系,考察當時的社會有多少人口,是怎樣一個生活水平,腦袋瓜子里裝著什么樣的宗教思想,譬如當看到一個皇家茶杯時,除了知道它是皇帝御用之外,博物館還關心這個文物所反映的人生百態。“一個茶杯的歷史不可能只是皇帝史,它裝載著的是整個人類的歷史。”在博物館里,沒有人在意一個文物有多好看,他們在乎的是如何讓斷掉的年代有所填充,讓人類的發展史飽滿地有所延續。


精展 與社會親密接觸
當文物收藏得當,文獻也已整理成策,下一步就是如何展出藏品,用管理者的話來說,就是“如何讓觀眾理解你”。博物館的庫存量是很大的,但展出的量卻很少,除了一些重要的固定陳列之外,多數展品都以專題展覽的方式在流動展出,而關于展出什么,博物館通常會做到兩年后的計劃,準備長遠,不是輕易功夫。
死的東西不能放在庫房中發酵,更何況博物館里也不是一個個死氣沉沉的玻璃柜子。精確展覽實質上是博物館在履行它的社會職能,讓人民從中了解到整個文化的發展。“展出不能光給出一個鐵疙瘩,那有啥意思?你拿出一個東漢時期的鐵劍,就要把鐵的知識都介紹,劍的知識也要,其鑄造的全國背景也要一一剖析在觀眾面前。”
雖說博物館這個存在的本身一定是高端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對其抱以崇敬之心,但葉館長承認,以前的博物館確實與社會有一點脫節,光是注重它的收藏與研究,這讓外人一看——“哇,真高深”,換言之是“不近人情”。因此現在的博物館都把身段放低,更多地面向社會,讓更多人從中參與,比如說義工和小講解員,這樣才能讓后代子孫對這些文物重視起來,也是一個博物館在時代洪荒中求新求變的新形式。
滲透 把博物館變成生活
在中國,博物館還是常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來往的場所,普通市民看博物館有一個特點,就是獵奇和盲目,一看全是陶瓷、石頭、青銅器,沒有美的造型便興致寥然。中國人缺乏科學的思維,更多的是情緒化的思維,不喜求證鉆研,挖一個墓,則總相信鬼神在側,因此中國人還不能做到徹底的唯物主義。而外國的博物館往往人山人海,他們對歷史抱有求知求真的態度,擁有充沛的知識量。館長認為,實際上人們對他有所了解的東西才會感興趣,因此中國的博物館,還需要有更接地氣的表現,這樣才能真正滲入人們的生活。他更強調博物館的文化功能,相信館藏能帶給人類的,不僅僅是走馬觀花的驚奇感。
隨著博物館定點講解的提升,人流量也在逐年遞增,更可喜的是,它在提供知識的同時,也在無聲無息中把人們的素質提了上來,時間證明了它在推動一個城市的軟實力。博物館實質上是一個科學館,它所呈現的文化意蘊和科學含量比一般的教科書豐富,因此博物館更應當成為學校外的大學校。館長希望,在應試教育橫行霸道的當下,學校應當少培養一些記憶的機器,讓中國的孩子對萬物學會詢問“為什么”,而首先就開始從歷史文物。葉館長如今也在嘗試與小學弄試點,把博物館的課程列入他們的基本教程。他要找一個突破點。
四山紋鏡
此鏡花紋驚喜,為戰國時期楚式四山鏡中之上品。圓形、素卷邊,以羽紋為地,主文為四山字紋,在四山之間有花瓣和陶紋作分區間隔。山字紋是戰國銅鏡的特色紋飾。
褐彩牡丹紋梅瓶
1982年深圳南頭后海元代土坑墓出土。從上而下繪有5層花紋,內容為蓮瓣、卷草和龜背錦地開光折枝牡丹,是元代廣東地方瓷窯的特色佳作。
乘法口訣刻文磚
1981年深圳南頭紅花園東漢墓出土。乘法口訣刻文磚在我國尚屬首次發現,反映了中原漢文化在嶺南地區的傳播。
1987年深圳土地有償使用拍賣槌
二級文物。為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和籌集城市建設資金,1987年12月1日,深圳決定采用公開拍賣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這是深圳,也是新中國第一次公開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
三彩白馬
唐代的能工巧匠,以其熟練的技法,靈巧的刀工,簡練的線條,以及對馬匹性情深刻細致的觀察,從而塑造出了無數“瑰麗多姿,絢爛多彩”的唐馬形象。這件三彩白馬是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杰出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
深圳博物館——歷史民俗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