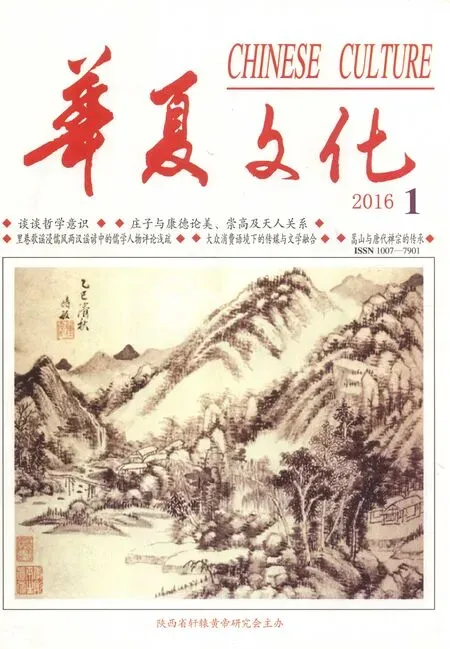莊子與康德論美、崇高及天人關系
□路傳頌
?
莊子與康德論美、崇高及天人關系
□路傳頌
一般認為,康德的自然觀代表了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對待自然的工具理性態度,主張人對自然的統治、主宰權利。近年來,有一些學者提出康德的美學理論為環境倫理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還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莊子與康德都是試圖通過“美”來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就此來說,莊子思想與康德哲學有許多可以對話交流的地方。但是,相比莊子而言,康德仍然沒有給予自然應有的尊重。
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別是《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中至少蘊涵了五種自然觀。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區分了作為“物自身”的自然和作為表象的自然。作為“物自身”的自然(亦即自然本體)超出了人類認識能力的范圍,人類的直觀、概念和理性法則都不能應用于本體之上。作為現象的自然是人類認知與科學研究的經驗對象,它是無價值的,完全受制于機械性的科學規律或自然法則。康德認為自然法則本質上是人的理性法則,是人類經驗的可能性條件,因此他說是人為自然立法。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作為表象的自然是與人類的道德性無關的存在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人類道德性的障礙,人唯有通過克服自然對自身的影響才能獲得道德性。在《判斷力批判》中,作為表象的自然首先是人類審美經驗的對象,它是美的、崇高的;其次,它是人類文化的工具性條件,人是自然的終極目的,自然是為了人類的幸福、文化的發展而存在的。簡言之,五種自然觀分別是:作為物自身的自然、作為科學對象的自然、作為道德性障礙的自然、作為審美對象的自然和作為工具存在的自然(后四種都是作為表象的自然)。
在這五種自然觀中,唯一蘊涵友好型天人關系的自然觀是作為審美對象的自然觀。作為物自身的自然是不可知的;作為科學對象的自然是冷冰冰的、沒有價值的;作為道德性障礙的自然是價值的對立面,是需要克服、超越的對象;作為工具存在的對象僅僅具有外在價值,也就是說,只有在它能夠服務于人類文化的前提下才具有價值,而這毫無疑問鼓勵了對自然的干涉、主宰行為。只有作為審美對象的自然才是“與主體的生活情感相關”的自然(李秋零譯:《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頁。以下僅注頁碼),才是具有內在價值的自然。康德認為審美經驗是“無功利性”(或譯“無興趣”)的,他說:“鑒賞判斷純然是靜觀的,也就是說,是一種對一個對象的存在漠不關心,僅僅把對象的性狀與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加以對照的判斷。”(第217頁)所謂“對一個對象的存在漠不關心”是指在審美經驗中,人并不試圖占有自然,不通過占有自然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利益。換句話說,在審美經驗中,人達到了忘我的境界,忘記了自己的欲望和功利訴求。
康德又把作為審美對象的自然分為美者和崇高者兩種,美者給我們帶來閑適、寧靜、自由的愉悅感,而崇高者是那些因其野性、粗暴、無序、威脅著人的生命安全的事物,它“通過一種對生命力的瞬間阻礙,以及接踵而至的生命力更為強烈的涌流的情感”(第254頁)而激起對自然的驚贊和敬重。對美者的經驗還只是忘我的,而對崇高者的經驗則是直接排斥人的感性生命的,使我們“認識到自己在物理上的軟弱無力”(第271頁),并“把我們所操心的東西(財產、健康和生命)看作是渺小的”(第272頁)。無論是對美者的經驗,還是對崇高者的經驗,人都超越了自身狹隘的自我利益和欲望,都對自然抱一種非工具、不干涉、不主宰的態度,因此,有學者認為康德美學為環境倫理提供了有意義的思想資源。
莊子并沒有完整、清晰、系統的美學思想,沒有像康德那樣系統地分析審美經驗,但在《莊子》一書中,有不少小故事以描述方式刻畫了審美經驗的特征,與康德的觀點有不少相合之處。例如,在《逍遙游》中惠施對莊子說,他有一棵很高大的臭椿樹,樹干臃腫小枝彎曲,沒有任何用處,工匠連看也不看,莊子回答說:
“子獨不見貍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罔罟。今夫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子·逍遙游》)
莊子首先用追逐私欲的野貓、黃鼠狼最終死在捕獸器中為喻,譏諷惠施只看到自然事物的工具價值,然后又主張平等地對待無用之木,與之和諧相處。“彷徨”“逍遙”是形容閑適、自得的審美體驗,“無為”“寢臥”是描述非功利的態度和行為。
《莊子》還塑造了幾個超脫生死的人物形象:子祀、子輿、子犁和子來。這四個人都把生死存亡看作是渾然一體的。子輿生了重病,脊背向上凸起,五臟的腧穴朝上,面頰陷進肚臍,兩肩高于頭頂,頸椎指向天空,然而子輿“其心閑而無事”(《莊子·大宗師》),甚至還來到井邊照照自己的樣子,以審美的態度贊嘆造物者用其神奇的力量將自己變成這副彎彎曲曲的模樣:“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同樣,子犁在子來將死之時贊嘆道:“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子來自己也豁達地說:“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子來把大自然看作一個大熔爐,把造物的大道看作技藝高超的工匠,把自己的生命歷程看作大道鑄造萬物過程的一部分。在這里,造物者就是作為驚贊和敬重的崇高者、偉大的藝術家,在它面前,個體的生命是渺小的,也是不足掛懷的。
由此可見,康德用抽象的分析性語言,莊子用形象的描述性語言,都表達了審美經驗的無功利性的理念,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然而,在康德與莊子之間有幾個顯著的區別。
首先,對康德而言,人是在對美者的體驗中獲得這種不同于純然感官快感(以滿足自我利益為基礎的快感)的審美愉悅感,和一種對待自然的非功利態度的。而對莊子來說,人首先要擺脫對自我利益的過分關注,以及對待自然的狹隘的工具理性的功利心態,才能在哪怕是無用之物上體驗到審美愉悅感。而且,這種審美愉悅感的獲得,不是來自于康德所謂的對自然的“純然靜觀”,而是來自于人與自然之間的游戲、共在(“無為其側”、“寢臥其下”)。
其次,康德認為,人是在對崇高者的體驗中才感受到自己的感性需求是微不足道的(盡管對康德來說,對崇高者的體驗首先要求心靈具有對道德理念的感受性)。而對莊子而言,只有做到“安時而處順”、“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莊子·大宗師》)才能夠以審美的心態看待造物者,并接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遭遇。這也就是為什么康德認為對崇高者的體驗需要我們處身于安全之中,沒有面臨現實的危險,而子輿、子來卻能夠在造物者威脅到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仍然驚贊、敬重造物者。而且,康德認為,我們把自然對象稱為崇高者,其實是某種偷換,因為真正值得敬重的對象是我們的人性理念,而自然中的所謂“崇高者”,只是激起、喚醒我們心靈中的力量,“使我們鼓起勇氣,能夠與自然表面上的萬能相較量”(第271頁)。康德的這種觀點被鮑桑葵稱為“貧乏的道德勝利”([英]鮑桑葵著:《美學史》,張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51頁),甚至被Ronald Beiner譏諷為“人類學的自戀癖”:人仰望著頭頂的星空,敬畏著他自己。而莊子則是把包容一切、創造一切、毀滅一切的造物者看作最直接的敬重對象。
最后,上述所有分歧都源于康德與莊子對天人關系的不同理解。盡管康德在其美學思想中提倡一種對自然的非工具的回應態度,但康德終歸認為人高于自然。人的理性意志具有先天的、自我決定的因果性,獨立于自然世界的因果決定性,而自然世界則是低等的,完全受自然法則的支配。美感與崇高感的真正價值在于它們都有助于培育道德感,而人作為道德存在者,是自然的終極目的,“整個自然都是在目的論上隸屬于這個終極目的的”(第454頁),“如果沒有人,整個創造就會是一片純然的荒野,就會是白費的”(第461頁)。
與康德不同,莊子的美學觀念是以天人一體、物我平等的理論預設為前提的。對莊子來說,美感和崇高感不是培育道德感的手段,恰恰相反,美感和崇高感的獲得首先要求人們對自然持有一種恰當的倫理態度。《逍遙游》暗示,唯有當我們尊重自然,平等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候,才能獲得閑適、自得的審美愉悅感。《大宗師》則暗示,唯有當我們超越狹隘的、孤立的自我,進而將自我認同擴大到整個自然,把自己的生命歷程看作宇宙大化的一部分,我們才能超越個體生命的生老病死,才能以驚贊、敬重的態度看待整個自然的變化過程。
正因為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最后把自然貶為工具,才有學者認為,康德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最終削弱了其美學思想所隱含的對環境倫理的允諾。而莊子的美學思想以其天人一體的理論預設為前提,給予了自然恰當的尊重。
(說明:本文受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比較莊子與康德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支持,項目編號14JK1685。)
(作者: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郵編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