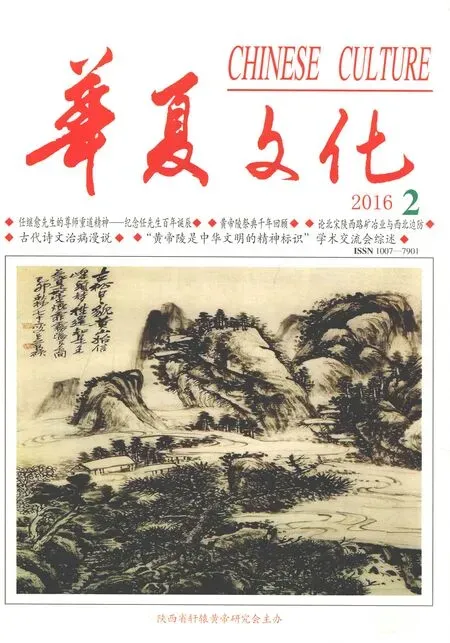論北宋陜西路礦冶業與西北邊防
□ 姚媛媛
?
論北宋陜西路礦冶業與西北邊防
□ 姚媛媛
北宋陜西路的礦冶業,由于礦產資源分布的客觀原因,產量不及南方,但從影響力來看,陜西路的礦冶業無論在經濟領域、國防領域還是民生領域都發揮著重大作用。相比其他歷史時期陜西地區的礦冶業,北宋時期則更多的與邊防相關,這是北宋陜西路礦冶業的特殊之處。西夏一直是北宋西北邊防大患,陜西路直接與西夏接壤,所以陜西路整體是對西夏作戰的關鍵環節,也是北宋西北邊防的重點部署地帶。這樣的地理區位,使得陜西路從一開始就承擔起了邊防的重任。而礦冶業的發展則對國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需要對陜西路礦冶業進行相關研究。本文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宋代陜西路的各個礦冶業進行分析,進而看待其在西北邊防中的作用,對于我們了解宋代西北邊防的政策以及把握宋代礦冶業的整體情況,有一定作用。
一、金銀
宋初陜西路金銀礦的產地主要在商州、虢州、秦州、鳳州、鳳翔府等。北宋陜西路的金礦主要在商州,“商州:洛南、商洛、上津、豐陽縣課金,元額三十九兩,元年收五十六兩”;“金坑冶祖額總計七千五百九十七兩,元豐元年收總計一萬七百一十兩”(《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6720~6721頁),可見,商州的元額及總額都占不到總數的1%。
宋初陜西路的銀礦主要有:“虢州:冶務舊置;商州:豐陽縣砂銀冶,太平興國元年置,上洛縣龍渦場,熙寧七年置;洛南縣麻稜冶場八年置;鎮北冶場九年置;秦州:太平興國三年,升大賈務為太平監;隴州:冶務舊置,汧源縣古道場,治平元年置。”(《宋會要輯稿》第6717頁)陜西路銀礦的主要歲額如下:
“商州上洛縣龍渦場,熙寧七年置;洛南縣麻稜冶場八年置;鎮北冶場九年置;元額九千七百九十七兩,元年收六千九百六十兩;虢州銀煎冶、百家川、欒川、密崖冶、姚谷冶、石甕冶,朱陽縣七場,元額三萬四千五百七十三兩,元年收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兩;鳳翔府橫正場元額一千八百八十五兩,元年收九百二十九兩;秦州子路、白石、黃孽、黃金、保安、杘谷、東毗、白花、白草、青陽、黃城、臨金十二場務元額二百二十二兩,元年收一百四十九兩;隴州,元額七萬七千二百六十二兩,元年收四千三百二十二兩;鳳州元額一百六十兩,元年收一百八十四兩”(《宋會要輯稿》第6721頁)。由以上數據可知,當時全國的銀坑冶祖額為四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兩,陜西路銀礦的元額達到總量的30%,而元豐元年收總計為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陜西路也占到了17.7%,對比金、銅、鐵資源,銀的產量已經非常高了,尤其是虢州和隴州,在陜西路中所占比例最高,發揮的作用也最大。由以上可知,銀礦的開采發掘,對于陜西路的經濟等其他方面都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二、銅鐵
陜西路的銅鐵坑冶業特點是銅少鐵多,這與銅鐵資源數量有關。
北宋初年的銅礦資源主要集中于南方,陜西路較少。另一方面,“(至道二年),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煉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眾庶共之。不許。”(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523頁))可見,政府對于資源還是采取保護的態度。宋神宗元豐以后,在虢州、隴州、鳳翔府、鳳州等地發現了銅礦。產量與南方各路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關于銅礦的歲額,“隴州古道場元額九千一十九斤,元豐元年收同;虢州百家川場、欒川冶,元額七千四百一十七斤,元年收六千三百九十二斤。” (《宋會要輯稿》第6722頁)當時全國累計額為:“銅坑冶祖額總計:一千七十一萬一千四百六十六斤,元豐元年收總計一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宋會要輯稿》第6723頁)。由此可見,隴州加上虢州的銅礦總共占不到全國的1%,陜西銅礦比例份額比較少。盡管如此,這些少量的銅礦也對當地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陜西路境內的鐵的范圍比較廣泛,主要集中于陜州、虢州、鳳翔府、鳳州、耀州等地;“陜州:集律冶務,舊置;同州:韓山冶務,舊置;虢州:盧氏縣馮谷冶、麻壯冶,舊置;坊州南北務、玉華務、舊置;鳳翔府:赤谷務,舊置;眉縣:斜谷冶,治平三年置” (《宋會要輯稿》第6717頁)。鐵礦的產量較大,其課額如下:“虢州:清水猯猴冶、上我槽冶,元額一十三萬九千五十斤,元年收一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斤;陜州:元額一萬三千斤,元年收同;鳳翔府:元額四萬五百六十斤,元年收四萬八千二百四十八斤;鳳州粱泉縣冶,元額三萬六千八百二十斤,元年收同”(《宋會要輯稿》第6723頁),而全國累計額元額為五百四十八萬二千七百七十斤,元豐元年收總計為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大體上,鐵的元額占到全國元額的4%,元豐元年額占到了4.4%,所以,陜西路鐵的資源相對豐富,課額數比較可觀。
三、鉛錫
陜西路的鉛錫資源主要是在商州、虢州、鳳翔等地。神宗時,擴展到了隴州。對于鉛資源來說,“隴州:元額一萬二百六十八斤,元年收二百六十三斤;商州:錫定場,熙寧八年置,元額九十萬五千五百七十四斤,元年收八十五萬二千三百一十四斤;虢州:元額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六十八斤,元年收一百六十二萬四百三十二斤;鳳翔府:元額三千二百四十五斤,元年收九千四百七十三斤”,總體元額是八百三十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七斤,元豐元年收總計九百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 (《宋會要輯稿》第6724~6725頁)。由此可見,陜西路的鉛資源的元額占到了總數的32%,元豐元年額占到了總數的27%,這個比例在整個北方礦冶業來看,數額很大,也打破了鉛在南方的獨占地位。
除去以上這些礦冶業外,還有錫、朱砂、水銀的存在。“商州:上洛、商洛、洛南三縣水銀、朱砂坑,元額水銀五百六十九斤,元豐元年收五百八十四斤,元額朱砂八十九斤四兩,元年收二百六十斤四兩;鳳州:河池縣水銀務,元額二百四十七斤,元年收七百四十三斤。”“坑冶祖額水銀總計四千九百三十七斤,元豐元年收總計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斤一十三兩七錢六分,元豐元年收總計三千六百四十六斤一十四兩四錢。”(《宋會要輯稿》第6725頁),陜西路的水銀的元額占到了總數的16.5%,元豐元年額占到了39.5%,而朱砂元額占到了總數的4.7%,元豐元年額占到了總共的7%,可見,陜西路的水銀朱砂,特別是水銀礦冶業,在全國來說,都有一定的地位。
以上是從具體的礦產資源方面對宋代陜西路進行了相關分析,由上可知,陜西路的礦產資源主要集中于虢州、陜州、秦州、鳳州、商州等地。宋政府在永興軍路和秦鳳路等地設立了一系列監來鑄錢,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錢幣缺乏的問題,這些機構能夠設立運行成功,無疑是因為當地的礦冶資源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錢幣流通的過程當中,由于銅資源稀缺等原因,需要鑄造鐵錢輔用,“(慶歷元年)是月,以虢州朱陽縣鑄錢監為朱陽監,又以商州洛南縣鑄錢監為阜民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183頁),所以,對于陜西路來說,豐富的鐵礦資源對于鑄幣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金資源主要集中于陜西路的商州,也和銅一樣,數量較少。除此之外,其他陜西路的資源相對比較豐富,為陜西路的發展,還是起到了相關方面的作用。
四、北宋陜西路的礦冶業與西北邊防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北宋陜西路的礦冶業有了大致的了解,除去金、銅外,其他的礦產資源數量比較大,所產生的效益也相對較高,對西北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積極方面
北宋陜西路的礦冶產量在北方地區看來,其優勢地位比較突出:“凡山澤之入,金一千四十八兩,永興軍路四兩;銀一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兩,永興軍路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兩,秦鳳路四百八十三兩;銅二千一百七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斤,永興軍路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五斤;鐵五百六十五萬九千六百四十六斤,永興軍路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斤,秦鳳路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七斤;錫六百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九十一斤,永興軍路三百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九十六斤;朱砂二千七百八斤,永興軍路二百五斤;水銀二千一百一十五斤,永興軍路六百二十一斤,秦鳳路一千四百九十四斤”(《宋會要輯稿》第6729頁),在這些礦產數中,銀占到了11%,鐵占到了24.6%,錫占到了53%,朱砂占到了7.5%,水銀占到了100%,由此可見,陜西路的礦冶業資源較為豐富,這直接為其他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動力;它對宋朝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國家戰備力量上,重視陜西路的礦冶開采與利用,可以極大限度滿足當地的需求,調整各地區的平衡狀態,利于整個國家國防力量的增強。
陜西路在整個北宋的地理位置特殊,是對西夏作戰的前線,是關乎西北戰局的關鍵一環。陜西路的安全便是整個西北地區的安全,也就是北宋政府的安全。所以,陜西路的各項事業發展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邊防;二是穩定。邊防上:主要是最前線時刻準備與后方后勤補給的高效。最前線的物資極其重要,而陜西礦冶業較為成熟,可以第一時間提供兵器、軍事裝備等,對于陜西本地的礦冶業的要求較高,而國家的重視程度也較高,礦產資源關乎國家命脈,對于礦產的流通也有眾多限制,宋初“西北邊內屬戎人,多赍貨帛于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為器。乃詔吏民闌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宋史》第4377頁)。穩定方面,主要從貨幣流通來看,陜西路的礦冶業,由于經濟效益不明顯,且國家控制過大,從錢幣的流通可看出,必須保證貨幣流通的穩定性,才能穩定民生,保證勝利。
(二)消極方面
相對優勢的資源會為西北邊防帶來眾多優勢,但若管理不善,一味狂斂,必定會使陜西路及西北邊防陷入危機。政府對于陜西路的礦冶業管理過多,政策并沒有持續性,而是一變再變,使得豐富的資源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經濟作用。礦產資源屬于北宋政府,再加上對西夏前線的特殊戰略地位,都使得國家從整體利益角度出發,設立官營機構,主要從事關于國計的有計劃的生產項目,這就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對于民生方面的投入;所擁有的經濟優勢,反而會更加側重于國防的投入,這便是北宋時期陜西路發展的方向。另外,當地雖然設立了鑄錢監,但流通量仍然受限,且陜西路經常變換錢幣,導致市場異常混亂,剛開始,銅錢千錢換鐵錢千百五;紹圣初,銅錢千錢換鐵錢二千五百,所以,“元符二年,下陜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于是詔陜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宋會要輯稿》第4385~4386頁)。另外存在的問題便是資源的浪費,浪費的結果便是更加狂暴的開采資源,大量設置鑄錢監,形成惡性循環。各種錢幣的通行,導致錢法混亂,以致民生艱難,后方不穩,則前方受挫,直接影響到了前線的士氣。況且從國家政策來看,主要還是預防為主,所以,長時期的防御政策,不斷地循環,最終拖垮了陜西路的經濟。這不僅僅是陜西路的癥結,北方各路均如此,所以,北宋經濟呈現出了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格局,便不足奇怪。
通過對宋代陜西路礦冶業的分析,我們不僅了解了陜西路礦產資源的分布,而且也對其歲額、功用進行了探討。雖然整體上它的產量不及南方地區,但在北方地區來看,戰略地位意義重大,主要還是著眼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國防意義,正是有了較為豐富的礦產資源,才為西北邊防帶來了可靠的后備保障。對于礦產資源集中地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設立各種監、務、場等對于促進當地資源的開發,有很大促進作用,這對于失去政治重心的陜西路來說,是個很好的經濟發展點。盡管陜西路資源相對較好,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國防性的投入更大,而民生基礎性的投入相對較少,且引發的民生問題較多,政府雖一再采取措施進行拯救,但效果微弱。陜西路礦冶業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沒有直接貢獻于經濟效益,這不僅僅是陜西路的個體原因,宋代北方諸路都存在類似的問題。邊防與經濟的關系,存在一種互相調和的狀態,相關政策的施行,也需慎之又慎。
(作者:陜西省西安西安市西北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郵編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