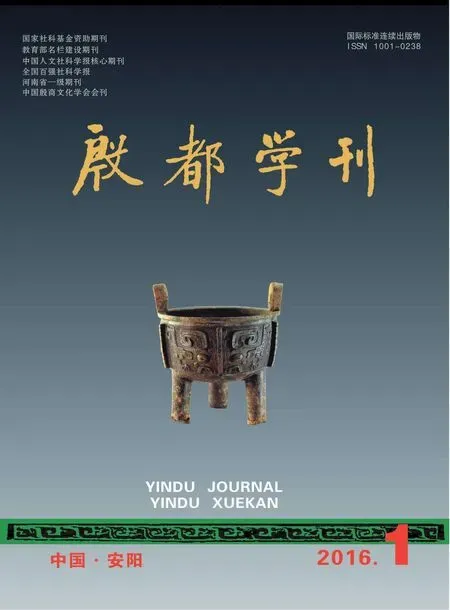楊億《漢武》唱和組詩新探
陳夢熊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
楊億《漢武》唱和組詩新探
陳夢熊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摘要:楊億等人所作《漢武》唱和詩是針對真宗朝“西祀”、“東封”和“祥瑞”頻降的現實政治有感而發,絕非單純意義的“以學問為詩”。傳統認識中對楊億及其“西昆派”的認識有頗多值得商榷之處,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禪泰山的真實動機、真宗皇帝與楊億的微妙關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對楊億的界定和他們對待“西祀”、“東封”的態度,將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楊億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漢武》唱和組詩的真實情感。
關鍵詞:楊億;《漢武》唱和組詩;諷喻
引言
《西昆酬唱集》本為楊億等館閣臣僚編纂《冊府元龜》之余應酬唱和之作,其中一組《漢武》唱和詩,后人多有爭議。《瀛奎律髓匯評》卷三引紀昀評:“此便欲真逼義山。”又《漢武四首》之二,方回評:“夏鼎幾遷空象物,秦橋未就已沉沒”一句為“言興亡之運,理所必有,雖漢武帝之力矩心勞,終亦無如此之何也。”[1](P127)即是認為此組唱和詩乃有感而發,是諷喻宋真宗。王仲犖《西昆酬唱集注》就指出此詩是:“館臣之為詩譏諷漢武,實即欲以諫帝并止其東封也。”[2](P42)此說當否,值得商榷。鞏本棟教授即認為:“論者或以為是諫真宗信王欽若之說,造為祥瑞,東封泰山。其實,宋真宗東封泰山要在作此詩兩年之后,很難相信諸位館臣當時已有此先進之明。”[3](P166)而羅爭鳴先生更是據鞏本棟教授的觀點和自己考證,認為此組詩歌“是楊億等秘閣文人在編修《歷代君臣事跡》時,在披覽典籍、分類部居、采摭銓擇之際對歷史典故的感懷之作,也是對傳統題材的再抒寫,不必作‘過分詮釋’。”[4](P26)兩種觀點似各有其合理之處,卻又難以令人完全信服。二派的觀點何以由此矛盾,關鍵在于后者缺乏從歷史維度審視問題的意識,非但沒有從真宗朝的歷史背景入手考察楊億對待宋真宗西祀東封的態度,也忽略了楊億與真宗的微妙關系,從而沒有準確把握到真宗朝士大夫群體走向分化的趨勢,也就無法從社會背景的角度去解讀《漢武》組詩。
本文將從真宗封禪泰山的真實動機、真宗皇帝和楊億的微妙關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對楊億的界定和他們對待“西祀”、“東封”的態度,對《漢武》組詩給出合理的解釋。
一、借古諷今是“《漢武》組詩”的本質
圍繞著《漢武》組詩的爭論形成了兩派觀點,矛盾的焦點在于此組詠史詩是否為諷喻宋真宗封禪泰山而作。以此問題為原點,雙方各自拿出了自己的證據。認定其為諷喻詩者指出:“此詩有說譏武帝求仙,徒費心力,用兵不勝其驕,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也。”[1](P127)否定其為諷喻詩者雖表述各有不同,觀點基本一致:鞏本棟教授從楊億等人作《漢武》組詩早于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封禪,不可能預見未發生之事,是從邏輯層面否定了其作為諷喻詩的合法性;羅爭鳴先生則認為這不過是后人的過度詮釋,《漢武》組詩是宋人“以學問為詩”的掉書袋式行為的具體表現,是從宋人作詩方式進行理解的產物。
筆者并不能認同二位先生的觀點。所謂“詠史詩”究竟是單純的炫耀學識,或者是“寄寓深意”需要我們加以辨析。人們討論某一時期的歷史、或者是點評某一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可避免地帶入當下語境的思考。“真實的情形往往是,對未來的估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著人們應回憶哪些歷史,凸顯哪一部分過去,強調什么樣的一場,突出何種傳統。所以,任何所謂的‘回顧’、‘檢討’,幾乎都是有立場,有預設的。歷史不是自我呈現的,而是被敘述的。”[5](P165)楊億等人匯集于館閣中編纂的《冊府元龜》原名《歷代名臣事跡》,其編纂目的絕非一般意義的類書集成,而是要為帝王治理天下服務。身兼此等重任肯定讓楊億等人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倍加小心,也不免在編選“祖宗故事”、“歷代事跡”的同時融入他們對真宗朝現實的思考。
真宗朝最大的現實在兩點:其一是“澶淵之盟”,其二是“神道設教”。二者相互滲透,前者是源頭,后者則是延伸。鞏本棟教授以真宗封禪在《漢武》組詩兩年之后作為否定的證據,是將《漢武》組詩理解為真宗封禪泰山的實錄,未免有一一坐實之嫌。歷史的真相是,封禪絕非真宗皇帝一時興起,而是他本人和部分朝臣共同努力、悉心營造的結果。真宗朝是趙宋王朝從“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轉折點,“作為有宋建國以來生長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他一方面缺乏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勢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建樹個人的形象和統治權威。”[6](P298)他需要尋找一種方式凸顯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能夠成為與太祖、太宗并列的圣君。
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夸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后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以圣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7](P1329)
正是在王欽若的提醒之下,真宗皇帝意識到“澶淵之盟”是對“天子”崇高地位的沉重打擊,就更加急迫地要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以及尋找自己統治下的趙宋天下已邁入“太平盛世”的各種證據——天降祥瑞和西祀、東封則成為最有簡便易行的選擇。“澶淵之盟”是真宗朝政治生態發展的轉折點,它直接促成了“天書”、“西祀東封”等事件的發生。我們不僅可以在正史中可以找到真宗皇帝和王欽若的對話,也能在宋人的筆記中發現類似的記載。司馬光《涑水記聞》中就寫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8](P120)兩段記述大致相同,后者多出了“引天命以自重”的表述。此一句道出了真宗封禪的真實目的。在“鎮服海外、夸示外國”的外衣下,真宗皇帝和他的臣僚們為了洗脫“澶淵之盟”的恥辱開始了一次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融合著證明趙宋政權合法性和粉飾太平于一爐。非但帝王將相無法置身其外,即便是曾經明確表示反對符瑞的寇準,也在遙遠的雷州獻上了“祥瑞”,這是真宗朝最大的現實之一。面對此種情景,士大夫階層不可能提前毫無覺察。他們或是主動投身于其中、或是持觀望態度,更多的人選擇了沉默,只是在自己的心中和筆下表達自己對這場“造神運動”的態度,楊億的態度表明他是不支持宋真宗親自發動的造神運動。正如鄧小南教授所言:“面對接踵而來的天書、封禪諸事,他們不得不選擇自己的立場。登基已近十年的真宗,不僅憑借其帝王身份,也依憑其統治經驗,在聽信于王欽若、丁謂等人的同時,籠絡住以王旦為首的國家行政班子,容忍了或明或暗的抵制與批評,也利用了大批不能淡忘于進身之途的文人。”[9](P322-323)
關于楊億的態度,我們可以從他為真宗起草的封禪詔書被修改一事中見出端倪。他奉命起草的封禪詔書有一句“不求神仙,不為奢侈”,被真宗皇帝下令改為“朕之是行,昭答玄貺;匪求仙以邀福,期報本而潔誠。”*李燾《續修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八.所謂“不求神仙,不為奢侈”是采用為尊者諱的表述方式,委婉地掩蓋了真宗封禪的真實目的。真宗默許之下的修改強調“匪求仙以邀福,期報本而潔誠”,表面的意思是說自己的行為是酬答上天所賜的祥瑞,并非是“粉飾太平”。對比之下,我們發現:楊億的封禪詔書是試圖為真宗封禪的真實目的“裝點門面”,其反對封禪的態度不言而喻;而真宗授意的修改則直接暴露了內心最真實的想法。由此可見,楊億對真宗“封禪”的真實動機可謂洞若觀火,接下來將要發生的西祀東封就不是無法預計的未來,而是必將發生的“事實”。因此,他在唱酬之余借由漢武故事諷喻真宗也在情理之中。
所謂“神道設教”則是真宗朝另一不可回避的重大事件,它直接表明了真宗對待封禪的態度,以及他向臣民解釋為何要“西祀”、“東封”的動機。《周易·觀卦彖辭》即有“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孔穎達疏曰:“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為而成,圣人法則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故云‘天下服矣’。”*《周易正義》卷三《觀卦》載王弼注.“神道設教”本是儒家為圣人設定的教化之道,由于圣人能夠掌握自然萬物的運行法則,為了能夠教化民眾、使其理解自然、遵從自然,選擇以“神道設教”的方式在普通人與自然之間搭建起信息溝通的橋梁。宋儒對于“神道設教”有著更為實際的理解,他們沒有闡發漢儒“應天感人”的學說,而是將其與宋代社會的現實聯系在一起,更加強調統治者對民眾的教化。司馬光認為:“君人者能隆內殺外,勤本略末,德潔誠著,物皆信之,然后可以不為而成,不言而化,恭己南面,颙然而已: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可見宋代士大夫們并不否認“神道設教”的合法性,而是多了一些現實的考量,“天道”的神圣性也就不再顯得那么重要。
如果將漢代的祥瑞、天命理解為臣子在帝王暗示、默許下的操作,真宗皇帝則是親自登臺,參與到“神道設教”的具體操作中。在大中祥符五年,他本人曾親作《祥瑞論》頒發給臣僚。此書今已不可見,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大旨以明王雖有丕祥,常用祇畏,中人一睹善應,即自侈大。圣賢思以防邪,故《春秋》不書其事;然神祇降監,亦以揚祖宗之烈,當欽承而宣布之。若恃休期以自肆,固宜戒也。”將“神祇降監”的“天書”、“祥瑞”闡發為“揚祖宗之烈”不能不說是真宗皇帝的發明,既是為了轉移“澶淵之盟”帶給自己的恥辱感,也是維護趙宋政權唯一性、合法性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但在當時并非沒有人質疑所謂“天書”,《曲洧舊聞》記載:“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逈。’逈云:‘臣讀世間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11](P88)
綜上所論,以真宗一朝的社會現實而言,楊億等人面對天書、符瑞頻降的景象,內心沒有任何想法是不可能的。但臣下的身份又決定了他不能采取太過直露的方式去表達個人意見,借吟詠歷史為載體的《漢武》組詩是他們表達諷喻之志的最佳方式。
二、《漢武》組詩的歷史背景
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重新考察當代學界對楊億及其《西昆酬唱集》的傳統認識。盡管很多人對于楊億及其編纂的《西昆酬唱集》多持否定態度,或認為“西昆體帶有濃厚的貴族趣味”;或視其為館閣臣僚的唱和之詞,與社會現實無涉。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楊億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說他們寫詩的目的是‘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在這種觀點指導下寫出的詩,其題材范圍必然是比較狹隘的。”[11](P30)學術界也有其他的聲音,曾棗莊先生在《怎樣讀〈西昆酬唱集〉》一文中指出:“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欽若等迎合真宗意旨,偽造天書,議封泰山。楊億不以為然,被命草東封詔,他以‘不求神仙,不為奢侈’之語規諷真宗。”學界不同的聲音提醒我們,對待楊億及其《西昆酬唱集》應持謹慎態度。
就楊億的道德品質而言,在當時得到了士大夫的普遍認可,歐陽修就有“性特剛勁寡合”的評語,蘇軾也贊其為“忠清鯁亮之士”。這提醒我們并不能將楊億僅僅視為潤色鴻業的“文學侍從”,在他的身上體現著宋代士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而樂”的高貴品質。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草答遼人書,云“鄰壤交歡”,帝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帝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帝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愿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孔平仲《談苑》)
楊億的品性不僅表現在人格層面,也落到現實政治操作層面。在寫給遼國的國書中,他所用的文辭本為外交常用辭令,卻令真宗感到不悅。根本原因是宋遼兩國的關系絕非“交歡”,而是處于緊張的對峙狀態。楊億觸及到真宗脆弱的心理防線,有其迂腐的一面。但在圍繞是否著冊立劉娥為皇后的原則性問題上,楊億沒有屈從于真宗,反倒給出“如此福貴,亦非所愿”的答復,展現了士大夫的氣節。綜合考察上述兩個方面,我們基本可以描繪出楊億的歷史面貌——他的身上兼具儒家文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摻雜了不知權變的迂腐。
以詩作為例,楊億將《受詔修書述懷三十韻》置于《西昆酬唱集》之首,詩中有“危心惟毅棘,直道忍蓬藤”之語,頗有身居高位者謹言慎行之感,正體現了楊億為宦的謹慎,而非阿諛者嘴臉。“與宋初館閣宰輔大臣徐茲、李防、李至、呂端等五代舊臣和宋朝宰輔相比,與真宗朝王欽若、丁謂、陳彭年等拋棄原則依附皇權的館閣詞臣相比,楊億作為西昆體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具有自覺的獨立于皇權的人格意識,在他身上體現出有宋一代士人典型的氣質人品。”[12](P6)筆者認為,視楊億及《西昆酬唱集》為貴族文人唱和之作的觀點弱化了它的精神內涵和審美境界。方智范先生就曾指出,將館閣文人視為宮廷詩的主力是不錯的,但不能據此認定他們的詩作都是貴族趣味,而是需要慎加甄別。對于楊億的認識同樣是如此。
厘清楊億與真宗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對于理解《漢武》組詩的真實含義十分重要。
蓬萊銀闋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光照竹宮勞夜拜,露溥金掌費朝餐。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長安。*李慶甲匯編校點 :《瀛奎律髓匯評》卷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7 頁.
上面是楊億所做《漢武》詩,充分體現了西昆派詩人高超的寫作技巧和豐贍的學術素養,展現出鮮明的館閣文學色彩。羅爭鳴先生根據詩中大量引用典故的寫作技法,并參考其他幾位唱和者的《漢武》詩,指出“楊億、劉筠、劉騭等人的《漢武》詩,主題并無多少創意,仍是感慨神仙虛幻、漢武妄求而不得的人生悲劇,進而表現慣常的諷喻之旨。就風格來說,這七首詩大掉書袋,用典繁密,不熟悉《孝武本紀》、《武帝紀》、《漢武故事》、《博物志》等原典,幾乎不能全然了解。”[4](P27)似乎是要徹底否定楊億等人寫作此組唱和詩的諷諫意味。他還援引楊億所做《大宋天貺殿碑》,認為此文詳細記述了“天書”發現的經過,從而證明楊億并未明確反對真宗封禪。事實上,這種官樣文章對于詞臣出生的楊億而言,不過是官場的形式而已,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內心真實的想法。至于“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楊億言,粟一本至四十穗。”[13](P3609)就更是無以作為例證,為官者久離樞要,為謀求仕進、或求得更好的境遇向皇帝獻上祥瑞是自古以來官場中就很常見的事情。將其作為理解詩歌的例證,甚至是延伸為判斷某人品格高下的證據,就很難保證不陷入理解的誤區。
楊億等人所作《漢武》組詩的確有堆砌辭藻之嫌,但真正的用意卻不是炫耀學識,更多是追求“下以詩諷上”的現實目的。羅盛鳴先生曾指出楊億并不反對真宗封禪,就宋人所著《儒林公議》的記載來看,事實并非如此。書中記載:“楊億雖以辭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為利變。……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為本。復為邪佞所排,眷寵浸衰矣。”《儒林公議》為田況所著,其人為仁宗天圣八年進士,著者官至樞密使,其書對太祖至仁宗朝野之事多有記載。根據此書所記,楊億在朝廷討論封禪時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意見,認為“不若愛民息用為本”。根據書中記載,楊億對于“朝廷議封禪”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并直接導致失寵于真宗。
問題討論至此,我們不禁會產生如此的疑惑:為何楊億的言行存在不一致之處?究竟何種面貌才是最真實的楊億?
這種現象在中國傳統文人的身上并不罕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極為普遍的情況。一方面,他們將自己作為圣人的弟子,希望逢遇明君、實現“得君之助”的夢想,從而完成“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臣下的身份和僚屬的地位使得他們只能仰人鼻息,在不斷揣測圣意的宦海沉浮中度日。二者的緊張關系塑造了士大夫階層微妙的心態:當他們憧憬著宏圖大志時就會留下“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的詩句;而當他們陷入人生迷茫時,又會寫下“古來圣賢皆寂寞”的嘆息。當詩歌不再作為外交辭令時,詩人們往往是將其作為療治心靈創傷的藥劑。正如弗洛伊德所說:“一個幸福的人從來不會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難以滿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動力是尚未滿足的愿望,每一個幻想都是一個愿望的滿足。”[14](P2)對于楊億而言,修齊治平的人生愿景早已被真宗“鎮服四海、夸示外國”的追求所摧毀。于是,寄居于“昆山之西”、“藏玉之室”的生活就是他最理想的選擇。但他卻無法超脫于“西祀”、“東封”的現實政治,轉而以詩為諷喻的工具訴說自我對現實的看法。一組《漢武》唱和詩講述的故事看似是典故的炫耀、辭藻的堆砌,實際卻是對現實最直接的控訴。詩中所謂“神仙”事并非是指漢武帝求仙訪藥的史實,而是直指真宗導演的種種鬧劇背后“引天命以自重”的真實目的。
楊億以《漢武》詩諷喻真宗并非他個人行為,我們可以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尋覓到相同題材的詩作。以崔遵度和楊億《屬疾》詩為例:
李白羹初美,相如渴漸療。八磚非性懶,三昧減心憂。筆苑多批風,詞鋒勝解牛。
舊山疑鶴怨,畏日想云愁。廣內勞揮翰,通中羨枕流。使星方屢降,客轄未容投。
好奏倪寬議,何須莊舄謳。朝衣熏歇不,侍史待仙洲。
此詩多用典故,帶有濃厚的“西昆體”色彩。崔遵度所用“倪寬事”語出《漢書》,是勸喻楊億順從真宗心意——即附和封禪事。可見當時士人對真宗封禪的認識是清醒的,而他們對楊億反對封禪的態度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將《漢武》唱和組詩認定為諷喻真宗西祀東封當無疑義。
[參考文獻]
[1]李慶甲匯編校點.瀛奎律髓匯評·卷上[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7.
[2]王仲犖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1.
[3]鞏本棟.關于唱和詩詞研究的幾個問題[J].江海學刊,2006,(3):166.
[4]羅爭鳴.<漢武>唱和詩述議——兼論<西昆酬唱集>的緣起與特征[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26,27.
[5]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J].歷史研究,2004,(1):165.
[6]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J].上海:三聯出版社,2006.298.
[7]脫脫.宋史·王旦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8.1329.
[8]司馬光.涑水見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9.120.
[9]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上海:三聯出版社,2006.322—323.
[10]朱弁.曲洧舊聞[M].北京:中華書局.2002,88.
[1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
[12]方智范.楊億及其西昆體再認識[J].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6):6.
[13]王應麟.玉海[M].上海書店出版社,1987.3609.
[14]胡經之,伍蠡甫.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讀·下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2.
[責任編輯:王守雪]
中圖分類號:I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238(2016)01-0069-05
[作者簡介]陳夢熊(1984—),男,湖北恩施人,西南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
[收稿日期]201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