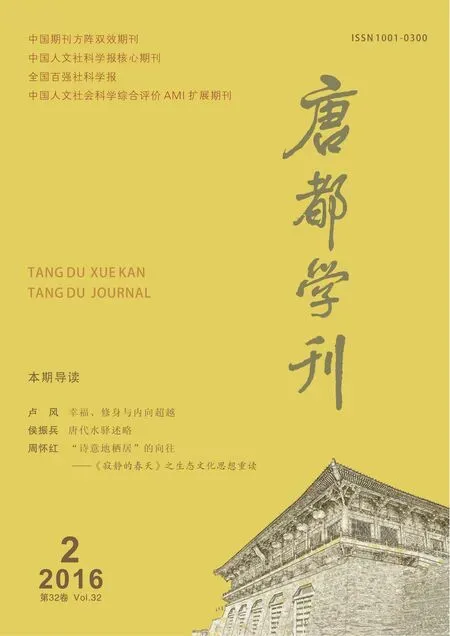洋務派的中西文化觀
——西學中源說與中體西用論之探析
劉錦權
(華中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近代史所, 武漢 430079)
?
【歷史文化研究】
洋務派的中西文化觀
——西學中源說與中體西用論之探析
劉錦權
(華中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近代史所, 武漢430079)
“西學中源”說與“中體西用”論是晚清兩種相似的理論范式,鴉片戰爭后,這兩種理論同時萌芽,至洋務運動晚期臻至成熟。這一過程中,二者既相互糾纏又相互促進,以不同的方式調適了中國近代社會。細觀這兩種理論,既有一致性也有差異性,如果加以比較,“中體西用”似乎更符合歷史演進規律,它匯通中西,調和新舊,滿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在實踐方面的引導,更是“西學中源”說的隨意比附所不可比擬的。
洋務派;西學中源;中體西用;比附探析
一、“西學中源”說在近代的演變與發展
(一)“西學中源”說的萌生
在鴉片戰爭失敗的刺痛下,一批有識之士如林則徐、徐繼畬、魏源、梁廷枏等,以知識分子的敏銳,深切感受到了西方不僅在器技層面領先中國,文化層面也在實踐著中國遠古的三代之治,繼而紛紛著書立說以介紹西學,給沉寂的中國思想界注入了一絲新鮮的氣息。在這一過程中,“西學中源”說開始重新流傳開來,既表現為用以比附的中學程度的加深,又表現為西學內涵的擴大。一時間,無論是開明士大夫還是守舊派,洋務派或者早期維新派,都把“西學中源”說看成是理解中西文化關系的紐帶,并以此作為闡述自己觀點的理論依據。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士大夫們已經意識到中國面臨的情況不再是傳統的“夷夏之辨”,而是千年未有之巨變。所以,他們主張“制洋器”、“采西學”,邁開了學習西方的步伐,洋務運動隨即開始。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廣、歷時最長的一次近代化運動。但它所倡導的內容對于傳統中國人來說是新生的,注定要受到來自傳統的阻撓和責難。“歷史已經證明,破除傳統的習慣勢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價值觀一旦形成,便具有極大的穩定性,它深深地根植于人們的頭腦中并指導人們的行為。”[1]為了減輕這種舊的傳統勢力的壓力,洋務大員們便試圖憑借“西學中源”說來化解矛盾,論證學習西方的可行性與合理性。他們首先指出西學“源出老子墨子”,然后又假想了中學西傳的途徑:“迄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碩彥抱器而西,致海外諸邦”[2]74。遂提出“禮失而求諸野,此其時也”的口號。這種天馬行空的臆想雖讓今人啼笑皆非,但在當時卻被相當一部分趨新人士所接受,原因在于這種臆想滿足了他們的虛榮心,又順應了時勢的發展,為引進西學提供了契機。
(二)“西學中源”說的發展
1866年,總理衙門試圖在同文館增設一個天文算學館,“招收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歲以外者”,“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年少聰慧愿入館學習者”。*參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這一舉措的目的在于訓練科甲人員和青年官吏,挑選一部分聰明子弟研習西方算學和聲光化電,為洋務新政培養人才。然而這一倡議在清廷內部卻遭到了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守舊派猛烈攻擊。這場由是否設立天文算學館而引起的爭論,很有趣味性:奕與倭仁在精神層面,都認為中國傳統的典章制度優于西方,但在是否引進上卻表現不一,尤其是在關于西方的歷法、數學、天文等自然科學知識問題上更是勢不兩立。倭仁等反對開辦天文算學館,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參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堅守“夷夏之防”,代表著全盤否定西方文化的中國舊知識分子的立場,流露出強烈的文化守成意識。針對守舊派的論調,奕首先反駁了他們以向西方學習為恥的觀點,“天下之恥,莫恥于不若人”,接著又以“西學中源”說為依據,指出采用西法并非就是“舍中法而從西人”,而是繼承中華燦爛的古代文明:“查西術之借根,實本于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猶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情性縝密,善于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術如此,其余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中國儻能駕而上之,則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匪淺鮮”[3]。這是典型的西學中源說,“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實為“西學中源”說定了調,代表了中國傳統士子中務實開明派兼收西方科學知識的一面。一時間,“西學中源”說成了朝野上下共同的話題,這為洋務運動時期思想文化開辟了新的方向。
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派,雖與李鴻章、張之洞屬于同一時期,但他們的思想在很多地方都超越了洋務大員,在提倡西學方面,他們要學習的內容已經牽涉到西方的制度層面,由于他們和洋務派生活的年代大致相當,部分思想與洋務派重合,部分思想又受到洋務思想的啟發而有所超越,分析他們的文化觀,可以看到洋務派思想的一個側面,尤其是在關乎中西文化關系的論述上。
馮桂芬曾指出:西方的天文歷數、光學,甚至民俗政治都源出于中國,“中華扶輿靈秀,磅礴而郁積,巢、燧、羲、軒數神圣,前民利用所創始。諸夷晚出,何嘗不竊我緒余”[4]。馮桂芬雖未言明緣由,但“前民所創始,諸夷晚出”中已蘊含有西學中源思想。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馮桂芬等已不滿足于西洋器技層面,而是在此基礎上謀求社會改革,提倡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同時為尋求合理的法理依據而將中國傳統與西方制度相比附。“泰西院之法,本古人懸鞀建鐸、閭師黨正之遺意,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即孟子所稱‘庶人在官’者。”并指出這是“英美各邦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海之根源也。”[2]107這種認識的指導思想仍是西學中源式的,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人已在這一思維模式的指引下拓展了文化的視野。王韜與馮桂芬論調相同,認為西方的禮樂、文字等都出于中國:“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他若祖沖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旋機自運;楊幺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中國為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5]這里王韜“西學中源”已經到了很自大的地步,不僅西方的火輪,而且文教典章都由中土而出。陳熾也說:“中國自格致無傳,典章散佚,高明沉潛之士,皆好為高論,而不知自蹈于虛無,遂使萬古名邦,氣象苶然,將為印度之續。天惻然憫之,皇然思所以救之,乃以泰西各國所竊中國古圣之緒余,精益求精,還之于中國。中國之人,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乃強分彼此,疑而卻之,竊以為非計也。”[2]126認為西方偷竊了中國古老的技術然后專研才有了今天的局面,但是到了今天,西人已忘記了當初東學西傳的恩情,并強分東西,在這里陳熾表現出了矛盾的心態,既不滿于中國現狀,欲向西方學習,又擺脫不掉華夏至上的傳統觀念。當然,這已不是陳熾一人的思想,而是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普遍困境。
(三)“西學中源”說的成熟
《盛世危言》是鄭觀應的杰作,因其特有的中西論而成為這一時期“西學中源”說的代表作。在此書中,他大講“西學中源”說,從光學、物理學、化學、電學等方面出發,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西方科技皆來自中國。在他看來,中華文明為各國文明的源頭,不僅“星氣之占始于臾區,勾股之學始于隸首,地圖之學始于髀蓋,九章之術始于《周禮》”[6]274,就連西方近代的化電聲光諸學也均出自中國,“一則化學,古所載爍金腐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此化學之出于我也。一則重學,古所謂均發,均懸輕重而發絕,其絕也莫絕。此重學之出于我也。一則光學,古云‘臨鑒立影’: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鑒大影亦大,遠中所鑒小影亦小。此光學之出于我也。一則氣學,《亢倉子》:‘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此氣學之出于我也。一則電學,《關尹子》:‘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亦可為之;《淮南子》:‘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此電學之出于我也。”[6]274-275這種化學、光學、重學、氣學都出于我的論述,是近代最為典型和代表的“西學中源”說。在此基礎上,鄭觀應還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指出中學失傳后為西人竊取,“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冬官》一冊,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6]242-243先指出了中國較早觀測、記錄和總結出關于成像、冶金、雷電現象,再分析西方光學、化學、電學等具體科學的原理,看似有禮有節,實則矛盾百出,強行附會,不問邏輯,甚至臆造邏輯,違背了自然科學的規律,稍有科學常識和歷史知識的人都能看出其破綻。另外,他是否真的掌握了中國古代原始科學知識和西方以邏輯分析為主的近代科學知識也是令人懷疑的。但這些都不是問題,可視為一種策略、一種引進西學的特有手段。西學中源就是以這種特有的方式促進社會進步的,近代中國社會的獨特性也恰在于此。這不能僅僅理解為早期維新派的一家之言,它應是這一時期中國有識之士的共同思維范式。
“西學中源”說之所以會在洋務時期盛行一時,并成為一種中西文化觀,根源就在于這一學說解決了洋務派所遇到的一個重大的思想或理論難題,既要“制洋器”、“采西學”,又要應對守舊派“以夷變夏”的攻擊。可以說,“西學中源”說既為洋務派傳播西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又爭取了廣大士人對學習西學的理解和同情。
二、“中體西用”論的成熟與變形
(一)“中體西用”文化觀的萌生
大多數大學生參加志愿服務活動都是選擇在自己大學生活的空余時間,只有時間條件的允許,大學生們才可能有機會去參加志愿服務活動。那么,這就要求參與者們合理選擇利用時間,為了志愿服務活動能夠順利地保質保量地完成,他們會在活動開始前對時間做一個充分的安排。所以,多參加志愿服務活動,有利于大學生培養時間意識,樹立珍惜時間的態度,并在此基礎上把時間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化。
鴉片戰爭前后外強挑釁所引發的嚴重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構成了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因素,也刺激著愛國志士去探求自強御辱之道。以魏源和林則徐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發出了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為挽救民族危機,他們積極主張學習西方的強國御辱之道。從“造炮不如購炮,造舟不如購舟”[7]391,發展到“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備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輪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選閩粵巧將精兵以習之,工匠習其鑄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7]324。這兩段話有一個認識深淺的問題,也有一個學習深入的傾向,他們察夷情,辦洋務,希望能使“西洋之長技盡為中國之長技”,增強清王朝御敵的能力。這種觀念和思維開創了近代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挽救民族危機之先河。
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本察“夷情”、學“夷技”的著作。但魏源卻在該書中專門開辟一節論述揚光先申斥天主教的《辟邪論》的文章,這固然有反襯該書向西方學習的主調,但更多是為了說明他的中國“情懷”和傳統根底,中國的孔孟之道才是他的“根本”所在和安身立命之處,并且這一“根本”在他的思想中是占據絕對地位的。學西學反而成了解燃眉之急的舉措,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鞏固清政權的統治。這表明在魏源等先進士大夫心目中,西洋諸國與華夏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中國為主、西洋為輔的觀念是不可動搖的,中國仍是上邦之國,西洋仍是下邦之臣,與傳統的“夷狄”沒什么兩樣;西器雖有可師之處,然器物背后的學術卻無學習之必要,中學和西學是不可比擬的。以上的論述透露了一個信息,即這一時期的仁人志士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仍然是“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秉持著鴉片戰爭前官方的立場,但走的路徑卻是洋務派的“中體西用”。
(二)“中體西用”文化觀的形成
李鴻章是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他切身感受到了辦洋務的必要,認識到了西方堅船利炮對鞏固清廷統治的重要。雖未過多地進行理論創設,但辦洋務的具體實踐卻使“中體西用”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一種思維范式,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張之洞的理論加工,這一范式已經達到了高度的系統化和理論化。李鴻章作為近代中國頗有影響力的洋務巨匠,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8]825和“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8]825的現狀,極力辦洋務,企圖用實力說話,李鴻章在中國近代的價值恰在于此,他以其卓越的洋務業績不但對中國的近代化有所貢獻,而且在無形中實踐了“中體西用”論,使其走向完善,“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折附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參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頁。。這是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函中的一段話,從學習外國“利器”到師其“制器之人”和“制器之器”,再從師其“制器之人”和“制器之器”到“專設一科取士”,這種深入遞進的西學路徑邏輯性非常強。可視為西學走向深入的典型例證。然而李鴻章畢竟是從舊營壘中分化出來的,他在創辦洋務企業,開設學校,派遣留學生的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羈絆。“中學”在其心目中仍然是不可動搖的,他們學習“洋學”的目的也是為“中學”服務的,離開了保衛清廷這一前提,他們的西學是不可想象的。
透過李鴻章的個案分析可展現當時社會思潮的新進展:從認識西洋船堅炮利而致力于引進西方先進軍事器械,進展到認識其自然科學和制造工藝,再進展到認識其富國有方而建議取其經濟模式,在中國實行經濟制度改革,最后承認西方有逾于我國之“學”,這一過程具有更加開放的文化趨向。既然李鴻章已經意識到西方有優越于中國的學術,并且在洋務實踐中已經著力引進,那么,從科技文化的意義上,他的這種觀念和認識,就不是“中體西用”那么簡單了,顯然已具有“西體西用”的意蘊了,然而李鴻章對此卻并不明了,他依然視所學習之物為“末”、為“用”,繼續循著“中體西用”的思維在前進。
馮桂芬的“中體西用”論是開創性的,說馮桂芬是明確表達“中體西用”觀念的人,一點都不為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9]17,可以視為“中體西用”說較完整的表述,這一方面堅持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西學評價的基調,取得了傳統的合法性,調適了人們的心理可承受程度。另一方面,馮桂芬的“本輔”說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提法又有所不同,存在很大差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視西學為異端,雖有部分肯定,但總體上是貶大于褒,馮桂芬的“本輔”說雖襲用前人成說,并非獨特的創建,但從實際動機來看,馮桂芬是要真心實意地采西學,他在論述中所提倡的內容已經突破了“接取其技能”,也不再有“禁傳其學術”之類的說法,有時甚至還突破了自然科學的范圍。他在所著《收貧民議》中明確主張“效法荷蘭設立收養和教育貧民的機構(養貧教貧局),效法瑞典設立強制性義務教育學校(小書院)”[10]。這表明馮氏已經將目光轉向了西方的社會政策和政治制度,并希望中國能夠擇善而從之。1866年,馮桂芬又言:“至西人之擅長者,歷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方能探賾索隱,由粗跡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藍。輪船火器等制,盡羿之道,似亦無難于洋務,豈曰小補之哉?”[9]17在這里,馮桂芬是要把單一的外語學校變為學習西方器物、歷算、理化等的現代化學校。在其表達層面,馮桂芬并未直接言明,顯得比較含糊,他將那些學西學的學校歸之于“輔”的范疇。說到這里,人們不禁要問:馮桂芬為何將“輔”由“堅船利炮”擴展到學校這個層次的?又是如何做的?這里隱含了一個“本”、“輔”的層次劃分:以學習西方以“堅船利炮”為始、為“輔”,然而這一“輔”是與其“本”相聯系的,提及“輔”,必然會順帶涉及其“本”,這就迫使馮桂芬在學理層次調適“輔”的范圍,將“堅船利炮”及其“本”都作為新的“輔”而引入。但他沒有意識到“小書院”和學校其實已是“堅船利炮”的“本”中之“本”了。值得玩味的是,馮桂芬這種不加分層梳理的處理方式,理性層面看似無序,實踐層面卻引導西學不斷深入,即先學習作為“輔”的“堅船利炮”,再學習仍然作為“輔”的“小書院”。最終,“輔”由器物轉向制度并延伸至文化。總之,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之論“中學”與“西學”的關系,雖對傳統說法有所承襲,但更多的是有所變異,它的時代作用在于首創性,即以“中體西用”論來提倡西學并開創出新的范式。可以說,從馮桂芬的“本輔”說起,“中體西用”范式的基本構架已經成型。
(三)“中體西用”文化觀的成熟
張之洞是洋務時期一位重要人物,不僅在洋務實業上成績斐然,理論建樹更是站在了時代的至高點。“中體西用”論的成熟雖有前人的奠基,但若離開張之洞也是不可想象的,張之洞以其優美的文筆、敏捷的思維使“中體西用”論不僅克服了守舊士大夫的防守底線,也取得了清廷的官方認可,同時還贏得了外國列強的一致好感,清廷以官媒將《勸學篇》強行推廣至全國就是最好的例證[11]。使得“長期以來習慣于孔夫子的陳詞濫調下變得死氣沉沉的中國人終于在時代的現實面前蘇醒過來。”[12]《勸學篇》是張之洞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標志著其理論建樹的制高點,“中體西用”文化觀是《勸學篇》的核心,經張之洞的理論加工,其調和新舊、平衡中西的思想內涵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成為了近代中國吸納西方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利器。
三、“西學中源”說與“中體西用”論的關系
(一)一致性
當“西學中源”說在晚清風行于世時,“中體西用”思想也開始流傳。它們都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頗具代表性的中西文化觀,二者互為補充、相互激蕩。綜觀這兩種文化觀,其產生背景、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思維傾向、最終目的以及歷史作用都有相當的一致性。
1.文化背景的一致性
從產生的背景來看,“西學中源”說的重新提出和“中體西用”論都源于鴉片戰爭后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西學中源”說萌芽于明末清初。到雍、乾年間,隨著禁教政策的實行而一度中斷,至晚清時期,又重新流傳開來,具體來講,因鴉片戰爭的失敗,一批有識之士開始正視先進的西方文化,并思考如何正確處理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西學中源”說因而得以復活,并因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呈現出典型的時代特征。“與明清之際‘西學中源’論者更多地從實用層面關注西學不同,鴉片戰爭后‘西學中源’說被重提,主要是受對外戰爭慘敗的現實刺激,源于一種文化上的危機感。”[13]這是一種典型的救亡式的調整和學習,泱泱大國竟被自己一向視為“蠻夷”的小國所擊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前所未有。隨著國門的打開,先進的西方技術和文化洶涌而入,強烈沖擊著中國傳統的各個方面。面對這一“千古變局”,向西方學習的呼聲甚囂塵上,強國御侮成為開明之士的共識。
這一時期的“中體西用”論,雖沒有西學中源論誕生得早,但此時也開始醞釀和萌芽。鴉片戰爭以前,歷史上中外文化的交流并非沒有,但這種交往是局部性的,中國人對外來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認可的,更談不上文化觀上的接納。但鴉片戰爭后情況則有所不同,千古變局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西方技術的進步和文化的先進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中國在這場對抗中繼續墨守成規,必然會遭到更大的失敗。于是,變法自強以求富的呼聲日益高漲。如李鴻章就以日本向西方學習并成功為例子,費盡口舌地上奏陳述“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建議中國積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強國御侮。具體如何做,洋務派遇到了更大的挑戰,守舊派的攻擊甚囂塵上,現實的壓力又刻不容緩,夾縫中“中體西用”論被提出,洋務派以自己的創造力,在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開啟了一條前進的路徑。
近代中國,西方的先進技術畢竟是伴隨著堅船利炮而來,這就使國人在驚嘆其“神技”的同時卻在內心深處對其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抗拒。所以說近代特殊的社會環境決定了國人只有在“西學中源”和“中體西用”的依靠下,才有可能開展學習西器、西技和西方文化,因而,以中學為根底弘揚民族文化,以西學為支節引進西方技術,便成了中國近代開明之士的特有路徑。
2.中西文化處理方式的相似性
從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傾向上來看,二者都采取了一種抑西揚中的方式,為的卻是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為引進西學提供依據和保護。無論是“中體西用”論還是“西學中源”說,所依據的都是華夏文明優越論和中心論的傳統觀念。“西學中源”說否認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人類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其實質是一種民族文化中心主義的反映”[14]。鼓吹者因長期受儒學的浸染而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核心,中國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從這一思路出發,他們在闡述中西文化關系時,就很容易表現出自大和虛驕的心態,把西方文化看成是“我已有之、竊我緒余”;“中體西用”論則將中西文化關系定義在“主”和“輔”、“體”和“用”這一對哲學范疇上:認為中學為“體”,是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西學為“用”,是事物的表象和支脈,本質和內在決定表象和支脈,后者反映前者,這實是為了使西學從屬于中學,從而凸顯出中學的核心地位。
雖然兩種文化觀都表現出揚中抑西的傾向,但在現實中卻具有目的的差異性,細加推敲,便不難發現,表面看似強調了中學,實際卻為引進西學開辟了道路。力圖突破固有的“夷夏之辨”之束縛,為西學的引進提供一個合理的依據。正如王韜所說,“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茍無禮也華則變為夷。”[15]這是王韜對歐洲考察,就夷夏之變得出的新認識,“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將傳統夷夏之辨顛覆,認為西方更懂禮儀,既然更懂禮儀,為何不學習呢,這就為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從學理上進行分析,提供了理論上的合理性和現實中的正當性。
3.最終目的、歷史作用的一致性
綜覽“中體西用”論和“西學中源”說者的著作,并結合晚清的歷史現實,可以看出,雖然二者都將中學置于“源”和“體”的主要地位,而將西學置于“流”和“用”的次要地位,但他們對中學的這種標榜是形式上的,內心深處真正要強調和學習的卻是西學,學習西方文明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無論是“中體西用”論者還是“西學中源”說者,他們并不是要為西學的引進制造障礙,而是希望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和國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來消弭中西文化的壁壘,引導中國社會步入近代,走向文明。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兩種文化觀實際上都是一種為西器、西技引進提供保護的手段。試想象一下,兩千年固守傳統之風洶洶,怎能在一夜之間重見天日,如果不將中學置于主體地位,那么引進西學會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這實為無奈之下的高明之舉。相當一部分“中體西用”論者也大力提倡“西學中源”說,致使二者已經達到了難解難分的地步。因為“中體西用”論在本質上是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文明,但礙于頑固勢力“以夷變夏”論的攻擊和阻撓,不能不迂回前進,“西學中源”說同樣具有此理。
“中體西用”論者搬出了“西學中源”說,結果“‘西學’中那些顯然難以歸納于形下意義的,關乎政教人心的‘西體’方面的內容,便被變相地塞進‘中學’那固有的框架之中,這樣具有雙重的意義:其一,它通過曲折的方式,表達了社會思潮對于近代西方技藝、政教的肯定評價和對社會進行全面變革的初步要求;其二,它以有限度的開放態度,在適合民族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的考慮下,將仿效西方、變革社會的方案限制在不根本突破中國傳統文化本體這樣一種溫和的、不徹底的基本構想模式之內”[16]。中國人就是這樣在學習西方的矛盾沖突中走向深入,“昔者宇宙尚無制作,中國圣人仰視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國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華,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17]這是薛福成的一段話,“中國圣人察,西人效之”,西學因而源出于中國,“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體現的則是向西方學習的一面,如何學習,既然中國圣人最早察之,那肯定是為中國圣人所察看之物為根本,即中學為體。西學源出于中國,中國圣人又最早察之,那么學習西學就應是理所應當的事,不必大驚小怪,這樣一來,態度和目的就達到了理論上的一致性。
(二)差異性
“中體西用”論和“西學中源”說雖然有著諸多的一致性,但它們畢竟是兩種異質的文化觀,從源流和認識水平上都存在著一定的不同之處。“西學中源”說從源流的角度來探尋中西文化的關系,視中國文化為西方文化的源頭,認為西方文化不過是“竊我緒余”;而“中體西用”論者“于中西學源流之辨中,更注重其主體與輔助之別。因而在強調中西學同源的同時,他們也強調中西學的差異與界限,反對事事瑣碎比附的做法,不像一般‘西學中源’論者那樣將中西古今一概混為一談”[18]。這主要是以“體”“用”、“本”“末”范疇為支撐點來論證中西文化的融合匯通問題,附帶性地進行源流考辨。
在中西文化關系的認識上,“中體西用”論較之“西學中源”說更高一籌。以《勸學篇》為例,舉了“西學中源”的例子,但其根本卻是“中體西用”。張之洞曾公開表示:“萬世之巧,圣人不能盡泄;萬世之變,圣人不能豫知”,“謂圣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圣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19]160。西方的技術早已被中國古圣所掌握,西人技術背后的學理也來自于中國古經賢傳,典型的一副西學中源的口氣,但要明白,這段話出自以“中體西用”為核心思想的《勸學篇》,是為“中體西用”論充當腳注,所要強調的是中學的根本和主體地位,而非學術源流問題,可以說在張之洞的論述中,“‘西學中源’論被他自覺地包容到‘中體西用’論的思想體系之內,成為其中有機的組成部分。一方面以它來溝通中西,另一方面又對其加以超越和限定。”[19]160相形之下,“中體西用”論以“體”、“用”模式來會通中西,較之“西學中源”說用源流之辨來解釋中西文化的關系,顯得更高一籌,因為“中體西用”將中西文化看成各有內涵的不同體系,較之“西學中源”的古今不分、事事附會,將中西文化混為一談的做法,顯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里的高,除了理論層面,還體現在對實踐的引導上,較之“西學中源”說的牽強附會和理論抽象,“中體西用”論更有利于實踐層面的操作,從“器、技”開始到制度到文化學理,實行起來更得心應手,中國近代社會的前行更多地依賴于這種實踐操作,而非理論抽象,這也是文明躍進的歷程,在某種程度上,文明是一個實踐的過程,牽強附會和理論抽象是創造不出文明的。文明的演進依賴人的行動,包括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活動和人民群眾的集體行動。這實為一個實踐的過程,近代國人不管是學習西方“器、技”還是文化,都是在進行著這一實踐,思想可以超前,但實踐卻只能一步一個腳印,任何企圖躍過某一階段的實踐路徑都是行不通的,在實踐之前和之中,可以挑選最簡潔的路徑,但卻不能否定實踐本身。中國文明或者世界文明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積累,近代中國的演進尤其如此,廣大學人長期以來關注近代中國的歷史,理論多于實踐,新理論、新思維層出不窮,但很多的是脫離當時中國的實踐,成為閉門造車。“西學中源”就有閉門造車之嫌,“中體西用”巧妙地回避了這一理論困境,它以前后矛盾的邏輯引領中國社會從基層實踐做起,使整個晚清“動”了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體”的范圍不斷被突破,社會也在突破中曲折前進。“中體西用”高于“西學中源”的地方就在于此。
當然,無論是“中體西用”論還是“西學中源”說,都是用非對等的方式來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理論上的缺陷都是明顯的。但是梁啟超說過:“須知凡一種思想,總是拿他的時代來做背景。”[20]所以說,我們應該看到“中體西用”論和“西學中源”說的時代大背景,畢竟是中西文化大規模碰撞初期,先進的中國人對中西文化關系的看法和態度,又是處在一個淺層的認識水平上,能有這樣的認識已屬不易,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衡量標準來評判它們,分析它們。
[1]王魯英.論洋務運動時期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J].齊魯學刊,2001(1):41-44.
[2]趙樹貴,曾麗雅.陳熾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7.
[3]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24.
[4]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97.
[5]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陳恒,方銀兒評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38-39.
[6]夏東元.鄭觀應集:上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魏源.圣武記:卷10[M].道光二十四年古徽堂重刻本.
[8]李鴻章.李鴻章全集:第2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9]馮桂芬.校邠廬抗議[M]∥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0]丁志偉,陳松.中體西用之間[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159.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3.
[12]白權貴,師全民.中國傳統文化概論[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332.
[13]楊錦鑾.比較視野中之晚清“西學中源”與“中體西用”文化觀[J].晉陽學刊,2007:95-99.
[14]馬克峰.文化思潮與近代中國[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117.
[15]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387.
[16]何曉明.返本與開新——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新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04.
[17]丁鳳麟,王欣之.薛福成選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81-582.
[18]曾建立.《格致古微》與晚清“西學中源”說[J].中州學刊,2000(6):146-150.
[19]張之洞.勸學篇[M].李忠興評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0]吳嘉勛,李華興.梁啟超選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33.
[責任編輯朱偉東]
Westernization Group View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Analysis of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and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LIU Jin-qu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wo similar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and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After the Opium War, these two theories appeared at the same time and were matured till the end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got confused and improved each other and adjusted to Chinese modern society in their different ways.A close study showed that the two theories had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seemed more suitable for the history evolution process since it combined China with West, reconciled the new with old, satisfied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practice guidance, was incomparable to th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when it came to random analogy.
Westernization Group;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analogy analysis
K256.1
A
1001-0300(2016)02-0102-08
2015-10-13
劉錦權,男, 陜西西安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