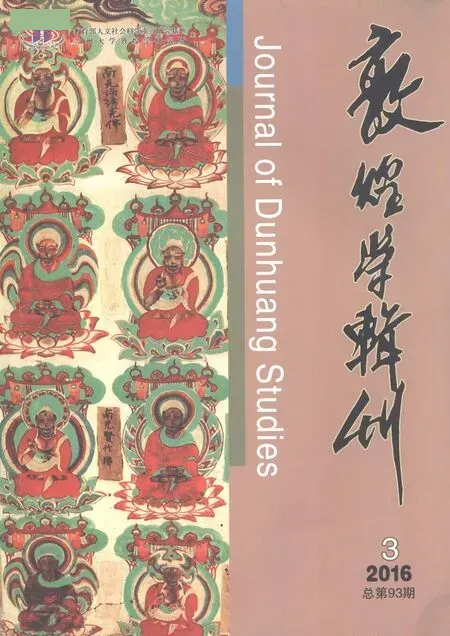中西文化交流視野下的敦煌學
王晶波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本文試圖從文化心態與文化交流的角度,重釋百年以來敦煌文化學術的發展歷史。因中外往來而產生而繁榮的敦煌,也曾因往來中斷而衰落沉寂,最終在新的世界文化交往中,成為絲綢之路上溝通中西、連接古今的重要文化坐標。百余年來敦煌文化學術的發展,也和兩千年的敦煌歷史一樣,深深受到中外文化溝通交流的制約影響。歸納起來看,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學術重要組成部分的敦煌學,其百余年來的發展歷史,可劃分為文化失守、文化保護(保守)、主動出擊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同時又分別對應著自卑退讓、保守自立、自強自信三種不同的文化心態。敦煌學百余年來的興衰歷程,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提出,是中國國力強盛與文化自信的必然產物。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率先走向國際的學科,敦煌學也必將在這一偉大戰略的實施中發揮重大作用。
一、文化失守與敦煌學初興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它與絲路相伴而生,休戚與共。從西漢至宋元的一千多年中,敦煌在溝通中西的道路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華戎所匯的一個重鎮,它的興衰命運也與這條通道緊密相關——當絲路暢通,國家強大,它就繁榮發展;而當絲路中斷,動蕩紛亂,它就衰敗落寞。漢唐之間是敦煌發展的輝煌時期,元明之后,隨著陸上絲路的中斷,它也被世界遺忘,湮滅于歷史的塵沙之中。敦煌再一次被世界矚目,也同樣是因為這條古老絲路的再次連通,焦點則是莫高窟藏經洞文獻的發現與流散。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西陸上交通在沉寂了數百年之后,在一些西方學者及探險家的關注下,這條綿延數千公里,連接古代中國與亞、非、歐的陸路商業貿易外交通道,得到了“絲綢之路”這樣的命名,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不過,這時絲路的“重新發現”是由西方國家所主導,帶給中國的并不是像之前那樣的貿易繁榮與文化交流。西方列強沿著絲路由西而東,挾強大的經濟、軍事、科學優勢,對衰落的東方古國進行文化侵略與劫奪,迫使中華文化一再的退讓與失守,敦煌文獻恰逢此時被發現,也就難逃被劫奪的命運。
從敦煌學的角度來講,這一階段的文化失守,首先表現在敦煌這個漢唐時期的絲路交通重鎮文化重鎮,長期淪落為文化荒漠與游牧之地,直至清初才重新設縣管理,但人口稀少,民生凋敝;其次,與敦煌密切相關的新疆地區的文物文獻被俄德英法等探險家大量劫奪;再次,藏經洞文獻由王圓箓發現并保管數年,看守文化高地的角色,落到一個沒有文化的道士身上,也同樣是文化失守的表現。而中國官府及文人對敦煌文獻的漠視態度,更是這種文化失守的突出表現。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中國傳統社會風雨飄搖之際,封閉許久的國門,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打擊下已然洞開,滿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也行將崩潰。雖然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并努力呼吁,但整個社會及學術文化界,尤其是官僚統治階層,仍處在與世界隔絕的狀態中,在巨大慣性的主宰下,麻木昏瞆,茍且偷安。國力衰弱文化落后,導致整個民族產生一種強烈的挫敗感與文化自卑心理,文化失守就在所難免。
所以,當王道士打開密藏千年的藏經洞,并把這一消息報告官府之后,并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與重視,無論是當時的安肅道道臺廷棟、敦煌縣長汪宗翰,還是甘肅學政葉昌熾等,他們都先后得知了這個消息,并看到了藏經洞所出寫經及佛畫,雖然也贊嘆其珍貴精美,但囿于觀念的陳舊及學識眼力,均未能認識到這一發現的偉大意義,甚至連被稱為“近代圖書館鼻祖”的繆荃孫在親耳聽到伯希和所說藏經洞消息后,也只是把它當作一件“奇聞”來看待。這些堪稱社會知識精英的學者、官員都未能認識到藏經洞文獻的意義,也未有一人對實際情況進行認真的調查了解,說明當時的中國文化學術界,確實已處在一種極度僵化守舊的境地,不僅遠遠落后于世界與時代,不了解時代學術潮流與學術的內容,也失去了鑒別其價值的能力,甚至失去了進一步了解的興趣和行動的意愿。自然,也就不會去保護這些珍稀的文物文獻。
故而,當西方考古家探險家在新疆大肆挖掘古墓,盜割精美壁畫時,人們毫不在意,甚或提供便利;當斯坦因、伯希和將敦煌藏經洞的寶物捆載而去時,學界渾然不覺;當西洋及東洋學者在書肆舊家廣泛搜購古本時刊之際,人們仍視而不見;更有甚者,當1910年清政府將劫余的敦煌文獻調運回北京,沿途屢經大小官吏豪紳的竊取,到京后又遭李盛鐸、劉廷琛等官員的公然盜竊,凡此種種,其實都在說明一個事實,在政治、軍事、文化屢遭挫敗的背景下,整個社會沒有文化自信,沒有文化保護,有的只是一再的退縮與失守,甚至自暴自棄。
可以說,敦煌文獻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吉川小一郞、華爾納們劫掠而流散國外,這個歷史罪責,更多應由那個時代、政府,以及知識文化界,甚至全社會來承擔。王圓箓只不過是那個具體經手的人而已。歷史選中他作為那個文化失守時代的象征,也算是他的不幸吧。
二十世紀初的敦煌文物文獻流散的慘痛現實,激起國人長達一個世紀的強烈文化反應,也從另一面為中國文化學術重新走入世界開啟了路徑。敦煌學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也正是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形成乃至確立的過程。敦煌文獻的發現及敦煌學的建立,為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中國學術界對敦煌文獻的正式認識,有賴于東西方學人的一次交流。這就是1909年秋天法國探險家伯希和與中國學者在北京的著名會面。這次文化交流的實質成果有三:(1)中國學界正式認識了敦煌文獻,并立即開始相關研究;(2)了解到藏經洞的情況,清廷學部將劫余寫卷提調至京加以保護研究;(3)開始了法國漢學界與中國學界的資料交流與研究合作。以這三項成果為基礎,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從此起步。
這次文化交流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實在應該大書特書,它的重要性僅次于王圓箓開啟藏經洞,正是有了這次交流,敦煌文獻才正式為中國學界所知,也才有了后來的敦煌學。因而可以說,敦煌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和國際文化學術交流密不可分。
若說敦煌文獻被劫奪有什么正面意義的話,那就是讓國人真切認識到敦煌及其文獻的重要,刺激起國人的愛國熱情,奮起保護文化遺產,并盡力對之進行研究。
二、文化保守與敦煌學的發展
在敦煌學初興后的數十年中,在文化危機和失守的背景下,國人從文化、學術、對外交往等不同方面,被迫融入世界,學習西方的同時,也對石窟壁畫、文獻文物進行積極的保護與研究。
如果說敦煌學初興階段的研究,還只是一些學者個人的自覺行動的話,民國建立后,越來越多的組織單位或派人去巴黎倫敦轉錄拍攝敦煌文獻,或對國內所藏劫余文獻進行編目整理輯存,或者由政府組織對莫高窟的調查編號,都表明敦煌學研究逐步進入了一個有系統有組織的階段。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標志著以敦煌為首的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正式納入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的范疇。新中國成立后,同樣堅持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的統一領導,為敦煌學研究創造了良好的客觀條件,尤其在敦煌莫高窟保護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這個階段的敦煌學研究,雖然經歷了中國社會發展與政權交替的歷史過程,但就其實質而言,可以概括為文化堅持與文化保守。
敦煌學發展中一個不可忽略的動力,就是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精神。早期的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董康等人的研究及推動有此因素,后一階段的學人也同樣懷著愛國的情懷。無論是劉復、王重民、陳寅恪、陳垣、向達、姜亮夫的歷史、文學、文獻研究,黃文弼、向達、閻文儒、夏鼐等人的西北考察考古活動,賀昌群、何正璜、衛聚賢、謝稚柳等人的藝術研究,以及王子云、吳作人、關山月、張大千等人的壁畫臨摹與藝術考察,其根底里,都有世危時艱的情況下搶救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初衷,這個動力支撐著幾代學人或遠涉重洋,去歐洲抄錄文獻拍攝照片,或在國內整理劫余文獻,或沖沙冒雪,去敦煌臨摹壁畫,在艱難條件下不斷取得成就。民國的短短幾十年中,敦煌學與中國現代學術能夠全面進步,從學術體系的創立,研究領域的拓展,到研究資料的取得與運用、研究方法的創新,等等,除了時代潮流、國際交往、學術自身因素等方面的影響之外,愛國情懷與民族主義精神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與保守。
這時期的學者,無論是固守傳統反對西學的人,還是思想開明接受新知的人,在面對敦煌文化藝術時,所體現的文化態度其實是相當一致的。比如常書鴻,他在巴黎了解到敦煌莫高窟及其藝術,受其吸引而回到戰亂中的祖國,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受命組建敦煌藝術研究所,從此便守護在敦煌莫高窟,從事敦煌藝術的研究與保護,無論家庭變故還是世事變遷政治動蕩,都未能動搖他的決心。他后來被譽為“敦煌的守護神”,“守護”二字,正貼切地反映出那一時代敦煌學以及中國文化學術研究的實質使命。
新中國建立至文革前的一段時期,在激進的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目標下,敦煌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實際上也同樣表現出文化保守的特點。首先,伴隨著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掠奪的批判,敦煌劫經史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材,包括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華爾納在內的外國探險家的文化劫奪行為一再受到揭露與批判。其次,敦煌學研究的中外合作交流也大多中斷,中國學者在一個逐漸封閉的條件下進行獨立研究;再次,研究領域較前有所收窄,一些領域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成為禁區,諸多成名學者的研究未能在以往基礎上繼續拓展,而是集中在對早期已有成果的結集出版與修訂上。有關文物保護、考古、史地、語言、經濟、社會和科技史料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進步,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得到全面的加固維修,一改以往任其頹圮的局面,是當時最重大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舉措之一。
比較極端的“文革”時期,中國的學術研究,包括敦煌學在內,幾乎全都趨于停頓。因此也就談不上什么特點。
可以說,在敦煌學從起步初興后的五十多年發展中,無論是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時間里,無論在前期國際交流合作條件下敦煌學的全面展開推進,還是在后來隔絕封閉下的局部深入,構成其總體基調與特點的,就是對民族文化的堅持與保守。這比起前一階段的不自信與失守,無疑是一個進步。
三、文化自信與敦煌學走向世界
1976年之后,伴隨著中國社會整體的改革開放,國人認識到與世界的差距,中國的文化學術從不同的方面奮起直追。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人文學術領域中最先具有國際學術視野與國際交往的學科,敦煌學也就率先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代表與先鋒。
敦煌學重建時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敦煌學重建也與中華民族的復興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說前一時期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動力是對“傷心史”的回應,這一時期的動力則是對所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說法的回應。這種回應,表面看來雖然仍是愛國主義的表現,但實質上已經超越了普通意義上的愛國主義,隨著改革進程和國家的強大進步,這一時期不再將敦煌看作一個孤立的文化遺存,而有了更加廣闊的胸懷與視野,將其看作整個絲綢之路上中西交通的一個節點,是中華漢唐文化強盛、繁榮、包容、開放、進取的象征。三十年來敦煌在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心中享有如此高的地位,也和中華民族渴望復興的愿望和對它所象征的這些精神的向往有關,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再回頭看百年前的劫奪史時,心態不知不覺中已變得平和了許多,不再只從一國一族出發,而是從人類的角度全面看待敦煌文化,這是中國恢復其大國文化自信,走向民族復興的精神自信的表現。
出于這種回應,中國的敦煌學從國家到學者個人都顯示出極大的熱情與自覺,很快完成了敦煌學研究從恢復到重建的進程,并逐漸步入全面繁榮的新時期,在歷史、文學、文獻、語言、藝術、考古各個領域都有可喜的進步,走到了世界領先的位置。
以敦煌與敦煌學為核心,國際間的交流合作分別在不同層面不同領域廣泛展開。作為中西交流的文化標志,有關敦煌歷史、文化、藝術、文獻等各方面的成果,在世界范圍內受到歡迎與喜愛,如大型舞劇《絲路花雨》率先走出國門,從文化藝術的角度帶動了世界對敦煌及敦煌藝術的關注與熱愛,成為展示敦煌文化藝術的使者,為中外文化交流拓寬了道路;敦煌文物壁畫在國內國際的巡回展覽,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藝術的代表,走入歐美的大型美術館,令世人更真切地感受敦煌的魅力。
學術研究的交流,也自80年代起就廣泛開展于中外學者與團體之間,各種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舉辦,參加者十分廣泛,不僅是早期就有敦煌研究傳統的國家地區學者如英法日俄德韓及中國學者的參加,近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廣大絲路沿線的中亞西亞及東南亞國家學者也積極參與,使得這一學術影響迅速擴大加深;各國敦煌文獻文物收藏單位通力合作,在中國國內出版了絕大部分的敦煌吐魯番及黑水城文獻文物圖冊,特別是,近年通過國際協作,建立了“國際敦煌項目:絲綢之路在線”的國際網站(IDP),“目標是使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其他考古遺址出土的寫本、繪畫、紡織品以及藝術品的信息與圖像能在互聯網上自由地獲取,并通過教育與研究項目鼓勵用戶利用這些資源”。這是老一輩敦煌學研究者所不能想象的一個巨大進步,當人們在互聯網上自由獲得這些收藏于不同國家地區的材料并進行研究時,誰還能說敦煌學僅僅屬于一個國家一種文化,而不屬于全世界?這正說明,最好的遺產保護,就是使其重獲世界影響,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
學術研究組織機構的完善與提升,人才培養系統化。1983年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敦煌研究院及一些大學及科研單位專門研究機構的建立,使敦煌學的研究走上了專業化、系統化的道路,培養了大批后備力量。
敦煌學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堪稱集大成的學術成果。資料方面,如大型敦煌石窟與壁畫圖錄的編纂,以及英、法、俄、日所藏文獻以及國內重要收藏單位藏品的影印出版之外,分類文獻的整理釋錄也取得眾多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都比較及時地得到譯介;研究方面,在新老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研究的領域得到充分拓展,在歷史、文學、文獻、語言、藝術、考古、宗教等各個方面取得新的進展與成果,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做到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這時的敦煌學研究,將反思傳統與回應西方結合起來,將證明過去與闡釋當下結合起來,在改革開放意識形態下,著重強調敦煌文化所體現的強盛、開放、豐富,強調民族的融合與中外文化的交流,敦煌及敦煌研究不僅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途徑,也成為海峽兩岸文化合作的一個平臺,在增強中華文化凝聚力與民族發展融合方面發揮著特殊的意義。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最終走出文化自卑與文化保守的階段,顯示出新的文化自信力,勇于走出去與國際學術文化接軌,敦煌學不僅成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象征,敦煌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瑰寶。
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目標為敦煌學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從文化失守、文化保守到文化復興,這是個很大的轉變,其中隱含著社會文化心理由不自信到保守再到自信的重大變化。
而在國力增強,經濟文化取得重大飛躍,中華文化重新獲得生命力的今天,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提出,可看作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與趨勢,是擺脫一百多年來落后失敗的陰影,重振中華文化自信的體現。在一帶一路國際戰略中,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學術重要組成部分的敦煌學,也必將在其中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