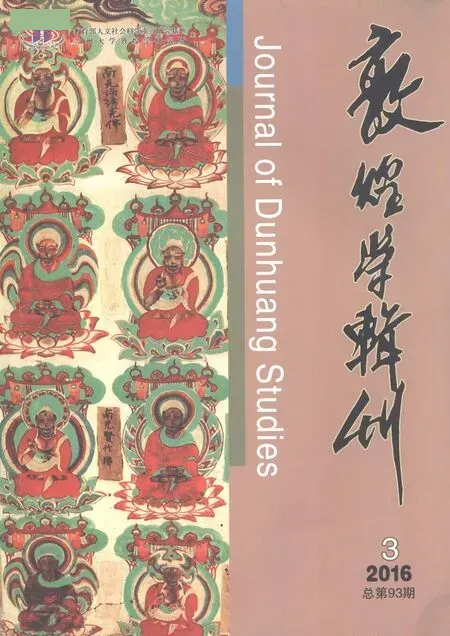也談《佛說要行舍身經》與三階教的關聯
楊學勇
(山西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目前學界基本已認定《佛說要行舍身經》是一部疑偽經,在對此經的整理分析中牧田諦亮認為此經和三階教有相當的關聯,也許是三階教信徒所撰*[日]牧田諦亮《敦煌出土〈要行舍身經〉》,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六),京都:法藏館,1963年,第187頁。,受此影響劉淑芬、曹凌、于淑健等人也基本認為此經與三階教有密切的關系*劉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二),《大陸雜志》第96卷第2期,1998年,第36-37頁。曹凌《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52頁。于淑健《敦煌偽經〈佛說要行舍身經〉考略——兼及與三階教的關聯》,《宗教學研究》2015年第1期,第96-98頁。。最近胡素馨、何珩介紹了德國新發現的一卷《佛說要行舍身經》,并認為“將佛說要行舍身經與隋唐時流行的三階教相聯系從而斷代的論證則需謹慎”*[德]胡素馨、何珩《德國新發現佛說要行舍身經》,《中華讀書報》,2016年4月20日。,對該經與三階教的關系提出了異議。結合學界成果,通過分析三階教的舍身林葬、“普”的特定含義、典籍目錄等內容,筆者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舍身經》是一部宣傳三階教教義的經典,就目前資料看來其與三階教沒有什么特殊關聯。
一、《舍身經》內容主旨及理論依據
布施屬于佛教強調的六波羅蜜之一,可能出現于玄奘歸國的公元645年至智昇撰成《開元釋教錄》的公元730年之間[注]曹凌《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第452頁。的《舍身經》就是一部宣揚布施的佛典。通過對于淑健最新校錄的《舍身經》進行解析,可歸納出該經主旨內容為:在尸陀林中舍身普濟有情,除一切有情饑渴苦,未來當獲正等菩提,一切罪惡,悉皆消滅,并將于龍華初會時得度。此經與布施直接相關的內容可分解為三層意思:其一,舍身尸陀林;其二,分身者所得功德與舍身人功德相當;其三,先死施,待悟得空理之后便能行生施。很明顯,此經強調的是布施身命的內布施,屬于財施中的最上布施。同時,既強調了死施,也強調了生施,并點明生施比死施層次要高。佛典中描述生施的內容較多,其理論依據主要有二點:一是大小乘佛典中記載的佛本生事跡,二是《法華經藥王品》宣揚的藥王菩薩。雖然效法佛本生事跡舍身與模仿藥王菩薩燒身一定程度上都被視作一種苦行,但兩種模式宣揚的舍身側重點實有所不同,佛本生事跡側重的舍身主要是佛前世作為世俗人的舍身,而《藥王品》則主要用于出家人的燒身供養。《舍身經》廣述屬于佛本生的薩埵、月光王、慈力悲王、雪山童子,而絲毫沒有提及藥王菩薩,由此可確定此經的理論依據當是佛本生事跡。
佛本生事跡中有不少涉及生施的題材,代表性的舍身事跡有薩埵王子舍身飼虎、尸毗王割肉貿鴿、雪山童子為半偈舍身等。這些舍身內容大量出現在佛教大小乘經典中,有意無意地影響著佛教徒。研讀《高僧傳》、《比丘尼傳》及《續高僧傳》可知,明確受到佛本生事跡影響的生施在南朝宋時有曇稱、法進、僧富三例,北周普圓一例,隋普濟、普安二例。一些宣揚生施的佛本生事跡也被描繪在佛教石窟中,如僅北周及隋時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就有六幅表現薩埵舍身飼虎的壁畫。[注]李永寧主編《敦煌石窟全集·本生因緣故事畫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7頁。此外,還出現了一些直接以舍身為主題的佛典,如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中就提及《以身施餓虎經》、《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抄為法舍身經》、《舍身記》、《妃舍身記》、《舍身序并愿》、《施曠野鬼食緣記》等等。[注][梁]釋僧祐撰,蕭錬子、蘇晉仁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08、143、232、451、456、480頁。這些都說明最遲到南北朝時生施對僧尼來說已不是陌生的事情。
既然《舍身經》格外強調生施,那么撰述此經的人或教派理應對生施非常重視才對,然而三階教資料中尚未發現有關內容,能找到的并與《舍身經》有關的內容只有屬于死施的尸陀林林葬一事。毫無疑問,屬于死施的舍身林葬在層次上低于強調生施的《舍身經》。
二、三階教的舍身林葬
三階教的布施實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林葬與無盡藏。尸陀林林葬是三階教重要的喪葬方式,信徒去世后舍身尸陀林,尤其是舍身到終南山鴟鳴埠尸陁林所,血肉施生,普濟有情。這屬于施舍身命的死施。無盡藏集中體現著三階教的布施觀,無盡藏法是其理論基礎,內容主要集中在《對根起行法》、《大乘無盡藏法》、《示所犯者瑜伽法鏡經》、日本本《三階佛法》(卷四)中,理論上施往無盡藏的布施物有二種“一者內財、二者外財。內財者即身命,外財者即金銀、七寶、田宅、財物、妻子、奴婢等是”[注][日]西本照真《三階教の研究》(資料篇),東京:春秋社,1998年,第502頁。,但在實際的無盡藏行方面則“側重于財物的施舍,主張在寺院中設置存放施舍物的無盡藏”[注]楊曾文《三階教教義研究》,《佛學研究》,1994年,第81頁。,也就是設置無盡藏機構。無盡藏機構是三階教的慈善中轉機構,信徒先向無盡藏施舍財物,再由無盡藏轉施出去。總體上看,無盡藏屬于施舍財物的外布施,與宣揚施舍身命的《舍身經》有所不同。于淑健認為《舍身經》與三階教關聯的根據之一即是籠統地認為《舍身經》的相關表述與三階教信徒的舍身實踐密合。但由于無盡藏布施與《舍身經》內容不符,同時《舍身經》的確有“舍身尸陀林”這層含義,那么與《舍身經》相合的就只能是指尸陀林林葬。
三階教最早舍身林葬的是教祖信行禪師(540-594),《故大信行禪師銘塔碑》載:“以開皇十四季正月四日卒于真寂寺。即以其月七日送柩于雍州終南山鴟鳴埠尸陀林所,舍身血肉,求無上道。生施死施,大士有苦行之蹤;內財外財,至人有為善之跡……恒欲碎骨于香城之下,投身于雪嶺之間,生事莫由,死將為禮,遂依林葬之法,敬收舍利,起塔于尸陀林下”[注][日]西本照真《三階教の研究》,第39-40頁。,據此可知信行實行的是林葬法。此后很多信徒圍繞著信行墓塔埋葬,漸漸形成塔林,以致后來把終南山梗梓谷鴟鳴堆信行舍身供養處作為三階教圣地。此后,確定實行林葬的三階教徒有靈琛(貞觀三年,629年)、僧邕(貞觀五年,631年)、德美(貞觀十一年,637年)、僧順(貞觀十三年,639年)、慧了(顯慶二年,657年)、P.2550號某禪師(咸亨三年,672年)、尚直(調露元年,679年)、法藏(開元二年,714年)等。[注]可參考楊學勇《三階教史研究——以敦煌資料為主》(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相關內容。鑒于這些三階教信徒舍身林葬,是否就能判定《舍身經》與三階教關系密切,甚至說《舍身經》是在三階教影響下撰述而成的、是一部宣化三階教教義及舍身功德的簡明普及讀本呢?未必。因為舍身林葬并非始自三階教,也不是三階教特有的實踐方式,而是五至九世紀流行的僧侶葬法。
林葬這種喪葬方式源自印度[注]劉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一),《大陸雜志》第96卷第1期,1998年,第23頁。,傳入中國后漸漸被越來越多的僧尼所接受,中國最早實行林葬的僧人是東晉慧遠于義熙十二年(416)“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注][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22頁。。此后,劉宋元嘉二十年(443)尼慧瓊敕弟子“吾死后不須埋藏,可借人剝裂身體,以飼眾生”,后來弟子不忍而“舉著山中,欲使鳥獸自就噉之”[注][梁]釋寶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6頁。;劉宋元徽元年(473)碩公臨去世時跟法進說“‘可露吾骸,急系履著腳。’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后”[注][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第389頁。,實行林葬;慧球“天鑒三年(公元五〇四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注][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第334頁。;梁天鑒六年(507),智順“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注][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第336頁。。這些實例都在信行開皇十四年(594)實行林葬之前,說明林葬早在三階教形成之前即已出現。七世紀以后,僧人林葬的記載明顯增多,但其中有很多僧人不是三階教徒,對此劉淑芬已有統計可資參考,[注]劉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二),第25-31頁。這足以說明林葬不是三階教特有的實踐方式,也不是判定三階教信徒的標準。林葬僧俗數量的增多,劉淑芬認為可能與三階教有密切的關系[注]劉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二),第31頁。。林葬或許是中古時期慢慢形成的風氣,在其形成過程中出現一二種促進因素是可能的,但到底是哪種外力推動了林葬的普及,則只能靠史料推測。終南山梗梓谷是北方一處重要的林葬場所,谷中有兩處有名的地方,即至相寺與信行舍身供養處。至相寺由淵法師創建,是華嚴宗祖庭,約在開皇十五年(595)時由梗梓谷內峽谷遷至原址西南坡阜,即現在的至相寺(國清寺)所在地。信行舍身供養處在梗梓谷口,是三階教的圣地,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之前于此地建立信行禪師塔院(據《大周故珍州榮德縣丞梁君墓志銘并序》)。由于至相寺創建時間比信行禪師塔院早,而且名聲巨大,使得許多僧侶都用至相寺來標示埋葬地,如慧藏、慧海及華嚴信徒劉晏、韓德曜[注]參段志凌《關于長安百塔寺和至相寺寺址問題的說明——與馮賀軍先生商榷》,《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3期,第70頁。馮賀軍《長安終南山至相寺多寶塔善業佛考》,《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第73頁。等,甚至三階教早期信徒也不例外,如裴玄證“生自制碑,具陳己德,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注][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602頁。。這些埋葬在至相寺附近的僧侶很多采用的就是林葬法,如《續高僧傳》記載的慧藏(大業元年,605年)、通幽(大業元年)、慧海(大業二年)、弘智(永徽六年,655年)等。這似乎說明華嚴宗至相寺對林葬的推廣起過重要作用。同時,基于《續高僧傳》可發現,在至相寺附近林葬的僧侶主要集中于七世紀初,而三階教徒的林葬則主要分布在七世紀中葉左右。若說兩者對林葬有影響,似乎至相寺的推動在前,三階教的影響在后。
三、三階教的“普”
牧田諦亮認為《舍身經》對“普”義的重視,顯示其和三階教有關聯。[注][日]牧田諦亮《敦煌出土〈要行舍身經〉》,第187頁。《舍身經》中說:“迦葉波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言在尸陀林普及一切有情。是義不然,不名為‘普’。若是‘普’者,水性有情,即無有分。唯愿如來示我‘普’義。’”佛對“普”的解釋為:若有有情能施身分,分為二分,一分水中,一分陸地。是人命欲終時,囑善知識、同志愿者分割其身以為二分……慈氏合掌即發愿言:“以此微供,普及有情。水陸空行,一切都食。”很明顯,此處的“普”指“普及一切有情”,包括陸地上的蚊蟲禽獸等,也包括水中的魚蝦等,“水陸空行,一切都食”。“普及一切有情”這層意思,其他的宗派或僧人也有類似表述,某些佛典也直接以“普”命名,如《出三藏記集》中提到的《普施經》、《食先普供養緣記》[注][梁]釋僧祐撰,蕭錬子、蘇晉仁點校《出三藏記集》,第162、484頁。等,而三階教的“普”卻有特別的含義,尤其特指普法普敬。
三階教認為第一階根機的人學一乘法,第二階根機的人學三乘法,第三階根機的末法眾生只能學普法,而不能學別法。普法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實際上是一種本體論[注]郭朋《隋唐佛教》,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第233-270頁。又見其《三階教略論》,《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第24-42頁。,認為如來藏、佛性等體是普法,一切凡圣、一切邪正,同是一體,一切凡夫,不管根機上下,學普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如來藏、佛性就是普真普正佛法,就是根本佛法。第二種普法是就普能信仰一切佛乘及三乘法的意義上說的,信行所強調的正是這一含義的普法,人們一般也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信行的普法。信行認為第三階根機的末法眾生想得到解脫,信一個或一些佛,念一種或幾種經,學一種或幾種法,是不夠的。不僅如此,甚至還可能謗佛謗法墮地獄,所以普歸一切佛盡、普歸一切法盡、普歸一切僧盡,必須正學一切普真普正佛法,才能成就真善,獲得解脫。此普法又稱作生盲眾生佛法。
普敬與認惡常常聯系在一起,是三階教的標志性內容。三階教實踐常不輕菩薩,把一切眾生都當佛看待,無問男女都加以禮拜。普敬八法即指如來藏佛、普真普正佛、無名無相佛法、拔斷一切諸見根本佛法、悉斷一切諸語言道佛法、一人一行佛法、無人無行佛法、五種不敢盡佛法。這普敬八法也可稱作生盲生聾生啞眾生佛法或死人佛法。與普敬相對的是認惡,認惡指認自己的惡,惡主要有十二種。普敬認惡簡單地說就是見他善認己惡。由于自他相對,所以不能既敬他善又見自善、不能見自身惡又見他人惡。若自他俱見善,則自見惡不徹底,若自他俱見惡,則敬他善不徹底。[注]參[日]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別篇),東京:巖波書店,1927年,第151頁。
普法普敬是三階教的獨特之處,是判別三階教徒的重要標準。單純地把“普”割裂出來,從“一切”、“所有”、“都”、“全部”等含義理解,并不能說明與三階教有聯系。
四、三階教沒有類似舍身的典籍
三階教典籍目錄乃至相關資料中曾未提及過有類似《舍身經》的典籍,而且三階教教義中沒有對舍身的相關論述。
在經錄及史書中,可以發現許多與三階教有關的典籍目錄[注]楊學勇《三階教史研究——以敦煌資料為主》,第129-144頁。,這些目錄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其一,佛教典籍提到的三階教典籍目錄。開皇十七年(597)費長房上《歷代三寶紀》,在其卷十二《大隋錄》中著有真寂寺沙門釋信行著作“二部(三十五卷,三階記)”[注][隋]費長房上《歷代三寶紀》卷12,《大正藏》第4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102頁中。;唐道宣《大唐內典錄》著成于麟德元年(664),在其卷五《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七》中著有信行著作“二部四十卷,三階集”[注][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5,《大正藏》第55冊,第277頁下。;唐道世《法苑珠林》著成于總章元年(688),在其卷一百《傳記篇·雜集部》中著有信行著作“二部四十卷”[注][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100,《大正藏》第53冊,第1022頁中。;僧明佺等編《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完成于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卷十五《偽經目錄》列有“三階雜法,二十二部二十九卷”[注][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15,《大正藏》第55冊,第475頁上。;唐智昇《開元釋教錄》著于開元十八年(730),在其卷十八《偽妄亂真錄》中列有信行撰“三階法及雜集錄,總三十五部四十四卷”[注][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18,《大正藏》第55冊,第678頁下。。其二,敦煌文獻中提到的三階教典籍目錄。時間上限為永徽二年(651)的P.2412R2《人集錄都目》(一卷)載有三階教典籍目錄共三十四部四十三卷;產生于永徽二年至五代晚期的P.3202《龍錄內無名經論律》中基本能確定屬于三階教的典籍有十部十五卷[注]此乃矢吹慶輝研究成果。見[日]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第176-178頁。;敦研345《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及北新329《見一切入藏經目錄》是長興五年(934)三界寺收藏的佛經目錄,載有一條三階教典籍目錄;P.4039《龍興寺藏經目錄》提到一條三階教典籍目錄[注]陳明、王惠民《敦煌龍興寺等寺院藏三階教經籍》,《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第54頁。;P.3869《金光明寺華手經就衙付平判官記》記載了大量佛經目錄,其中可能涉及八條三階教典籍目錄[注]陳明、王惠民《敦煌龍興寺等寺院藏三階教經籍》,第56-57頁。。其三,日本、朝鮮所著三階教典籍目錄。著于天平十九年(747)至天平勝寶二年(750)之間的日本正倉院文書中列有四部三階教典籍;高麗沙門義天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1090年撰[注]參[日]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第151頁并155頁注(二八)。)在《海東有本見行錄》(下)中提到兩條三階教典籍目錄[注][高麗]義天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大正藏》第55冊,第1178頁中。;日本永超集《東域傳燈目錄》完成于寬治八年(1094),其中載有六部八卷三階教典籍目錄[注][日]永超集《東域傳燈目錄》,《大正藏》第55冊,第1150頁中、1155頁中。。其四,石窟中的刻經。唐高宗龍朔二年至咸亨元年(662—670年)期間[注]張總、王保平《陜西淳化金川灣三階教刻經石窟》,《文物》2003年第5期,第72頁。另外,可參考張總《陜西新發現的唐代三階教刻經窟初識》,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第172頁。的陜西淳化金川灣刻經窟刻有四部明確的三階教典籍。
除信行撰述的三階教典籍之外,在資料中還發現一些其它的與三階教有關的典籍目錄,如下:
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
頓教一乘(廿卷)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序
大乘十輪經鈔
十輪經疏
十輪經音義
分疏
行記
當根破病藥
瑜伽法鏡經(二卷或一卷兼有偽序)
這些列有三階教典籍目錄的資料時間范圍從信行禪師去世不久的公元597年至11世紀末,種類既有列入大藏經的佛典,又有敦煌文獻、石窟刻經,既有國內資料,又有朝鮮、日本資料,所列三階教典籍有多有少,但沒有一部與舍身有關。在已發現的三階教典籍中也沒有對舍身內容的闡述。
五、小結
《舍身經》提到了死施,但同時強調了生施,指出生施高于死施。三階教舍身林葬與《舍身經》包含的“舍身尸陀林”死施一致,但舍身林葬并非始自三階教,也不是三階教特有的實踐方式,進一步說即使林葬與三階教關系密切,也不等于說《舍身經》與三階教關系密切。《舍身經》對“普”的解釋僅是泛泛的表層含義,與三階教所特有的普法普敬沒有關系。同時,在所有的三階教典籍目錄乃至相關資料中曾未提及過有類似《舍身經》的典籍,而且三階教教義中沒有對舍身的相關論述。這些方面劉淑芬等學者基本都已注意到,但仍認為《舍身經》乃至《尸陀林經》和三階教有關聯[注]劉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二),第36頁。,很可能僅是一廂情愿的想法,牽強了聯系忽略了差異。就目前資料看來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舍身經》是一部宣傳三階教教義的經典,其與三階教應當沒有什么關聯。
判斷某件典籍是否三階教典籍,應以三階教特有的教義為依據,普敬、普法、普真普正佛法、別真別正佛法、對根起行、人集錄、三階佛法等獨特用語是判別的關鍵詞,然后再進一步分析這些詞句表達的含義。若僅是一看到這些關鍵詞就想當然地認為是三階教典籍,很有可能也會誤判,如東漢安世高譯《佛說普法義經》雖然內有“普法”二字,但明顯不是三階教典籍。同時,缺少這些關鍵詞,而僅有一些與三階教有關而又不是三階教所獨有的特征,更應總體上綜合判定以確定是否為三階教典籍。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典籍,作為研究三階教的學者往往感情上已經偏向認定就是三階教典籍,生拉硬扯的按上三階教標簽,然而的確難以找到讓人信服的證據。筆者在博士論文中曾認為S.8290A號與S.8290B號可能屬于三階教典籍,而理由僅僅是“此兩斷片具有三階教口吻”[注]楊學勇《三階教史研究——以敦煌資料為主》,第173-175頁。。嚴格來說,就現有資料實在無法證明此兩斷片與三階教有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