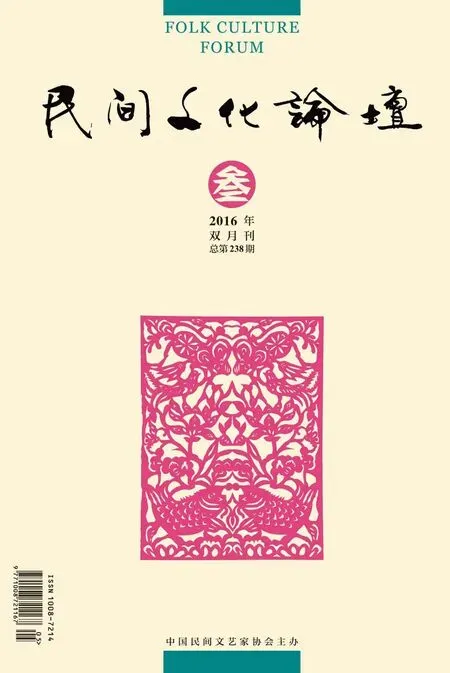童話現(xiàn)象學(xué):苦心孤詣?wù)l愿識?
戶曉輝
民間文學(xué)研究
童話現(xiàn)象學(xué):苦心孤詣?wù)l愿識?
戶曉輝
麥克斯?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在世界童話研究領(lǐng)域獨樹一幟,它不僅使歐洲童話研究大為改觀,也從根本上轉(zhuǎn)變了人們關(guān)于童話的常識和印象。相對于對童話變異規(guī)律的研究而言,童話現(xiàn)象學(xué)對童話不變成分或恒定因素的尋求構(gòu)成了歐洲童話研究的另一種更值得繼承的傳統(tǒng),也是20世紀童話研究的一大特征。盡管這個傳統(tǒng)在當代歐洲已經(jīng)有些式微而且后繼乏人,盡管中國學(xué)者對這個傳統(tǒng)的興趣有限,但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仍然是歐洲童話研究乃至民間文學(xué)研究深刻而寶貴的遺產(chǎn),值得我們重視和發(fā)揚光大。
童話;現(xiàn)象學(xué);形式意志
瑞士著名學(xué)者麥克斯?呂蒂(Max Lü thi,1909—1991)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獻給了文學(xué)研究尤其是童話研究事業(yè)。他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不僅別開生面,而且讓更多的人明白了一個道理:即簡單和幼稚的不是我們的研究對象——童話,而是我們自己;一門學(xué)問是否有深度往往不取決于它研究什么,而是取決于它怎樣研究。套用康德研究專家鄭昕的話來說,呂蒂的重要性在于:在呂蒂之后,穿過呂蒂可能有好的童話研究,而繞過呂蒂只能有壞的童話研究。因為呂蒂的劃時代意義在于:他不僅使歐洲童話研究大為改觀,也從根本上轉(zhuǎn)變了人們對于童話的常識和印象。為了更好地理解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我們必須從19世紀的童話研究開始說起。
一、人類學(xué)派的童話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在歐洲,對童話的系統(tǒng)收集和研究始于格林兄弟。《兒童與家庭童話集》第1版在1812年問世以后,迅速成為歐洲各國學(xué)者收集童話或民間文學(xué)的范例,格林兄弟為童話寫的說明文字,也成為民間文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①戶曉輝:《現(xiàn)代性與民間文學(xué)》,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89頁。格林兄弟對他們從成年人那里收集來的故事做了加工和潤色,使它們更像“童話”,更容易讓兒童接受。換言之,在他們的心目中,童話“風(fēng)格”的標準就是赫爾德意義上的“自然詩”(Naturpoesie),它是民眾的集體創(chuàng)作,也是民眾精神的體現(xiàn),因而不同于個人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詩”(Kunstpoesie)或“人造詩”。①關(guān)于赫爾德的“自然詩”與“藝術(shù)詩”概念及其對歐洲民間文學(xué)研究的影響,參見戶曉輝:《返回愛與自由的生活世界——純粹民間文學(xué)關(guān)鍵詞的哲學(xué)闡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95頁。顯然,格林兄弟對童話的“發(fā)現(xiàn)”和關(guān)注與其說屬于民俗學(xué),不如說屬于文學(xué)或文本研究,但他們的影響卻波及了各個學(xué)科,也就是說,在格林兄弟的影響下,“民間童話得到了一系列學(xué)科的關(guān)注。在我們的時代,它尤其是民俗學(xué)、民族學(xué)、心理學(xué)和文學(xué)科學(xué)的研究對象”②麥克斯?呂蒂:《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戶曉輝譯,即將出版。以下凡引此書,不另注明。。格林兄弟的影響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他們從赫爾德那里繼承下來的浪漫主義情懷為歐洲19世紀的童話研究奠定了基調(diào),這意味著童話更多地被看作其它東西的體現(xiàn)而不是童話本身,因而不同學(xué)科學(xué)者研究童話的角度可以不同,但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往往把目光聚焦在童話之外而非童話自身;其次,格林兄弟在《兒童與家庭童話集》的各版中反復(fù)強調(diào)了一個觀點,即童話是失落的、變形的或碎裂的神話,童話的真正起源是神話。這種觀點對歐洲的童話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并催生出相反的觀點,即認為童話早于神話和傳說,是“最早的敘事形式”③參見Max Lüthi, M?rchen, Vierte Aufl ag, S.60,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tuttgart, 1971。。
無論如何,在格林兄弟對童話與神話關(guān)系的暗示和引導(dǎo)下,19世紀的童話研究者主要關(guān)注童話的來源和演變關(guān)系,即童話的發(fā)生學(xué)問題。發(fā)生學(xué)與進化論的結(jié)合演變出人類學(xué)派的童話觀,即認為童話是人類“童年”的產(chǎn)物,如今的兒童文學(xué)形式——童話是原始人的文學(xué)形式,至少二者存在發(fā)生學(xué)的同構(gòu)關(guān)系。這種童話觀在19世紀非常流行,只消看一看日本和中國對“童話”概念的接受情況,就足以顯示它在當時的波及面之廣和影響之深了。
眾所周知,“童話”一詞非漢語固有,而是20世紀初從日本引進的一個外來詞。④據(jù)考證,最早出現(xiàn)“童話”一詞的文獻是1903年《心理學(xué)教科書》第二篇:“至教授之序,則原造想像先現(xiàn)于兒童之游戲。夫列?別魯氏所以苦心于玩具,黒嚕巴嚕脫氏所以留意于童話,皆為此也。”1907年佚名《論幼稚園》:“談話:每日占半小時。一為寓言及童話,二為事實談話,三為偶發(fā)事項。”參見黃河清編著:《近現(xiàn)代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第744頁。正如周作人所指出:
童話這個名稱,據(jù)我知道,是從日本來的。中國唐朝的《諾皋記》里雖然記錄著很好的童話,卻沒有什么特別的名稱。十八世紀中日本小說家山東京傳在《古董集》里才用童話這兩個字,曲亭馬琴在《燕石雜志》及《玄同放言》中又發(fā)表許多童話的考證,于是這名稱可以說完全確定了。童話的訓(xùn)讀是Warabe no monogatari,意云兒童的故事;但這只是語源上的原義,現(xiàn)在我們用在學(xué)術(shù)上卻是變了廣義,近于“民間故事”——原始的小說的意思。童話的學(xué)術(shù)名,現(xiàn)在通用德文里的M?rchen這一個字;原意雖然近于英文的Wonder-tale(奇怪故事),但廣義的童話并不限于奇怪。至于fairy tale(神仙故事)這名稱,雖然英美因其熟習(xí)至今沿用,其實也不很妥當,因為講神仙的不過是童話的一部分;而且fairy這種神仙,嚴格的講起來,只在英國才有,大陸的西南便有不同,東北竟是大異了。所以照著童話與“神仙故事”的本義來定界說,總覺得有點缺陷,須得據(jù)現(xiàn)代民俗學(xué)上的廣義加以訂正才行。⑤1922年1月21日周作人答復(fù)趙景深的信,見趙景深編:《童話評論》,上海:新文化書社,1934年,第67—68頁。
也許是在周作人的啟發(fā)下,李長之也指出:
童話這個名詞是從日本來的,據(jù)說是在十八世紀中山東京傳在骨董集中首先用的,原來只是兒童小說的意味,在現(xiàn)在自然是特別指著一種文學(xué)上的體裁和內(nèi)容了。
趙景深君曾下了這樣的定義:童話是從原始信仰的神話里轉(zhuǎn)變下來的游戲故事。他這樣說法,也未嘗沒有部分的真實。不過好像限于流傳的傳說的意味。
正當?shù)恼f來,童話在西洋的原名,英文上叫做Fairy Tales,德文上叫做M?rchen,二者的含義有著來源的不同。現(xiàn)在用去并沒分別;但我以為德文字的來源更近于現(xiàn)在所謂的童話的內(nèi)容。而且我現(xiàn)在譯的是德國大詩人的童話,更應(yīng)當明白這個德字的定義。
我查Brockhaus Konversations-Lexikon和Meyer Konversations-Lexicon二書的解釋,還是后者好,我現(xiàn)在就采它的說法:
M?rchen ist diejenige Art der erz?hlenden Dichtung, in der sich die überlebnisse des mythologischen Denkens in einer der Bewusstseinstufe des Kindes angepassten Form erhalten haben.
我譯:童話是敘述詩的一種,那是在適用于兒童的想像的步驟之形式中,把神話的思想之痕跡保持著。
我以為這個定義再確切再好沒有了。在那書的這條底下,還更說這個字M?rchen的來源,是由于古代的德字Maere來的,那意思即是erzahlende Poesien——敘述詩——的意思,在中古,這個字又變?yōu)镾pel。還說,M?rchen有兩種,一是藝術(shù)的童話Kunstm?rchen,一是民間的童話Volkm?rchen。①李長之譯:《歌德童話》,成都:東方書社,1945年,第38—39頁。
以周作人和李長之的觀點來看,首先,漢語“童話”一詞來自日本,而日本的“童話”一詞則是對德語M?rchen和英語fairy tales的翻譯;其次,當時日本和中國的“童話”概念主要接受的是歐洲人類學(xué)派的觀點,即“童話”既是兒童故事,也是原始人思維方式的遺留物。周作人認為,“童話的最簡明的界說是‘原始社會的文學(xué)’。文學(xué)以自己表現(xiàn)為本質(zhì),童話便是原人自己表現(xiàn)的東西,所不同的只是原人的個性還未獨立,都沒入群性之中而已”②1 9 2 2年1月2 1日周作人答復(fù)趙景深的信,見趙景深編:《童話評論》,上海:新文化書社,1934年,第69頁。。李長之在轉(zhuǎn)述了趙景深的人類學(xué)派童話定義之后,又引述了德語詞典上的人類學(xué)派童話觀,即把童話看作一種用適合兒童意識階段的形式保留著神話思維經(jīng)驗的敘事文學(xué)作品。
與歐洲進化論派人類學(xué)者一樣,中國學(xué)者對童話概念的接受和理解同樣受到浪漫主義情懷的驅(qū)動,但本文關(guān)注的要點不在于此,而在于強調(diào):在中國童話研究開始起步時,進化論派人類學(xué)的童話觀起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③不僅童話研究,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xué)或民間文學(xu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人類學(xué)派的影響下開始起步的,正如鐘敬文所說:“我年青時在踏上民俗學(xué)園地不久,所接觸到的這門學(xué)科的理論,就是英國的人類學(xué)派,如安德留?朗的神話學(xué),哈特蘭德的民間故事學(xué)等。不僅一般的接觸而已,所受影響也是比較深的”;“從我國早期的民俗學(xué)理論思想史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學(xué)壇上露臉的學(xué)者們,如周作人、江紹原、茅盾、趙景深和黃石等,大都是這一派理論的信奉者、傳播者、乃至于實踐者。我不過是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罷了”(鐘敬文:《從事民俗學(xué)研究的反思和體會》,《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98年第6期)。20世紀初,周作人將人類學(xué)派的童話觀用于中國文獻的研究,他把中國的世說和志怪視為童話,認為“童話(M?rchen)之源蓋出于世說(Saga),惟世說載事,信如固有,時地人物,咸具定名,童話則漠然無所指尺,此其大別也”①周作人:《童話研究》,原載《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見周作人《兒童文學(xué)小論》,上海:兒童書局,1932年,第19頁。。因此,“中國雖古無童話之名,然時固有成文之童話,見晉唐小說,特多歸諸志怪之中,莫為辨別也”②周作人:《古童話釋義》,原載《紹興縣教育會月刊》1914年第七號,1914年7月,見周作人《兒童文學(xué)小論》,上海:兒童書局,1932年,第39頁。。不僅如此,在談到童話對兒童的教育功能時,他還指出:
童話作于洪古,及今讀者已昧其指歸,而野人獨得欣賞其在上國,凡鄉(xiāng)曲居民及兒童輩亦猶喜聞之,宅境雖殊而精神未違,因得仿佛通其意趣。故童話者亦謂兒童之文學(xué)。今世學(xué)者主張多欲用之教育,商兌之言,揚抑未定:揚之者以為表發(fā)因緣,可以輔德政,論列動植,可以知生象,抑之者又謂荒唐之言,恐將增長迷誤,若姑妄言之,則無異詔以面謾。顧二者言有正負,而于童話正誼,皆未為得也。③周作人:《童話研究》,原載《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見周作人:《兒童文學(xué)小論》,上海:兒童書局,1932年,第34頁。
童話之用,見于教育者,為能長養(yǎng)兒童之想像,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聰疾,使在后日能欣賞藝文,即以為之始基,人事繁變,非兒童所能會通,童話所言社會生活,大旨都具,而特化以單純,觀察之方亦至簡直,故聞其事即得了知人生大意,為入世之資。且童話多及神怪,并超逸自然不可思議之事,是令兒童穆然深思,起宗教思想,蓋個體發(fā)生與系統(tǒng)發(fā)生同序,兒童之宗教亦猶原人,始于精靈信仰,漸自推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執(zhí),或得超脫,則但視性習(xí)之差,自定其趨。④周作人:《童話研究》,原載《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見周作人:《兒童文學(xué)小論》,上海:兒童書局,1932年,第35頁。
這里,把兒童等同于“原人”并把童話視為兒童或“野人”文學(xué)的觀點清晰可見。20世紀20年代致力于童話研究的趙景深更是直接接受了人類學(xué)派的觀點,把童話看作神話的蛻變形式或晚期形式:
現(xiàn)在姑且下一個定義,“童話是原始民族信以為真而現(xiàn)代人視為娛樂的故事”。簡單而且明了的說:“童話是神話的最后形式,小說的最初形式”。⑤趙景深:《童話學(xué)ABC》,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根據(jù)世界書局1929年版影印),第4頁。
不僅如此,他還斷言,“從根本的初民心理來觀察童話,是進化的人類學(xué)派的方法,也就是研究童話的正宗”⑥趙景深:《童話學(xué)ABC》,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根據(jù)世界書局1929年版影印),第6頁。。當時,趙景深、張梓生等也注意到“童話”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但他們?nèi)园淹捪薅椤皟和膶W(xué)”。20世紀30年代,呂伯攸仍認為,“童話(Marchens)就是一切憑空虛構(gòu)而成的,與現(xiàn)實距離得很遠的故事,其中所敘的時、地、人物,不必具有確定的名稱。這一類文學(xué)的構(gòu)成,實在還是由于神話和傳說所演進”⑦呂伯攸:《兒童文學(xué)概論》,大華書局,1934年,第56頁。。也就是說,童話是神話和傳說的一種退化形式,它以文學(xué)的形式表現(xiàn)了兒童和原始人的幻想。按進化論人類學(xué)派的看法,人類的種系發(fā)生與個體發(fā)生“同序”,所以,兒童就相當于原始人。
當時也有學(xué)者注意到“童話”這個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上述引文中,周作人從廣義上把“童話”理解為“民間故事”或“原始的小說”;而趙景深在致張梓生的信中明確指出:“甚至我以為Fairytales or M?rchen不可譯作‘童話’二字,以致意義太廣,最好另立一個名詞,免得混淆,你以為如何?”張梓生在答復(fù)趙景深的信中說:“因為童話一個名詞,是從日本來的,原意雖是對兒童說的話現(xiàn)在卻成了術(shù)語,當做M?rchen的譯名;正如‘小說’二字,現(xiàn)在也不能照原意解說了。如恐混淆,便不妨用兒童文學(xué)這個名稱。包括一切。”①均見趙景深編:《童話評論》,上海:新文化書社,1934年,第9頁,第11—12頁。他們兩人又從狹義上把童話限定為“兒童文學(xué)”。這些觀點,與松村武雄的觀點如出一轍:“‘童話’與‘神仙故事’,普通被人用作同樣的意義。但在本書中,是把‘童話’解作‘給與兒童的故事’之意,將一切種類的故事都包括在它里面。所以‘神仙故事’不過是童話的一種而已”②[日]松村武雄:《童話與兒童的研究》,鐘子巖譯,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第70頁。。盡管作者指出了童話與神仙故事的區(qū)別,但仍把童話限于兒童。
由此可見,一百多年來,進化論人類學(xué)派的童話觀支配著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童話的認識和想象,迄今仍決定著我們對童話的定義。《現(xiàn)代漢語詞典》《辭海》等權(quán)威工具書在不斷修訂和再版的過程中一直把“童話”解釋為“兒童文學(xué)的一種體裁,通過豐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張編寫的適合于兒童欣賞的故事”。近年來,只有極少數(shù)專業(yè)學(xué)者采用了新的定義,例如,黃濤在《中國民間文學(xué)概論》(第二版)中指出:
童話又叫“幻想故事”,是一種用“超人間”的形式來表現(xiàn)人間生活,具有濃厚幻想色彩的故事,包括魔法故事與動物故事兩種,以前者為主。③黃濤編著:《中國民間文學(xué)概論》(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176頁。
事實上,德語M?rchen概念的形成與傳到德國的東方故事有關(guān),④Karl Reuschel,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r Volksm?rchen,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3,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3.它有廣、狹兩種含義,廣義上可以指一切類型的民間故事⑤Kurt Ranke, Die Welt der Einfachen Formen. Studien zur Motiv-, Wort- und Quellenkunde, S.2, Walter de Gruyter, 1978.,狹義上則特指那種“沒有時空約束的幻想敘事,其中揚棄了自然規(guī)律而讓奇跡占據(jù)支配地位”⑥Gerhard Wahrig (Hg.), dtv-W?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S.523,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8.,即“童話”。德語的《文學(xué)體裁手冊》中認為“童話是部分地通過口頭傳承、但通常具有套路的散文敘事,其中會‘不言而喻地’遇到奇跡”⑦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Gattungen, Herausgegeben von Dieter Lamping im Zusammenarbeit mit Sandra Poppe, Sascha Seiler und Frank Zipfel, Alfred Kr?ner Verlag Stuttgart, 2009.。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童話的描述性定義中都沒有出現(xiàn)“兒童”這個限定詞。換言之,德語M?rchen的定義絕不限于兒童,而這種定義正與呂蒂等德語地區(qū)學(xué)者對童話的深入研究有關(guān)。
呂蒂討論的“童話”,是對人類學(xué)派童話觀的徹底顛覆,也是對常識意義上的童話印象的根本轉(zhuǎn)變。因此,如果我們不首先改變流俗的童話觀,就不能進入歐洲童話的研究語境,也難以理解呂蒂的論述。在呂蒂看來,童話不僅不限于為兒童創(chuàng)作,更不僅僅是兒童文學(xué),而是對成年人甚至整個人類都具有存在論意義的一種敘事體裁。呂蒂對童話的分析也大大開闊了我們對童話的理解視域。
二、20世紀童話研究的本體轉(zhuǎn)向
呂蒂在回顧童話研究史時曾指出,19世紀的興趣中心是討論童話的起源和含義,20世紀更強調(diào)童話在共同體中的功能(童話生物學(xué))和童話的本質(zhì)特征問題(類型學(xué)、結(jié)構(gòu)研究和風(fēng)格研究),而與這兩個世紀的研究工作相伴隨的是對童話廣泛傳播的原因的探討和假設(shè)。①參見 Max Lüthi, M?rchen, Vierte Aufl ag, S.61,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tuttgart, 1971。如果說19世紀的童話研究大都把童話看作別的東西的產(chǎn)物或影子而沒有如其本然地看待童話本身,那么,20世紀的童話研究則開始向童話本身返回。如果說從前學(xué)者們大多上下求索童話的外部原因和關(guān)系,那么,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學(xué)者收斂目光,“聚焦”于童話本身。當然,這不是說20世紀無人研究童話的外部原因和特征,而是說出現(xiàn)了與以往不同的另一種看待童話的眼光或研究方式。如果說19世紀的研究更多的是在進化論的時代潮流影響下從外部觀察童話如何“變”,那么,20世紀的新眼光則更多的在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的關(guān)照下從內(nèi)部注視童話的“不變”成分。相對而言,前者構(gòu)成了民俗學(xué)的童話研究傳統(tǒng),后者則構(gòu)成了文學(xué)科學(xué)的童話研究傳統(tǒng)。假如沒有這兩種傳統(tǒng),就不可能有呂蒂的童話研究。
當然,芬蘭學(xué)派的研究似乎介于這兩種傳統(tǒng)之間,因為他們的研究主要通過“變”來尋求“不變”。該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卡爾?克隆(1863—1933)自1880年開始對童話做真正科學(xué)的研究,他在父親朱利斯?克隆(1835—1888)的啟發(fā)下,先后發(fā)表了《朱利斯?克隆先生的方法》(1889)和《芬蘭的民俗學(xué)方法》(1910)兩篇文章②[美]阿蘭?鄧迪斯:《民俗解析》,戶曉輝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172—173頁。,并于1926年出版了《民俗學(xué)工作方法》一書,對芬蘭學(xué)派的童話研究方法做了系統(tǒng)闡述。③Kaarle Krohn, 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de, Oslo, 1926.克隆從廣義上把童話理解為“故事”,他的目的是通過對某個童話或故事的所有異文做微觀研究來找到它的起源或原始形式(Urform)。在這個意義上,芬蘭學(xué)派已經(jīng)開始返回童話或故事本身。但是,芬蘭學(xué)派仍然是從工作假設(shè)出發(fā),而不是從童話本身的“事實”出發(fā)。為了發(fā)現(xiàn)某個童話或故事的完整的生活史,他們假定:絕大多數(shù)母題最初都屬于某個特定的童話,然后才移入其它童話或故事。為了發(fā)現(xiàn)這個原始童話(Urm?rchen),他們?nèi)媸占陬^故事的許多異文,然后對這些異文進行分類,按年代分布劃分書面異文,按地理分布劃分民間異文。④Emma Emily Kiefer, Albert Wesselski and Recent Folktale Theories, pp.17-18, Indiana University, 1947.克隆開創(chuàng)的方法得到他的學(xué)生安蒂?阿爾奈(Antti Aarne,1867—1925)以及瑞典的馮?西多(Carl Wilhelm von Sydow,1878—1952)、愛沙尼亞的瓦爾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1885—1962)等學(xué)者的響應(yīng)和發(fā)揚光大。阿爾奈著有《童話類型索引》(1910)和《比較童話研究入門》(1913);馮?西多著有《佩羅的一個童話及其原始形式》(1916)、《地理學(xué)與民間故事的地方類型》(1934)和《遷徙理論評注》(1938);安德森著有《阿普列烏斯的小說與民間童話》(俄文版,1914;德文版,1923)和《國王與修道院長》(俄文版,1916;德文版,1923),他們都對芬蘭學(xué)派的方法有所運用和完善。安德森還發(fā)現(xiàn),童話或故事具有驚人的穩(wěn)定性,復(fù)雜的長故事歷經(jīng)數(shù)個世紀在全世界口耳相傳,卻沒有任何大的改變,因此,他認為,童話或故事類似有機體,它們在流傳過程中保持著自動修正律(Das Gesetz der Selbst-Berichtigung),即能夠自動保持或回到它的最初形式或原始形式。正如呂蒂概括的那樣,“所謂芬蘭學(xué)派的著作常常被看作純粹的民俗學(xué),如今它已經(jīng)擴展為芬蘭—斯堪的納維亞—美國學(xué)派。該學(xué)派致力于證明單個童話類型的遷徙路線、找到起源中心,試圖通過仔細比較所有已知異文來區(qū)分出亞類型的譜系,最終向某個原始形式(原型)或至少是某個基本形式推進。正如威爾—埃里希?波伊克特和其他學(xué)者已經(jīng)指出,這其中隱藏著文學(xué)學(xué)科的一種重要關(guān)切。如今這類研究的熱情以及參與這種研究的人數(shù)都減少了,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大量的材料使這種研究費時耗力,也不僅僅因為人們對是否可能建構(gòu)可靠的原始形式的信心發(fā)生了動搖,而且因為與此同時,研究的興趣(在其它科學(xué)中也是如此)從依附關(guān)系轉(zhuǎn)向了現(xiàn)象本身。無數(shù)的異文可能讓視線離開單個的敘事,今天,我們又更加強烈地感到了單個敘事本身的價值。不過,即使拋開芬蘭人和瑞典人的特殊目標和教條,這些偉大的著作仍然保存著它們自身的價值。它們提供的雖然不是各種童話類型的風(fēng)格史,卻是結(jié)構(gòu)史,正如它總體上被人們理解的那樣。研究某個童話的人,誰也不會忽視這種對相關(guān)類型的全面研究”。
實際上,芬蘭學(xué)派的觀點在20世紀初的歐洲引發(fā)了諸多思考和討論,也啟發(fā)歐洲學(xué)者關(guān)注童話自身的特征和不變成分。例如,在論文方面,1909年,阿克塞爾?奧爾里克(Axel Olrik,1864—1917)在《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史詩律》一文中把民間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共同規(guī)則稱為“史詩律”,并且為包括童話和傳說在內(nèi)的歐洲民間文學(xué)總結(jié)出諸多規(guī)律,如開場律、收尾律、重復(fù)律、對立律、單線性(die Einstr?ngigkeit)、聚焦于主要人物(die Konzentration um Hauptperson)、尾部重量(das Achtergewicht)等。①Axel Olrik, Epische Gesetze der Volksdichtung, in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s Altertum und deutsche Literatur,51. Bd., 1. H., 1909.其中有些術(shù)語被呂蒂直接采納。1924年,弗里德里希?馮?德爾萊恩在《論童話的形式問題》一文中指出,太初是混亂,最早的童話表現(xiàn)為松懈的形式,即對形式的追求,以對抗過于強大的混亂和任性,民間文學(xué)作品向我們顯示的只是這種對形式的追求,而不是形式本身。②Friedrich von der Leyen, Zum Problem der Form beim M?rchen,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79-80,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3.1926年,弗里德里希?潘策爾在《童話》一文中指出,童話一般并不通過精神聯(lián)系和倫理思想來發(fā)展并聯(lián)系情節(jié),童話情節(jié)的原理是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它的因果關(guān)系是“魔法的因果律”,因此,精神因素在童話中不起作用。③Friedrich Panzer, M?rchen,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 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92-93,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3.1939年,維爾納?施潘納在《作為體裁的童話》一文中認為,主人公總是童話中惟一的人物,次要角色、他的朋友或敵人只有為了確保情節(jié)進程才是必需的,一切不直接推動情節(jié)并決定主人公命運的成分都被取消了。要在童話中尋找觀察和評價的細微差別,那是白費心機。我們說的童話以一種發(fā)達的文化為前提。④Werner Spanner, Das M?rchen als Gattung,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 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161-176,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3.這些觀點或許都對呂蒂有所啟發(fā)。
在專著方面,1928年普羅普(1895—1970)出版了《神奇故事形態(tài)學(xué)》,他的“神奇故事”相當于“童話”,所以德譯本譯為Morphologie des M?rchens(《童話形態(tài)學(xué)》)。⑤Vladimir Propp, Morphologie des M?rchens, übersetzt von Christel Wendt, 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1975.他以阿法納西耶夫(1826—1871)編選的俄羅斯童話集為文本對象,研究了童話的不變因素——功能。1929年,安德烈?約勒斯(1874—1946)出版了《簡單的形式》,該書從形態(tài)學(xué)角度研究了圣徒傳說、傳說、神話、謎語、格言、案例、回憶錄、童話、笑話這些“簡單的形式”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在語言中獲得實現(xiàn)的形態(tài)特征。①安德烈?約勒斯:《簡單的形式:圣徒傳說、傳說、神話、謎語、格言、案例、回憶錄、童話、笑話》,戶曉輝譯,即將出版。1931年,阿爾貝特?韋塞爾斯基(1871—1939)出版了《童話理論試探》一書,認為童話是一種敘事的藝術(shù)形式,它除了使用共同體母題(Gemeinschaftmotive)之外,還以決定情節(jié)發(fā)展的方式使用奇跡母題(Wundermotive)。童話通過復(fù)述變成簡單的形式或故事。童話的特征是沒有空間性和時間性,它擺脫了一切物的和人的約束。②Albert Wesselski, Versuch einer Theorie des M?rchens, S.104, S.118, Verlag Dr. H. A. Gerstenberg,Hildesheim 1974;關(guān)于韋塞爾斯基童話理論的詳細討論,參見Emma Emily Kiefer, Albert Wesselski and Recent Folktale Theories, pp.38-57, Indiana University, 1947。1935年,日本學(xué)者松村武雄的《童話與兒童的研究》漢譯本出版,他在書中也指出:“童話是一個藝術(shù)作品,當然也非如此不可。就是:一個童話,非完全隔離了它和別的東西的聯(lián)絡(luò),藉它自身來構(gòu)成渾然的統(tǒng)一體,使和它相接觸的人以安息之念,沒入在它里面不可。若欲如此,童話的結(jié)論,便非完全不是那童話的連續(xù)和連續(xù)到別的故事的東西不可。”③[日]松村武雄:《童話與兒童的研究》,鐘子巖譯,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第127頁.
呂蒂正是在對前人的接受和批判中才發(fā)展出自己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他的文章和書中隨處可見與前人的對話和討論。例如,1943年,呂蒂在博士論文中寫道:“30多年前,阿克塞爾?奧爾里克就說出了這樣的認識:在童話中,屬性是通過情節(jié)來表達的。另一個與此對比的定律是:在童話中,關(guān)系是通過禮物來表達的。這些定律不能逆轉(zhuǎn)。”④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94,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1947年,呂蒂在《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對約勒斯的童話觀做了專門討論,并在“童話研究”一章中對童話研究的學(xué)術(shù)史做了綜述和評價。1974年該書再版時,又增加了一章,專門評述普羅普的結(jié)構(gòu)主義童話研究。實際上,呂蒂的幸運在于他能夠處身于歐洲傳統(tǒng)來思考童話。保羅?青斯利(Paul Zinsli,1906—2001)在為呂蒂《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寫的短評中指出,如果把呂蒂童話研究的提問方式和研究方式與歌德對自然的考察和沃爾夫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對藝術(shù)的考察加以比較,會格外有收獲。⑤Der Kleine Bund, 22. Februar 1948.如果再往前追溯,我們可以把這個思想傳統(tǒng)的根源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xué)。相對于對童話變異規(guī)律的研究而言,對童話不變成分或恒定因素的尋求構(gòu)成了歐洲童話研究的另一種更值得繼承的傳統(tǒng),它也是20世紀童話研究的一大特征。
三、童話文本的選擇或確定標準
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選擇童話或以什么樣的標準確定童話文本。在這方面,他受到一些民俗學(xué)家的批評。例如,盧茨?勒里希認為,呂蒂主要根據(jù)的是《世界文學(xué)的童話》中的書面文本來分析歐洲童話,沒有考慮東方的和原始民族的敘事作品。⑥Lutz R?hrich, Die M?rchenforschung seit dem Jahre 1945, Zweiter Teil, in Deutsches Jahrbuch für Volkskunde, zweiter Band, Jahrgang 1956.塞巴斯提諾?羅尼格羅認為,呂蒂的主要缺點在于他沒有考慮口頭傳統(tǒng)的活態(tài)現(xiàn)實。①Sebastiano Lo Nigro, Die Formen der erz?hlenden Volksliteratur,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391,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3.丹麥民俗學(xué)者本格特?霍貝克曾指出,呂蒂對單個故事中體現(xiàn)的普遍觀念的關(guān)注使他無法從講述人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故事,也使他遺忘了這些單個的故事。呂蒂帶我們爬上了抽象的階梯,在梯子的頂端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大量實例中的形式相似性,但他給自己施加的嚴格限制使他無法透過故事的表層抵達個體講述人的內(nèi)心動機。霍貝克無意苛求呂蒂做原本沒打算做的事情,他只是想表明呂蒂方法的局限,即呂蒂讓我們對創(chuàng)造童話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人們所知甚少。②參見本格特?霍貝克(Bengt Holbek)為呂蒂的《作為文學(xué)作品的民間童話》(Das Volksm?rchen als Dichtung. ?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寫的短評,見Fabula, 17. Band, Heft 3/4, 1976。這些批評可能說出了許多民俗學(xué)者的看法。
然而,呂蒂一再強調(diào),他對童話做的不是民俗學(xué)研究,而是文學(xué)科學(xué)的研究。德語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學(xué)科學(xué),或譯“文藝學(xué)”)深受Kunstwissenschaft(藝術(shù)科學(xué))概念的影響,它們都把重點從純粹的藝術(shù)史或文學(xué)史轉(zhuǎn)向了形式美學(xué)和類型學(xué)研究,而且都有反歷史的傾向。③參 見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Begründet von Paul Merker und Wolfgang Stammler,Zweiter Band, S.195, Zweite Aufl age,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1965。文學(xué)科學(xué)指的不是文學(xué)鑒賞或評論,也不是對文學(xué)的經(jīng)驗研究,而是對文學(xué)的“科學(xué)”研究。這里的科學(xué)不是自然科學(xué)意義上的,而是客觀的人文科學(xué)意義上的,即相當于詩學(xué)或形式主義的研究。它研究的主要不是“變”的東西,而是“不變”的東西,這種東西類似于亞里士多德的“實體”(? ο?σ?α),④庫爾特?蘭克已經(jīng)使用了Substanz des M?rchens(童話的實體)這樣的說法,參見Kurt Ranke, Die Welt der Einfachen Formen. Studien zur Motiv-, Wort- und Quellenkunde, S.7, Walter de Gruyter, 1978。只不過不一定是直接存在于現(xiàn)實之中的實體。
從學(xué)科分工的角度來看,呂蒂認為不同學(xué)科的童話研究不應(yīng)相互排斥和互不信任,而是應(yīng)該相互補充。他十分重視民俗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認為“童話的真正呵護者,既不是文學(xué)科學(xué)家也不是心理學(xué)家,而是民俗學(xué)家”“任何一個從自己的專業(yè)出發(fā)來細心理解童話的人,也會對其它學(xué)科有所裨益。文學(xué)研究者要貼切地解釋民間童話,他就同時也要做民俗學(xué)的研究,而民俗學(xué)者同時也要做文學(xué)史的研究。心理學(xué)家同樣表明可以給這兩門科學(xué)提供幫助,并且本身也能夠得到民俗學(xué)研究和文學(xué)研究的支持。無論單個的研究者還是不同的學(xué)科,都沒有理由互不信任,只有通力合作,他們才能取得最佳成果”。當然,目的不同決定了眼光的不同,而眼光的不同又決定了方法的不同。文學(xué)科學(xué)家呂蒂與民俗學(xué)者的不同首先表現(xiàn)在對如下幾個問題的看法不同:
(1)關(guān)于童話的個體變異問題
民俗學(xué)者一般關(guān)注童話體裁的變異和動態(tài)的流傳規(guī)律。當然,呂蒂也沒有忽視“變”的東西,相反,他完全承認童話的個體差異和變異。在《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他明確指出,“我們關(guān)注的問題在于,描述歐洲民間童話的本性并把握它的功能。童話風(fēng)格的表現(xiàn)形式會隨著講述人、民眾和時期的不同而不同,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可是,仍然存在著童話敘事孜孜以求的一種基本形式。這種形式幾乎不曾純粹地實現(xiàn)過,但它卻無形地閃現(xiàn)在每個童話的背后。活態(tài)的敘事就圍繞著它,在它周圍嬉戲。每個童話中出現(xiàn)的特征,都不能完全符合這種形式。通過對許多敘事的比較,才可能把握真正童話式的本質(zhì)。當某個童話說出了地點、時間和歷史人物的名稱時,只要它還保持童話的結(jié)構(gòu)和風(fēng)格,這個相關(guān)的敘事就仍然是童話。不過,地點、時間和人物名稱是它里面的異物,不屬于真正的童話風(fēng)格;因為童話風(fēng)格具有抽象的特征”。顯然,呂蒂看到了童話的變異情況,但他的目光沒有停留在單純的變異現(xiàn)象之上,因為變化或變異不是文學(xué)科學(xué)家呂蒂要把握的東西,相反,他要觀察的是變中之不變,是變的基底。“單個的敘事具有唯一的價值和魅力,但它同時也具有這樣的優(yōu)越性,即它屬于超出個人而有效的體裁并且分享這種體裁的內(nèi)在必然性。因此,童話把我們帶到民眾與個人的千變?nèi)f化的生活中間,與此同時,也把我們帶到了人類存在的偉大恒量上”。如果說民俗學(xué)者研究童話的變化或變異,那么,呂蒂研究的就是變化或變異“之前”和“之后”的童話①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爾特?蘭克說,民俗學(xué)者恰恰可以在呂蒂止步的地方開始他們真正的研究,參見Kurt Ranke, Betrachtungen zum Wesen und zur Funktion des M?rchens,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 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346,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1973。,“我們有必要試著描述歐洲民間童話的本質(zhì)特征。在本書中,我們不是要尋求單個民族突出的某個比較特征,而是要尋求所有這些突出特征中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這里讓我們感興趣的,不是在敘事者之間和民眾之間能夠觀察到的個體差異;我們尋求使童話成為童話的東西。這種類型絕不會純粹地出現(xiàn)在現(xiàn)實之中。共同的東西被保留下來,而偶然的東西、在個體之間變動的東西則被排除了出去”。實際上,呂蒂要研究的“使童話成為童話的東西”就是童話的本質(zhì),問題是到哪里去尋找這種本質(zhì)?首先,不能從“偶然的東西、在個體之間變動的東西”中去尋找,因為這些東西不是本質(zhì)。其次,不能從尚未完成或尚未完全實現(xiàn)的童話形態(tài)中去尋找。他并非不理解民俗學(xué)家對童話語境的強調(diào),也并非不知道童話會隨時空發(fā)生變異,但他仍然堅持用童話的文本形式或固定形式作為分析的樣本。在這方面,呂蒂的看法與其說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不如說是柏拉圖式的,或者是兩者的綜合,因為他明確表明,他要尋找的“這種形式幾乎不曾純粹地實現(xiàn)過,但它卻無形地閃現(xiàn)在每個童話的背后”“這種類型絕不會純粹地出現(xiàn)在現(xiàn)實之中”。換言之,童話的本質(zhì)是一種理想類型或觀念類型,它不會在任何一個童話中完滿地、充分地實現(xiàn)或展示出來,現(xiàn)實中的任何一個童話都不能密合無間地充分而完滿地體現(xiàn)童話的本質(zhì)。因此,呂蒂把童話的本質(zhì)或理想類型稱為目的形式(Zielform),它是現(xiàn)實中的童話共同趨向并力求實現(xiàn)的目的形式。盡管現(xiàn)實中的童話不能完滿而充分地體現(xiàn)或?qū)崿F(xiàn)這種目的形式,但它們都在圍繞著這種形式“嬉戲”,因而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就是要對現(xiàn)實中的童話進行本質(zhì)還原。在希臘語中,所謂τ?ε?δο?(本質(zhì))也就是決定一個事物之所以是這個事物的外觀或形式,因此,本質(zhì)還原也可以理解為形式還原。
如果把芬蘭學(xué)派的原始形式(Urform)與呂蒂的目的形式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異同。在一定意義上說,它們都是還原或建構(gòu)的產(chǎn)物。呂蒂說的“通過對許多敘事的比較,才可能把握真正童話式的本質(zhì)”,既是他的還原步驟,也是芬蘭學(xué)派的工作方法。換言之,芬蘭學(xué)派和呂蒂都對童話做了“還原”,但方式和內(nèi)涵不同。阿爾奈指出,在確定童話特征的原始形式時要考慮如下情況:到處出現(xiàn)的形式往往比很少出現(xiàn)的形式更原始;在某個更大區(qū)域出現(xiàn)的形式一般比在某個更小的區(qū)域遇到的形式更有優(yōu)勢;還要考慮童話的傳播路線;出現(xiàn)在某個保存完好的異文中的形式比出現(xiàn)在被毀壞的異文中的形式價值更大;那些能夠吸引聽眾感官的情節(jié)保存得更好而且更容易流傳;自然成分應(yīng)該看作比不自然的成分更原始;除了原始特征的自然性之外,研究者在尋找原始形式時還要借助于邏輯一致性。僅僅出現(xiàn)在一個童話中的特征可能比在別的童話中也出現(xiàn)的特征更原始,在某些情況下,特征的相似性也可能出于偶然。①參見Antti Aarne, Leitfaden der vergleichenden M?rchenforschung, S.42-47, FF Communications N. 013,Hamina, 1913。由此可見,盡管芬蘭學(xué)派還原出來的原始形式也是一種觀念的或理想的原型(idealer Archetyp)②卡爾?克隆明確指出,芬蘭學(xué)派用一切標準重構(gòu)出來的基本形式或原始形式不是一個抽象物,而是包含著某個傳說的一切特征的一個已經(jīng)完成的創(chuàng)作,參見Kaarle Krohn, Folklore Methodology,F(xiàn)ormulated by Julius Krohn and expanded by Nordic Researchers, p.119, Translated by Roger L. Welsch,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1。,但他們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而在于尋求童話特征的地理分布關(guān)系和時間先后關(guān)系。芬蘭學(xué)派還原出來的原始形式,在時間上被設(shè)定為童話最原初的形式,類似于傳播和擴散的一種源頭,而呂蒂的目的形式更多地是邏輯上在先而在時間上處于童話發(fā)展階段的最后或終極。在《傳說和童話中的原始形式和目的形式》一文中,呂蒂指出,瓦爾特?安德森認為,通常閱讀一個故事的20 到30個異文就足以讓我們看出它的標準形式是什么。這種形式簡直從我們面前的材料中呼之欲出。但呂蒂的問題恰恰從安德森的問題開始——原始形式是我們從大量異文中得出的還是只有一點一點才能形成的一種敘事類型?標準形式出現(xiàn)在開端還是在流傳過程之中?它是處于開端的原始形式還是只有在發(fā)展過程中才可能發(fā)生的理想形式?通過對瑞典童話個例的分析,呂蒂表明,當一種形態(tài)(無論它是人、動物還是不確定的某物)被人察覺時,它的萌芽中總是已經(jīng)具備了特定的生長可能性,即它具有完全實現(xiàn)的某些可能性。在童話口頭流傳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xiàn)符合童話特征的敘事,也可能出現(xiàn)瓦解童話敘事的相反情況。呂蒂指出,辨認某個原始形式是一項困難的任務(wù)。芬蘭學(xué)派也意識到他們的方法所固有的誤差根源,但似乎仍對這些根源估計不足,因為后來的形式可能完全取代并掩蓋早期形式,因此,呂蒂認為,通過比較各種異文得到某個標準形式可能比得到某個原始形式更容易。呂蒂更贊成阿徹?泰勒(Archer Taylor,1890—1973)等人的觀點,即我們能發(fā)現(xiàn)的只是原始形式的一些要素而不是原始形式本身。經(jīng)過發(fā)展的東西可能是更高級的東西或完滿的東西,呂蒂稱之為目的形式,但它也可能是不完滿的東西,呂蒂稱之為衰落形式(Verfallformen)或碎裂形式(Zerrformen)。因此,呂蒂不是要用目的形式反對原始形式,而是指出,重構(gòu)可能的原始形式有其合理性,但不能成為研究的主要目標。無論是否完滿,每個異文都值得研究,都有其自身的價值,因為它本身就是人的特性、人的藝術(shù)和人的失誤的見證。③參見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199-210,F(xiàn)rancke Verlag Bern, 1970。在這方面,呂蒂具有亞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論思想,正如他在《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所指出:“原始是沒有展開的聚集物”,他要尋求的則是已經(jīng)展開的和經(jīng)過發(fā)展的目的形式,即童話的本質(zhì)。由此看來,芬蘭學(xué)派的原始形式主要是時間和地理意義上在先的形式,它作為“標準形式”的意義也在于它在時間和地理上處于敘事形式傳播的開端,因而才是“標準”形式;但呂蒂的目的形式卻與時間和地理無關(guān),或者說,它是超時間和地理的,它作為標準形式的意義在于,童話作為童話以它為目的。換言之,芬蘭學(xué)派的還原只是“源頭”還原而不是本質(zhì)還原,呂蒂的還原才是對童話的本質(zhì)還原。在博士論文《童話和傳說中的禮物:論這兩種形式的本質(zhì)把握和本質(zhì)區(qū)別》中,呂蒂說:“童話有意不考慮或不建立原始形式。如果要確定童話的本質(zhì),那么,每個純正的民間童話都是合適的源頭,無論它在發(fā)展過程中是否有所變化都無關(guān)緊要。也許民間童話使這些變化歪曲走樣了,也許這些變化恰好被塑造為童話的特質(zhì)——如果按我們已有的理解它恰好符合民間童話這個名稱,它就是合適的源頭。活態(tài)的形式無論如何都比虛構(gòu)的原型更受歡迎”。①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7,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這是真正的現(xiàn)象學(xué)觀點,因為現(xiàn)象學(xué)注重當下直觀和本質(zhì)形式的直接開顯。現(xiàn)實中活態(tài)的單個童話不一定完全實現(xiàn)或體現(xiàn)童話的本質(zhì)形式,卻是實行本質(zhì)還原的“合適的源頭”。
(2)關(guān)于文本形式的童話能否算真正的民間童話問題
在回顧童話研究的歷史時,呂蒂指出,在他之前的研究者主要從口頭傳播方式推導(dǎo)出童話的風(fēng)格特征,但呂蒂認為這種研究是不充分的,因為傳說、薩迦、圣徒傳說和流言故事都是口頭傳播的,卻具有不同于童話的風(fēng)格。在呂蒂看來,盡管一切存活的東西既靠自身、又靠環(huán)境的力量而存活,但首要的是靠內(nèi)在規(guī)律。同樣,童話雖然也依賴于被口耳相傳的外在可能性,但首要的是它自身的特性。“對于童話能否存活而言,內(nèi)在與外在兩方面的因素都同等重要。但從精神上說,內(nèi)在規(guī)律占據(jù)首位。只有從童話自身而且僅僅從它自身來把握它的本性,我們才能理解童話及其在人類世界中的功能。這些本性同時讓口頭傳播的方式成為可能,這純屬機遇,正如哪里有生命哪里就必定會出現(xiàn)機遇一樣”。也就是說,口頭傳播相對于童話的本性來說只是偶然,而文學(xué)科學(xué)的主要任務(wù)是把握必然。
因此,呂蒂并非不討論童話的變異或個體差異,但他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這些問題。在他看來,“單個的童話可能部分地偏離理想類型,它可能在這里或那里包含著瑣碎的描寫或直接的情感表達;如果它的其余部分仍然符合童話的規(guī)律,我們?nèi)匀环Q之為童話。任何有生命的東西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但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總是要追求某種特定的形態(tài)。任何單個的童話都不會死板地滿足體裁的一切規(guī)則要求,但許多敘事就接近嚴格的形式,并且在它的周圍愉快地嬉戲”。如果說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xué)主要是對個體事物的本質(zhì)還原,那么,呂蒂的現(xiàn)象學(xué)眼光則是對諸多童話的動態(tài)的和辯證的還原,他把民間童話看作一個動態(tài)的系統(tǒng)。換言之,在呂蒂眼里,書面童話與口頭童話是動態(tài)互動的關(guān)系,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民間童話”這個整體。
呂蒂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探求童話作為藝術(shù)作品的普遍本質(zhì)。他把童話稱為“純粹的文學(xué)作品”或“純詩”(reine Dichtung)和“詩的典范”(Kanon der Poesie,諾瓦利斯語),認為它是“詩中之詩”并探求童話如何實現(xiàn)并完成自身,達到目的形式(Zielform)。呂蒂說的Dichtung既指文學(xué)作品又指無韻之詩(Poesie)。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童話的完美構(gòu)成表明它是文學(xué)作品的一種終極形式”②Endform,或譯“目的形式”。,呂蒂關(guān)注的主要不是童話的歷史起源,而是其定型于文字的晚期形式,即所謂書面童話(Buchm?rchen),當然包括書面與口頭的互動關(guān)系。換言之,書面童話是口頭童話的發(fā)達形式或完善形式,因而完全有理由或者更有理由成為童話現(xiàn)象學(xué)的直觀對象,但口頭童話與書面童話之間不是涇渭分明的關(guān)系,而是動態(tài)的“互補”關(guān)系。因此,呂蒂認為,只有從許多講述人那里聽到了同一個故事,收集人才能成功地確定普通民眾的精神立場和創(chuàng)造力所在。民間童話的講述人常常從幾個人那里聽來了他的故事,在他本人講述時要力求達到最佳形式。同樣,通過比較不同的異文,收集人和編者也幾乎會自發(fā)地創(chuàng)造出由此得到的理想形式。這種理想的形式只能通過比較相似的敘事來獲得,而不能像格林兄弟那樣通過合并相對異類的異文來獲得。
(3)民間童話的“集體創(chuàng)作”問題
正因為童話是一種高度發(fā)達和完美的藝術(shù)形式,所以,一方面,呂蒂認為它不是來自狹義的民眾,“民眾是童話的傳承人和保護人,卻幾乎不是童話的創(chuàng)作者。在我看來,童話是先知式的詩人送給民眾的一個禮物。誰是最初的童話創(chuàng)作者,我們已經(jīng)無從知曉。很難查明,詩人們在多大程度上用一種適合民眾和口頭傳播的形式把童話傳遞給民眾,又在多大程度上經(jīng)過民眾口頭傳播本身才恰好打磨出了真正的民間童話。我們的形式研究致力于闡明童話中非常明確的風(fēng)格意志,它讓我們推測,比通常認為的更多的因素,應(yīng)該記在真正的童話創(chuàng)作者的賬上”。但另一方面,呂蒂也承認廣義的民眾對童話“創(chuàng)作”的參與,因為民間童話與個人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童話的區(qū)別恰恰在于,民間童話在民眾中的流傳和講述仍屬于它的創(chuàng)作過程。1968年11月23日,在蘇黎世大學(xué)的就職演講《民間文學(xué)中的人的形象》中,呂蒂指出,人們一般說的民間文學(xué)首先指的絕非民間讀物,而是民眾在極大程度上參與創(chuàng)作的那些文學(xué)體裁,它們是民眾自身承載著并共同塑造的文學(xué)形式,即傳說、圣徒傳說、童話、笑談、笑話、軼事、個人回憶錄、格言、諺語、謎語、民歌和民間戲劇。與“文學(xué)”的字面意思相反,民間文學(xué)基本上不是書面文學(xué)作品,而是口頭文學(xué)作品。數(shù)百年來,“民間童話”都在成年人圈子里講述,它們并非由“民眾”創(chuàng)作,可以證明它們受到書面文學(xué)的影響。但它們被稱為“民間童話”卻名不虛傳,因為外行的講述人改變它們,其中有些是講壞了、弄糟了,但有些則是講對了、使它們完滿了而且進一步發(fā)展了。聽眾共同參與了對這些敘事的保存和塑造,敘述人自一開始就考慮到聽眾的需求和愿望、喜好和反感。①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8-9, Francke Verlag Bern, 1970.呂蒂認為,民間童話是不知名的創(chuàng)作者、能夠保存并繼續(xù)創(chuàng)作它的復(fù)述者以及對復(fù)述者有所要求并最終接受了童話的聽眾共同“創(chuàng)作”的作品,這意味著,詩人、講述人和聽眾的渴望讓這些敘事和整個敘事類型得以產(chǎn)生并存活。②參見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179, Francke Verlag Bern, 1970。
當然,呂蒂也指出,“民眾”這個概念在近年已被心理化,如今人們想到的“民眾”不再只是社會和文化的底層,而是每個人的底層性,不再只是群體性的民眾(vulgus in populo),而且也是個體的民眾(vulgus in individuo)。民歌、民間傳說和民間童話不僅是在農(nóng)民、手藝人、女仆和流浪漢那里安家落戶。我們每個人身上都不知不覺地具有某種農(nóng)民的成分和流浪漢的成分。尤其是自18世紀人類整體的分化被覺察以來,民歌和民間童話一再得到提升并且進入高雅文學(xué),這就表明,人們認為它們是必不可少的東西,對民間文學(xué)的研究有助于對人的研究。③參見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9-10,F(xiàn)rancke Verlag Bern, 1970。因此,“我們都屬于民眾,民間文學(xué)的片斷不斷影響著我們。我們所有人在某種程度上共同塑造的民間文學(xué)所提供的人的形象并非膚淺的和露骨的,而是豐富的和有細微差別的,其中的許多形象雖然自相矛盾但并非沒有整體的統(tǒng)一性和內(nèi)在的一致性”。④參 見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21, Francke Verlag Bern, 1970。既然我們作為普通民眾都參與了民間童話的塑造,而且書面童話與口頭童話之間不存在靜態(tài)的分界線,它們自然都可以算作民間童話的合法“樣本”,供呂蒂做現(xiàn)象學(xué)分析。
四、童話:本質(zhì)與形式意志
庫爾特?蘭克指出,究竟什么是童話?它的本質(zhì)和意義是什么?這些存在論問題是一切科學(xué)的童話研究的核心。①參見Kurt Ranke, Die Welt der Einfachen Formen. Studien zur Motiv-, Wort- und Quellenkunde, S.1,Walter de Gruyter, 1978。呂蒂試圖回答的恰恰是這樣的問題。1943年,他在博士學(xué)位論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此項研究的目的是進一步厘清童話與傳說這兩種形式的特點和本質(zhì)并且使它們互相突出各自的特征。它從如下觀察出發(fā),即童話和傳說中出現(xiàn)了同樣題材的母題:同樣的人、物和事件,但這些題材核(Stoffkerne)在這兩種類型中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塑造和應(yīng)用”。②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5,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1947年,他在《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進一步明確指出:“我的書試圖為我在歐洲見到的童話敘事提供一種現(xiàn)象學(xué)。它是對民間童話的一種文學(xué)科學(xué)式的解釋,它的目標是突出這種體裁的本質(zhì)規(guī)律。”1988年,歐洲童話學(xué)會把瓦爾特?卡恩(Walter Kahn)童話獎授予呂蒂。呂蒂在答謝辭中談到了這兩本書的寫作經(jīng)歷:
我在童年時曾聽過并讀過格林以及貝希施泰因(Bechstein)的童話。大學(xué)時代,我聽過日耳曼語言文學(xué)家赫爾穆特?德博爾(Helmut de Boor)教授在伯爾尼講授的民間童話課。我覺得它非常棒。幾年后,我請求德博爾先生允許我寫一篇有關(guān)民間童話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我當時首先想到了童話的敘述風(fēng)格。德博爾建議我寫一篇有關(guān)傳說和童話的比較研究著作,而且要依據(jù)在這兩種體裁中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處理的禮物主題。我就此寫了一部內(nèi)容豐富的研究著作,這篇博士學(xué)位論文的第二部分結(jié)尾是對傳說和童話的一般對比。可是,德博爾對這第二部分不太有把握,他認為它過于大膽。于是,他把整部手稿寄給了他的朋友——巴塞爾的中世紀研究專家和傳說研究家弗里德里希?蘭克。所幸,蘭克恰恰認為第二部分盡管大膽卻很有價值。德博爾建議我把第一部分專題作為博士學(xué)位論文出版,而第二部分獨立成書。我采納了這個建議,于是就有了我的頭兩本書,在其中的第二本書里,我以童話為核心,而傳說只用來比較,它的書名是《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
在《歐洲民間童話》以及隨之寫出的幾篇論文發(fā)表之后,我誤以為自己大概對童話永遠不再寫多少東西了,于是就轉(zhuǎn)向其它任務(wù)。但幾年后,許多做報告的邀請和稿約紛至沓來,我發(fā)現(xiàn)我對民間童話還有新東西要說。此前我主要著迷于童話的抽象化敘事風(fēng)格以及以童話中的男女主人公形式出現(xiàn)的人的形象,而現(xiàn)在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民間敘事和民歌的世界所突出表現(xiàn)出來的豐富變化。我只想給后來發(fā)表的論著起兩個題目:童話和傳說的原始形式和目的形式以及童話和傳說的心理學(xué)。”③引自Ursula Schmid-Weidmann, Prof. Dr. Max Lüthi: Sein Leben und Wirken, in Troubadour M?rchenzeitschrift, Jahrgang 1989, M?rz Nr. 1, S. 24。
由此可知,呂蒂最重要的兩本書其實幾乎同時構(gòu)思完成,只是出版時間間隔了四年。這說明他對童話的現(xiàn)象學(xué)考察早已成竹在胸。呂蒂在精神與感官之間做了明確的區(qū)分,“對眼睛和感官而言,具體的、個別的事物一般具有不確定的和多義的特點,因為它的輪廓模糊不清,感官無法把握它的內(nèi)在無限性。對感官而言,抽象的、帶線條的東西是簡單的東西、確定的東西。但對精神而言,恰恰具體的、唯一的東西是以不可改變的和毫不含糊的方式得到規(guī)定的;它的終極本質(zhì)之所以從來不能得到把握,是因為我們的認識器官在這方面不夠用;個體的東西自身可是受到極其深刻的規(guī)定的,是以特有的方式被區(qū)分出來的,而且受到獨一無二的限制。反之,對精神而言,抽象的圖形則是能從多方面加以規(guī)定的”。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打開的是精神之眼而非感官之眼,或者說,他要對歐洲民間童話打開精神之眼而關(guān)閉感官之眼,這樣才能使他見他人之未見,想前人之未想。
呂蒂選擇歐洲童話的文本形式作為分析對象固然因為他非常熟悉和喜愛這些童話——他在為報紙、電臺寫的大量稿件中分析過許多著名的歐洲童話,還編過《歐洲民間童話》的德語讀本①參見Europ?ische Volksm?rchen, Ausgew?h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Max Lüthi, Manesse Verlag,Zürich, 1951。——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現(xiàn)象學(xué)的眼光不能脫離具體作品,它要從具體作品中直觀并還原童話的本質(zhì)。在博士學(xué)位論文中,呂蒂以這種新的方式實驗了他對童話和傳說這兩種類型的“本質(zhì)把握和本質(zhì)差別”的存在論理解。呂蒂所謂“禮物”,不僅指物品,也包括有益的建議和有害的魔法。他把童話中的禮物界定為“內(nèi)在于形式的”(formimmanent),即它總是某個幻想情境中的某個幻想片段,而傳說中的禮物則是“超越于形式的”(formtranszendent),即它跨入現(xiàn)實世界。童話是“純粹的文學(xué)作品”或“純詩”(reine Dichtung),與作為“原始構(gòu)成物”(primitives Gebilde)的傳說形成對立,因為傳說的“老家在民間”。呂蒂認為,童話和傳說獨立于神話,它們都不是向神話發(fā)展的某個階段或者從神話發(fā)展而來的某個階段。這三種形式都有各自的權(quán)利和方式,每一種形式都想展示不同的東西,因而也都有各自的結(jié)構(gòu)。神話是對人之外的世界的詩意的眺望,童話以抽象的風(fēng)格化手法描繪人與彼岸世界所有交往的遭遇,而在傳說中,這種交往體驗本身構(gòu)成講述的中心并規(guī)定著它的形式。②參 見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113,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通過對禮物的觀察,呂蒂發(fā)現(xiàn),童話中的禮物不觸及受贈者的內(nèi)在存在,而傳說中的禮物卻深入他的內(nèi)心。在童話中,惟一能闖入接受者的深處并且似乎完全使他變形的禮物是魔法,它相當于傳說中的詛咒,但這兩種禮物截然不同。魔法并不改變受害者的本質(zhì),它只是在某段時間讓他變成另一種形式或者讓他去遠方,在解除魔法之后,又讓他毫發(fā)無損地進入原先的生活。解救者常常與被救者結(jié)為夫妻,他們恰恰站在同一個平面上。③參 見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80,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因為童話主人公是圖形。他受到引導(dǎo)和推動,他是發(fā)生的遭遇的承載人,但歷盡千辛萬苦,他本人也毫無改變;在結(jié)尾時,他站在另一個地方,但他依然是同一個人。④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77,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
盡管呂蒂的博士論文新見迭出,但畢竟限于專題研究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仍是一個“序曲”,而《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則是呂蒂童話研究的真正“高潮”——“在我公開出版的著作中,本書是奠基性的著作”。在此書中,呂蒂秉承博士論文的論題進一步指出:“童話的秘密不在于它使用的母題,而在于它使用母題的方式。也就是說,在于它的形態(tài)。”所謂形態(tài),不是靜態(tài)的形式,而是獲得形式的過程和機制。呂蒂對童話的觀看方式以及他的現(xiàn)象學(xué)目光的運轉(zhuǎn)恰恰圍繞著童話作品如何獲得形態(tài)或形式而展開。在瑞士著名美學(xué)家和藝術(shù)史家沃爾夫林的諸多概念——平面與深度、封閉形式與開放形式、多元與統(tǒng)一、清晰與不清晰①參 見Heinrich W?lffl in, 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Das Problem der Stilentwickung in der neueren Kunst, Zweite Aufl age, Hugo Bruckmann Verlag, München, 1917。——的啟發(fā)下,呂蒂對童話的風(fēng)格和形式做出直觀的描述和呈現(xiàn)。所謂Stil(風(fēng)格)本來就指藝術(shù)作品創(chuàng)作或構(gòu)成的方式。當呂蒂將沃爾夫林考察藝術(shù)史內(nèi)在形式的現(xiàn)象學(xué)眼光用于童話時,他看見的是童話的內(nèi)在形式及其獲得機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對呂蒂使用的兩個術(shù)語做一個大致的區(qū)分,即Form主要指靜態(tài)的、已經(jīng)完成的形式,而Gestalt主要指動態(tài)的、尚未完成或正在完成的形式,即形態(tài)。所謂民間童話的變異,指它處于運動或未完成狀態(tài)即在獲取形式的過程中,因而變異中的民間童話具有形態(tài),但還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形式。這正是呂蒂要把本質(zhì)“定位”在靜態(tài)的書面童話的根本原因。但我們不能由此說呂蒂的目光僅僅關(guān)注靜態(tài)的童話形式。盡管呂蒂的目的是尋求民間童話的形式,他的目光卻聚集在民間童話的形態(tài),即觀察民間童話如何獲得自己的形式以及如何實現(xiàn)并完成自身,達到目的形式。獲得了形式就是獲得了本質(zhì),因而民間童話的形式就是它的本質(zhì),二者是同一個東西。
正是在對民間童話形態(tài)的觀察過程中,呂蒂發(fā)現(xiàn),“從原則上說,童話的題材向一切可能性開放”,也就是說,一切東西都能成為童話的題材,因為童話把玩一切母題,但“童話的存在并不依靠母題的特殊種類,而是依靠形態(tài)的特殊種類。童話從‘故事’以及傳說和神話中,有時甚至直接從現(xiàn)實中汲取它的母題。但是,它改變了所有這些母題。通過空洞化、升華化和孤立化,它給它們賦予童話的形式。不存在原本的童話母題,相反,任何母題,無論世俗的還是神奇的,一旦被納入童話而且被童話賦予童話般的形態(tài)、以童話的方式得到運用,就變成了‘童話的母題’”。傳說這種“簡單的形式”(約勒斯語)是題材決定形式,而童話則是形式?jīng)Q定題材。也許正是從母題著眼,呂蒂才發(fā)現(xiàn)了童話的秘密在于它在不止一種意義上是一種平面藝術(shù)。②參見Europ?ische Volksm?rchen, Ausgew?h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Max Lüthi, S.567, Manesse Verlag,Zürich, 1951。這也就意味著童話是一種抽象藝術(shù)。民間童話中的一切首先具有情節(jié)意義。③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73, Francke Verlag Bern, 1970.進入童話的一切母題都被平面化了,都獲得了一維性。有學(xué)者指出,呂蒂的術(shù)語“一維性”與“平面性”彼此矛盾,④參見Lutz R?hrich, Die M?rchenforschung seit dem Jahre 1945, in Deutsches Jahrbuch für Volkskunde,Zweiter Band, Jahrgang 1956。因為平面是二維的,而奧德?維爾馬?門克伯格(Oder Vilma M?nckeberg)在1967年6月3日給呂蒂的信中也說,“我仍然不相信您的‘平面性’”。⑤參見Regula N?f, Max Lüthis wissenschaftlicher Nachla? im Universit?tsarchiv Zürich, in Fabula, 36. Band,Heft 3/4, 1995, S.285。不知呂蒂對此是否有過明確回應(yīng),但沃爾夫林的觀點可以看作對上述質(zhì)疑的回答:“平面的要求造成的情況并非把一切排成一個平面,而是主要形式必須處在同一個平面上。這個平面必須一再作為基本形式來進行滲透”。⑥Heinrich W?lffl in, 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Das Problem der Stilentwickung in der neueren Kunst,Zweite Aufl age, S.108, Hugo Bruckmann Verlag, München, 1917.呂蒂的“一維性”并非嚴格的幾何學(xué)概念,它主要指童話把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看作同一個維度,這里的“維度”相當于平面,至少指主要形式處在同一個平面上。童話的平面化意味著抽象化和空洞化,只有去除了既有的東西,才能賦予新的形式,因此,“童話中所有母題的這種空洞化,同時意味著失與得。失在具體性和現(xiàn)實性、體驗的深度和關(guān)系的深度、細微差別和內(nèi)容的重量。然而,得在形式的確定性和形式的亮度。空洞化同時就是升華化。一切成分都變得純粹、輕盈、透亮并達成一種毫不費力的配合,人類生存的一切重要母題都在這種配合中發(fā)出聲響”。
平面化造成了空洞化和升華化,但這些只是民間童話抽象風(fēng)格①塞巴斯蒂亞諾?洛尼格羅指出,呂蒂的術(shù)語“抽象風(fēng)格”容易發(fā)生歧義,我們最好代之以“線性的、純圖形化的風(fēng)格”(linearer, rein fi gurativer Stil),參見Sebastiano Lo Nigro, Die Formen der erz?hlenden Volksliteratur, in Wege der M?rchenforschung, Herausgegeben von Felix Karlinger, S.390,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3。的一個方面,而抽象風(fēng)格的主導(dǎo)特征是孤立化。呂蒂認為,童話的整體風(fēng)格就是孤立化。②參見Europ?ische Volksm?rchen, Ausgew?h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Max Lüthi, S.572, Manesse Verlag,Zürich, 1951。其實,平面化已經(jīng)意味著孤立化,即取消一切深度和聯(lián)系。童話中的人和物成為活動在同一個平面上的單純的圖形或形象,承載著童話情節(jié)向前發(fā)展,它們彼此孤立,缺乏深度聯(lián)系,而“這種孤立化也是童話能夠把整個世界全面納入自身的前提。童話這種史詩般的簡短形式,不可能用任何其它方式變成含世界的”。也正是這種孤立化使童話中的人和物能夠聯(lián)結(jié)一切。
可見的孤立性,不可見的聯(lián)結(jié)一切,這些都可以被稱為童話形式的基本特征。在無形的引導(dǎo)之下,孤立的人物恰好配合得天衣無縫。這兩個方面互為條件。只有不在任何地方扎根,不受外在關(guān)系和自身內(nèi)在約束的制約,才能隨時隨地發(fā)生聯(lián)系,并且再次解除這種聯(lián)系。反過來說,只有通過這種聯(lián)系一切方面的能力,孤立性才獲得它的意義。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外在的孤立成分就必定會四處離散。
因此,孤立與聯(lián)結(jié)一切互為前提、相互依存。呂蒂對童話的直觀有一系列的發(fā)現(xiàn),大體順序是:一維性→平面性(圖形化風(fēng)格的一個方面)→孤立化(含世界和聯(lián)結(jié)一切的前提)→空洞化和升華化→含世界和聯(lián)結(jié)一切→童話風(fēng)格的強制性和形式確定性→童話的形式意志(沖動)、風(fēng)格意志。呂蒂的這些概念都不是簡單的對立關(guān)系,而是互相包含或?qū)α⒔y(tǒng)一的關(guān)系,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概念不僅具有否定的含義”,比如,“失重”同時意味著“升華”,“空洞化”同時意味著“精神化”,“抽象的”不等于“非形象的”或者“形象的”反面,而是指更具有視覺暗示性的形象。換言之,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推演:童話的形式意志(沖動)、風(fēng)格意志→童話風(fēng)格的強制性和形式確定性→含世界和聯(lián)結(jié)一切→空洞化和升華化→孤立化(含世界和聯(lián)結(jié)一切的前提)→平面性(圖形化風(fēng)格的一個方面)→一維性。這些辯證的概念構(gòu)成呂蒂童話現(xiàn)象學(xué)的基石。在一定意義上說,只有在西方思想傳統(tǒng)中,呂蒂才能把童話自身當作一個無關(guān)系的獨立考察對象,才能發(fā)現(xiàn)童話的孤立性、平面性等特征,也才能看到童話主人公最終被孤立卻能夠建立普遍聯(lián)系的辯證特征。《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隨處可見這種具有辯證關(guān)系的對立概念,它們構(gòu)成呂蒂童話現(xiàn)象學(xué)的基石。該書在語言上的明快、犀利,在分析上的深入淺出以及在哲學(xué)洞見上的敏銳直覺,使它不亞于任何一部現(xiàn)象學(xué)的哲學(xué)著述。呂蒂的哲學(xué)天賦和藝術(shù)敏感在其中畢現(xiàn)無遺,在不長的分析文字中佳句迭出,但這種佳句并非賣弄文采或逞才傲物,而是精神活動自身的忠實展示和記錄。因而,作為分析童話的學(xué)術(shù)著作,它本身就成為一首純正的童話,成為“詩中之詩”。我把呂蒂書中的一些原話串起來,就是對他的準確而精彩的轉(zhuǎn)述:
在童話中,一切皆有可能。它歡迎任何要素。它是一種包容世界的廣博形式。就“含世界的”這個詞的本意而言,童話是一種含世界的文學(xué)作品。它不僅有能力以升華的方式把任何成分納入自身,而且還真實地反映了人類存在的一切本質(zhì)要素。童話以詩性的形式向我們顯示世界的本質(zhì),不問各種潛力的本質(zhì)和本性,而傳說追問單個事物。它對此岸生靈和彼岸生靈都很著迷,它以自己的方式“解釋”它們,它給出部分答案。它不放過單個事物。它以認識和解釋的方式向黑暗挺進。它照亮部分領(lǐng)域,或者說,它意在照亮。童話以詩的方式虔誠地提供了一個暫時的有關(guān)世界和人的整體展示。作為純文學(xué),它保留著純粹的潛在性。在童話中,世界大概首次以詩的方式被克服。在現(xiàn)實中困難的和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的事情,在童話中變得輕盈而透明,而且像在自由游戲中一樣順應(yīng)了事件的關(guān)系網(wǎng)。在現(xiàn)實中,我們只能看到一部分進程和幾乎不能理解的命運,而童話為我們展現(xiàn)的是一個自身充滿極樂事件的世界,每個要素在其中都有被精確指定的位置。在童話中,我們也看不到“事物的背后”;我們瞥見的只是行動著的人物,而不是他們來自哪里和去向何處,他們的原因和目的。對事件和人物的抽象描繪,讓童話明快而自信。情節(jié)的輕易運轉(zhuǎn)和快速進展以及主人公的漫游,給它賦予了自由的輕松色彩。束縛與自由、沉靜與運動、固定形式與輕易進展的情節(jié),在童話中聯(lián)結(jié)為藝術(shù)的統(tǒng)一體,并對聽眾產(chǎn)生了一種巫術(shù)般的效果。從形式和內(nèi)容來看,童話是“對魔鬼的一種回答”。線條的明快、形態(tài)的清晰,同時又放棄總體編排以及圖形和事件的系統(tǒng)化,這些都決定了童話的面貌。恰恰是這種對任何編排的拒絕,才表明了民間童話的極度真誠。它說出的莫過于它知道的,而它知道的也只是它看到的。它不編造任何東西。民間童話絕非蓄意幻想的游樂場。它虔誠地描述世界和人,就像它看到的世界和人那樣形象而生動。可能直接為某個無限的精神演出的一場戲劇,在童話中卻變成了為有限的精神演出的一場戲劇。事實證明,童話是純粹史詩般的展示。如果說傳說產(chǎn)生于內(nèi)在的激動,那么,童話就出自內(nèi)在的平靜。正因為童話的創(chuàng)作者自己是不動的,他才能夠純粹而自信地讓動者被看見并且被展現(xiàn)出來。童話中充滿了史詩般的光線、史詩般的開朗。童話用最明晰的表達方式把史詩般的活動和史詩般的明快結(jié)合在了一起。童話這種詩體本身是一種終極形式,它以精湛的技藝把玩著總是相同的、變得空洞化的母題,而且像童話一樣表現(xiàn)出兒童似的單純。因此,沒人認為它原始或幼稚。它處于發(fā)展的終點,它根本不是幼稚的,它的單純是藝術(shù)式的單純。關(guān)于產(chǎn)生童話的環(huán)境和時間,我們沒有得到任何外在的學(xué)科知識。然而,它的內(nèi)在形式的特性讓我們確信,童話既不原始也不幼稚,而是高度發(fā)達的藝術(shù)。童話并非源于美化世界、神化世界的愿望。毋寧說,在它看來,世界由自身顯出神采。童話怎樣描述世界,它就怎樣看世界。童話描述了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并由此滿足了人的終極的和永恒的愿望。它想成為這種愿望的一種真正的滿足,而不是替代式的滿足。它不想虛構(gòu)現(xiàn)實中不存在的東西和從來不可能存在的東西,不如說,它看見現(xiàn)實變得清澈而透明。它沒有隨口瞎編一個美好世界,讓我們在其中暫時忘卻其它的一切而流連忘返。恰恰相反,它相信,世界就是它看到和描繪的那個樣子。童話只是在無意之中講出了向它的詩性目光所顯示出來的內(nèi)容。童話也不能直接被稱為應(yīng)然的文學(xué)作品。它的目的不是向我們顯示世界上的事情應(yīng)該如何進行。相反,它試圖看出和表達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實際上如何進行。它想顯示的并非一個單純可能的世界,一個如我們所愿或者如我們所要的世界。它要構(gòu)造的不是一種理想。不如說,它用真實的信仰、把世界在它眼中顯現(xiàn)的原樣呈現(xiàn)出來。童話不是如下意義上的應(yīng)然的文學(xué)作品,即它把我們放進一個單純可能的世界,這個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對立方式就表現(xiàn)在,它應(yīng)該存在,而且是現(xiàn)實世界的衡量標準。童話向我們顯示的不是井然有序的一個世界,它向我們顯示的是井然有序的惟一世界。它向我們顯示了一點:即世界如它應(yīng)該存在的那樣存在。童話把實然①Sein,或譯“存在”。的文學(xué)作品與應(yīng)然②Seinsollen,或譯“應(yīng)該存在”。的文學(xué)作品集于一身。童話是全面的、自身封閉的詩性展示。童話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對部分要求的滿足。它的目的不是欺騙。它的抽象描述讓我們一刻也不懷疑:它要描述的是本質(zhì),而不是現(xiàn)實。歐洲民間童話向我們展現(xiàn)為一種多節(jié)的、含世界的、具有抽象風(fēng)格形態(tài)的冒險敘事。它把世界納入自身。然而,它顯示的不是世界最內(nèi)在的整體關(guān)聯(lián),而是世界的意味深長的游戲。不變的、自身不動卻仍在發(fā)揮效力的純粹形式,在支撐著速朽的現(xiàn)實中的那些處于變化和枯萎中的形式。童話為我們呈現(xiàn)了這些純粹形式的圖像。
在呂蒂看來,童話風(fēng)格一旦被破壞,就會在進行講述的民眾口中重新恢復(fù),因為講述者和聽眾要求形式清晰性和形式確定性,舍此,童話可能就不再是童話了。③參見[瑞士]麥克斯?呂蒂《童話的魅力》,張?zhí)镉⒆g,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25頁;Max Lüthi, So leben sie noch heute. Betrachtungen zum Volksm?rchen, S.35, 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ttingen, 1969。盡管童話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但童話和傳說一樣想在更高階段重新實現(xiàn)自己。呂蒂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促成童話和傳說獲得實現(xiàn)的這種“形式意志”。他認為,童話“這種完全平面式的描述并非源于一種無能,而是源于童話的非常果斷和自信的形式意志”,不僅童話而且傳說的固有結(jié)構(gòu)必定自動揭示了對它們起規(guī)定作用的那種形式意志。④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6,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童話和傳說給內(nèi)容相同的母題賦予的不同特征讓我們推測,在這兩種類型中有一種指向非常明確的形式意志在起作用,這種形式意志抓住這些母題并為它們賦予了符合它的形態(tài)。不是特定母題(題材核)的出現(xiàn),而是這些母題被塑造以及被納入整體結(jié)構(gòu)的方式,決定著某種敘事可以被稱為傳說還是被稱為童話”;⑤Max Lüthi, Die Gabe im M?rchen und in der Sage. Ein Beitrag zur Wesenserfassung und Wesensscheidung der beiden Formen, S.5, Bern: Buchdruckerei Büchler & Co., 1943.“同一種形式意志貫穿著全部童話。一切情節(jié)片段都從這種形式意志中噴涌而出”。呂蒂并沒有對“形式意志”做清晰界定。所謂形式意志,當然是在人身上發(fā)生作用的客觀力量,但它并不完全是人自己隨心所欲的創(chuàng)造力,不如說,形式意志通過人起作用。或者說,形式意志在支配人,而非人在支配形式意志。這同時也說明,個人創(chuàng)造的自由不是無限的、無規(guī)律的創(chuàng)造,而是在形式意志的作用下以有限的手段進行創(chuàng)造。“支撐童話的不僅有個人的藝術(shù)意志,而且在象征暗示的意義上,也有超個人的藝術(shù)意志”。
但是,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呂蒂之所以沒把形式意志、風(fēng)格意志和形式?jīng)_動完全歸因于人,是因為他并不在人的心理層面考慮這些問題。“我們追問的不是童話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因為很難確定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有意識地創(chuàng)作故事,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無意識地臨摹所看到的東西。但是,查明作品本身及其秘密,已經(jīng)足以讓人心醉神迷;對它的創(chuàng)造者的追問,則是將來的事情”。也就是說,我們在田野調(diào)查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具體的情況。例如,在心理層面,除了上述有明確形式意志的講述者之外,也有不表現(xiàn)出或者不關(guān)心形式問題的講述者。在民間文學(xué)的具體演述過程中,講述者的心理是多變的甚至可能是捉摸不定的,當然也是因人而異的,有人想改變傳統(tǒng)的形式而不能,有人不想改變已有的套路而不成,因此,民間文學(xué)的形式意志、風(fēng)格意志和形式?jīng)_動主要指的不是民間文學(xué)講述者的心理動機,而是每一種民間文學(xué)體裁都有各自的形式規(guī)定和形式目的,人對某個具體民間文學(xué)體裁的講述實際上就是(無論在心理上是有意還是無意)被卷入這種體裁的傳統(tǒng),在這種體裁傳統(tǒng)的規(guī)定下去實現(xiàn)(踐)體裁形式的目的,無論講述者的主觀心理是想創(chuàng)新還是守舊,無論實踐的目的是否實現(xiàn),講述者在客觀上都必須服從這種體裁本身的形式意志和形式目的。正如呂蒂所說,“盡管有各種自由,民間童話仍然一再奔向某種確定的內(nèi)在形式,這當然不是因為它的作者或講述人了解這一體裁的要求,并且有意識地運用某些規(guī)則,而是因為,如我們已經(jīng)試圖表明的那樣,這些體裁符合并滿足了人類心靈的某些需要”。如果僅僅局限于心理層面的考察,就可能陷入矛盾。
五、人的形象與童話的功能
呂蒂對民間童話的現(xiàn)象學(xué)考察旨在弄清童話的形式和本質(zhì),但他的立足點是童話中人的形象以及童話在人類生存中的實踐功能。換言之,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提供的不是有關(guān)童話的知識,而是對童話的實踐價值和功能的認識。在《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呂蒂說,“童話是一種含世界的冒險敘事,具有簡約的、升華的風(fēng)格形態(tài)。它用不現(xiàn)實的輕盈性孤立并聯(lián)結(jié)它的人物。它把線條的分明、形式和顏色的明亮與斷然放棄對有效關(guān)聯(lián)的教條式解釋統(tǒng)一了起來。它使明亮與神秘集于一身。具有如此特性的一種作品,在人類存在的結(jié)構(gòu)中占有什么樣的位置呢?”
應(yīng)該說,童話的形式和本質(zhì)最終歸結(jié)為童話中呈現(xiàn)的人的形象。童話以自身特有的抽象化、圖形化和孤立化風(fēng)格描繪了一種人的形象。童話表達的是對人及其存在的一種特殊理解。①呂蒂在《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zhì)》中指出:“我把童話看作一種以簡短的、升華的和井井有條的形式描述人類存在的本質(zhì)關(guān)系的冒險敘事。”1968年11月23日,呂蒂在蘇黎世大學(xué)的就職演講《民間文學(xué)中的人的形象》中指出,民間文學(xué)展現(xiàn)了豐富多彩而又各不相同的人的形象。例如,在諺語中,人把自己理解為一個認知者,同時也是一個要請求和要讓自己受到請求的人,這意味著兩個方面:即他覺得自己受共同體和傳統(tǒng)的約束,而且他承認一種應(yīng)然(Seinsollen)。 在民間傳說中,人表達了對自身的一種不同于諺語和謎語的理解。這里出現(xiàn)的是沒把握而且沒得到保障的人,因而也是一個激動者、問詢者和探求者。民間童話中出現(xiàn)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的形象。民間童話中的主人公主要是一種有弱點的存在者(Mangelwesen)。這種有弱點的存在者恰恰有一個前提,即他的成長超越了其它一切東西。民間童話把人描述為面臨各種考驗但最終在世界上得到攙扶和保護的人,把人看作有能力成功卻有弱點的存在者,由此也表明他是一種迂回的存在者(Umwegwesen)。童話主人公不能洞穿存在的各種關(guān)聯(lián),但這些關(guān)聯(lián)卻承載著他。“這樣一種人的形象的內(nèi)在真理是自明的:人終究是孑然立世,但各種佑助仍然一再向他涌來,他甚至可以讓自己擁有無法參透其整體關(guān)聯(lián)的各種力量,正如童話主人公看不透他遇到的‘彼岸’宇宙一樣”。傳說仿佛是一個問題,而童話則仿佛是一個答案。童話從遠景描繪了在整個世界中得到保護而且懷著自信走自己路的人的形象;傳說的構(gòu)造方式比一成不變地風(fēng)格化的童話更具個體性,它提供的是近景,而且描繪的是處于一籌莫展和無望失落情境中的人。這兩種人的形象都具有真實性。童話更多地瞄準的是人類,而傳說更多地瞄準的是個人。諺語、謎語、傳說、童話、笑談中出現(xiàn)的不僅是各種各樣的人的形象,而且也是相互矛盾的人的形象。即使在童話中,人的形象也并非統(tǒng)一。民間文學(xué)表達了對人的實然(Sein)和應(yīng)然(Seinsollen)的最重要的陳述。①參 見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13-21,F(xiàn)rancke Verlag Bern, 1970。
在《作為文學(xué)作品的民間童話:美學(xué)與人類學(xué)》一書中,呂蒂進一步指出,民間童話中的人的形象是真實的,因為與其它生物相比,人作為人實際上相對容易脫離周圍世界,因此能夠在許多方面產(chǎn)生聯(lián)系,他需要幫助,而且終生都有助手陪伴他左右。人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危險,但同時又能達成遙遠的、雄心勃勃的目標。他是一個行動者,他能夠忍辱負重,用間接和迂回的方式達到目的,他可能是解救者,也可能是被解救者。這種人的形象的有效性不依賴于時間和地點;它不是以現(xiàn)實主義手法而是通過神奇的陌生化手法呈現(xiàn)出來的,這就使它給人們留下了加倍深刻的印象。但它沒有表明完整的人,它需要補充而且得到了補充。民間敘事的其它體裁如傳說和笑談就是對童話的補充。②參見Max Lüthi, Das Volksm?rchen als Dichtung. ?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 S.168, Eugen Diedrichs Verlag, 1975。呂蒂認為,在民間童話中,人主要(雖然不只是)表現(xiàn)為行動者;在民間傳說中,人主要(盡管不僅僅)表現(xiàn)為體驗者、震驚者、摸索者、探求者和苦思冥想者。③參 見Max Lüthi, Das Volksm?rchen als Dichtung. ?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 S.169, Eugen Diedrichs Verlag, 1975。傳說創(chuàng)造家鄉(xiāng),而童話創(chuàng)造世界。童話通向廣度,它們擴展并愉悅精神,而傳說通向深度,它們把人的精神和靈魂織入景色之中。④參見Max Lü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Menschenbild- Thematik- Formstreben, S.36, Francke Verlag Bern, 1970。
民間童話中的行動者揭示了人的存在處境和真相。“童話絕非單純的游戲之作,它們把聽眾帶進人的存在的本質(zhì)”。⑤Max Lüthi, So leben sie noch heute. Betrachtungen zum Volksm?rchen, S.69, 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ttingen, 1969.這是童話最大的功能。呂蒂認為,童話固然有其天真幼稚的方面,但是,既然它的核心人物不僅是一個與這些人物認同的“我”的代表,而且是一般人的風(fēng)格化形象,它就直接關(guān)涉一種更高尚的倫理學(xué),也就是康德說的“要這樣行動,即任何時候都把你自己的人格以及別人的人格同時當作目的,絕不單純用作手段”。⑥參見 Max Lüthi, Das Volksm?rchen als Dichtung. ?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 S.182, Eugen Diedrichs Verlag, 1975。民間童話及其主人公形象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人不僅要不斷創(chuàng)造一個給人尊嚴的社會,而且同時必須在與社會無法割舍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中盡可能廣泛地探求人的存在的本質(zhì)和特點。童話主人公既非哲學(xué)家也非研究者,但童話的講述人和童話聽眾在某種意義上卻是哲學(xué)家或研究者。他們想消遣、想弄懂卻沒注意到特定的人的形象。呂蒂的研究已經(jīng)表明,恰恰是在一個受到大眾化、虛無主義、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威脅的時代,童話中的這種適合于人的形象是頗有裨益的。⑦參見 Max Lüthi, Das Volksm?rchen als Dichtung. ?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 S.178, Eugen Diedrichs Verlag, 1975。
呂蒂之所以說民間童話不是愿望詩或單純關(guān)于應(yīng)然的文學(xué)作品,是因為他看到民間童話中不是反映主觀的幻想、愿望和應(yīng)然。首先,他看到了童話中的惡。不過,呂蒂認為,童話中的惡,從敘事方面來說是情節(jié)的酵素,從人類學(xué)上說則是各種可能性發(fā)展、展開和實現(xiàn)的酵素。童話集魔正論(Diabolodizee)和神正論(Theodizee)于一身,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是同一個人的兩面。童話中的惡變善以及“善”中之惡恰恰是對人的存在以及人的各種可能性的整體反映。①參見 Max Lüthi, Das Volksm?rchen als Dichtung. ?sthetik und Anthropologie, S.183-184, Eugen Diedrichs Verlag, 1975。其次,他指出,童話把人本身看作需要拯救的,這與基督教的觀點相去不遠。②Max Lüthi, So leben sie noch heute. Betrachtungen zum Volksm?rchen, S.85, 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ttingen, 1969.但是,呂蒂并不是單純從基督教的角度看童話以及童話中的人,他甚至認為,童話“既不受現(xiàn)實的束縛,又不受教義的束縛。它也不再依附于單個的事件或體驗,對它來說,一切單個的東西都只是元件。童話不需要教堂的支持;它甚至在與教堂敵意的對抗中存活了下來。盡管如此,童話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對人類存在的迫切問題給出了一種回答,而且是一種令人喜悅的回答”。
對中國讀者來說,我們可以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之外來理解呂蒂的上述論述:即人是有弱點的存在者,也是有限的非全知全能者,因而是需要救助者。這是民間童話為我們呈現(xiàn)的人的形象。這種人的形象的真實性不依賴于基督教信仰,也不局限于歐洲文化內(nèi)部。換言之,即使沒有基督教信仰,我們也同樣會面臨一個問題:既然我們不會否認自己是有弱點的、有限的存在者,那么我們是否需要一種對絕對他者的純粹信仰?如果沒有這種信仰,人生在世能否獲得一種完全的自信和保障?正如童話主人公若沒有彼岸世界的佑助能否在童話中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一樣。但無論如何,“作為敘事的童話同時提供了娛樂與存在的澄明。它不要求對所述內(nèi)容的外在的實在性有任何信仰,它甚至禁止這種信仰;抽象風(fēng)格和一些反諷式的結(jié)語或引語讓我們覺得,童話世界與外在的實在性根本就是分離的,它們從來不會相互逾越。它也不給我們提供自覺的世界解釋。與傳說和圣徒傳說不同,它不說明和解釋,它始終不渝地放棄任何分類學(xué)。它只描述。但是,作為純正的文學(xué)作品,它要求對被描述內(nèi)容的內(nèi)在真實性的信仰。它自身并不表現(xiàn)為閑散的游戲,而是讓自己成為一種世界體驗的圖像。”童話是對非本真生活的去蔽和隔離,只有這樣,童話才能自成一格,把本真的存在顯露和呈現(xiàn)出來。因此,呂蒂才認為童話是一種真正的本質(zhì)直觀(Wesensschau)。③參見Europ?ische Volksm?rchen, Ausgew?h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Max Lüthi, S.573, Manesse Verlag,Zürich, 1951。當然,我們同樣可以說,呂蒂對童話的現(xiàn)象學(xué)研究也是一種真正的本質(zhì)直觀。童話的本質(zhì)通往人的形象和人的存在。純粹的形式研究導(dǎo)向道德哲學(xué)和倫理學(xué)。
盡管中國學(xué)者對這個傳統(tǒng)的興趣有限,而且即便在德語地區(qū),呂蒂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也面臨后繼乏人的局面④呂蒂培養(yǎng)的學(xué)生很少,其中,克蒂?克努瑟爾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是《童話與傳說中的言說與緘默》(Reden und Schweigen in M?rchen und Sagen. Abhandlung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t I der Universit?t Zürich, vorgelegt von K?thi Knüsel, Angenommen auf Antrag von Herrn prof. Dr. Max Lüthi, Druck: Kopierservice Bern, 1980)。,但呂蒂的童話現(xiàn)象學(xué)仍然是歐洲童話研究乃至民間文學(xué)研究深刻而寶貴的遺產(chǎn),很值得我們重視、繼承和發(fā)揚光大。我相信,能不能懂首先取決于愿不愿懂和想不想懂的意志或決心。既然有些根本問題是我們每代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那么,總會有少數(shù)人不愿繞過這些難題,默默地擔負起學(xué)科未來的希望。
[責任編輯:王素珍]
I207.7
A
1008-7214(2016)03-0031-22
戶曉輝,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