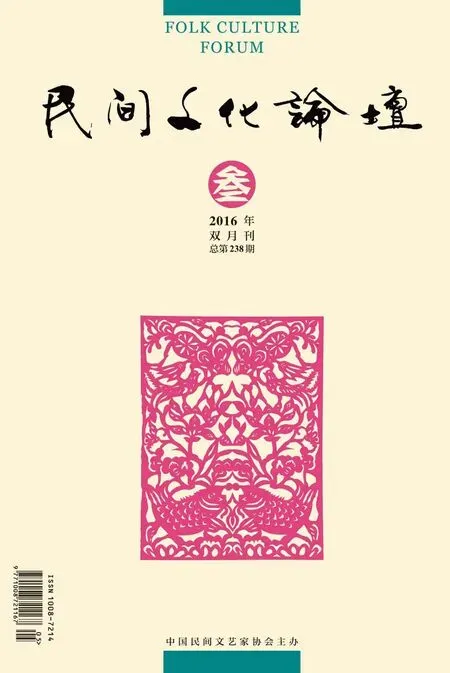“棄老”故事與長生成仙信仰
海力波
民俗研究
“棄老”故事與長生成仙信仰
海力波
“棄老”實為古代人生禮儀中從老年走向死亡的過渡儀式,老人在特定的年齡階段從公共生活中隱遁,在社會身份與生活空間上與世人相隔離,以等待死亡的到來。“仙”之原意當為老年年齡等級之稱謂;長生成仙信仰起源于古人對曾經存在的“棄老”習俗與儀式的曲折記憶與美化想象。處于儀式閾限狀態的老人形貌與“野化”生活方式成為早期仙人形貌與仙界生活的原型;飛升與尸解極有可能源自火葬與食尸葬等喪葬形式。
棄老;死亡儀式;長生成仙;過渡儀式
一、仙的原始含義
如何面對死亡?文化不同,答案各異。中國傳統文化選擇長生成仙信仰來回避死亡問題的負面答案,其特點在于相信肉體不死,而非虛幻的靈魂不滅。①彭磊:《從“靈魂不死”到“肉體不死”——從思想之嬗變看道教神仙信仰之興起》,《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2期。春秋以前尚無“仙”之觀念,儒家十三經與《老子》中皆無仙字。②黃云明:《論仙崇拜及其產生的原因》,《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4期。仙字最早見于《詩經?小雅?賓之初宴》:“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仙仙”,“仙仙”指稱醉后拋開禮儀束縛,自在起舞無拘無束之態。③陳 靜:《仙字溯源》,《中國道教》,2003年第3期。據《史記?封禪書》等篇記載,戰國時齊威王、宣王與燕昭王等皆使人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仙人與不死之藥。④(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69頁。漢武帝時求長生成仙、肉體不死之風盛行,魏晉南北朝時長生成仙信仰被道教所吸收,成為早期道教的主要追求。⑤卿希泰、詹石窗編:《中國道教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345頁。成仙之事虛無縹緲,但仙之觀念卻有現實生活的基礎。東漢劉熙在《釋名》中將“仙”釋義為人生的某個階段:
“人始生曰嬰兒。
七年曰悼。
十五曰童。
二十曰弱。
三十曰壯。
四十曰強。
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
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
七十曰耄。耄,頭發白,耄耄然也。
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九十曰鮐背,背鮐文也。或曰黃耇,鬢發變黃也,耇,垢也,皮膚驪悴,恒如有垢者也。或曰胡耇,咽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如凍梨色也。或曰齯齯,大齒落盡,更生如小兒齒也。
百年曰期熙。熙,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也。
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①劉熙:《釋名?釋長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54頁。
“老而不死曰仙”,據《禮記?曲記》所記: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髦。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
又三國韋昭注《國語?吳語》稱:“六十曰耆,七十為老”,可知古人以年至七十則為老,老而未死便可稱之為仙,可見上古時代的仙其實是人生終點年齡階段之稱謂。古人(通常指男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安排不同的責任,如十歲入學,二十成年,三、四十歲時身心強壯、成家入仕,五十聰明剛毅可以為首領,六十氣力衰竭但仍可口頭指導他人,七十以后則應將家業傳與子孫、不再參與世務。人類學者稱此安排為“年齡級序”(age gracle)或“年齡等級”。非洲、美洲諸多古代民族中都流行年齡等級制度。如非洲肯尼亞境內的南迪人有七個年齡等級,未成年的小孩子為第一等級,十多歲時參加嚴酷的割禮儀式后成為第二等級即成年人,此后每隔七、八年即在舉行儀式后升入更高等級如“勇士”“長者”“老人”“真正的老人”“最老之人”。不同等級者身份、責任皆不相同,第一等級者被視為孩童;第二等級之成年人被視為部落正式成員,但尚無資格與女性發生性行為;勇士等級專以作戰為業,已有與女性交往的權利;但直至長者等級方可娶妻生子成家立業;進入老人等級的一輩人還要進行莊嚴的“移交部落”典禮,殺白色閹牛獻祭祖先,將部落管理權力轉交給下一等級人群,自此以后只負責提出建議、敦正風俗。隨著年齡漸老,等級越高,就越發從世俗生活中隱退,轉而專注于與祖先和神靈的神秘溝通和相關儀式活動中,直至最終老去。②[英]雷蒙德?弗斯:《人文類型》,費孝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78—80頁;[美]E?S?米勒、C?A?維茨;《按年齡進行社會分層》,《民族譯叢》,1982年第1期。類似的習俗也存在于東方文化中,如上文所引“大夫七十而致事”、日本傳統文化中家長在兒子成年后移交家產與權力的“隱居”制度,③江新興:《日本隱居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40—55頁。都是很明顯的例證。
年齡等級的轉移不僅意味著社會責任與身份的改變,也伴隨著生活方式與生活空間的變化,如日本傳統文化中隱居的老人要從家中主屋遷出,搬到附近的“隱居屋”中居住,不再參與村落的公共活動。除年老之外,成仙尚有另一重要的條件:“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仙人與山有密切的聯系,年老之人還需遷入山中方可稱為仙。故而《說文》釋“仙”為:“仚(即仙之古體字),人在山上貌,從人山。”《說文?人部》中“仙”又作“僊,長生僊去也,從人,從僊,僊亦聲”,“僊,升高也”,“登也”。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第383頁。“長生僊去”者即為仙,“長生”即為年老,先有長生之年齡,再“僊去”山中,脫離日常社會生活的束縛,即可稱為仙,故而仙字古意又有拋開禮儀束縛、無拘無束之意。
由此可知,古人認為在生命中經歷足夠長的時間維度而到達所謂“老而不死”的階段,同時又在空間維度上脫離世俗的生活空間,進入充滿神秘色彩的“非人間的山中”,②關于中國民間信仰中,“山”這一意象所具備的神秘性和同時兼具恐怖與誘惑雙重象征意義,可參考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所著《中國的妖怪》(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9年)中相關論述。即可在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上發生改變,而改變之后的新身份即所謂“仙”。聞一多曾指出:“仙在最初并不是一種特殊的人,只是人生活中的一個理想的階段而已。”③聞一多:《神仙考》,《神話與詩》,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74頁。理想與否尚待討論,但早期所謂的仙確實只是指人生的最后階段,則人人皆有成為仙的可能,這是仙與神之區別;成仙之后,肉身依然存在,區別于虛幻的靈魂鬼魄,這兩個特點使長生成仙的信仰別具特色。
二、棄老故事與死亡儀式
仙字之古意與“棄老”故事講述的棄老習俗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意味著老人根據習俗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隔離于山野之中并改變其原有的社會身份與角色;都體現出步入老年所帶來的生理、心理變化以及相伴隨的角色身份、生活空間的改變乃至直面死亡本身時的態度,其中寓意頗值得玩味。
棄老故事至今仍流傳于中、日、韓等國,④李道和:《棄老型故事的類別與文化內涵》,《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在類型上可分為980A“換位觸動”與981“智決難題”兩大亞型,⑤李道和:《棄老型故事的類別和文化內涵》,《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具體參見丁乃通編著:《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段寶林等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棄老故事的研究頗受關注。⑥參見畢雪飛:《中日棄老故事比較研究——以“原谷”型與“姥捨型”為中心》,《民俗研究》,2015年第5期;金寬雄:《略論“棄老”型故事在中韓兩國的流變》,《延邊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陳繼淑、陳昌珠:《多學科視角下的古代賤老習俗——從湖北寄死窖談起》,《民俗研究》,2005年第4輯;李道和:《棄老型故事的類別與文化內涵》,《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等。
棄老是人類特定歷史階段廣泛存在的古老習俗,即將老人遺棄于日常生活之外,與社會生活相隔絕令其自生自滅的習俗。盡管有學者認為“棄老”型故事是受到印度佛經《雜寶藏經》中“棄老國緣”故事的影響而產生,⑦金寬雄:《略論“棄老”型故事在中韓兩國的流變》,《延邊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但馬長壽在1936年就已結合文獻資料與山西田野考察所得考古資料、民間傳說,撰寫《中國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與再現》一文,指出中國古代北方部分地區直至金元時期還存在“花甲生藏”的習俗,即年過六十的老人被送入墓壙中生活,死后該墓壙即為老人葬身之地。生藏之俗為歷史上東北、蒙古乃至西伯利亞匈奴、鮮卑、蒙古、雅庫特等游牧與游獵族群盛行的習俗,華北居民歷史上與北方游牧族群互動密切,故而生藏之俗在中國北方部分地區至金元時代仍很常見。馬氏一文不僅證明棄老生藏之俗在中國歷史上的真實存在,更指明該習俗與北方族群的關聯,可視為國內學界研究棄老習俗的濫觴之作。①馬長壽:《中國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與再現》,《馬長壽民族學論集》,馬長壽著、周偉州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48頁。近年來,劉守華等學者在漢水流域發現大量“棄老”故事乃至“寄死窖”等考古遺址,②劉守華:《走進“寄死窖”》,《民俗研究》,2003年第2輯。宮哲兵:《野蠻“棄老”俗的見證——武當山寄死窖》,《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閆勇、王桂芳:《湖北的“寄死窖”與膠東半島的“模子墳”》,《民俗研究》,2005年第1輯。劉守華:《“寄死窖”棄老習俗與傳說交融生輝》,《文化月刊》,2010年12期。徐永安:《漢水流域“自死窖”遺址類型及其傳說的民俗信仰內涵》,《湖北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徐永安:《人類學視域下“老人自死”習俗的民俗信仰本質與文化價值》,《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等文。證明了巴蜀荊楚歷史上也曾經長期存在棄老習俗。
棄老習俗的成因常常被功利性地解釋為物質生產水平的低下和生活資料的匱乏令老人被迫做出犧牲。③陳繼淑、陳昌珠:《多學科視角下的古代賤老習俗——從湖北寄死窖談起》,《民俗研究》,2005年第4輯。本文作者已在另文中指出“棄老”故事及習俗背后存在著“老化異類”的民間信仰,即高齡老人能夠變身為獸類乃至妖魅等異常之物,甚至會危害家人與社會,也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對人生老年狀態特殊的禁忌與信仰。④參見海力波:《老化異類故事中的老年意象與人觀表述》,《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6期。如秦漢魏晉時人們普遍相信“物老則為怪”,⑤(東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九“孔子談五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頁。人老則為魅,如:
“夏縣尉胡瑣,詞人也,嘗至金城縣界,止于人家,人為具食,瑣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發,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戶。瑣就而窺之,納母于檻中,窺望兩眼如丹。瑣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為魅,乃七代姑祖也,壽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鎖之檻,終歲如常。忽得出檻,偷竊飯食得數斗,故號為魅。’瑣異之,所在言焉。”⑥(宋)李 昉:《太平廣記》“妖怪”第六十七“胡瑣”,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1988頁。
“魅者,老精物也。”⑦(東漢)許 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88頁。據學者研究,魅是中國傳統信仰中獨立于天神、地祇、人鬼的一種神秘存在,⑧楊清虎、周曉薇:《論中國古代文獻中的“魅”觀念》,《文化遺產》,2012年第3期。魅之信仰起源于先秦、形成于漢魏,隋唐時期趨于成熟,對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深遠,宋元以后,漸漸與狐精鬼怪等民間信仰對象融為一體。⑨楊清虎:《淺論魅觀念的緣起》,《安順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魅之含義,據《山海經?海內北經》稱:“祙(魅),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⑩方韜譯注:《山海經海內北經》,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19頁。許慎《說文解字》釋“魅”為:“魅,老精物也。從鬼 彡 ,彡,鬼毛。”鬼身而有須毛,為可見之實體。鬼者,歸也,鬼無實形,魅則有實體存在。漢魏隋唐時人常常將“老魅”連稱,認為魅乃人之極老者所化,人至于極老而不死,則化為魅,除上文故事之外,唐代敦煌變文中所記《孫元覺》故事亦可作為佐證:
“孫元覺者,陳留人也。年始十五,心愛孝順。其父不孝。元覺祖父年老,病瘦漸弱,其父憎嫌,遂縛筐輿舁棄深山。元覺悲泣諫父。父曰:‘阿翁年老,雖有人狀,惛耄如此,老而不死,化為狐魅。’遂即舁父,棄之深山。元覺悲啼大哭,隨祖父歸去于深山,苦諫其父。父不從,元覺于是仰天大哭,又將輿歸來。父謂覺曰:‘此兇物,更將何用?’覺曰:‘此事成熟之物,后若送父,更不別造。’父得此語,甚大驚愕:‘汝是吾子,何得棄我?’元覺曰:‘父之化子,如水之下流,既承父訓,豈敢違之。’父便得感悟,遂即卻將祖父歸來,精勤孝養,倍于常日。”
此則故事屬于棄老故事中的980A“換位觸動”亞型。①李道和:《棄老型故事的類別與文化內涵》,《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隋唐以前之《孫元覺》故事中老人被認為“年老,雖有人狀,惛耄如此,老而不死,化為狐魅”,應該棄于深山,與他人相隔絕,體現出將老人視為不潔與不吉之物的古老禁忌,②具體論述參見海力波:《老化異類故事中的老年意象與人觀表述》,《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6期。有趣的是,唐代以后的《元覺》故事雖仍作為盡孝故事的一個重要故事類型,但原有的“老而不死,化為狐魅”之關鍵語句,卻不再見于故事文本中,亦可見此觀念已隨時代變化逐漸退出人們的信仰視野。也是棄老習俗得以存在的信仰與觀念基礎。老年人體貌變形、言行遲緩、體味濃烈、性格乖戾等明顯的衰老特征會令人在本能上產生反感、排斥的心理。人的壽命有限,超出大多數人生命歷程的的壽數,會被認為不可思議、超出常情常理: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③(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五,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82頁。
甚至有可能被認為是通過某種不正當的手段對他人生命力的竊取。④海力波:《老化異類故事中的老年意象與人觀表述》,《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6期。以此禁忌觀念為基礎,古人對進入特定年齡階段的老人進行某種隔離或過渡儀式,助其順利過渡生與死之間的閾限階段,也就不足為怪了。
“棄老”故事正是此種死亡儀式的記憶與反映。蘇聯故事學家普羅普指出:
“常有這樣的情況,盡管故事起源于儀式,可儀式卻十分模糊,倒是故事將往昔保存德如此真實完好,以至于儀式或其他現象只有通過故事才能得到其真正的解釋。換句話說,即可能會有這樣的情形,在經過進一步研究的情況下,當故事從本來是被解釋的現象變為能做出解釋的現象時,它可能成為研究儀式的文獻資料。”⑤[俄]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維奇?普羅普:《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賈放譯,施用勤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4—15頁。
棄老故事中的棄老習俗雖已消弭,但仍有歷史殘留存在。如鄂西利川縣土家族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尚流行被稱為“做活夜”的儀式:
“所謂做活夜,就是當老人做六十、七十等大壽時,一切活動按老人逝世后辦喪事的規矩進行。堂屋內扎靈堂,兒女子孫戴孝舉哀,道士做法事,孝獅孝龍齊舞,而老人則坐于靈前接受參拜,三日后結束,一切舉孝設施燒毀。境內人士認為‘生朝滿日’是人之大事,子、媳、女、婿必須到場祝賀,忘了則必受到呵斥。”⑥湖北利川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利川市志》,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489頁。轉引自蔣芝蕓:《魚木寨“做活夜”民間習俗的文化意蘊初探》,《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利川土家族地區遺留著“智解難題”型棄老故事和大量“寄死窖”遺址。根據當地流傳的“過去老人六十歲要被送到寄死窖中等死”的情節,我們可以將“坐活夜”視為某種象征性的葬禮,此后老人被送入寄死窖之類的地點,與家人和社會生活相隔絕,在另一生命狀態中等待肉體死亡的來臨。這樣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也有西南少數民族的民族志資料為佐證,如貴州安順市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蒙正苗族居住區,直至20世紀50年代初仍存在棄老習俗:
“就是覺得老了,做不得事情了,那就什么呢,大家坐一下吧,辦一點酒菜,招待親友,然后修一座墳墓,就把這一個(老)人埋進去了,里面放著幾天的食物,然后把墳封死,這種墳墓被當地人稱作‘活人墳’。”①徐永安:《中國“老人自死習俗”相關歷史記憶重釋》,《江漢學術》,2014年第3期。
蒙正苗族歷史上聚會、辦酒菜招待親友,為老人送行的儀式,應該與“做活夜”大同小異。中國北方漢族“花甲生藏”的傳說中也講到與“坐活夜”類似的“活祭”儀式:
“在遠古時代……一個人僅可過一個甲子年……但不幸有人在六十開外還活著,皇帝便不準他活在人間,請他去‘生藏’中去過活,事前,子孫為他修筑生藏。……修妥后,回家宰殺牛羊,宴請賓客,然后各親友家屬對于這位活祖宗舉行活祭,祭畢便把他送到陰黑的藏里,由此便不能重見天日。”②馬長壽:《中國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與再現》,《馬長壽民族學論集》,馬長壽著、周偉州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頁。
由于棄老故事逐漸轉化為以道德訓誡為目的,文本中對老人進入“等死”這一過渡狀態后的描述往往語焉不詳,老人或因各種原因免于被棄,或稱老人被棄置于山林或石穴中不久即死,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棄老習俗盛行的時代,老人從社會和家庭生活中隔離直至肉體死亡有可能要經歷相對較長的時間過程。如北美瓦拉吉印第安人中有棄老之俗,有一老婦因雙目失明,而被子女所棄,漫游于坎山四野。西伯利亞勒那河的雅庫特人古時風俗,年老者自請子孫安頓他們,子孫在野外營造洞穴、設置碗筷用具,兼備少許食物,推送老人于其中,有時老年夫婦合送一處,直至于死。③馬長壽:《中國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與再現》,《馬長壽民族學論集》,馬長壽著、周偉州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7頁。皆可為證。湖北荊山的當陽縣、遠安市漢水兩岸多有棄老故事和“自死窖”“老人洞”遺址,這些人工開鑿的洞穴遺址中可見依山開鑿的灶、架木為床的孔樁、儲糧石柜和裝門樞用的石孔,當地的考古發掘也在老人洞中發現數百件銅鏡、銅錢、銅熨斗、鐵剪、瓷器與裝飾品等,年代從兩漢到隋唐不等。如果當地“自死窖”“老人洞”傳說屬實,被遺棄的老人有可能在其中生活較長的時間,相對平緩而悠長地渡過生命中最后的閾限狀態,否則無法解釋老人洞中上述日常生活實用設施的存在。④稅曉潔、成志平:《漢江“老人洞”:懸崖里的迷》,《中國國家地理》,2009年第3期。當地民間也傳說曾有個別老人在洞中活到93歲仍未死,反而童顏鶴發、精神矍鑠。⑤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c483f01009ij3.html老人洞大多集中排列,少則數個、十幾個一字并列,多則數十個,分為兩、三層、個別地方多至五層。過去生活于其中的老人應該不止一人,很有可能是同時有多人集中生活,形成某種老人社群,甚至與山下世界保持某種聯系。柳田國男就曾指出日本古代很多村落附近都有被稱之為“蓮臺野”的地方,通常與被稱為“壇之塙”的村落墓地遙遙相對,老人們集中在此生活,共同等待死亡的來臨:
“照古時的習俗,年過六十的老人都會被趕到這個叫蓮臺野的地方。老人們一時不會輕易死去,只好白天下到村里去干一些農活糊口。所以現在土淵一帶還把早上去田里干活稱為‘出墳’,晚上從田里回家叫做‘進墳’。”⑥[日]柳田國男著:《遠野物語》,吳菲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12年,第63—64頁。
明清兩代云南彝族亦有棄老習俗,明朱孟震《浣水續談》稱川滇:
“又一種玀夷(彝族)變秋胡者,居深山窮谷,平生食荍面,少嘗鹽鹵之味,至九十余或百歲,尾閭骨漸長,如獸尾禿根,遍體生毛,手行于地,漸食生物。其子孫預于深林挖一深窟,置諸腥果食物于其中,一日以氈衫包擁其頭目,舁至窟所,潛自散匿,而彼遂忘歸,乃食所置之物,久則成獸,如熊猿之類,矯健勇勁,登木臥草,水飲洞居,數百歲不死,子孫以為榮福。冬月夷人采降真香于山中,時或見之,猶知近人。”
明謝肇淛《滇略》卷九“夷略”中稱:
“蒙山老爨不死,久則生尾,不食人食,不認子女,好山惡家,健走如獸,土人謂之秋狐。然亦不恒有。元時羅武蠻羅僄百年尫弱,子孫以氈裹,送之深箐后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不知所終。”
秋胡為漢人之稱謂,當地人稱之為綠瓢,如清嘉慶年間曹樹翹所著《滇南雜志》“綠瓢”(志作秋胡)條記:
“云南黑白??往往有壽至百數十歲者。相傳至二百歲則子孫不敢同居,舁之深山大箐中,為留四五年糧,此?漸不省人事,但知食臥而已,遍體遂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尾長于身,朱發金睛鉤牙铦齒。其攀徙巖壑,往來如飛,攫虎豹麞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為綠瓢(今臘撒后山野人有生尾者,人恒見之)”①(清) 曹樹翹著:《滇南雜志》卷九?十六,臺北:華文書局有限股份公司,1969年,第349頁。
秋胡綠瓢之說實際是對當地彝族居民中存在的棄老習俗的渲染附會之辭。②朱雙和:《從“綠瓢”與“秋胡”看中國的老虎外婆型故事》,《文學與文化》,2012年第3期。從子孫為老人在山林中挖窟做屋、留四五年食來看,老人應該在山林中生存較長一段時間,甚至還可以有采香、打獵等謀生活動——也因此偶爾會與當地人相遇“時或見之”——“登木臥草,水飲洞居”說明過著“野化”的生活。雖然在進入老人階段后“子孫不敢同居”,但棄老之后則“子孫以為榮福”,可知其背后存在著某種信仰習俗。
人死曰喪,入土曰葬,葬者,藏也。東北與巴蜀西南地區流傳的棄老故事中有部分與腹葬相關。腹葬也稱食尸葬,即老人死后,家人親族出于禮儀或信仰的原因分食其尸體的葬俗。③參見李天雪:《淺論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食尸葬禮儀》,《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6期;李天雪:《我國西南少數民族歷史上的腹葬習俗及其歷史演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1期。西伯利亞雅庫特諸族歷史上多有棄老、賤老之俗,我國東北少數民族歷史上亦有相似習俗,如鄂溫克族傳說過去有老人上百歲后,因年老無用,雖身為薩滿,也無法避免被兒媳殺死的命運,死后反被作為家族守護神而得到祭拜。④呼格吉樂瑪:《“通古斯”鄂溫克薩滿儀式及其象征》,內蒙古師范大學學位論文,2011年,第21頁。清時當地尚有此俗,如《嘯亭雜錄》“和真艾雅喀”條記:
“吉林東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剪魚皮為衣裙,以捕魚為業。去吉林二千余里,即金時所謂海上女真也。其舊俗,父母至六十誕日,即聚宗族會飲,剮其父母軀肉,以供賓客,埋其骨于戶樞前,歲時以為祭奠,其鄉黨始稱孝焉。”⑤(清) 昭梿撰:《嘯亭雜錄 續錄》“和真艾雅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2頁。
“和真艾雅喀”即東北世居族群之稱謂,其舊俗雖有“剮其父母軀肉”行為,但并非是野蠻、殘忍之行為。當時之人已有盡孝的觀念,老人遺骨不得遺棄,而是必須埋于戶樞前,以方便經常祭奠,也是希望老人的靈魂能夠抱有后代居所的平安,可見食老人之肉、祭老人之骨是出于某種信仰實施的腹葬儀式。據近代西方旅行者稱,蒙古高原上的韃靼人也有殺死老年父親的習俗,然后焚其尸體,每日餐中置尸灰少許吃下。①馬長壽:《中國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與再現》,《馬長壽民族學論集》,馬長壽著、周偉州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頁。這應該也是腹葬習俗的表現。漢水流域的“老人洞”“自死窖”遺址中未發現死者遺骨存在,有學者認為“自死窖”又稱“寄死窖”,應當只是老人生命結束之地,而非喪葬之地,老人死后還應有喪葬儀式的舉行。又有學者聯系當地流傳的“六十老人殺了當菜招待客人”的民間故事,認為“自死窖”與食葬(腹葬)有關,②稅曉潔、成志平:《漢江“老人洞”:懸崖里的迷》,《中國國家地理》,2009年第3期。湖北武當山丹江口市流傳的“人吃人肉”故事恰好為“自死窖”與腹葬之間提供了文本的過渡:
“很早很早以前,人屁股上有尾巴,……尾巴上的毛一變白,人就要死了。人死以后,按照當時的風俗,死人的尸身要用刀子割成碎塊,分給親戚、朋友和鄰居們吃。……有某子外出時,其母發現自己尾巴上的毛變白了,就跑進大山,藏進巖洞中,死了。兒子找到媽媽,尸身已臭,不能給別人吃,就在脊梁上墊塊麻布將其背回家。然后上山打了一些野獸,將獸肉分給大家,煮熟后發現比人肉好吃,從此以后就不再吃人肉了。兒子將媽媽的尸身背到野外土葬了。披麻戴孝和土葬的風俗就一直流傳至今。”③出自徐永安:《中國“老人自死習俗”相關歷史記憶重釋》注7所引文本,《江漢學術》2014年第3期。
老人死于山中巖洞,是棄老習俗的表現,死后依俗分尸食之,因兒子外出延誤而令肉體發臭,不能舉行腹葬儀式。此后因獸肉味道更好而放棄食人習慣固不可信,腹葬被土葬代替,實為以披麻戴孝為象征的新的道德倫理獲勝的結果。
類似習俗變遷的歷史過程在西南地區普遍存在,如貴陽市烏當區布依族傳說:“人吃人的朝代,人到八十不死也要殺。”“老人死了,三親六戚都要拿著刀子來割老人的肉吃。”④《迪靈砍牛祭喪的傳說》(今擬),羅紹禹口述,徐新建采錄,見其《羅吏實錄:黔中一個布依族社區的考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頁。貴州《開州志》記:“狆苗(布依族),親喪,舊俗分食親肉,后變用牛,視之如親,謂之‘替例’。”⑤《開州志》,轉引自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南卷下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514頁。布依族與壯族同源,廣西東蘭縣壯族傳說:“過去我們祖先也是吃人肉的”,“人病了,或者老了,都被殺來吃。”⑥廣西師范大學僮族文學史編輯室編:《廣西僮族文學資料:故事歌謠及文人作品》(內部資料),1960年,第92—93頁。其原因在于:
“聽老人說,古時候,人老死了,肉要分給眾人吃,骨頭要留下埋掉,這樣才算尊敬老人。還說這是天上雷王定下的規矩。”⑦《雷鼓的傳說》,李哲等講述,流傳地:廣西東蘭、巴馬等縣,《壯族民間故事選》,藍鴻恩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53頁。
由此可以看出,食老本是棄老習俗的一個環節,老人死后,將老人肉體安葬在親人腹中,“這樣大家才記得他”,分食死者肉體也是將死者的生命力轉移至自身,令靈魂或生命本身得以生生不息的崇高行為,直至新的道德倫理出現,腹葬才普遍被殺牛祭祀所代替。
至此,本文已復原故事文本背后古老死亡儀式之形貌:進入社會所認定的老年階段后,老人在“做活夜”“活祭”等儀式中喪失其原有的社會身份與職能——脫離社會空間、進入山林、“自死窖”等荒野之地,經歷或長或短的野化生活——迎來肉體死亡,通過腹葬等儀式使自身的靈魂或生命力與子孫結合在一起,實現生命的新流轉。不難看出,死亡儀式在結構上與仙話即神仙故事中常見的敘事模式:棄世——山林隱逸——蛻化為仙、長生不死(重生)在結構上的相似之處。
三、長生成仙信仰與棄老習俗
長生成仙信仰興于戰國,盛于秦漢,魏晉時期被道教信仰所發揚光大,凡軀不死、肉身成仙成為神仙之道的核心,保留了較多長生成仙信仰的原始觀念。唐代以后,肉身不死之說式微,而修煉內丹、煉氣化神的靈魂成仙說盛行,①弋舞:《道教成仙說的流變及其原因淺談》,《中國道教》,1992年第2期。長生成仙之說故而走向衰微。
唐前仙話多收錄于《太平廣記》“神仙”“女仙”卷中,②(宋)李昉著:《太平廣記》“神仙”“女仙”,陳成國、蔣冀騁、梅季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1—311頁。本文所引文本,凡未特別注明者,皆出此版本,下不贅注。其中頗有與棄老習俗有關者,如《李清》(出自《集異記》)中記:
“李清……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飲食,……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為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云門山,神仙之窟穴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縋而下,以纖縻為媒焉。’……眾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赍酒饌,遲明,大會于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乃棄簣游焉。”
李清七十生日之行為與上文所引“活喪”儀式頗為相近,屬于主動的棄老行為,《嵩山叟》(出自《神仙拾遺》)則是某種被動的遺棄行為:
“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淺,百姓每歲觀游其上。叟嘗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倘不死,投食于穴,墮者得而食之。”
雖云誤墮,卻不施救,知其不死,投食于穴,聯系到河南俗語稱老人去世為“上山”,即來源于古時讓老人到山上等死的習俗,③李道和:《棄老型故事的類別和文化內涵》,《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老人墮入穴中、他人投食于穴應該也是棄老的表現。除老人之外,病弱垂死之人,也在被棄之列,如《趙瞿》(出自《神仙傳》):
“趙瞿者,……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于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為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哭泣,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乃以松子松柏松脂各五升賜之……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
趙瞿因病危被家人送入山中石室,以木砦之,留糧待死,其悲傷恐懼之細節描述詳盡,是棄老習俗的真實寫照,所遇三人未見神跡,只是以山中松柏為其治病,實為被精通醫術之山民所救。與此類似的還有《李衛公》(出自《原仙記》)記有賈販之徒“少染大風,眉發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于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老人將其帶入草堂中,醫治二月余,病愈后得歸人間。又“女仙”中《玉女》(出自《集異記》)記華山有婢女名玉女“大疾,遍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后食山中青草病愈,“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有趣的是,玉女病愈后在山中過著某種野化的生活,也因此被人們視為神明,“雖屢為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為玉女耳,……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直到某行為粗狂的書生將其獵捕,“扃之一室”,才發現其實只是“皤然一媼,尪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計其年蓋百有余矣。眾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剔除文中神異情節,不難發現這只是一位老嫗被棄后野化生存直至死亡的曲折寫照。
仙話中棄世之后修仙隱逸之情節多源自棄老習俗中老人閾限狀態下的生活狀態,以下三則皆出自東晉葛洪所著《神仙傳》,為早期修仙生活之寫照:
《孔元方》:
“又鑿水岸邊,作一窟室,方廣丈余,元方入其中斷谷,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柏樹,生道后荊棘間,委屈隱蔽,弟子有急,欲謁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
《焦先》:
“居河之湄,結草為庵,獨居其中,不設床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人交游。衣弊,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夏單衣。”
《劉根》:
“后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余丈。”
修仙者需隔絕塵世,或結草為庵、或避居石室洞窟頗近于老、病弱之人被棄于日常居所之外的習俗,如古代日本阿依努人即有隔絕垂死者之俗:“蝦夷人(阿依努人舊稱)為了保存舊有的住所,他們往往為行將死去的老弱者另搭一個小窩棚,將他們供養在里面。待其亡故后將小窩棚燒毀,用以替代過去那樣的捐棄。”中國古代亦有相似習俗,①王仁湘:《史前捐棄房屋風俗的再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皆為死亡儀式中閾限狀態的寫照。
仙人以松柏芝草為食物,《毛女》(出自《列仙傳》)中云: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此。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馀年矣。”
《秦宮人》(出自《抱樸子》)中云:
“漢成帝時,獵者于終南山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齊人逾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餐,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后稍便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
草根樹皮、松子松脂確是現實生活中饑民之食物,服食松柏成仙正來自這一現實生活背景。②唐娜:《仙道小說中服食松柏成仙的現實背景》,《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又據《搜神記》神仙第一引《淮南子》中《若士》記: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谷之上。而見若士焉,其為人也,深目而玄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盧敖就而視之,方踡龜殼而食蟹蛤。”
則仙人如若士者,居于深谷之中,形體怪異憔悴、見人則逃于墓碑之后,以龜蟹蛤蜊及草根樹皮松子為食,確乎符合于仙之古意,即為野化生存老人之形象。早期仙人之形貌大多丑怪,尤以體生綠毛、背生雙翼為特征,如《蘇仙公》(出自《洞神傳》)中:“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又《劉清真》(出自《廣異記》)中“其人……通體生綠毛”; 《劉根》(出自《神仙傳》)“后棄世學道,……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須鬢,皆黃,長三四寸。”《玉女》《蕭氏乳母》(出自《逸史》)中皆有類似“食松柏,長綠毛、可飛行”的描述,《姚泓》(出自《異史》)中更以“唯餐松柏之葉,年深日久,遍身生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將體生綠毛作為成仙之體證。王充在《論衡?無形》中明確表示:“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于云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漢墓畫像磚與青銅器造型中仙人多為羽人狀,有學者認為仙人形貌應是傳統飛鳥圖騰與西方雙翼天使造型相結合的產物,①賀西林:《漢代藝術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義》,《文物》,2010年第7期。但本文作者認為“體生毛”這一特征應是野化生存惡劣條件下,營養不良導致新陳代謝紊亂而發生的體貌變異。若士“深目而玄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頗近于因缺乏食鹽而導致的所謂低鈉血癥狀,如皮膚變黯、頭發灰白、四肢細、眼窩與前鹵凹陷等癥狀。民間傳說中“白毛女”因缺乏食鹽而導致頭發變白,前文所引西南彝族所信仰之“秋胡”大多有“少嘗鹽鹵之味”的特點,應該都是對類似野化生存狀態的反映。
唐前仙話中的神仙世界雖有瓊樓玉宇、云霄洞府之描述,卻也不乏較為寫實的場景,如《韋仙翁》(出自《異聞錄》)中記韋君至華山腳下,與老者攀談,知其為己之高祖,老父謂之:“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有一布袱,袱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賣。”韋君隨老父“入山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余,俱垂發,皆以木葉為衣。”可知韋姓高祖、祖、父輩皆有棄世入山中之傳統,雖為仙道,仍需自作自食,以山中特產與外界市貿,則山中石室也大致與前文所引日本古代“蓮臺野”之地相似,甚至可能為韋姓家族世代相傳之“自死窖”“老人洞”,故而該族之老人在其中仍結群生活,未死之前仍需勉力謀生,與日本被棄之老人下到村落中干農活,或彝族“綠瓢”老人于林中采香皆相近。
唐前仙話中主人公潛隱林谷而成仙,成仙后也只是形體變化、肉體長生不死而已,未見有后世所謂禁咒鬼神、幻化萬端之道法仙術,時人因此有仙人未足為羨之觀念,此點尚未得到后世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如在魏晉時期,成仙與得道尚被視為兩種不同的長生之法,仙人與得道者存在很大區別,如《神仙傳》中《彭祖》云:
“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結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乃可貴耳。”
得道者需主動修煉,借房中術、服氣、吐納導引諸術而“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然后“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永享人間世俗生活之樂。仙人雖有不死之壽,但卻需遠離俗世、體貌變異,失去人之情感,“失其本真”,雖長壽亦不足榮樂。且仙人是被“異氣”所感,“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 是某種被動變形的產物。如《搜神記》卷十二《五氣變化論》所云:“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海為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皆為年深日久、自然化成之結果。如前文所介紹之老魅信仰,人極老而化為魅,則或檻之于牢籠,或送之于山野;禁于檻中,與人世相雜處,恐有害于人,則被蔑稱為魅;遷之于山野,無害于人,則稱為仙。王充《論衡》中稱魅為“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①黃暉:《論衡較釋》卷二十一,《訂鬼》,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3頁。殆與仙相似,皆為棄絕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老人之曲折寫照。而上古之仙,亦未足為人所羨焉,如司馬相如《大人賦》中云:“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葛洪《抱樸子內篇?論仙》引《仙經》稱:“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蛻,謂之尸解仙。”晚唐杜光庭在《墉城集仙錄》中將成仙之道歸納為:“夫神仙之上者,云車羽蓋,形神俱飛;其次牝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托象,蛇蛻蟬飛。然而沖天者為優,尸解者為劣。”②(唐)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頁。聞一多于《神仙考》中認為仙道中“飛升”登霞為西方羌人相信火葬時靈魂乘煙霞上天之反映,尸解中所謂兵解其實是因“以戰死為吉利”的觀念,而在垂死時以兵刃自殺而求得靈魂即刻解放,確為的論,不需贅述。但靈魂解放與肉體不死兩者間也存在實際的區別。如果將飛升、尸解與腹葬儀式相聯系,則可知靈魂不死與肉體不死實為一體。登霞之前、兵解之后,親族將死者肉身分食,即可保證死者肉體亦長存于世。《史記?封禪書》稱燕人宋毋忌等:“為方僊(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形解銷化”依張晏注云:“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世人見山中古生物化石,骨存肉銷,則謂之化去,仙人之化去亦如此,則仙人亦為骨存肉銷。所謂仙人依注解實即老人,可見張晏尚知仙之本意;老人解去故骨,則可變化為仙,亦當令老人骨存而肉銷,其實即為上文所引《嘯亭雜錄》“和真艾雅喀”條記,骨或焚或埋,各依其俗,但肉身則多分而食之,以存其魂于世。《酉陽雜俎》中記:
“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鉤鎖,附苔絡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煉形濯魄之士乎?”③(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0頁。
此骨極可能為前代棄老腹葬之后所遺之物。而仙道中食人肉以長生成仙之記載亦頗有致。如《維揚十友》(出自《神仙感遇傳》)記:
“維揚十友者,……慕玄知道者也。忽有一老叟,……領十人來,以造其會。……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帊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既撤油帊,氣潼潼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眾就食,……因謂眾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為上仙。’”
又有《陳師》(出自《稽神錄》)云豫章梅氏遇道士陳師,設齋共食,陳師“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道士嘆息:‘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時出游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④(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五,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203頁。草木能化為血肉精髓,仍是視人之血肉為生命力與靈魂之轉喻。新幾內亞胡亞人以為生命生生不息之精髓“奴”(nu)存在于人之血肉與體液中,但其數量有限無法增加,只能通過代代相傳而承續,故而親族會將死者的血肉體液分而食之,外人不得染指,以確保“奴”在家族內的保存延續,而骨頭則被秘密放置在獵場、園圃、森林中的洞穴樹縫中,以令死者在“精靈世界”中復活。①[美]桑迪著:《神圣的饑餓:作為文化系統的食人俗》,鄭元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93—126頁。其處置血肉骨骸之象征含義恰與“形解銷化、解去故骨”之說相類似。
四、棄老習俗與長生成仙信仰的歷史聯系
聞一多認為,神仙思想出自西北羌人,隨羌人自西北經陜、晉、燕趙而傳播至齊魯之地,②聞一多:《神仙考》,《神話與詩》,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71頁。秦漢之后,神仙思想在巴蜀荊楚之地盛行,與西南氐羌夷蠻各族群原始信仰相結合,巴蜀成為早期神仙道教的淵藪。③卿希泰:《道教在巴蜀初探》(下),《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5期。童恩正曾指出,東北自西南的邊地半月形山地、高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以氐羌族群為主的北方游牧、游獵族群往來遷徙,形成一個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傳播帶,④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南方文明:童恩正學術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年,第371—410頁。長生成仙信仰之起源應當是該傳播帶內游牧、漁獵族群與農業族群文化交融的產物。
長生成仙信仰不見于三代,其興起于春秋戰國時期,正是此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內族群遷徙與交融劇烈之時。“周貞王八年(前461年)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逾汧隴。”即北方羌戎與中原華夏族群發生激烈沖突之表現,后“秦獻公初立(前384年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旄牛種,越寯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⑤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69—2902頁。此即氐羌戎夷諸族群向西南地區遷徙之過程。族群沖突的同時也帶來文化的交融互動,此時也當是游牧、狩獵族群中棄老習俗逐漸見于中原、西南諸農業族群視野的時代。巴蜀是新月形文化傳播帶中游牧與農業族群文化交融最深入、也最輝煌之地。在巴蜀古代傳說中尚可發現文化交融之痕跡。據楊雄《蜀王本紀》記:
“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去。魚鳧田于湔山,得仙。今廟祀之于湔。時蜀民稀少。”
“蠶叢”“柏濩”“魚鳧”諸王皆為神話中之人物,其年代固不可確定,但從其田獵為生、蜀民稀少來看,仍處于游牧漁獵階段,當為南遷之氐羌族群代表。諸王皆“神化不死”,其實與《華陽國志》中所記其后蜀王杜宇“升西山而隱”一樣,是按照族群棄老習俗,隱化于湔山中,《太平御覽》卷八八八注曰:“(魚鳧)王獵至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于湔”,可見魚鳧諸王無墓無葬,皆隱于山中不見蹤跡,故稱其“不死”,后人無所寄托,只得立廟于山前祭之。“其民亦頗隨王去”反說明此俗有著深厚的民俗基礎,在民眾中亦頗盛行,民眾多棄老隱化于此山中,故而雖貴為王酋,亦須遵照當時部落棄老習俗主動隱化。稱其“得仙”,正說明“仙”與棄老之關聯。
《蜀王本紀》中又記:“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號曰望帝。”據《華陽國志》記杜宇“教民務農”,于是巴蜀之地始有農業,有城郭、池澤、畜牧、園苑之制,①(晉)常璩著:《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第26—43頁。望帝杜宇能夠令蜀與“巴亦化其教而力務農”,得力于其相鱉靈:“望帝積百余歲,荊有一人,名鱉靈,……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為荊楚之人、擅長農業水利,當為荊楚之地農業族群之代表,望帝“升西山而隱”后,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據《華陽國志》稱,開明帝之后,蜀地“始立宗廟、酒曰醪、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說明蜀地氐羌族群與自荊楚東遷入蜀的農業族群逐漸融合,接受中原華夏禮樂制度,望帝之后,蜀王不再入山隱化成仙,而是“每王薨,則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始有宗廟陵墓之制。自望帝倡導農業開始,蜀地“化民往往復出”,當為隨著農業與定居生活推廣,棄老之俗逐漸淡化。從《華陽國志》與《蜀王本紀》中曾有“望帝與鱉靈妻通(奸)”之記載來看,當時的氐羌族群與荊楚族群相互通婚,在文化上開始受后者影響,棄老習俗逐漸式微,在大多數地區變為怪異傳說,淡化出人們的歷史記憶,當然這一變遷過程為時甚長,歷經數百上千年之久,某些仍然以游牧、漁獵為生的人群囿于自然和人文環境的限制,在相對較晚的歷史階段依然實行棄老習俗亦并不足怪。
當然,對于荊強調“壽終正寢”的楚華夏居民而言,面對北方、西南少數族群之棄老習俗及死亡儀式時,自然會帶來既驚且駭的“文化震蕩”(culture shock),但其中所蘊含之坦然面對死亡、無懼生命終結、主動選擇生命結束等觀念也給后者帶來新的啟迪和思考。在華夏族群少數地區,棄老習俗與死亡儀式亦可能于現實中被接受,但主要而言,其觀念上的沖擊力更甚。方仙道與神仙思想固然是對棄老習俗的美化想象與扭曲反映,荊楚之地的老莊之道亦很可能受其影響。道家絕塵、隱逸的傳統很可能就是來自棄老習俗中對閾限階段生活狀態中神秘體驗的升華。非洲的霍丁督人“常把衰老的老人,馱在牛背上,一顛一跌地把他送到沙漠里去。事前族人在沙漠地方,筑一小屋,略備食物,老人直至吃完而死”②馬長壽:《中國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與再現》,《馬長壽民族學論集》,馬長壽著、周偉州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頁。豈不也可從中看到老子最終騎青牛西出函谷關的影子。然而求仙者企圖早早放棄社會責任與角色、主動迎接社會性死亡以換取個體生命在其后的閾限中無窮地延續,最終也只能化為幻影。老子雖消逝于西方流沙中,但其五千言卻千古不朽。肉體生命如流沙般實無法把握,只有立德、立功、立言之途能將個體融入亙古長存的社會之中。
[責任編輯:馬海燕]
K890
A
1008-7214(2016)03-0079-14
海力波,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科學研究工程“優青特色研究團隊”珠江-西江經濟帶民族文化發展研究團隊階段性成果;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13年度研究項目“美洲作物的傳播與壯族社會文化的變遷”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DMZ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