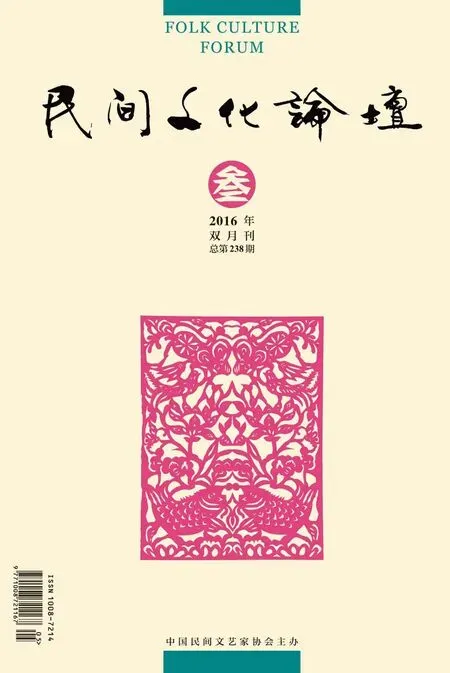論節日事項的“共有”“擴散”與“移借”諸問題—以端午節為例
宋 穎
論節日事項的“共有”“擴散”與“移借”諸問題—以端午節為例
宋 穎
我們可以用“共有”“擴散”與“移借”等幾個概念,來探索節日事項之間的關聯性,概括并解釋節日事項的繁雜多樣性。“共有”構成了節日事項在群體內世代共享的傳承基礎,它承載著一個民族群體內部共同的記憶和文化情感,是構建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擴散”涵蓋了人們在生活實踐中對同一個節日的文化元素的擇用,精準性和模糊性同時存在。“移借”是指將系列文化符號成組搬移,不局限于某一節日,體現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慣性。節日事項的“共有”“擴散”與“移借”,有利于習俗的在地化,呈現出適應性的細節變化,為人類的實踐和創新提供了可能性。
節日;共有;擴散;移借;端午
中國傳統中的重大節日,像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均名列在2006年5月20日由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往往被稱為“我們的節日”。其中,端午節于2009年10月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作①參見東方網10月3日消息:2009年9月2 8日至1 0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阿聯酋阿布扎比開幕,審議并批準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76個項目,包括了中國申報的22個項目,中國端午節名列其中。,是中國節日中惟一入選的傳統節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和生活智慧的代表。
從古至今,對于像端午節這樣的傳統節日事項的記錄和闡釋,都不無巨細地要列舉和描述當地過節方式。因此,我們能夠大致勾勒和講述一個節日“怎么過”,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民眾生活中,始終呈現著事項繁雜、變化多端的現實。因此無論哪個“共有”的傳統節日,我們仍然能夠發現在群體內有些地方或有些人聲稱“不過”或者“不是這樣的而是那樣的”。
盡管傳統節日擁有特定的名稱和相對固定的節期,并進入到國家層面的行政工作范圍,但仍然非常明顯地隨著地域和人群的變化而呈現出紛雜的多樣性,這使得某一共同體內“共有”的節日,往往成為一種概念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僅憑“共同的”或“我們的”籠統闡述,無法捕捉和交流具體的民俗細節;另一方面,倘若單憑某些標志性的事項來界定某個節日,就會發現其他區域或其他時間也出現相同或相近的事項,而陷入難以辨識的困境,更遑論厘清節日的源流。像端午節吃的粽子,用的艾草,劃的龍舟,祭祀的神靈,人們發現在其他時間也有相似的使用。這些一直以來都困擾著民俗學者和節日研究者。
因此,對于傳統節日的研究,除了收集、記錄、描述和比較節日事項的具體形態,更需要具有學術闡釋力的概念,能從根本上把握表面上多元化的復雜現象。筆者從對端午節跟蹤近十年的事項研究中,嘗試使用“共有”“擴散”和“移借”等幾個概念,來探索節日事項的變動性和關聯性。
一、“共有”:構建傳承的基礎并衡量群體的認同程度
節日事項的“共有”,形成了節日在群體內部共享并世代傳承的基礎,承載著一個民族群體內部共同的記憶和文化情感。這一方向的討論涉及到值得關注的民俗國家化過程①參見宋穎:《“一國”的文化共享:〈中國年俗〉的民俗國家化過程探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7—117頁;另見杰伊?梅克林著,宋穎譯:《論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民俗共享與國民認同》,《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1期,第250—256頁。,對此的持續觀察和深入分析另文專述。一個節日擁有獨特的名稱,不僅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保持,還見于歷史文獻記載,能夠在某些群體內世代傳承,保持著在時間上流布和空間上散播的活力,這種文化流脈中具有某種“共有”的要素,從而構成了傳承的基礎。
從理念上來看,劉魁立曾強調,基質本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髓和靈魂。他指出,“非物質文化對于具體的創造者和擁有者來說具有本真性,而對其他人來說具有共享性。……非物質文化與物質文化的重要差別就在于共享的可能性的差別”②參見劉魁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九次國學論壇上的發言》,《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26日;另見劉魁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享性、本真性與人類文化多樣性發展》,《中國民俗學會2009年年會論文》。。節日事項也具有“基質本真性”,使得人們能夠“共有”某一個節日。從具體節日事項構成要素來看,節日中的“核心元素”③關于核心元素和變動元素的分析,參見宋穎:《端午節研究:傳統、國家與文化表述》,第一章.中央民族大學2007屆博士論文。是節日得以“共有”的基礎,而對于節日諸多元素的使用和分享,是保持節日得以“共有”的表現方式。
在中國節日體系中,有的是法律規定的或人為設定的紀念日,有的是有著深厚生活積淀、跟隨自然節律的變動而產生的傳統節日。后者在歷時關系和共時關系上都具有廣泛的共有性。節日事項積淀著隨時間推移而萌生又消失的種種細節,凝聚和連接著一方水土上的民眾生活,蘊含著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中生活經驗的精華,承載著人們對于自然、人生和社會的看法。節日事項通常是人們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在特定時刻的特殊講究,往往是因為祖輩如此而世代傳承下來,大多數人都在這一天做同樣的(或相似的)事情,形成節日中“家家如是”④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7—350頁。的情形。人們在同一時間采取共同的行為,在節日中出現的這些相同的民俗細節,構成了一個節日的“核心元素”,這讓人們具備了彼此對話和相互交往的基礎,形成一定范圍內居住區域中的凝聚力,從而共有著某種程度上的群體認同和文化認同。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常會遇到,由于地域不同、族群不同,生活環境和條件不同、觀念和文化上的差異,使得某一地域的人們在這一天吃的、穿的、用的、講究的內容,也不盡相同。這些差異就逐漸形成了“地方性知識”,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被人們使用、接受和理解,而呈現出一定的節日事項的適應性和由此產生的地域性。這些不同的生活細節,提供了具有差異性的節日文化“變動元素”,讓人們之間充滿著對彼此的興趣和好奇,存在著分享、交流和移借、搬演的可能性。這些變動元素的多樣化使用,會在后續的“擴散”和“移借”中詳細討論。
端午節的習俗事項也不例外①參見中國民俗學會編:《中國端午節叢書》(六卷本),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端午節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被認可為中華民族“共有”的一個傳統節日。在韓國“江陵端午祭”于200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列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在“共有”層面上引發了究竟是“我群的”還是“他者的”大討論。一個節日的事項究竟在這一個或那一個群體內部“共有”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的差異能夠大到什么程度,都值得分析。盡管人們共有著這一節日,但在具體的度過方式上,既有相通的內容,能夠相互理解和接受,并用于個人的生活,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地域差異。
關于端午節事項的歷史記載既久又多,時間上的事項層疊與沉積,以往梳理較多,暫且不談。這里僅從湖北和湖南兩地的地方志記載來看,主要有以下十項內容,如節期、角黍類、艾草類、五色絲類、采藥、競渡、屈原、祭祀類、送瘟、親友往來等。對此,使用歸類統計法②標明“類”是指,在該項下,還存在細節上變化了的其他類似元素。如供食用的角黍類,還包括饅頭、粽等食品和物品。供使用的艾草類,還包括菖蒲、葛根等相似物。供佩戴的五色絲類,包括了香囊、蒜囊等。艾草類和五色絲等物都用于厭勝。采藥,包含了斗百草以及用藥草沐浴的習俗。祭祀類的神靈,包括了除屈原外對瘟神、水神、張天師、楊泗、伏波、城隍等神靈的拜祭。,來具體說明節日事項在空間上的共享程度。這十項內容的歸納基于地方志的記載,根據材料的詳略而盡可能的合并類似物,但是對于記載較多的事項,盡管可能屬于同一類文化符號,還是單列出來,以便進行較為細致的比較和對照。
以下的統計,一方面關注較為普遍的共有事項的記錄,這將有助于了解端午節的大致形態;另一方面,對于特異的元素記錄,如能體現出“變動元素”的適應性等內容,也適當予以關注。
這十項內容的比照,在有關湖北過端午的65種地方志③湖北65種地方志和湖南的60種地方志,均來自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記載中,節期上五日為端午的有65種,有4種將這天稱為“天中節”,其中還要過“大端陽”的有9種,均在十五日,另有1種單記為十八日,1種記為從十五日到十八日。角黍類的記載,有38種用于食用,有23種用于贈送,其中6種記載贈送時配有鹽蛋,1種記載用于祭祀屈原。艾草類的記載,有53種記載使用艾草,23種使用菖蒲,30種飲用菖蒲,52種用雄黃酒。五色絲類的記載中佩戴五色絲有11種,香囊有17種,其中有的混合佩戴著蒜枚、艾虎等。采藥的記載19種。競渡的記載有42種,2種記載提及“吊屈原”,2種提及豐年要持續3天,還有1種是初一到初六。提及屈原傳說的有11種,其中1種記載當地有“三閭祠”。祭祀類有13種,祭祀張真人、水神、瘟神等,或者前往廟宇道觀求取道符。送瘟的記載有10種,有迎船、送船、打龍船、祈神會、打醮等不同的稱呼。記載親友往來有13種。
在有關湖南過端午的60種地方志記載中,節期上五日為端午的有60種,6種稱為“天中節”,2種稱為“地臘”,2種稱為“敬節”。其中還要在十五日過“大端陽”的有10種,另有1種記載為初十過節。角黍類的記載,有37種用于食用,有18種用于贈送,其中4種配有香囊,3種配有蒲扇,2種配有咸蛋,1種配有艾糕,1種配有鞋襪。艾草類的記載,有57種記載使用艾草,8種配有葛藤,1種配黃荊條,30種使用菖蒲,28種飲用菖蒲,52種用雄黃酒。五色絲類的記載,其中4種為五色絲,9種為香囊(有彩蛛、獼猴、葫蘆、雞心、瓜豆等樣式),1種為雄黃囊,5種為蒜。采藥的記載22種,拜“天醫星”的記載有2種,3種記有“燃燈灸穴道”,6種記有沐浴或用來“澡洗”。競渡的記載有43種,有2種提及初一到初五。提及屈原傳說的有4種。祭祀類有7種,祭祀瘟神、伏波、關帝、城隍等,或使用朱書道符。送瘟的記載有1種,稱為收瘟,不在十五日而在五日端陽進行。有4種記載親友往來。
統計數據顯示出①筆者梳理地方志材料時,發現的問題是,縣志多襲用府志的說法。,兩省普遍共有的事項是:食用角黍、懸掛蒲艾、灑涂雄黃酒、有龍舟競渡等,局部地區除了過端午,還過“大端陽”。相比較而言,湖北重祭祀,除了吊屈原外,還有其他神靈,送瘟船活動較多;湖南則有“天醫星”的說法,記載較多的事項是采藥治病或沐浴;湖北親友往來贈送角黍時配用鹽蛋較多,湖南則更為多樣些,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過同一節日時所存在的地域偏好、差異和特點。
從“共有”的概念入手,能夠更好地分析某一群體內部長期傳承的節日事項,把握節日的內核,即“核心元素”。正是節日當中所“共有的”這些核心元素,能夠使得某一節日呈現出較為固定的形態,而得以整體把握,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上升為國家軟實力和文化傳統的象征,標明和區別“我群”與“他群”,獲得在更大范圍上“共有”的可能性。
二、“擴散”:在精準與模糊之間把握節日事項的多樣形態
從上節的統計可以看出,端午節的節期主要是五月初五,節期可視為節日的“核心元素”,地方志記載中一般稱這一天為“端午”或“端陽”,某些地方這天過節外,還另有以十五日為主的“大端陽”。在過大端陽的地域,五日會被稱為是“小端陽”。有的地方還有二十五日為主的“末端陽”。
如《益陽縣志》②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74頁。(二十五卷,清同治十三年刻本)記載,除了龍舟競渡外,“俗好祀鬼神,取肩輿舁神像,鼓吹相從,沿街往返,或裝諸雜戲及種種鬼神,謂之‘迎會’……以初十夜為‘葛公會’,十六日為‘天符會’,二十六日為‘城隍會’。”
又如《恩施縣志》③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437頁。(十二卷,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記載,“清江龍舟競渡,至十五日乃止。十五日,俗名‘大端陽’,懸門蒲艾始去之,飲食如前。二十七日,相傳為‘城隍神生日’。邑人仗衛迎神于市。是月,鄉農縛草為龍,鉦鼓繞田,謂之‘趨(驅)蟲’。”
再如《來鳳縣志》①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448頁。(三十二卷,清同治五年刻本),記有,“五日,俗以是日為小端陽,十五日為大端陽,云始于馬伏波。俱競渡龍舟,十五日尤盛。……五六月間,雨殤不時,蟲或傷稼,農人共延僧道,設壇誦經,編草為龍,從以金鼓,遍舞田間以禳之,亦迎貓祭虎之遺風也。”
這里簡要舉出的幾個例子,是要說明節期上的“擴散”,一般表現為:初五的事項,有的也在初一到初五、初一到初六之間進行,主要是親友往來,尤其是未定婚的、或者是姻親的,在這幾天之內都可以來往,贈送角黍等物,而不限于初五當天。十五日的大端陽,在某些地方是十六、十七或十八,主要舉行迎船送瘟的儀式。有的地方是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擇取日子來舉行平安醮。過大端陽的某些地方因節期的跨越,或將十三日也納入,一并祭祀關帝。而二十五日的末端陽,有的地方延至二十七、二十八,將“城隍日”②對于城隍的祭祀,與城隍的職能和端午節的文化意義有很大的關系。也一并納入,由于城隍具有的一種職能是管鬼,而端午節有清理水域、去污驅邪的意義,因此特意要祭祀城隍。綜合來看,節期的擴散主要有三段,由五日擴散到初一至初五,由十五日擴散到十四至十八,由二十五日擴散到二十八等。
由歷史形成的節期,存在由點及線或由線及點的雙向變化,引起了相關習俗事項的擴散形態,節期作為一種文化元素,在生活實踐中所要求的(講究的)過節方式的精準性和模糊性同時存在。節日事項的擴散,使得節日相關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在文化交往中,為習俗的在地化和適應性提供了必要的空間,為人類的實踐和創新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可以說,“擴散”及由此引起的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重要的節日事項,限定在五日當天,甚至講究具體在午時發生,如以午時水洗眼,午時來取藥等;另一方面,某些節日事項,不限定在五日進行,可以在前后幾天,或者十五左右、二十五左右,甚至模糊到“五六月”等,均有可能。
而節日習俗事項的擴散形態,主要是節日適應性而引起的地域性的“變動元素”的變化,既包括對于具體事項的類似選擇,也包括對于這些文化元素的多種使用方式③參見宋穎:《從“少數民族過端午”模式看文化的涵化與誤讀》,《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1期,第 145—156頁。。如上述的神靈祭祀,包括對于傳說人物的祭祀,也存在擇取屈原、伍子胥、曹娥、勾踐、水神、瘟神、張真人、伏波、楊泗等人物符號上的變化。
以伏波故事的記載為例,與人們熟知的屈原傳統對比來看,可以說明節日傳說的擴散變化。如見于《溆浦縣志》④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13頁。(二十四卷,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的記載:
“俗以初五為‘小端午’,望日為‘大端午’。相傳伏波征五溪蠻于五日進兵,士卒有難色。伏波曰:‘端午令節,蠻酋必醉,進可成功。今日乃小端陽也,后當與諸將過大端陽。’即進兵,諸蠻果醉,剿平之。乃于十五日大享士卒,遂名曰‘大端午’。至今仍之。”
五月舉行的迎神形式也比較多樣化,主要是祀鬼神,涉及的儀式和神靈較多樣,如上述征引了其中的一部分。與“擴散”相伴隨的是,出現了文化元素的“移借”現象。如《恩施縣志》提及用草龍驅蟲,不限定在端午日當天進行,也不在擴散的日期,而是不定期舉行。這種模糊化,不僅表現了時間上的擴散性,也意味著這種節日事項可能會被移借到其他節日或平常日期來使用。而用草龍驅蟲的事項在生活實踐中亦確實如此,這種活動本身可以自由移借,為了發揮實際的功能,并不限于五月。
端午節日事項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所涉及的材料,往往具有地方性,也呈現出變動元素的擴散形態。角黍的用途主要是自己食用、親戚之間贈送和祭祀祖先。而角黍制作中所使用的葉子,往往是就地取材,以當地常見的植物為主。湖南地方志記載用于包角黍的葉子就有6種,如箬葉、蒻葉、菰葉、楝葉、檜竹葉、竹籜(竹筍葉)等。人們用來保護家宅的草藥,也有幾種選擇,如艾葉、菖蒲、葛根等,還有的地方用到雄黃、蒼術、朱砂等。其中,艾草主要是插在門上,或制作成艾人、艾虎佩戴,有的地方用于沐浴。有關菖蒲的大多記載是做成酒飲用,少數是用來插在門上。制作的雄黃酒,主要是用來灑墻角,小兒涂額,有的在使用時配以朱砂。在對藥草的使用上,也存在多種方式,較為細膩多樣。僅以地方志中湖南一省用法為例,動詞包括了如下種種:結、懸、掛、刻、切、拌、和、飲、煎、煮、灑、涂、釀、簪、系、刈、切、搗、研、杵、泛、劈、拳、燃、灸、饋、遺、送等。這些使用方法,也是地方特有的知識和生活經驗。
三、“移借”:節日事項在生活實踐中的創新
如果說 “擴散”主要體現在同一個節日當中的同一事項或同一文化元素的模糊化變動,那么“移借”中文化元素的使用則更為自由和多樣化,常常不限定在同一個節日,表現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創造性和實踐性。在地方志中,正月、十二月等屬于過年期間,時間段較長,各種節日民俗事項的記載最多,次之是五月事項的記載。其他月份的事項較少也相對簡單。其中,端午節的一些具體事項,并不限于端午節這天出現;相應的,其他節日的一些事項,也會出現在端午節;不同節日之間分享相似的文化符號(這些符號常是成組或成系列出現的),這樣兩種雙向交錯情形,都屬于節日事項的“移借”。這樣的移借現象,出現在“變動元素”的置換和實際應用的層面上。而節日事項中出現這種現象,是由于背后的文化結構和思維結構在發揮著作用。有意或無意地將系列的文化符號成組搬移,這些文化符號背后固定的所指意義,可以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或者發揮實際的功能,具有社會交往的效用,體現出日常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行為慣性。
上文提過節期的擴散形態,提及的五日和十五日之間的事項,往往還會伴隨移借現象。例如,
《岳州府志》①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481頁。(三十卷,清乾隆十一年刻本)記有,“五日,沿門插艾,罷市競渡,或編葦為船,肖龍形泛之,謂之送瘟。”
《續修永定縣志》①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26—627頁。(十二卷,清同治八年刻本)記有,“端午,……河內龍舟競渡,鉦鼓喧嘈。前二十年,具鹵簿儀衛迎關帝至觀音橋給競渡者食物,謂之‘賞標’。競渡者并力爭先,上領食物,謂之‘搶標’。今因關帝祀典尊隆,寖不復迎。惟二十五、六日迎城隍神,一如當日。”
這里舉出的例子,其中一則,十五日的送瘟在五日進行。另一則,把祭祀關帝的儀式移借到龍舟競渡奪取勝利的程序中來。有些地方過節的日期跨過了五月十三的關帝誕辰,不但要一并祭拜關帝,還把這一祭祀儀式和其他節日活動融合在一起進行。像這段競渡的記載,就提及迎關帝的儀式成為當地競渡時“賞標”和“搶標”的重要環節。與一般競渡在湖中爭奪勝利不同的是,這里的競渡是爭奪來自神靈的護佑式的獎賞,神圣的意味顯得更加濃厚。而隨著時間推移,由于關帝祭祀愈發隆重起來,或許也是出于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的考量,就不再重復迎來觀競渡了。
更多的移借現象,表現在與正月、三月、六月等節日事項之間的相互移借。如親友交往、避惡躲病、送瘟迎會等,其他節日也有類似的活動。其中,親友來往,特別是姻親之間和師生之間,在傳統的重大節日均有類似的事項。一般而言,端午的親友往來禮儀,大致像新年伊始的元旦那樣進行。
如《通城縣志》②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377—378頁。(二十四卷,清同治六年活字本),“親故以角黍、腌蛋相饋遺,盛者金花表禮,如‘正旦’。”
又如《安福縣志》③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61頁。(三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本),“扎彩為龍舟,喧金鼓,往來波心,謂之‘競渡’。……姻族拜慶,略如元旦,館師尤有加禮。”
端午節使用植物清潔、避惡、祛災、除病等儀式,在其他節日也有所借用。
如《保靖志稿輯要》④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43頁。(四卷,清同治八年多文堂活字本),“正月十三夜,鄉間老少婦女入城,在各寺廟觀燈,謂之走百病。端午,角黍,蒲艾,雄黃酒,競渡。”
又如《龍山縣志》⑤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46頁。(十六卷,清光緒四年刻本),記有, “三月,三日,女童摘地菜花簪首,曰辟疫氣,或和作飯。清明,插柳葉于門,童男以柳圈首,亦曰辟疫。”
再如《直隸澧州志》⑥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56—657頁。(二十六卷,清同治八年刻本)記有,“正月初三日,祛柏葉及女貞葉爆之,云辟蚤蟲。衛生清潔事物。端午,禳毒,辟毒氣。開聾,飛鳧。除毒疾。取蟾蜍實墨于口,倒懸干之,磨以涂癰癤。六月,伏日,作湯餅,名辟惡。”
這里的幾個例子,與端午插蒲艾于門首、小兒涂口鼻、佩香囊等行為來辟邪祛病大致類似。在正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等時節都可以進行這樣的活動,只是變換使用了當季的植物,相比較可以發現,這些避惡祛病事項背后的思維結構和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共同的。發生“移借”的這些事項,集中在春夏,到了秋冬,便很少有祛病的記載了。
如迎神送瘟中像抬閣和送船等儀式,在地方志中也不少見,除了端午節,其他節日或不定期的某些日子也會舉行,用祈禳儀式來祛除災疫、求得平安。在關于湖北和湖南的地方志記載中,在民眾生活中如此突出而重要的送瘟儀式往往會移借到其他時間段使用,種種記載可以與大端午的送瘟船相互映照,具體形式區別不大。例如,
《常德府志》①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49頁。(二十卷,一九六四年上海古籍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影印)記有,“正月,至十八日燒燈,以草為船,實以紙馬,送至江滸焚之,謂之‘禳災’。”
又如《慈利縣志》②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64頁。(十八卷,一九六四年上海古籍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萬歷本影印)記有,“正月,朔日,翌日,寺觀僧道擊鐃鳴鼓,為各家收瘟,復作紙船,設懺悔以遣瘟。”
再如《永綏廳志》③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39頁。(三十卷,清宣統元年鉛印本)記載的大多為苗俗,其中有,“正月,秋千戲,延巫師,將五色紙禳之,十二日,民間共延巫師上刀梯以除瘟疫。”
例子中提及的正月習俗事項,借用了端午的五色符號所制作的五色紙,是用來除瘟疫的。正月的秋千戲,有時也移借到其他節日,端午習俗事項中至今還保留有秋千戲的活動。上述禳災、收瘟等儀式,一般稱為“打醮”,除了前引的正月外,在其他月份的事項中也時有所見。
《巴東縣志》④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441頁。(十六卷 ,清光緒六年刻本)記有,“平安醮 每歲三四月,邑民咸出金錢延黃冠誦經,分東西上下街,揚幡掛榜,市中貼過街幡,書‘解瘟釋疫’、‘祈福迎祥’各四字。往年于設壇之三四日,裝演雜劇、龍燈之屬,名曰‘清醮’。近年無之,名曰‘素醮’。撤壇之日,以紙糊船送之江中,謂之‘放瘟船’。里中亦誦經二三日不等。”
《寧鄉縣志》⑤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680頁。(四十四卷,清同治六年刻本),“端陽競渡,以初一日劃起。……以二十日為‘龍會’,二十五日為‘分龍會’。此二日有雨,謂可免旱災。是月斂錢延僧道建壇,結彩張燈,鼓吹五七日,曰‘請水’,迎經曰‘游船’,以弭災迓福,曰‘打清醮’。亦或以六月舉行”。
《鄖西縣志》⑥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457頁。(二十卷,清同治五年刻本)“舊于天河碼頭競渡,于火星廟開壇作醮,扎舟送神,謂瘟火會。六月六日,是日為楊泗將軍誕辰,沿河祀神演劇,各舟子賽會爭勝。”
《保靖志稿輯要》記有,“三月三日,鄉俗聚會,殺羊祭鬼,一說祭伏波將軍。”
可見,祛疫送災的祭祀儀式,人們根據需要常常移借而來搬演進行,內蘊意義相同,并不只限于端午。與大多數地方不同的是,后兩種的記載中提及,祭祀伏波在三月三日出現,祭祀楊泗在六月六日出現。送瘟的活動不僅時間上可以有移借,地點上也可以變換,如例子中在碼頭邊的火星廟舉行,而競渡爭勝移借到六月六日祭祀楊泗時舉行。六月六日,一般稱為“過半年”,是端午—夏至由熱轉涼時節的另一節點,倘若不限于一個具體時間點,而從較大的時間段上去解讀,也可歸于與冬至—新年相對應的結構范疇內①關于“過半年”的討論,參見宋穎:《端午節研究:傳統、國家與文化表述》第三章,中央民族大學2007屆博士論文。。在文獻資料中,六月六日“過半年”中有不少民俗事項與五月五日“過端午”是完全相同的。
綜上所述,節日事項在不同時間和場合中,出于近似的功能、使用目的和內涵意義而有可能出現相互挪移、疊加、借用等現象。在時間的縱軸上,同一年之內的不同月份之間,五月的節日事項與正月、三月、六月等相關事項之間還存在進一步比較和研究的可能性。
余 論
在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的中國境內,生活著多個族群,他們因地制宜而擁有著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李濟從考古資料中提出過“多源中國”論,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蘇秉齊“滿天星斗”的文化闡述,無不指出了一個共同的事實,即在某種程度或某些層面上的共享與共有,并不能改變同時還存在著的多樣性、多元性,甚至多源化的相互雜糅與整合的文化現實。
對于節日事項的研究,既不能以偏概全,又不能一葉障目。因此,上述討論和例證使用“共有”“擴散”與“移借”等幾個概念,來概括并解釋節日事項的繁雜多樣性。節日事項的“共有”,是建構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證了節日的整體性、延續性,不僅是某一群體的標志物,而且能夠成為文明之間相互交往和對話的基礎。而節日事項的“擴散”和“移借”恰恰是節日生命力的有效保障,是人類在生活實踐中的智慧結晶,為創新和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帶著這幾個概念去認識細碎的民俗生活細節,就能夠透過現象看到節日的本質。
[責任編輯:馮 莉]
K890
A
1008-7214(2016)03-0093-09
宋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