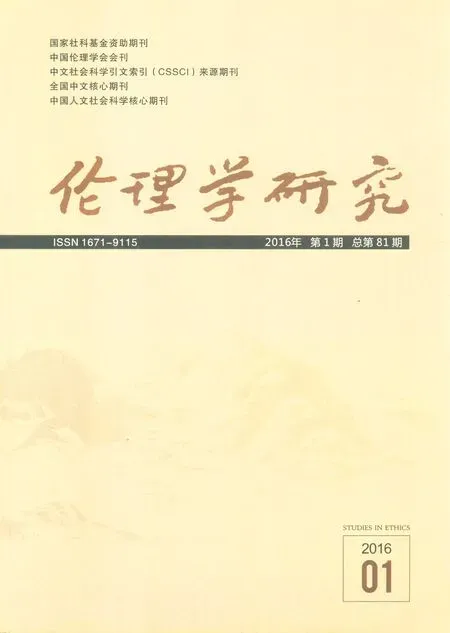代孕的合法化之爭及其立法規制研究
劉長秋
代孕的合法化之爭及其立法規制研究
劉長秋
代孕,無論在生命倫理學界還是在生命法學界都引發了巨大爭論。在代孕應否合法化問題上,學術界存在“應合法化說”與“不應合法化說”兩種針鋒相對的學說,這兩種學說都基于各自的立場提出了相應的論據。立足于倫理與法律關系的角度,倫理是法律的基礎,法律對于代孕的定位應取決于倫理對于代孕的定性。而在倫理上,代孕是一種違背人類天性的不合理行為。對于這種行為,法律應當予以禁止。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孕規制立法來看,代孕應當為立法謹慎規制。當前,我國對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規制模式,但在具體制度設置上還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進一步完善。
代孕;合法化;人性;規制
一、引 言
在當代生命倫理學乃至生命法學領域中,除了克隆人與人體器官買賣,恐怕沒有哪一個問題會像代孕這樣引發了巨大的觀念分歧與激烈的學術論戰。近年來,國內有關代孕市場的報道時常為媒體捕捉,引起了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而2011年12月在廣東惠州發生的“八胞胎事件”、2012年10月在深圳發生的“買賣卵子事件”以及2013年3月發生在北京在“中國最大代孕機構被查案”則更是將代孕問題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實際上,有關代孕的話題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國外,都算不上是新的話題,而國內代孕的風潮更早已是甚囂塵上。只要在百度搜索欄中輸入“代孕”一詞,則有關的廣告就會鋪天蓋地。在很多代孕網站上,代孕母親不僅已被明碼標價,而且相關的操作也已經流程化、體系化和規模化。代孕已經儼然成為了一個新的灰色產業,在地下暗流涌動。在這種背景下,有關代孕合法化的爭議不斷涌起,令代孕成為當代生命倫理學以及生命法學最為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本文擬從梳理代孕合法化的學術爭議入手,就我國代孕的法律規制問題淺發拙見!
二、有關代孕合法化的學術爭議
醫學充滿著倫理難題[1],代孕就在其中。作為現代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副產品,代孕自其產生之日起即受到了廣泛關注,成為輔助生殖領域最具爭議的規程之一。[2]而有關代孕應否合法化的爭議也一直都沒有停息過。梳理各國有關代孕倫理與法律問題的研究,在應否允許代孕合法化的問題上,學界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其一是應合法化說,即認為代孕應當被合法化,尤其是那些利他性代孕,由于不存在牟利動機,在倫理并不具有非難性,應當為法律所支持。其二是不應合法化說,即認為代孕是一種違反倫理的反社會行為,應當為法律所禁止。
1.應合法化說
應合法化說主要從以下角度來論證代孕的合法化。具體包括:
(1)代孕合法化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必然選擇。首先,代孕合法化是保障公民生育權的需要。生育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一些夫妻由于生理上的原因而不能實質行使生育權,但法律不能因此就事實上剝奪他們的生育權。法律并沒有規定生育權的方式,只要不違法違德,通過任何方式實質享有生育權都應該被允許,并且國家應積極尋求其他方式來保障公民能真正享有權利。而“代孕”技術的出現正好為這些夫妻行使生育權提供了技術支持。為此,國家應該積極主動地進行相關立法,在制度層面上肯定“代孕”的合法性,保護不育者的生育權。[3]其次,代孕合法化也是保障代母身體權的必然選擇。對代母而言,代孕只是利用其子宮的生育功能和妊娠功能實施代孕,幫助委托夫婦實現他們的生育權,這正是基于身體權而依法支配自己身體,處理其自身的身體利益,是其自由行使身體權的表現形式。對此,法律應予以支持。以此為基點,該學說對我國現行立法禁止代孕的做法進行了批判,認為法律對代孕不加區分地進行全面禁止其實是對代理孕母身體權的一種侵害。[4]只有開放代孕,才能使委托代孕的夫妻之生育權以及代母的身體權得到保障。
(2)代孕不會對代母帶來負面影響。代孕是一種直接關涉代子、委托人以及代母等多方利益的行為。為此,對代孕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考察不能僅僅及于代子的健康成長、委托人實現生育愿望的迫切性以及社會大眾對代孕的認知上,還必須要考慮代母本人的利益,考察代孕對代母身心的影響。假如代孕會給代母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則出于對代母利益的考量,不宜開放代孕。但英國城市大學的Vasanti Jadval等學者的調研結果似乎令人們無需再擔憂這一方面的問題,因為其調研結果表明,代孕母親在交付孩子之后的確很快經歷了一些心理及感情等方面的問題,但并不嚴重,通常時間比較短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流失而逐漸消融。就此而言,代孕對代母來說似乎是一種積極的經歷。[2]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不應當禁止代孕,而應當將其合法化,從立法上給予支持。
(3)禁止代孕妨礙公平正義的實現。公正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之一,也是衡量法律合理性與正當性的一個基本依據。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公正和正義是人類對法律應有倫理品質的最重要的界定,也是人類對法律應有功能的最基本的預期。”[5](P4)而禁止代孕,正如一些持“代孕應合法化說”的學者所指出的,違背了法律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有些人在社會中處于劣勢,并非其自身的原因所造成,如不孕夫婦對其不孕病癥沒有任何過失責任,屬于此類劣勢者,國家沒有對這些婦女或家庭給予積極的協助已屬不當,怎么還可以反過來要立法禁止代孕母行為……”[6](P176)而且,否認代孕的合法性也會引發新的公正問題。具體而言:首先,禁止代孕會使國家司法行政的某些錯誤無法彌補。有時,國家司法行政錯誤(如結扎、絕育)會導致公民部分喪失生育能力,這本身已經構成對公民生育權極端不公正的對待。如果立法再不允許這些公民通過實際可行的技術措施予以彌補,這種規定本身無疑是對這些公民的再次傷害。其次,由于完全禁止代孕政策的實施成本過大,很難將其貫徹到底,結果造成一些有錢有勢的人低成本偷偷地剝削代母,而真正的窮人被迫“斷子絕孫”的社會惡果。再次,完全禁止一切代孕行為,可能間接導致部分販賣、偷盜嬰兒的罪惡行為。[7]
(4)代孕無關剝削與出賣。反對代孕者認為,代孕是剝削性的。針對這一觀點,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學者認為,生育作為女性為他人生育子女的一種方式,其本質是女性出賣勞動的一種方式。這種勞動方式與其他勞動方式并無本質性不同。與其他勞動方式一樣,這種勞動方式并不會產生剝削。因為“只有當個人不能自主和自愿地同意,或者被直接強迫或由于貧困或能力不足而被間接強迫時,才會發生剝削”[8](P149)。而代孕是代母與委托方通過代孕協議達成的自愿行為,其間并無任何強迫發生,不會涉及剝削。“從商業的角度上,代孕為那些低收入的婦女提供了一個在不用——至少是理論上——出賣其身體或孩子的情況下獲利的、具有誘惑性的途徑。”[9]不僅如此,代孕作為一種生育服務,也無關買賣。代孕者提供的是一種不存在性接觸的懷孕服務,即合同中所規定的適于胚胎生長的子宮環境。代孕者既不是買賣孩子,也不是出賣子宮,只是代行撫育權且將代行撫育的時間前移。[10]以此為基點,將代孕等同于剝削或買賣而主張立法禁止是不恰當的。
(5)禁止代孕會導致嚴重的負面問題。代孕合法化論者認為,簡單的禁止并不會根除代孕,只會使其地下化。而地下化的代孕行為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會引發道德、法律和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如導致不符合條件的機構實施代孕,術前不進行嚴格的健康篩查,造成某些疾病的遺傳;由于法律規定模糊,導致代母得不到法律保護,其權益容易受侵害,孩子監護權易產生混亂,日后引發糾紛等等。相反,“代孕可能帶來的問題通過嚴密的制度設計卻是可以解決的”[11]。為此,面對代孕這場洪流,我們與其冒著洪流沖垮堤壩的危險去封堵還不如適當開放以求破堤引洪,將損害減小到最少。[12]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很多學者都主張將代孕合法化,但絕大多數人都主張對代孕實行區別規制或曰“二元規制”,即根據代孕類別的不同而分別給予禁止和開放。對于商業性代孕,一般都主張法律給予嚴厲禁止;而對于無牟利目的的利他性代孕,則多主張立法給予開放。
2.不應合法化說
針對應合法化說提出的各方面論據,不應合法化說從以下幾個方面有針對性地論證了代孕不應合法化的理由。具體而言:
(1)禁止代孕不損及公民權利。原因在于,權利的行使是有限制的。法律在設定權利的同時,也預設了權利的疆界,即權利不得濫用[13](P204)。民事主體行使自己的生育權本無可非議,但其行使權利并非是絕對的,必須在遵守法律和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行使且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和人的本性,否則即為濫用權利。[14]在人工授精這一法律關系中,主體在行使自己權利的同時,亦應遵守上述權利不得濫用的原則,不得將其權利的邊界劃定于特定的限度之外。代孕作為一種違背公序良俗的生殖行為,已經超出了生育權以及身體權的權利邊界,實際上已經衍生為一種不正當的利益需求。以此為基點,無論是委托夫妻的所謂“生育權”,還是代孕女性的所謂“身體權”,都是受到法律規范、倫理道德多方面限制的。代孕合法化與其說是保護人們的生育權與身體權,不如說是縱容人們對生育自由及身體自由的濫用。就此而言,禁止代孕并不損及公民權利,生育權與身體權都不足以成為支撐代孕合法化的理由。
(2)代孕有害代母的健康與尊嚴。從醫學上來說,生育行為有很大的生命危險,特別是一些高齡產婦,不僅僅意味著對身體的損害,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代孕”婦女出于對金錢或其他目的的追求而將自己的身體作為機器出租、出借,其自賤人格的行為既是對人類種族延續過程神圣性的踐踏,又是對母愛偉大性的褻瀆。“代孕”行為實際上將代孕母親的身體視為“生育機器”,子宮走向工具化和商業化。[15]法律對此不應給予支持。
(3)代孕與傳統倫理相悖,允許代孕會帶來倫理秩序的混亂。反對代孕的人認為,代孕侵犯了諸如尊嚴之類的基本倫理原則以及母親與孩子的自主權:它包含著一個人(無法生育的女性)將另一個人(代母)作為手段而非目的來利用。[16](P415)不僅如此,代母作為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與作為代孕母親的現代公眾人物這一角色之間存在著不協調[17],這種行為明顯偏離了傳統女性在生育和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違背了中國社會傳統的倫理和道德思想,給社會和家庭倫理帶來混亂。[18]如果允許代孕合法化,則意味著法律將放任代孕對傳統倫理的顛覆以及對現行生命倫理秩序的沖擊。
(4)代孕是剝削性的。反對代孕合法化的學者認為,代孕是一種具有剝削性質的行為,無論是商業性代孕,還是不含任何商業目的的利他性代孕。就商業性代孕而言,“給婦女金錢以代為生子制造了剝削的可能,特別是因為委托夫婦通常要比代母富裕”[19](P898)。而對于利他性代孕而言,這種代孕盡管表面上看似乎的確無關剝削,但實際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利他性代孕不會涉及到任何脅迫與剝削的期望是建立在婦女家庭作用的西方理想模式之上的”[20],但實際上這種理想模式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養兒防老”觀念濃厚而女性更多時候依舊被認為以承擔傳宗接代為最基本使命的東方國家。利他性代孕的實質是一個本沒有義務懷孕生子的女性承擔了為他人懷孕生子的義務,對于代母而言,這就是一種剝削。
(5)代孕合法化會直接挑戰和沖擊現有的法律秩序。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學者主張,不孕夫婦的生育權必須得到法律保障,為此,應通過特別立法,有限度地開放代孕,并使委托方夫婦中的女性成為代子的嫡親母親。然而就目前來看,依據分娩事實確定生身母親的法律地位是各國民法的傳統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只有受委托的代孕女性才能成為出生子女的生身母親。針對這一難題,主張開放代孕的多數觀點認為:可采用“子女最佳利益說”認定代孕中的母子關系,或根據私法自治的法律精神,在代孕合同中約定提供受精卵的委托方夫婦是代子的生身父母,根據代孕合同確定父母子女關系。但實際上,上述觀點與我國現行親子關系的法律制度相抵觸,忽視了我國身份法律制度的安定性需要。從法理上來說,身份法秩序是社會公共秩序的根本,民法中有關身份法秩序的基本原則以及基本理念是國家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基石,必須安定,而鑒于身份制度安定性之需要,嫡親父母子女法律地位的確定標準必須明確且統一,不宜在認定時給予法官較大裁量權。[21]就此而言,代孕合法化勢必會挑戰和沖擊現行的法律秩序,引致法律上的沖突與混亂,在滿足了少數人個別“權利”需求的同時,招致更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
三、代孕不應當合法化
筆者以為,從倫理與法律的關系來看,倫理是法律的基礎。“法律天然具有一種道德理性,在其形式的外殼之下,流動著倫理的血液。”[22]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有一定的倫理背景與道德動機,其內容也都離不開一定倫理道德規范的支持,脫離了一定社會的倫理道德,法律將無以存在。在價值取向上,倫理規范指導并且影響著法律規范,法律背后所存在的倫理價值觀念支配并影響著法律的性質和價值取向。而法律所維系的則通常都是最低限度的倫理,作為最低限度的倫理,“法只能從倫理的有效性推導出自己的有效性,法的規則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們作為倫理規范而擁有道德之品格”[23](P10)。以此為立足點,代孕之法律問題說到底其實更是倫理問題,是從倫理層面轉入法律領域的難點問題。對代孕的法律判斷與應對離不開對代孕的倫理分析。倫理分析是法律判斷的前奏,是法律對代孕作出定性并據以采取立法對策的學理前提。所以,從法律上明確代孕的定位及其立法對策,需要首先從倫理上明確代孕的性質。
而從倫理上來說,代孕是一種嚴重違反倫理的輔助生殖行為,是一種違背人性而為主流倫理觀念所不容的現代醫學活動。原因在于:從醫學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生育作為女性孕育并產子的生物過程,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技術化過程,而更是一種生理、心理過程和社會活動。假如我們將女性的生育過程視為一種勞動,則女性的這種勞動與其他勞動形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生育勞動不僅是一個身體的過程,更是一個情感的、社會的和心理的過程,該過程的產品不是一種物而是人”[16]。代孕支持說將生育行為簡單化為一種純粹技術化的身體活動,使得原本神秘而高貴的生命可以通過技術和契約來加以生產,這客觀上必然會造成人類生命的物化及其在倫理位序中的降格,直接沖擊現存的社會倫理秩序。不僅如此,代孕構成對人性的違背。盡管主張開放代孕的學者大都打著正義與人性的大旗,認為開放代孕是保護少數不孕不育者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是對人性的尊重和保護,鼓吹所謂的“作為多數人之代表的立法者,在立法時應該為那些沉默的少數設身處地地著想,才更能彰顯法治的人性關懷”[11]。但實際上,代孕本身是一種最不講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輔助生殖活動,因為這一活動完全忽略和抹殺了母性這樣一種最基本的人性。當代醫學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懷孕期間孕婦會產生特別的母性情結,將自己與胎兒緊緊維系在一起。[24]這種母性情結是女性作為母親在懷孕和生產時必然會產生的而且是無法抹殺的一種情節,是人作為一種動物所生而俱來的天性。①基于此,對于代母來說,代母與孩子的感情紐帶是難以割舍的,這是人最純真和樸素的天性使然。“十月懷胎”形成了事實上的母子情,而分娩以后將孩子送給養育母親,對代理母親感情上的打擊將非常大,即使當時似乎并不覺得什么,但日后可能成為她的終身遺憾。[25](P140)
此外,從醫學上來說,生殖作為一種生物活動本身是有一定風險和健康損害的,其對代母身體帶來影響和傷害的事實是無法回避的。例如,代母在代孕過程總中至少需要直面對藥物的反應(包括陣發性皮膚熾熱感、情緒低落或易怒、頭疼以及心神不定等)、多胎風險乃至更為嚴重的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癥以及宮外孕、羊水栓塞等健康損害或風險。2014年發生在湖南省湘潭縣婦幼保健院并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的“產婦死亡事件”就充分印證了生育作為一種生物活動所具有的風險與損害。[26](PA18)由此不難看出,代孕——無論是何種目的與形式的代孕,都無法改變代母冒著損害甚或犧牲自身生命健康之風險為他人生育子女并將該子女交付委托方的事實,都無法抹殺基于代孕而在代母與代子之間建立起來的血緣聯系以及源自人類天性的親情與感情,也因此而無法回避其違背人類天性和抹殺人倫的倫理宿命。在這一意義上,主張代孕合法化而開放代孕,其實質是要求立法忽視和抹殺代母基于懷孕和生產的事實而與代子之間形成的血緣聯系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感情與親情,要求代母違背自己的天性將一個在自己子宮里生活了近十個月的小生命拱手送給他人。而這樣的立法顯然是違背人性的,是無法得到社會的接受和遵從的,必然為社會所遺棄。②“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旋渦所侵蝕,并逐漸地潰滅。”[27](P30)
此外,具體到我國這而言,代孕作為一種無視和傷害母子親情和血肉聯系的現象,更應當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很顯然,法律反映了各個國家不同的民族性、宗教背景以及倫理觀念。”[28]我國國民具有典型的東方文化人格,極為重視人倫,重視親情與感情。這一特點必須要得到生長于這一土壤中的我國法律之正視和重視,并在相關的立法制度中體現出來,否則,法律就會失去其正當性基礎而無法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同和接受。涉及代孕之法作為當代生命法的一個重要分支領域,必須形成對我國社會特性的起碼尊重。為此,它必須明確禁止代孕,甚至可以將代孕作為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反社會行為而給予刑事制裁。這是使法律契合我國社會現實的內在要求。就目前來看,發生在我國的代孕事件中近乎全部的代母之所以選擇做代母并非基于所謂的幫助他人實現生兒育女夢想之考量,而更多的是基于經濟利益之盤算,“選擇做代理孕母的女性一般都是在權衡了自己可能從事的工作之后自主決定的,是基于其生育能力獲得經濟與情感利益的一種現實選擇。在她們看來,代理孕母這份職業比其他工作方式在經濟上更為可取,能夠使自己在短時間內擺脫經濟拮據的困境”[29]。在此背景下,“無論于法技術的安排,抑或我國國情下倫理與法理的共同考量,代孕行為非法化之理由充分”[30]。正因為如此,我國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禁止代孕,這一規制策略是完全合理的,在學理上是經得起推敲的。③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科學探索所內含的求真本性及其由此所激發出的巨大能量以及社會進步所可能會帶來的人性的嬗變可能會幫助代孕沖破“保守”觀念與“僵化”倫理規范的束縛,并最終促進生命倫理以及生命法的更新。就此而言,無論是生命倫理還是生命法,放開對代孕的制度禁錮或許會是必然的趨勢。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現在就應當從倫理和法律上開放代孕。相反,為了保障人類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法律乃至倫理——至少是現在以及今后某一特定時期內——都還應當繼續限制乃至禁止代孕。而法律禁止代孕并不意味著立法者看不到倫理或法律將來或許會放開代孕的趨勢,而是為了在代孕開禁之前為人類社會提供一個必要的緩沖期。這如父母在子女尚幼小之時禁止子女玩火或拿刀其實是一個道理!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以為,對于代孕,我國現行立法持完全禁止的立場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我國立法在規制代孕時必須堅持以下立場:(1)在社會倫理道德觀念以及必需的社會建制尚不足以支撐代孕,貿然開放代孕只會引發更多負面問題的宏觀背景下,立法應當堅決禁止代孕,無論是何種類型的代孕。(2)立法需要介入解決圍繞代孕而引生的各種社會問題之中。立法對于代孕的禁止不會完全消滅代孕,而只會將代孕控制在社會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就如立法永遠不可能消滅犯罪而只能將其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一樣。為此,立法必須設置相應的制度,以解決好圍繞代孕引生的相關法律及社會問題。如代子的撫養問題、衛計部門查獲的代孕用胚胎的歸屬與處置問題等。(3)對于醫療臨床上的確存在的代孕需求,立法應當通過鼓勵收養以及完善我國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來予以應對。從生育倫理的角度上來說,遺傳關系對于構建親子關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卻絕非必不可少,對于做父母來說,關懷照顧和養育一個孩子比提供遺傳物質或妊娠環境更重要。因此,養育的父母較之遺傳學上的父母更具有倫理學的優勢。而這也正是收養制度能夠作為一種合理制度而為法律確認和保護的主要倫理依據。就代孕在我國存在的實際原因來看,醫療臨床上之所以存在強烈的代孕需求,與我國“養兒防老”的觀念以及現行社會保障機制尤其是養老機制不健全有著直接的關系。對于那些無法通過自身生育的夫妻來說,通過代孕實現擁有后代的愿望顯然是保障自己老有所養的主要途徑。基于此,立法應當在鼓勵收養以及完善我國養老機制上給予足夠的制度支持,以解決好那些無法自己生育子女的夫婦將來養老的后顧之憂,盡量阻斷那些基于養兒防老壓力而形成的代孕需求。
四、各個國家和地區代孕的立法規制:概況及規律
近年來,伴隨著環境污染、電磁輻射以及工作壓力加大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不孕不育已成為很多人的困擾。謀求通過代孕來解決自身生育缺陷所產生的困境,已經成為不少不孕不育者的重要選擇。在此背景下,代孕應運而生,成為各國生命倫理學界乃至生命法學界所關注并熱議的話題。基于代孕對于人類文化乃至文明所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立法,對代孕進行了規制。
1.各個國家和地區規制代孕的立法概況
由于民族性、宗教背景與倫理觀念等因素的差異,各個國家和地區對于代孕的規制策略并不相同,表現出了一定的差異性。具體而言:(1)德國、法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對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規制策略,甚至對從事代孕業務的機構與個人施以刑事懲治。德國1991年實施的《胚胎保護法》明確禁止“借腹生子”的代孕行為,根據該法,違法實施代孕手術的醫生將被判處三年徒刑。法國1994年通過的《生命倫理法》,也以法律的形式對代孕予以全面禁止,并對代孕行為人予以嚴厲懲罰,至于那些組織策劃代孕的協會或醫生,都將面臨3年監禁和4.5萬歐元的罰款。[31]日本雖然未對人工生殖技術以特別立法來管理,但在執法上明確禁止任何形式的代母,在親子關系的認定上也一直堅持分娩為母的傳統法律原則,拒不認可代孕委托人作為代子法律上父母的地位。在2008年著名的“曼吉案”(Manji’s case)當中,日本法院就堅持了分娩為母的法律原則,即使委托代孕的夫妻在代孕母親分娩之前已經離婚,委托代孕的丈夫也沒有取得親權。新加坡則明訂法律,不允許任何以人工生殖技術執行代孕行為。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法典》以及《法國民法典》、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的《魁北克民法典》都明確規定代孕協議無效,從民事立法的角度明確否定了代孕的合法性。(2)也有些國家則未對代孕加以統一規制,而是交由各個地方自行立法。如在澳大利亞,聯邦層面上并沒有出臺統一的代孕規制法,有關代孕的問題交由各州自行規制。絕大多數地區都已經將商業性代孕非法化:如新南威爾士州的《輔助生殖技術法案2007》、塔斯馬尼亞州的《代孕合同法案1993》、維多利亞的《輔助生殖醫療法案2008》以及首都領地(ACT)的《親子關系法案2004》,而也有些州則全面禁止代孕——不論是是商業性代孕還是利他性代孕,如昆士蘭州的《代孕父親身份法案1988》、南澳州的《家庭關系法案1975》[16]。而在美國,聯邦層面也沒有制定統一的代孕規制法,有關代孕的立法規制也是由各個州自行進行的,實踐中的做法并不一致。有些州全面放開代孕——無論是商業性代孕還是非商業性代孕,如新澤西州、加利弗尼亞州和俄亥俄州等通過司法判例的形式承認代孕合法。但有些州則禁止代孕,如華盛頓州、密西根州、維吉尼亞州、猶他州、紐約州等,而密西根州的處罰最為嚴厲。在密西根州,對代孕母親以破壞善良風俗的罪名,最高可處10000美元罰金以及1年徒刑。對安排代孕母親的人也將被判重刑,罰金高達50000美元,還有可能獲判5年徒刑[32](P134-137)。(3)有些國家對代孕實行“二元規制”,對部分代孕開放,對其他代孕則禁止。如英國及我國香港地區將商業性代孕視為犯罪予以懲治,但對于非商業性且無強制性安排的代孕則未予明確禁止。荷蘭也是對代孕采取有限開放的國家之一,在荷蘭,利他性代孕是被允許的,而商業性代孕則被嚴厲禁止,甚至受到刑法的規制。《荷蘭刑法典》專門就涉及代孕的刑事責任做了明確規定,該法典第151b條規定,在擔任職務或從事商業活動中,故意達成、促成代孕母親或希望成為代孕母親的婦女與他人進行直接、間接談判,或安排雙方見面的;公開提供某種服務,該服務可達成、促成談判或見面;披露知道某婦女原因擔任代孕母親、尋找愿意擔任代孕母親的婦女,或可以代為尋找符合以上條件婦女等信息的,判處1年以下監禁或第4類罰金。[33](P125)以色列也是在代孕規制問題上采取有限開放型的國家。在以色列,由主管機構批準的代孕并不為法律禁止,但未經批準的代孕則要受到嚴懲。根據以色列1996年3月通過的《關于代孕的法律》,未經批準委員會授權而簽訂代孕協議為犯罪行為,將被處以1年監禁。在未經委員會準允的情況下,當事人因為參加這樣的協議而提供、交付和索要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行為屬犯罪行為。[34]而對于政府允許的代孕,以色列則做了特定限制,如法律要求代母須為單身媽媽,男同性戀者及單身人士不得雇傭代母,打算做代母的女性須接受反復的體外授精-胚胎移植嘗試以證明其能夠勝任代孕工作。與此同時,法律也保護委托人、代母及代子,政府確保所有當事人得到認真檢查且保障所有合同的有效性。依照規定,在孩子出生后,委托方必須接受孩子,即使其生來殘疾;代母須將孩子交付給委托夫婦,而且代母可以要求為自己和孩子提供心理幫助。[35](P291-292)(4)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并未制定規制代孕的立法,但其司法實踐則對代孕持默許甚或縱容立場,如烏克蘭、印度、俄羅斯等。但總體來看,這類國家和地區居于極少數。
2.各個國家和地區規制代孕的立法規律
從以上對各個國家和地區規制代孕立法的簡單介紹中,我們不難發現以下規律:
(1)代孕作為一種頗具倫理爭議的現象需要受到法律的規制。代孕是一種直接關乎女性生殖健康、后代利益與人性尊嚴及家庭責任和生育正義的生殖現象,在倫理上具有很大的爭議性,反對者有之,力挺者更是大量存在。這種爭議為各國立法介入對代孕的規制帶來了現實的困難,因為它需要立法者準確地把握法律介入的界限,以防規制不足或過當所產生的不良反應。但另一方面,這種倫理爭議也為代孕的立法規制提供了現實的必要性與立法介入的正當性,即:代孕這一極易引發糾紛的現象需要作為倫理之底線的法律的及時介入,以便為人類多元的、模糊不清的倫理判斷劃定一個準確的界限,從而將人類的輔助生殖活動限定的底線倫理能夠允許以及社會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引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朝向有益于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方向邁進。正因為如此,在多數國家和地區,盡管人們對代孕的爭議不斷,但其立法或司法都以相對較為慎重的態度及時介入了對代孕的規制。這為防止代孕在各國的泛濫起到了重要作用。
(2)各國對代孕普遍進行了限制。就代孕在各國的立法規制來看,代孕在各國都受到了普遍限制,尤其是對商業代孕。“由于代孕在道德與倫理上的模糊性,大多數國家都對商業代孕給予了最大的謹慎。”[36](P12)“多數工業化國家都拒絕或極大地限制代孕操作。”[37](P23)即便是對代孕比較寬容和放任的國家和地區,代孕也絕非完全自由,沒有絲毫制約的;相反,出于對女性健康、孩子利益以及社會觀念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代孕在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被施以了必要限制,如將代母的范圍限制在身體健康且有過有生育經歷并達到一定年齡的女性、代母必須通過有無吸毒、喝酒、吸煙的測試并限制男性同性戀者雇傭代母等等。也有很多國家和地區則完全禁止代孕,甚至將其上升到刑罰規制的高度,利用刑罰的威懾來防范和打擊代孕。這些限制顯然是保障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就各國規制代孕的立法的范圍和種類來看,代孕并非完全被拘泥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專門法中加以規范,而是被分散規定的多個部門法中,如生命倫理法、刑法、婚姻家庭法、母嬰保健法等。“代孕的立法應對涉及多個領域的法律,而不是僅指直接規制代孕的立法,包括兒童福利法、收養及父母責任法、一般的規范生殖技術的法、個人身份(包括公民身份)法、刑法以及移民法。”[38]這表明了代孕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易言之,代孕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涉及醫學、倫理、法學與社會等眾多領域,需要各個部門法協同配合,共同規制。此外,從數量上看,承認代孕合法性的法域很難說占據多數,相對來說,美國更為開放一些,有部分州在立法或者判例當中變相接受了——至少是某些類型的——代孕協議,但很多州并不認可代孕協議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這說明,美國這些州的立法或判例并不在于要放開代孕,而是在代孕發生后面對代子撫養等一系列難題而采取了一種相對更為功利和務實的做法,其本意并不在于肯定代孕合法,而更在于解決因代孕所產生的代子的利益保障問題。而在歐洲,盡管歐洲人權法院對待代孕的態度有所松動,但是歐盟各成員國當中持禁止態度的仍然占大多數,即使承認代孕的國家通常也只接受某些類型的代孕。而在否定代孕合法性的法域當中,跨國代孕并不因為代孕地的法律承認代孕合法而在委托代孕方本國獲得合法性;無論代孕發生在哪里,違法代孕協議均構成違反公共政策或者法律原則或者強制性法律規定而無效。[39]
(3)各國對代孕的規制立場與策略并非一成不變。就各個國家和地區代孕立法規制的演進來看,代孕的禁止、限制或開放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人們倫理道德觀念的變化以及政府的立場而有所變化的。就此而言,我國目前對代孕的禁止并不代表將來不會開放代孕。但反過來,將來可能會開放代孕并不能成為現在就有必要對代孕進行有限度開放的理由,因為開放代孕與否除了考慮社會發展與人們倫理道德觀念的變遷之外,還必須要認真考量整個社會的環境以及制度建設是否已經具有了抵御代孕負面效應沖擊的能力,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環境以及制度建設是否已經具備了以上能力之后,開放代孕的正面效果才能夠大于其負面影響,開放代孕或至少是有限度開放代孕才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
(4)各國對代孕進行規制的目的在于保障社會倫理秩序的穩定。由于文化傳統以及國民性格等的不同,各個國家和地區對于代孕的規制策略并不一致,有的全面禁止,而有的則有限開放,有的則完全放任。但在謹慎規制代孕以確保社會倫理秩序穩定上,各國立法并無本質不同。“考慮到社會的利益在于不鼓勵性以及生兒育女的商業化、預防對女性的剝削以及鼓勵對已存在的孩子的收養,各國對代孕規制的徘徊在禁止和容忍代孕協議之間。”[40](P152)代孕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發展所衍生的一種違反自然生殖規律的生命現象,是生命倫理要直面并同時也是生命法要解決的問題。生命法作為法律化的生命倫理,其本質使命在于維護作為人類倫理社會秩序基本內容的生命倫理社會秩序,以保障整個人類社會的有序發展。而各國對代孕的立法規制顯然也承擔了這樣的使命。正因為如此,各國代孕規制無論是被規定在生命倫理法中,還是被規定在親子關系法中,抑或是被規定于民法典或人類輔助生殖法與刑法中,都顯現出了明顯且濃厚的維護社會倫理秩序尤其是基本人倫秩序的價值取向。就各個國家和地區人類輔助生殖立法的內容來看,凡是那些明顯且嚴重違背生命倫理的代孕現象——尤其是以牟利為目的的商業性代孕,一般都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所嚴厲禁止(當然,也存在俄羅斯、烏克蘭以及印度等這類極少數例外)。這充分表明了各個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來維護本國或本地區生命倫理秩序穩定的基本立場。
五、結束語:兼論我國代孕規制的立法缺陷與對策建議
近年來,全世界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呈逐年上升趨勢。據國際婦產科聯合會的統計:全世界有500~800萬人不能正常生育,其中由于男性因素造成的不孕不育占8%~22%,由于女性因素造成的占25%~37%,由于雙方共同因素造成的占21%~38%。在我國有2.3億育齡夫婦,約有1100萬個家庭存在生育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曾預測,不孕癥將成為僅次于腫瘤與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41]在此背景下,謀求運用醫學技術手段來解決不孕問題,已經成為很多不孕不育家庭所面臨的一種選擇。而伴隨著我國人工生殖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在醫學臨床上的日益廣泛應用,代孕作為一種醫學替代方案逐漸成為很多不孕不育者所傾向于求助的救命稻草。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代孕黑市在我國逐漸興起,并呈現出產業化的畸形發展趨向。代孕的暗流涌動不僅引發了諸如精子買賣、卵子買賣、代母商業化以及親子關系認定等在內的眾多問題,而且也對我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尖銳挑戰。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已經成為今后我國人工生殖立法必須要予以正視的一個問題。我國衛生部2001年出臺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以行政規章的形式對代孕作出了明確禁止,即: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④。這是我國目前現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對代孕所做出的明確禁止性的法律規制。但從實踐操作的層面來看,這樣的規制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以致近年來代孕黑市甚囂塵上,已經日益呈現出產業化的發展趨向。
筆者以為,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國現行代孕規制機制的欠缺。具體體現在:(1)我國對代孕的禁止僅限于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但卻并未禁止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種機構和個人組織代孕的行為,客觀上造成了“法規態度曖昧,試圖通過規范醫務行為來間接禁止代孕,卻實際軟弱無力,陷入了困境”[42]的尷尬狀態。⑤而代孕客觀上能夠帶來的巨大的利益誘惑必然會促使各種代孕中介沖破倫理的防護網,與個別無良的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相勾結,共同促成代孕的實現。⑥不僅如此,現行代孕規制立法僅為部委規章,其規制范圍明顯受限,效力層次明顯偏低,這無益于代孕的全面禁止。(2)現行代孕規制沒有得到其他立法的有力支持。在刑法中迄今還未專門針對代孕(無論是商業性代孕還是一般代孕)設置任何形式的罪名⑦;而在《民法通則》或《合同法》這類以倫理性為特征的民事立法中也沒有任何宣示代孕協議的非法性或無效性的規定⑧;就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示。這些疏漏都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現行代孕規制模式的效果,成為代孕在我國禁而不止的制度原因之一。
基于此,筆者以為,在我國今后的立法中,應當考慮采取相應的措施對以上立法缺欠進行彌補。具體包括:(1)提升現行人工生殖技術法的效力層次,進一步擴大禁止代孕所適用的范圍。應當考慮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出臺一部《人類輔助生殖法》或至少由國務院出臺一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并將禁止代孕的范圍由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擴展到所有機構和人員,以擴大代孕規制立法的效力和適用范圍,使其更適合規制代孕的需要。與此同時,加大立法對于代孕的處罰力度,提高對于非法開展代孕活動的機構與人員的罰款額度;對于開展代孕活動的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則可以考慮在相關立法中增設資格罰,通過撤銷其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或醫師執業許可證的方式加大其違法成本,令其不敢從事代孕活動,從技術上阻斷代孕的開展。(2)在刑法及民法中增加專門針對代孕規制的條款。在刑法中,應針對目前刑法中沒有設置代孕方面之犯罪及其刑罰的問題,增加“組織他人代孕罪”、“組織出賣人類精子、卵子或胚胎罪”、“非法散發、刊登代孕廣告和訊息罪”等犯罪。就目前而言,考慮到現階段發生在我國的代孕幾乎全部為商業性代孕的現實,可以在刑法中明確增加商業性代孕犯罪,至少先將旨在借助代孕牟利的商業性代孕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之內。同時,考慮到這類犯罪與其他犯罪在性質及社會危害性方面的差別,應當設置相對較輕的刑事責任。而在民法中,則應針對目前民法中尚無涉及代孕協議合法性問題及代孕所生子女之法律地位問題等之規定,明確宣示代孕協議的無效性,并就因代孕而引生的代子之法律地位及其權利等問題做出明確規定。例如,可以考慮在我國正在醞釀制定的《民法典》或《人格權法》中明確宣示:任何為第三人生育或妊娠之協議均屬無效;代孕所生子女的親生母親為通過分娩使其出生的婦女,負有對孩子的撫養義務;代孕所生孩子的權利受法律保護。這是全面禁止代孕,保障代孕規制效果的必然選擇。
[注 釋]
①這種天性來自于代孕母親在孕育代子時所付出的精力、心血以及肢體與言語方面的交流。盡管從基因學的角度而言,代孕母親與代子可能并不具有基因上的聯系(尤其是在不借助代母的卵子進行代孕的情況下),但二者之間卻依舊存在血緣關系。原因在于:代母與代子之間有一根臍帶相連,這根臍帶在連接著代母與代子身體的同時,將代子生存和發育所需要的營養和水分借助血液的流動(通過這根臍帶)由代母輸送給代子。這注定了二者之間血緣關系的不可抹殺性。
②有學者認為,人類行為不完全考慮自利,個體決策在更多的情況下受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成為所謂的“制度人”,他們并不完全追求自我利益,而是也追求非自我利益的東西,如公平、社會認可等。家庭中的利他主義較之家庭之外更為明顯,人們更愿意為親朋做出犧牲,因而無償代孕的合法化有其人性基礎(參見羅滿景:《中國代孕制度之立法重構——以無償的完全代孕為對象》,《時代法學》2009年第4期)。其言下之意在于,非以牟利為目的的利他性代孕體現了一種互助精神,體現了人善性的一面,法律應當給予支持和保護。對此,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人的天性與善性其實分別體現了人性在倫理道德領域的兩個層次,其中天性是人在倫理道德要求上較低的一個層次,屬于“義務道德”層次的一個人性范疇。而人的善性則是人在倫理道德要求方面較高的一個層次,屬于“高尚道德”層面的人性范疇。法律作為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顯然應當首先保護人最低限度的人性要求,即保護人的天性(母性);在人的天性獲得保護的基礎上,才能夠去謀求對倫理道德層次更高的人的善性的關愛和保護。而在人的天性與善性發生沖突時,法律應當首先考慮保護人的天性,而絕非善性,否則,就會很容易被倫理道德所綁架。
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代孕合法化者經常以代孕禁而不止為理由反對禁止代孕,但實際上,代孕禁而不止并不能成為支持代孕合法化的正當理由。原因在于,任何禁止模式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說,任何現象都是禁而不止的。這就如同販毒、搶劫、強奸等犯罪行為在各國的法律中無一不被全面禁止但販毒、搶劫、強奸等犯罪現象在各國依舊層出不窮一樣。事實上,任何反社會現象都只能夠被控制而無法被消滅,這是一種客觀規律,是社會存在的必然。假如僅僅因為法律的禁止不可能真正防范和杜絕代孕的發生就反對全面禁止代孕,則包括販毒、搶劫、強奸甚至是殺人等在內的所有犯罪行為顯然也應當為法律所開放,因為它們也有著與代孕合法化的相同理由。而這顯然是荒謬的。
④參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3條。
⑤這種現狀主要成因于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自身的效力,因為作為部委規章,其只能規范在其職權管轄范圍內的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
⑥就媒體曝光的非法代孕事件來看,代孕的非法收入一般可達數十萬元,甚或數百萬元,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受其作為部委規章的限制,最高的處罰額度卻只有3萬元,加之沒有刑罰措施的輔助,客觀上造成了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實施代孕違法成本過低的問題,立法禁止代孕的意圖沒有能夠實現。
⑦我國1997年出臺的新《刑法》設置了“組織他人賣血罪”及“強迫賣血罪”以及“非法采集、供應血液罪”等罪名,但卻遺漏了“組織他人出賣器官罪”、“組織他人代孕罪”、“組織出賣人類精子、卵子或胚胎罪”以及“對非法摘取、騙取他人器官罪”等罪名;2011年通過并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彌補了刑法遺漏人體器官犯罪的缺憾,但卻依舊遺漏了“組織他人代孕罪”、“組織出賣人類精子、卵子或胚胎罪”等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領域的犯罪。這使得我國的代孕規制無法獲得刑法的必要支持,其實效大打折扣。
⑧這一點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不同的法院在處理代孕糾紛時適用法律的不同。例如,2008年8月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代孕糾紛中,法院就以原告與被告簽訂的《代孕協議書》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協議內容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為由而認定該代孕協議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參見:陳宇、海鵬飛:《“借腹生子協議”無效 法院仍將孩子判給男方》,《南方都市報》2010年8月17日,第A12版)。而同年9月在廣西南寧市江南區審結的一起代孕糾紛中,法院則認定代孕協議無效,理由是該協議違背公序良俗(參見王斯等:《是“借腹生子”還是非婚生子?》,《當代生活報》2008年9月13日,第3版)。而在法國、澳門、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的部分州,代孕協議的無效性是為法律所明確宣示的。
[1]Sophie LM Strickland,Conscientious Objection in Medical Students:A Questionnaire Survey [J].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12,Vol.38.
[2]Vasanti Jadva1,Clare Murray,etl,Surrogacy:the Experiences of Surrogate Mothers[J].Human Reproduction,2003,Vol.18.
[3]林玲、黃霞.非傳統生育的合法性和制度構建——以代孕為例[J].人民論壇,2011(29).
[4]張月萍.淺析完全代孕的有條件合法化[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3).
[5]鄭成良.法律之內的正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6]張燕玲.人工生殖法律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楊遂全、鐘凱.從特殊群體生育權看代孕部分合法化[J].社會科學研究,2012(3).
[8]Max Charlesworth,Bioethics in a Liberal Societ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9]Emily Stehr,International Surrogacy Contract Regulation:National Governments’and International Bodies’Misguided Quests to Prevent Exploitation[J].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2012,Vol.35,(8).
[10]湯嘯天.生命法學與民事訴訟中的特別程序[J].政治與法律,2001(1).
[11]周平.有限開放代孕之法理分析與制度構建[J].甘肅社會科學,2011(3).
[12]張燕玲.論代孕母的合法化基礎[J].河北法學,2006(4).
[13]趙萬一.民法的倫理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4]蔣云貴.人工授精主體權利義務的辯證思考[J].長沙大學學報,2008(6).
[15]于皓.試談社會和諧前提下的代孕行為規范措施[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12).
[16]Ian Kerridge,Michael Lowe,Cameron Stewart,Ethics and Law for the Health Professions[M].the Federation Press,2009.
[17]周云水.代孕——親屬關系中的自然與文化[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
[18]冀睿、裘晟.無妊娠能力女性的生育權問題[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1).
[19]EmilyJackson,Medical Law:Text,Cases,and Material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0]Rakhi Ruparelia,Giving Away the“Gift of Life”:Surrogacy and the Canadian Assisted Human Reproduction Act[J].Canadian Journal of Family Law,2007,Vol.23.
[21]夏蕓.衛生法學研究任務以及體系構建思考[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22]胡旭晟.論法律源于道德[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4).
[23][德]拉德布魯赫.法律智慧警句集[M],舒國瀅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24]Garcia S.Reproductive Technology for Procreation,Experimentation and Profit[J].The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1990,Vol.11.
[25]翟曉梅、邱仁宗主編.生命倫理學導論[M].北京:清華出版社,2005.
[26]趙力等.湘潭否認產婦身亡醫護失蹤[N].新京報,2014-08-14.
[27][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28]Naoki Takeshita,Kanako Hanaoka,etc.Regulat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 Japan,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2003,Vol.20,(7).
[29]楊素云.代孕技術應用的法倫理探析[J].江海學刊,2014,(5).
[30]吳才毓.代孕行為非法化的復合思路——以代孕行為探討進程中的三步程序為中心[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3(3).
[31]席欣然、張金鐘.美、英、法代孕法律規制的倫理思考[J].醫學與哲學,2011(7).
[32][美]李·希爾佛.復制之謎:性、遺傳和基因再造[M],李千毅,莊安祺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33]熊永明.現代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規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4]Abraham Benshushan,Joseph G.Schenker.Legitimizing Surrogacy in Israel[J].Human Reproduction,1997,Vol.12,(8).
[35]Elly Teman.Birth a Mother:The Surrogate Body and the Pregnant Self[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36]Amrita Pande.Wombs in Labor: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Surrogacy in India[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37]SusanMarkens.SurrogateMotherhoodand thePoliticsofReproduction[M].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7.
[38]Mary Keyes.Cross-border Surrogacy Agreements,Australian Journal of Family Law,2011,Vol.26,(12).
[39]王萍.代孕法律的比較考察與技術分析[J].法治研究,2014(6).
[40]Martha A.Field.Surrogate Motherhood:The Legal and Human Issus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1]高波.倫理與法律對沖下的代孕思考[J].醫學與哲學,2008(7).
[42]任汝平、唐華琳.“代孕”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7).
劉長秋,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山東省高校證據鑒識重點實驗室兼職教授,上海市法學會生命法研究會副會長,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