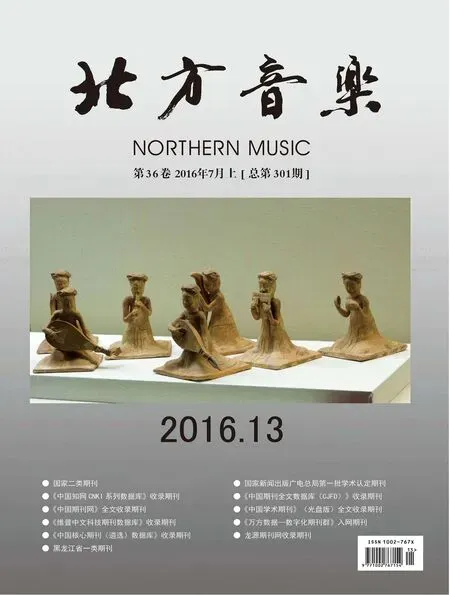從“紅色舞蹈”看政治因素對舞蹈語言形態(tài)的影響
趙 然(晉中學院音樂學院,山西 晉中 030600)
從“紅色舞蹈”看政治因素對舞蹈語言形態(tài)的影響
趙 然
(晉中學院音樂學院,山西 晉中 030600)
本文將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這一特殊時期的舞蹈作品為研究對象,進一步論證政治因素對舞蹈藝術的發(fā)展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以及舞蹈藝術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政治影響;紅色舞蹈;毛澤東文藝思想
政治作為一種制度文化,決定和制約了舞蹈這一精神文化的發(fā)展。政治價值作為一種社會價值的存在,是舞蹈社會性的一種體現(xiàn),因此,政治價值成為中國當代舞蹈社會價值中的一部分,這是由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系決定的,藝術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制度文化決定和制約著精神文化。正確合理的政治價值,可以促進舞蹈的發(fā)展,在階級社會中,統(tǒng)治階級往往將舞蹈作為輔佐政治的一種重要手段,因而在舞蹈的價值觀念中,往往滲透著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意志。政治價值不是僅對中國當代舞蹈的發(fā)展產(chǎn)生作用,而是存在與中國舞蹈歷史發(fā)展過程中。
毛澤東文藝思想對前人的理論進行了發(fā)展,對中國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和社會主義文藝運動規(guī)律進行了理性概括,對“藝術批評中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關系”這一問題,毛澤東辯證的說明了政治和藝術的關系,同時也提出了“階級社會中的”第一和第二的問題。針對藝術的特殊性,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tǒng)一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革命的政治內(nèi)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tǒng)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毛澤東文藝思想對特殊時期的中國舞蹈發(fā)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由此充分的體現(xiàn)了政治因素對舞蹈發(fā)展的深遠影響。
一、長征路上的舞蹈
長征是一次讓世界為之震驚的壯舉。二萬五千里的長征路上,革命歌舞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長征途中,紅軍一方面要與敵人作戰(zhàn),一方面還要經(jīng)受來自大自然的考驗,宣傳隊員們在這個挑戰(zhàn)面前顯示出罕見的信心和力量,他們時時刻刻不忘鼓動宣傳的任務。1935年6月,在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夾金山下的達維會師,聯(lián)歡會上,一方面軍宣傳隊表演了《烏克蘭舞》、《紅軍舞》、《農(nóng)民舞》等,四方面軍宣傳隊表演了《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開》等,受到了與會指戰(zhàn)員們的熱烈歡迎。1936年3月,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西康甘孜藏族地區(qū),由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及敵人的反對宣傳,致使藏族同胞對紅軍產(chǎn)生了敵對的情緒。4月下旬,四方面軍成立紅場委員會,在紅場上舉行了軍民聯(lián)歡會,李伯釗及宣傳隊員們教藏族同胞跳《海軍舞》、《烏克蘭舞》,藏族同胞教宣傳動員跳“鍋莊”、“弦子”。紅軍文藝戰(zhàn)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礎上編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紅軍與藏族同胞手拉手,肩并肩,以整齊劃一的節(jié)奏和步調(diào)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現(xiàn)了紅軍與藏胞的團結與友誼。
二、抗日烽火中的舞蹈
(一)孩子劇團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滬東臨青學校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fā)的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中國共產(chǎn)黨國難教育社黨組織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劇團成立初期,在上海街頭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及《仁丹胡子》、《做漢奸》等兒童劇,激發(fā)了人們的抗日熱情。其后,劇團又陸續(xù)出演了《孩子血》、《這怎么辦》、《孩子們站起來》,吳曉邦創(chuàng)作排練的《法西斯喪鐘響了》收到了強烈的宣傳效果。
(二)抗敵演劇隊
抗敵演劇隊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以演劇方式進行抗日宣傳教育的文藝團體,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隊”。其先后創(chuàng)作演出了舞蹈《黃花曲》、《綾子舞》、《銅棍舞》、《劍舞》,改變民間舞蹈《推小車》、《打蓮湘》、《采蓮船》、《走馬燈》、《啞子背風》、《新王大娘補缸》等。其中《啞子背瘋》原是表現(xiàn)一個啞子背著兩腿風癱的小姑娘在屋外玩耍的情景。后來,戴愛蓮把它改編成一位身板健壯的老爺爺背著天真活潑的小孫女在公園撲蝴蝶游玩。表演者穿戴簡單的服飾,一個人同時扮演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邊唱邊舞,十分生動風趣。改編后的《老背少》,既保留了原來的舞蹈藝術特色,又使人物更加完美可愛。
上述劇團演出的舞蹈,基本上是繼承土地革和紅軍時代的舞蹈傳統(tǒng),利于民間藝術形式,反映現(xiàn)實生活。《豐收舞》表現(xiàn)了農(nóng)民喜獲豐收的情景,動作敏捷,技巧性強。該舞在陜甘寧地區(qū)深受人們喜愛。《紅色機器舞》以舞蹈形象摹擬汽缸的發(fā)動,齒輪和轱轆的轉(zhuǎn)動,發(fā)動機的轟鳴,展示了未來的機器時代的遠景。《收割舞》由八路軍一二九師文工團在太行五堡村軍民聯(lián)歡會上演出,表現(xiàn)了根據(jù)地軍民生產(chǎn)、收割的勞動場景。在抗日戰(zhàn)爭中,藝術工作以空前的影響發(fā)生著巨大作用。各根據(jù)地的人民,為反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以自己喜愛的民間舞蹈,以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抗戰(zhàn)到底。
三、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舞蹈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舞蹈藝術,從不同角度致力于迅速表現(xiàn)士兵、工人、農(nóng)民的火熱生活,顯示了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愿望。其中部隊舞蹈成為了當時特殊歷史時期的閃光點,如《紅星舞》、《花環(huán)舞》等等。抗日時期,多數(shù)是在慶祝活動時,開展 群眾性的扭秧歌、打腰鼓等民族民間舞蹈活動,正式成立舞蹈專業(yè)隊伍是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
《進軍舞》 反映部隊戰(zhàn)斗生活的舞蹈:進軍舞是東北民主聯(lián)軍總政治部宣傳隊舞蹈分隊在舞蹈家吳曉邦的指導下,由胡果剛、查列領導全分隊創(chuàng)作的。這個大型舞蹈的產(chǎn)生,正值我軍“三下江南”和“四保臨江”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時候。《進軍舞》共分五大段:第一段為騎兵舞,表現(xiàn)我騎兵英勇殺敵的英雄氣概。舞蹈一開始就把人們帶到緊張的戰(zhàn)斗環(huán)境中去。戰(zhàn)馬奔馳,刀光閃閃,給人以鼓舞。第二段是步兵舞,表現(xiàn)我軍苦練殺敵本領,掌握“三大技術”(射擊、投彈、刺殺),表現(xiàn)出步兵戰(zhàn)士瞄的準、投的遠和刺刀見紅的真功夫。第三段是炮兵舞,表現(xiàn)炮兵操炮練炮的訓練生活。第四段是表現(xiàn)步、騎、炮的協(xié)同作戰(zhàn)。第五段是一段歡慶勝利的集體舞。結束時是一幅勝利進軍的造型。這個大型舞蹈的產(chǎn)生,對解放軍舞蹈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通過延長受到了廣大工農(nóng)兵的熱烈歡迎,并獲得較高的評價。
四、延安秧歌運動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楊家?guī)X召開了由當時一百多名文藝干部參加的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在會上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時糾正了邊區(qū)文藝運動的方向。在此精神的鼓舞下,魯迅藝術學院組織起第一支秧歌隊,一場規(guī)模空前的秧歌運動轟轟烈烈的展開。新秧歌運動的蓬勃發(fā)展,反映了革命文藝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能動的創(chuàng)造。從舞蹈功能來分析,新秧歌已從原來民俗性、自娛性的陜北踢場子秧歌轉(zhuǎn)化為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隨之而來的則是舞蹈形態(tài)的變化。那強勁的節(jié)奏,放大了的步伐,挺胸昂首及大幅度的甩臂,均擺脫了封建時代遺留的審美印跡,群眾之所以親切的稱之為“解放秧歌”,正是因為他賦予了昂揚的革命精神。20 世紀40年代,以延安為中心影響到全國范圍的秧歌運動,成為革命與舞蹈的又一次歷史性融合,其以廣為流傳的民間秧歌形式,將全民抗日、全國解放的時代心聲,傳遞到根據(jù)和國統(tǒng)區(qū),并一直影響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舞蹈事業(yè)發(fā)展。
《兄妹開荒》,王大化、李波、羊路由編劇,安波曲,創(chuàng)作于1943年初。這一年春節(jié),由魯迅藝術學院秧歌隊首演于延安。內(nèi)容反映解放區(qū)大生產(chǎn)運動,據(jù)當時陜甘寧邊區(qū)開荒勞動模范馬丕恩父女的事跡編寫。原名“王二小開荒”,后以群眾通稱的“兄妹開荒”定名。是秧歌運動中產(chǎn)生的第一個秧歌劇,反映了新的社會生活,發(fā)展了民間傳統(tǒng)的秧歌。《兄妹開荒》創(chuàng)作和演出的一舉成功,標志著新秧歌劇的正式誕生,并由此帶動和促進了延安新秧歌運動的蓬勃發(fā)展。
《義勇軍進行曲》男子獨舞,中國現(xiàn)代舞的早期作品,吳曉邦的“抗戰(zhàn)三部曲”之一,1937年首演于江蘇無錫,自編自演吳曉邦,音樂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同名抗戰(zhàn)歌曲,實事求是的說,舞蹈《義勇軍進行曲》的大獲成功,首先得歸功于那個抗日救國的偉大時代,歸功于這首同名歌曲中燃燒的愛國激情。在它高亢激昂的歌聲中,舞臺上飛旋出一位身穿中式白色上衣、黑色褲子的青年男子,他扎著紅腰帶,赤著兩只腳,滿身正氣,昂首闊步,投入了抗日戰(zhàn)爭的洪流之中,并且振臂召喚,不愿做努力地惡人們起來反抗。他拿起步槍,上戰(zhàn)場,端起刺刀,殺敵忙,在槍林彈雨中一次有一次的沖向敵方,表現(xiàn)出保家衛(wèi)國的大無畏精神!
五、結語
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的舞蹈發(fā)展不難看出,舞蹈成為了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同時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舞蹈藝術本身語言形態(tài)的發(fā)展,藝術家們充分發(fā)揮其能動的創(chuàng)造力,在當時特殊歷史背景下,讓舞蹈藝術打上了“革命、反抗、團結……”的政治烙印。
[1]王克芬著.《中國舞蹈史》.武漢大學出版社.
[2]馮雙白,茅慧著.《中國舞蹈史及作品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