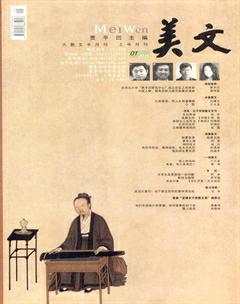在西北大學(xué)“賈平凹研究中心”成立會(huì)議上的致辭
我是西北大學(xué)的學(xué)生,我于母校,有著如海外華僑對(duì)于中國(guó)的那種感情。西北大學(xué)要成立這個(gè)研究中心,我知道后,真是誠(chéng)惶誠(chéng)恐,一方面我感激學(xué)校對(duì)我的關(guān)注愛(ài)護(hù),另一方面又覺(jué)得這樣好不好?因?yàn)槟感H缥业募亦l(xiāng)一樣,無(wú)論我在外干了多大的事,回到家鄉(xiāng)永遠(yuǎn)是“賈家的老大回來(lái)了”。見(jiàn)人招呼就敬煙,把一根塞進(jìn)人家嘴里了,還得在耳朵上再夾一根,要站起來(lái)敬酒,人家讓我干什么就干什么,還得臉上笑笑的。否則人家就罵了,我的一個(gè)朋友曾在我家鄉(xiāng)的街上說(shuō),你們這兒出了個(gè)賈平凹啊,回應(yīng)的是:噢,像他這樣的,這里拿車?yán)ǎ∷匝剑谖鞅贝髮W(xué)辦這個(gè)研究中心,我不知道好不好。
但回想起來(lái),母校給了我知識(shí),給了我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起根發(fā)苗,尤其當(dāng)年《廢都》被批得我昏頭黑臉,在西安城里淪落到無(wú)立錐之地,西北大學(xué)給了我房子,讓我在此療傷,在此重新上路。我記著西北大學(xué),記著那時(shí)的郝克剛校長(zhǎng),記著中文系的那屆班子和老師。又是二十多年過(guò)去,西北大學(xué)有了這么好這么大的校園,郭立宏校長(zhǎng)上任后對(duì)文學(xué)院如此重視和支持,文學(xué)院一批老師在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研究上成就斐然,段建軍院長(zhǎng)給我說(shuō):一切條件都成熟,是該成立個(gè)研究中心的時(shí)候了。我聽(tīng)從他的意見(jiàn),心里面仍很忐忑不安。段建軍是著名的評(píng)論家,他的評(píng)論文章見(jiàn)解獨(dú)到,不同凡響,才情淋漓,又有非常好的品格和人緣。我是同意了,也只是同意,并沒(méi)參與,甚至沒(méi)有建議,他和院里的老師很辛苦,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精力、時(shí)間、心血。我雖來(lái)也沒(méi)來(lái)過(guò),但我在一旁感念著。古語(yǔ)講:樹(shù)有包容鳥自知。我這只鳥再次感謝西北大學(xué)的這棵大樹(shù)能讓我在樹(shù)上停歇。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寫了些什么,竟混得出了名?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出版的作品,有人寫過(guò)幾篇評(píng)論,這不就是研究了么,還值得再研究嗎?總覺(jué)得是不是太夸獎(jiǎng)了,有些做夢(mèng)一樣不真實(shí)。這種感覺(jué)我不停地追問(wèn)我自己,使我有時(shí)出一身冷汗。好在我現(xiàn)在才稍稍懂得了些文章怎么寫,知道了自己還缺什么,自己的軟肋在哪,命門在哪,年紀(jì)大了,精神卻不濟(jì)了,人的一生真是可悲。常后悔當(dāng)年為什么選擇了文學(xué),到現(xiàn)在了干這行還沒(méi)個(gè)盡頭,還驚恐和無(wú)措。陜北民歌有一句:淚蛋蛋本是心頭油,誰(shuí)不傷心誰(shuí)不流?真的是有時(shí)候想起來(lái),就一個(gè)人流眼淚。
想我過(guò)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里見(jiàn)過(guò)彩旗和鮮花,也見(jiàn)過(guò)黑暗和荒涼,為自己寫出某個(gè)作品而興奮過(guò)、得意過(guò),也為自己寫不出自己向往的作品而焦躁、煩惱、無(wú)奈,也怪天怪地,最后只是罵自己。我這六十年里是個(gè)可憐人,敏感又呆板、孤寂又倔強(qiáng),像撲燈蛾一樣,只要有光就撲,像夾子一樣,見(jiàn)什么都想夾,但干什么都比周圍人慢一步,老是后悔。
無(wú)論將來(lái)我能走到哪一步,我現(xiàn)在覺(jué)得我還有寫作的饑餓感和強(qiáng)烈的沖動(dòng),過(guò)去的一切讀書、學(xué)習(xí)、采風(fēng)、寫作都是在增加我的能量,都是在擴(kuò)大我的格局。我要說(shuō)的是,既然這個(gè)中心揭牌成立了,我會(huì)以此為動(dòng)力,你們喊加油,我就盡我的能力跑甚至超能力跑。寫出好作品才不枉成立這個(gè)中心,才不會(huì)讓這個(gè)中心成立得毫無(wú)意義,才不讓別人嘲笑和非議。
我始終認(rèn)為,創(chuàng)作和評(píng)論是一回事,都是文學(xué)愛(ài)好者從事的不同的寫作方式,評(píng)論和創(chuàng)作一樣需要對(duì)文字的敏感,對(duì)文學(xué)有一種特有的感覺(jué)。然后,雙方相互對(duì)峙、激蕩、影響,形成文學(xué)的命運(yùn)共同體。
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我的第一個(gè)作品研討會(huì)就在西北大學(xué)進(jìn)行,那時(shí)全是陜西的評(píng)論家,幾十年過(guò)去了,有的評(píng)論家已經(jīng)過(guò)世,有的評(píng)論家已離開(kāi)了評(píng)論工作,現(xiàn)仍對(duì)我的創(chuàng)作關(guān)注、指正的,還有李星、暢廣元、肖云儒等人,而晚一輩又起來(lái)了,那就是今天到會(huì)的各位評(píng)論家。
我一生有兩大幸運(yùn),一是我大學(xué)畢業(yè)后,從事了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相關(guān)的文學(xué)編輯工作。二是周圍有一批又一批關(guān)注我的評(píng)論家。今天,除了在陜的各位,還來(lái)了幾位文壇權(quán)威、評(píng)論大家李敬澤、丁帆、吳義勤、白燁等等,我深深地感謝你們!
最后我再說(shuō)一句,我這個(gè)人不善交際,不愛(ài)走動(dòng),膽怯、軟弱,但好處是我能吃苦、能忍耐,能為了我心中的所謂大事而看淡別的利益,能不為所動(dòng)。所以,有這個(gè)研究中心的牌子給我壓力,有大家的目光關(guān)注,我當(dāng)窮力了再窮力,一旦我寫不出好的作品,辜負(fù)了大家的期望,這個(gè)研究中心就取消,牌子摘掉,或換成別的牌子,我就歸隱老家深山去,銷聲匿跡,自個(gè)兒去喘息待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