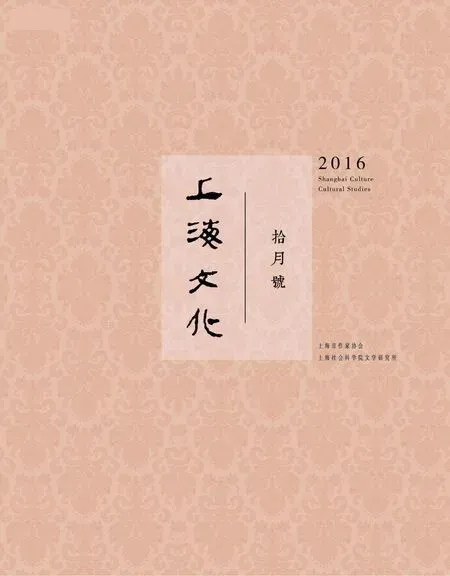穿梭于文化政治地獄的《太凱爾》(上)
理查德·沃林 著 董樹寶 譯
穿梭于文化政治地獄的《太凱爾》(上)
理查德·沃林 著*董樹寶 譯**
本文以法國“五月風暴”時期著名雜志《太凱爾》為中心,闡述了該雜志核心人物菲利普·索萊爾斯、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羅蘭·巴爾特等人與中國問題的密切關系,折射出法國思想界對中國“文化大革命”與法國“五月風暴”的深層思考。
《太凱爾》 存在主義 結構主義 “中國迷”
哦,我對左岸進行了調研。我曾在大學里與那些腋下夾著《太凱爾》雜志到處游蕩的人交朋友。我太熟悉那種垃圾雜志,你甚至不忍卒讀。
——菲利普·羅斯:《反人生》
20世紀60年代,《太凱爾》在文學造詣極高的主辦者菲利普·索萊爾斯的領導下聲名狼藉地追逐著幾乎每一個稍縱即逝的知識潮流:新小說、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一點也不足為怪的是該雜志的政治忠誠同樣是反復無常的。在培育了一種謹慎的“非政治主義”(apoliticism)后,它突然跌跌撞撞地從最僵化的斯大林正統觀念中沖出來,轉而同樣狂熱地去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中國—— 一個革命浪漫主義例子,這種革命浪漫主義在一次著名的1974年北京旅行中達到頂點。作為共產黨的忠誠分子,《太凱爾》派與“五月風暴”“失之交臂”。在一個如今傳奇的事件中,索萊爾斯——順便提一句,他的父親是波爾多重要的工業家——極力譴責學生運動缺乏無產階級品質。不同于薩特和福柯,《太凱爾》派回避了毛主義學生團體,在“五月風暴”后的歲月中,這些團體正試圖改造法國的政治風景,通過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特質轉譯為一個法國固有的習語——“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術語。而作為文學知識分子,他們容易被毛澤東這一人物形象所誘惑,這一形象既像一個空談的哲學家——好像一個現時代的哲學王——又像一個詩人。因此,《太凱爾》群體發誓直接效忠北京。大字報(中國大規模的墻壁海報)開始裝飾位于時尚的雅閣街(rue Jacob)的《太凱爾》辦公室。
《太凱爾》故事的必要組成部分關系到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突然從一個一文不名的保加利亞獎學金學生一舉成為左岸備受推崇的人。不同于索萊爾斯,他的著作幾乎沒有找到大西洋彼岸的回聲,而有關美國人接受法國理論的史話,如果不詳細敘述克里斯蒂娃的關鍵性作用就不可能被書寫。像其他法國知識分子一樣,她賭注中國共產主義在第三世界主義時代中可以在其他道路均已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最后,《太凱爾》派當然像法國其他左派分子一樣遭到了應有的譴責,而且幻想破滅。他們采取極端措施,破釜沉舟,埋葬了他們自己的文化革命的過去,解散了《太凱爾》,并創辦了一份新的、替代它的純文學刊物《無限》(L'Infini)。作為一種對其先前的政治失策(與效仿許多前左派分子)的贖罪行為,他們也在70年代后期吵吵鬧鬧地支持東歐持不同政見者的事業。
的確,恰恰這一極為奇特的故事,要想完全理解它,就必須完整地加以講述。
一、只為了藝術
1960年3月,一本新的文學評論雜志出現在巴黎街頭,雜志封面上公然炫耀著尼采的格言:“我想擁有這個世界,我想按照它本來的樣子(tel quel)擁有它,我一再想擁有它,永遠擁有它;我貪得無厭地大喊道:再來一次!——不僅僅為了我自己,而且為了整出戲劇和整個表演;也不僅僅為了表演,而且基本上為了我,既然我需要表演——因為它需要我——而且因為我使之成為必要的。”①Tel Quel 1, 1960, 1.這份評論雜志是23歲的波爾多青年菲利普·索萊爾斯(本姓Joyaux)的創意,大家常說他命中注定是為了輝煌的文學事業而生的。索萊爾斯20歲時,他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挑戰》(Le Défi)就獲得了費內龍獎(Fénéon Prize)。一年后,他的小說《一種奇特的孤獨》(Une solitude curieuse)贏得了天主教小說家弗朗索瓦·莫利亞克(Fran?ois Mauriac)和超現實主義神童、后轉變為斯大林主義者的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的高度評價——這當然是一個極為獨特的組合,令人生疑的是這兩位來自政治光譜對立端的文學巨匠除了認可索萊爾斯的杰出才華之外到底能否就其他事情達成一致性意見。對于索萊爾斯來說,他早年就聚焦于文學贊譽的榮耀,因而他做事謹慎,不留漏洞。在他意識到才華與成功在巴黎知識分子政治的超政治化氛圍中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具有關聯性后,他就有條不紊地培育那些可以將他置于文化快速通道的社會關系。他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太凱爾》的主編——這是由進步的天主教出版社瑟伊出版社(Seuil)所表現出來的高度信任。不過,巴黎出版商不斷地尋找下一個文學轟動性人物——下一個紀德,下一個薩特,鑒于索萊爾斯令人贊嘆的成就,瑟伊出版社把賭注押在他身上似乎是很好的決定。
刊在雜志封面上的尼采格言被視為一種挑釁,因為《太凱爾》的事業在俄狄浦斯情結的層面上直接反對統治法國的思想主人薩特。雖然他在1964年出版《詞語》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當時他快60歲了,但是薩特的“星運”毫無疑問開始走下坡路,決定其繼承人的連續爭斗顯然已經開始了。他在50年代早期,也就是忠誠的親莫斯科時期,當然有過令人尷尬的政治失策。此外,他在40年代和50年代所倡導的存在主義突然不流行了,不久就被據稱是更加嚴密的結構主義方法所取代。不過,通過1948年有影響力的小冊子《什么是文學?》——在這本小冊子中,薩特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占領時期的陣痛之后唱出了“介入文學”的贊歌(“假如文學并不是一切,那么它就一文不值。這就是我所說的‘介入’。”)①T Sartre, The Purposes of Writing, in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pp.13-14.——哲學家薩特為那種已變得不可能忽視的文學努力樹立了標桿。因此,正是在反對文學行動主義信徒薩特的意義上,索萊爾斯及其同仁才在《太凱爾》的創刊號上瞄準了目標。像薩特一樣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癡迷于“改變世界”的律令,而索萊爾斯在尼采“愛命運”(Amor fati)思想的啟發下試圖返回到上一代人頹廢的唯美主義——普魯斯特、瓦萊里和紀德那代人。正如雜志編輯人員在創刊號上所宣布的那樣(以斜視薩特及其同仁的方式),“空想理論家長久地統治著表達……現在該是分道揚鑣的時候了;容許我們去關注表達本身、表達的必然性及其特殊法則”。②D é claration, Tel Quel 1, Spring, 1960, p.3.
索萊爾斯按照本來樣子“回歸文學”的號召可能被認為有一點兒爭議,這只有根據困擾法國政治文化的“維希綜合征”(Vichy syndrome)才能被理解。到60年代初期,法國在很多方面還不得不在心理上從40年代的“奇異的潰敗”中恢復過來,根據這一點,共和主義——這個國家所熟悉的唯一民主傳統——的成就不可挽回地被玷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治再生的希望在一場冷戰的地緣政治規則與慣常的議會事務的可恥回歸中破滅了。正當法國50年代初期似乎正要恢復政治基礎時,殖民主義——第三共和國另一項引起歧義的遺產——開始猛烈地反噬。1954年,法國軍隊在印度支那北部一個隱蔽的前哨基地奠邊府遭到了恥辱性的戰敗。同一年,阿爾及利亞爆發了一場重要的殖民地起義,這同時突然引發了法國本土的內戰危機與第四共和國終結。法國1940年面對進攻的德國軍隊發生了突如其來的、令人費解的潰敗,事后對這一事件的主導性解釋之一就是“文化墮落”(cultural decadence):因其忠于“為藝術而藝術”的傳統,法國變成了一個超世脫俗的唯美主義的國度,不能應對20世紀現實政治的挑戰。這樣的辯解無疑是太言過其實了。即便如此,他們仍享受著一種由法國多方面的戰后外交政策慘敗助長的、可怕的固執。(在這一點上,人們可以在這張慘敗清單上加上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對于薩特這一代人來說,他們在30年代的政治挫敗期間(詩人奧登說是“卑下的、虛偽的10年”)——阿比西尼亞戰爭、西班牙內戰、慕尼黑陰謀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走向成年,回歸美麗時代的唯美主義似乎是一種恣意妄為的退化。而索萊爾斯及其同齡人在50年代富裕社會的玫瑰色光輝下長大成人,對于他們來說,《現代》左派分子的政治約束似乎是令人窒息的、壓迫的—— 一種遠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暴行的步伐。
因此,《太凱爾》創刊宣言被視為一篇反薩特的宣言,這具有某種合理性。當然,這種宣言形式是歐洲先鋒派的顯著特點之一。然而,先鋒派(達達主義、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為了改造生活而采用宣言形式(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一文中宣布:“人必須練習詩歌”),而索萊爾斯為了分離人生與文學的明確目的才使用了宣言形式。他在創刊號上聲稱:
每當思想從屬于道德與政治的律令,思想就不再是我們從中所期待的:我們在場的基礎,其清晰而又晦澀的藝術表達;每次思想以這種方式被貶低……布道,它足以滿足愛的需要,而文學有時遭受鄙視,但仍然凱旋而歸,問心有愧地被辯護……如今談及“文學品質”或“文學激情”可能正好是所需的。①D é claration, Tel Quel 1, Spring, 1960, pp.3-4.
瑟伊出版社編輯弗朗索瓦·華爾于1974年陪同《太凱爾》派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一次考慮不周的考察,他為將這個群體的計劃與100年前“為藝術而藝術”運動的開端進行比較時提供了一種恰當的歷史類比:“我們正進入第二帝國時期,將要出現一個新帕爾納斯派(Parnassus)。這個新帕爾納斯派必須表達自己……這個新帕爾納斯派將是《太凱爾》。”②Wahl語,引自Faye,Commencement d'une figure,p.68。華爾的描述方法暗示了路易·波拿巴的專制統治(他通過1851年政變殘暴地終止了“四八志士”[forty-eighters]的共和希望)與法國統治的專制者戴高樂的專制統治之間的相似之處。薩特從“介入”角度為寫作進行辯護,而索萊爾斯,這個自命不凡的家伙、反其道而行者,似乎贊美一種“非介入”(disengagement)的美學。
索萊爾斯的唯美主義甚至反映在他精心設計的筆名上,Sollers這個筆名來自拉丁詞sollus與ars的結合,意思是“只為了藝術”(solely art)。他假定的典范是法國20世紀最有聲望的文學雜志《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aise,簡稱NRF)。在30年的鼎盛時期(1910—1940年),《新法蘭西評論》曾是普魯斯特、紀德和馬爾羅以及青年薩特等作家的根據地。不過,法國淪陷后,在德國侵略者的命令下,法西斯主義作家皮埃爾·德里厄·拉羅歇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擔任主編,而且《新法蘭西評論》逐漸被視為一種懦弱合作的典型。就其本身而言,這是一個引發歧義的先例。《太凱爾》早期的贊助人、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爾特以下列措辭恰當地描述了《太凱爾》的使命:“一份雜志——比如你們的雜志——道路狹窄,似乎就在于把世界看成了像是通過一種文學意識所形成的那種樣子,就在于周期性地把現時性看做一種秘密作品的素材,就在于將您自己安排在了一種非常脆弱和相當不明確的時刻——而在這種時刻里,某一個真實事件的關系將被文學意義所抓住。”③Barthes,Literature Today,p.157。譯文參見《當今文學》,懷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9頁。——譯注
索萊爾斯為文學形式主義所做出的不妥協辯護當時看起來是多么地有爭議,兩個同代人的反應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初期,共事的編輯讓-勒內·于格南(Jean-Rene Huguenin)開始脫離雜志,他擔心索萊爾斯如此這般地向語言問題讓步,索萊爾斯就會冒膚淺的危險,因為當文學從自我指涉的層面上被審視時,文學就排除了表達更高目標或訴求的可能性。按照于格南的看法,索萊爾斯狹隘的唯美主義缺乏“悲劇感、冒險的趣味、野性的放縱、悲觀絕望”。①Huguenin, Journal, p.77.這本雜志如此費盡心思地去追逐這一生死攸關的冒險,以致它有可能變成純文學的雜志。作家、哲學家讓-皮埃爾·費耶(Jean-Pierre Faye)參加了編委會,參與時間短暫,即便是不定期的,但他對當時難以承受的政治命令表達了看法,當提及這個群體的創刊宣言時,他說:“在擺脫‘政治和道德的指令’束縛的‘表達’決定自理的時刻,法國軍隊就忙著占領阿爾及利亞、殺人一百萬,并嚴刑拷打數千人。”②Faye語,引自Knapp,French Novelists Speak Out,p.84。從這一角度看,《太凱爾》的事業在顯然否定的意義上是“不合時宜的”(untimely)。
假如《新法蘭西評論》代表了索萊爾斯的文學標準,那么他的社會角色模型似乎應該是司湯達筆下的于連·索雷爾(Julien Sorel):一個想方設法想擠入上流社會的人,他冷酷無情地爬到了上層社會,而在這一過程中卻喪失了靈魂。假如有人仔細地描繪《太凱爾》蜿蜒曲折的知識軌道,那么似乎可以公正地說索萊爾斯長久以來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迎難而上。縱觀雜志22年暴風雨般的歷史——1982年停刊,只是為了在更具聲望的《新法蘭西評論》出版商伽里瑪出版社的管轄下改名為《無限》,似乎唯一沒變的是:索萊爾斯極其渴望成為知識分子焦點人物。
二、從新小說到結構主義
《太凱爾》將它的聲譽壓在了文學現代主義的復興上,援引了福樓拜、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普魯斯特、卡夫卡和喬伊斯等著名前輩作為“斗爭的同伴”(compagnons de lutte)。但是除非該雜志能夠涵蓋合乎現代主義標準的當代代表,否則它就招致一種古玩癖的危險,這種古玩癖對于一本試圖繼承20世紀先鋒派衣缽的雜志來說是一種無法接受的姿態。通過培育對新小說“大佬”阿蘭·羅伯-格里耶的忠誠態度,索萊爾斯及其同仁解決了這個問題。50年代,《窺視》和《橡皮》等作品(也許最好描述成為了對象或物的“意識小說”[novels of consciousness])獲得了大量好評。羅伯-格里耶的創新性技巧(在這一技巧中,19世紀小說情節和人物等創作慣例已無足輕重)天衣無縫地與《太凱爾》的形式主義訴求及其對現實主義的厭惡嚙合在一起。他對形式革新的偏愛符合《太凱爾》所強調的重點,《太凱爾》以馬拉美的方式強調了文學語言非交流性的、自律性的特征。
巴爾特成為新小說最重要的批評健將,他在一部標志性的隨筆《寫作:一個不及物動詞》(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③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ed. Macksey and Donato.中整理了這些規則。他主張(如他先前在另一部作品《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所做的那樣)語言的再現或實用的功能次于語言的詩學功能——《太凱爾》派在他們的創刊宣言中所贊頌的“表達”的自律維度。對立于“介入文學”的主張,巴爾特主張,作者不再“根據他的角色或價值,而應通過某種話語意識(awareness of language)來定義”。①Barthes, Criticism and Truth, p.64.也不難識別羅伯-格里耶的文學技巧——著名的“戲中戲”技巧(mise en ab?me),或者有意識的意義懸置,他對排斥心理要素的非個人化寫作方式的信奉——完全反對薩特感情外露的、有時單調乏味的“主題小說”(romans à thèse)。在《太凱爾》一代人反對《現代》正統觀念的代際斗爭中,羅伯-格里耶及其新小說家同仁是理想的同盟者。一位批評家恰當地指出:“通過借助語言來擺脫政治的方法,《太凱爾》拒絕歷史本身,歷史不是由他們而是由他們的長輩——薩特和阿拉貢那代人——創造的,而且他們只是被猛然推入歷史之中而已。”②Marx-Scouras,Cultural Politics of Tel Quel,pp.39-40.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后羅伯-格里耶自己挑戰了像巴爾特和《太凱爾》派這樣的人所提出的、對新小說的形式主義解釋。他堅持認為他在《在迷宮里》(In the Labyrinth)與其他作品中發展的“客觀現實主義”(objective realism)表現了他與前10年歷史創傷達成妥協的特有方式:戰爭、政治潰敗、占領與叛國通敵。然而,到了他詳盡解釋這些免責聲明時(1984年),新小說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了20年,幾乎沒有批評家注意到這些解釋。早在50年代,雅克·萊納爾(Jacques Leenhart)和盧西安·戈德曼對羅伯-格里耶的新小說提出了極具影響力的、創造性的政治解釋。在《文學社會學》(Toward a Sociology of Literature)中,戈德曼認為羅伯-格里耶的小說(物優先于人)討論了社會物化的問題。在后來的一部作品中,羅伯-格里耶自己質疑了對其作品的“去政治的”解釋;參見Alain Robbe-Grillet,Le miroir qui vient,Paris:Editions de Minuit,1984。
1961年,福柯出版了《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事后回想起來,索萊爾斯將該書的出版視為這10年中最重要的出版事件之一。③Philippe Sollers, De Tel Quelà L'Infini, Autrement, 69, April, 1985, p.8.在該書的結尾,福柯贊頌了4位“被詛咒的詩人”(poètes maudits)的“大拒絕”(Great Refusal):荷爾德林、奈瓦爾(Nerval)、尼采和阿爾托(Artaud)。這4位詩人都以瘋癲結束了生命。他們的寫作表達了福柯的看法——福柯贊美了“非理性不受干擾的工作……”,通過現代精神病學的強制方法“永遠不可化約為那些可被治愈的精神錯亂異化”。④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p.278. 譯文參見《瘋癲與文明》,劉北成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257頁。另參見《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709頁。參見法文原著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Paris:éditions Gallimard,1972,p.530。此處譯文參照中譯本、法文原著。——譯注在這個被詛咒詩人的先賢祠中,福柯很快又加上了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他最新的崇拜者若爾日·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年)的名字。
在福柯的影響下,《太凱爾》派突然開始疏遠“為藝術而藝術”的輕盈飄渺的歡愉(巴爾特稱之為“文之悅”),反而關注生命體驗的種種問題。他們不再把文本性本身視作目標,并開始討論文學想象在顛覆衰弱而熟悉的日常生活慣例中所發揮的作用。
使這種對“僭越”動力學(強制執行令人聯想到超現實主義的文化反抗行為)的新關注與《太凱爾》早期的文學純粹性保持一致,這證明是很難的,要不就是不可能的。“僭越”希望具有一種改造性效果,而唯美主義非常高興按照“本來的樣子”(tel quel)來拋棄這個世界。這種情境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與新小說家斷絕關系的理由,而這些新小說家們的成就鞭策索萊爾斯和其他人成為知識分子名流。
60年代初,一種革命性的理論范式結構主義開始攻克巴黎知識分子的舞臺。隨之而來的是其他哲學方法——最突出的是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似乎是乏味的、過時的。結構主義的源頭追溯到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該書第一版于1916年出版。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由二元對立決定的,符號或詞語基本上是任意的;索緒爾主張它們存在主要與其他詞語有關,而不是存在于與它們所命名的事物的必然關系之中。通過區分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相對于其變量的語言的結構性常量與個體言語行為的偶然體現,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似乎給真正科學的語言研究提供了基礎。
出于同樣的原因,他的方法遮蔽了語言同等重要的歷時的或歷史的維度。最終,對歷時性或歷史的忽視——結構主義的說法是“事件”領域——結果證明是結構主義的“阿基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因為結構主義鐘愛的常量如果像這種范式所主張的那樣是全然決定性的,那么解釋新事物的來臨變成不可能的。根據結構主義的教義問答,一個言語行為、一首詩歌和一場革命本質上是預定的結構常量的例證。“事件”的特殊性幾乎仍然是不可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索緒爾的范式捕獲了新一代人文學者的想象。在《親緣的基本結構》(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中,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借助這本著作指出親屬體系也被不可改變的二元對立所控制。叛逆的弗洛伊德信徒雅克·拉康也追隨索緒爾的指引,眾所周知地宣布“無意識是像語言一樣被結構的”。他對人格的“想象的”維度與“象征的”維度之間所做的獨具特點的區分也同樣受惠于索緒爾極具影響力的構想。在《閱讀〈資本論〉》中,路易·阿爾都塞依靠結構主義概念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主張,以便使敵對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范式陷入困境。
不過,60年代結構主義最著名的實踐者是《太凱爾》陣營與偶爾投稿的撰稿者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和《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福柯試圖描繪具有地質特征的常量或“知識圖式”(epistemes),后者構成了人類思想短暫的、不尋常表現的基礎。在這些著作中,他聲稱正在尋找與人類科學的表層實踐對向的、結構性的同源性或同構性。這樣福柯以經典的結構主義方式找到了“實證的知識無意識:這個層面雖然規避了科學家的意識,但還是科學話語的組成部分”,因為不為他們所知的,“博物學家、經濟學家和語法學家將同樣的規則應用到適合于他們自己研究的對象,來形成概念,并創建他們的理論”。①Foucault, Order of Things, p.xi.在《太凱爾》創刊最初的幾年中,結構主義實際上已經滲透到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每個學科之中。
索萊爾斯意識到結構主義方法是未來的潮流,他突然中斷了與新小說家們的聯系。到1964年秋,羅伯-格里耶及其文學同行們的名字永遠從《太凱爾》雜志上消失了。索萊爾斯說:“所有這些(新小說派)作品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極為常規的、心理的、實證性的或技術專家的。尤其是它有助于隱藏20年代到40年代之間出現的、真正的理論的革命。”①Philippe Sollers,Réponses, Tel Que, 43, Fall 1970, pp.71-76.通過把自己的命運與結構主義的巨大力量連在一起,索萊爾斯以及同仁成功地跟上了時代的發展潮流,當時新小說的“星運”開始衰退,“理論”時尚毫無異議地統治著左岸知識分子。②關于索萊爾斯命令編輯部改組的敘述,參見Huguenin,Journal。亦參見Forest,Histoire de Tel Quel,pp.174-176。
借助這一策略上重新定位的狡詐行為,索萊爾斯能夠立刻實現一些目的。他設法使《太凱爾》雜志脫離“文學貧民窟”(literary ghetto),這一策略根據10年來迫在眉睫的政治地震來看似乎是特別富有洞察力的。在與時代思潮變化的進程保持一致的情況下,索萊爾斯以及同仁當時嚴厲譴責文學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表達。文學仍局限于“‘美文’(belles lettres)概念的化約論的范圍之中,而‘美文’概念則是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產物”。③Felman,Writing and Madness,p.15.《太凱爾》信任阿爾都塞和結構主義的描述參見ffrench,Time of Theory,p.115:“在《太凱爾》中,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概念很快就開始暴露了基本缺陷……經由一種更具活力的、能量基礎的理論,這可以被視作一種結構主義批評……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一種質問或強加于主體的結構工具……主體性、過程和語言的構想不予考慮。70年代初……克里斯蒂娃和(路易-讓·)包德利……發展了意識形態概念,并將這一概念銘刻到意指實踐和主體性建構性發展之中。”
在追尋這一進程的時候,他忠實地遵從結構主義的指引。拉康通過象征階段把主體性構成描繪為是對想象界(the imaginary)或原初自戀(primary narcissism)的背離。想象界先于嬰兒6—8月時出現的鏡像階段而發生。此時孩子從模糊不清的、未充分發展的自我感中脫穎而出(拉康稱這種自我感是“破碎的身體”[the body in pieces]),以便接受一個更加統一的自我。④這一討論參見Roudinesco,Jacques Lacan,p.111:“所謂的鏡像磨難是一種嬰兒6—8月之間發生的必經階段。它允許嬰兒在空間上辨識自己、統一自我。因此,這種體驗象征著從鏡像界向想象界過渡,然后從想象界向象征界過渡……在拉康的意義上,鏡像階段是一個預示著自我進化到想象界的矩陣。”對于拉康來說,通過那經由語言進行的社會化,原始自我借助預先存在的象征的網絡實現了重構,這些象征以幾乎是永久不變的方式塑造它的命運。一位評論者說:“沉湎于象征界,主體在其中只是被表征,不得不通過話語的中介來轉譯自己,主體將變成迷失的、被引誘的,遠離了自身,并且根據他人的樣子來塑造自己。對各種典范的認同與使施加于自身的話語合理化具有很多形式,在這些形式中,主體變成穩定的,并背叛了他自己。”⑤有關拉康這一點的解釋,參見Lemaire,Jacques Lacan,p.178。Lemaire繼續寫道:“象征界……是人類異化的起因……異化是放棄自我一部分給另一個自我。異化的人生活在他自己的外圍,能指的囚徒,其自我形象的囚徒或理想形象的囚徒。他依靠他人投注到他身上的目光生存,此時他竟沒察覺到這一點。誤認與想象的生活體驗是平行的。”(第176頁)類似的是,阿爾都塞將偏離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科學正確性的資產階級思想描述為一種類似于拉康想象界的話語神秘化:一種“癥狀形成”(弗洛伊德的術語),表現了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的”無意識真理的意識形態扭曲。借助同樣的結構主義方法和程序,索萊爾斯相信文學如今可以被分析為一種手段,憑借這一手段,資產階級的自我在意識形態上被綜合了、被塑成了。
此后索萊爾斯將文學的建制視為一種學科機制,類似于福柯在70年代分析的全景監獄實踐。索萊爾斯主張文學充當了“一種手段,用以建立一系列遠勝過獨特的圖書市場的長期訓練。小說是這個社會與自身進行交流的方式,是個體必須自立以便在那里可以被接受的方式”。①Sollers, 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in Writ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pp.186-187.此外,通過追逐結構主義潮流,《太凱爾》派能夠獲得與才華橫溢的、日漸重要的一代“理論家”的合作:巴爾特、福柯、雅克·德里達、熱拉爾·熱奈特(Gerard Genette)和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②托多洛夫和熱奈特大約1968年與《太凱爾》斷絕關系,因為雜志開始了“理論恐怖主義”階段(與法國共產黨的斯大林主義開始了注定失敗的聯盟),以便建立更具學術意義的詩學。因此,索萊爾斯及其同仁在聯絡一批極具影響力和創造力的新支持者方面是成功的:求知欲極強的拉丁區學生,他們的購買力很快就創造了《太凱爾》最好的銷售記錄。③關于《太凱爾》轟動性的出版成功的詳細解釋,參見Kauppi,Tel Quel。
《太凱爾》受結構主義啟發的“理論”時尚將該雜志的形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德里達的引領下,此時的流行語變成“書寫”(écriture)。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曾聲稱要解開那種顯示人類文化超歷史真實的“編碼”一樣,《太凱爾》派相信“文本性”或“書寫”是理解歷史現在時的鑰匙。索萊爾斯及其同仁推論說,如若沒有客觀化寫作或外在化文本性的實例,那么究竟是什么社會?
批評家認為《太凱爾》派已經屈從于一種特殊的(也就是典型法國特色的)語言理想主義:相信“文本”優先于“現實”。根據索緒爾的語言構想,詞語首先與其他詞語有關,而不是與“物”有關。而且,能指與所指(它所指示的概念或觀念)的關系完全是任意的。所以,“現實”就其本身而言永遠是遙不可及的。因而,在《小說與極限體驗》(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一文中,索萊爾斯主張現實“并不顯現在任何其他地方,而是顯現在語言中……一個社會的語言和神話是決定視作現實的東西”。④Sollers, 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p.194.同樣,1966年在《文集》(Ecrits)中,拉康在融合了索緒爾和弗洛伊德之后就宣布:“正是詞的世界創造了物的世界。”⑤Lacan, Ecrits, p.65.在《寫作:一個不及物動詞》一書中,巴爾特頌揚新的認識論正統理論,他公開聲明:“是語言講授了人的定義,相反則不然。”⑥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in Language of Criticism, p.135.索萊爾斯及其同仁沒有意識到文本性的新宗教與其說顯示了現實自身的本質,倒不如說它可能顯示了左岸知識分子的文學習慣與稟性。
《太凱爾》改頭換面,轉變成一份極端結構主義的刊物,這并沒有贏得一致好評。在1963年一次題為“新文學”的研討會上(在這樣的場合中,與新小說斷絕關系是精明的),一位《世界報》記者打斷了索萊爾斯《小說的邏輯》(The Logic of Fiction)的演講,尖銳地質問索萊爾斯是否擁有某種專業的哲學訓練。①卜正民:《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書寫》,第194頁。Forest, L'Histoire de Tel Quel, p.207.漸漸地這份雜志無緣無故地被視為不可及的、難以閱讀的,它的支持者將這一點解釋為一種區分標志。詆毀者公開地譴責索萊爾斯及其他人踐行了“理論恐怖主義”:高舉“理論”,或由此使《太凱爾》的版本達到了固守教條的層次,進而驅逐或譴責那些接受不同立場或方法的對手們。甚至像福柯這樣的堅定同盟者一度被迫表達了其極端懷疑的態度:“我們60年代所見識到的、完全無情的書寫理論化無疑只是一場告別演出。經由它,作者正在為維護他的政治特權而斗爭。”②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p.127. 關于《太凱爾》“理論恐怖主義”的討論,參見Forest,L'Histoire de Tel Quel,pp.299-303 (“Le théoricisme terroriste de Tel Quel”)。福柯強烈地感覺到,一個人通過把文本性提升到毫無爭議的認識論至高無上的位置,他喪失了對現實或“事件”加以概念化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權力的運作幾乎不可能化約為“文本性”或話語的效果,它仍然是無法辨認的。在批評者的眼中,《太凱爾》派及其同盟者屈從于一種自戀的妄想:他們只是將他們先前的知識訓練的方法(法國特色的文本解釋學說)投射到整個世界。對文本性和意指的種種問題的過度關注毫無疑問是《太凱爾》沒有認真地參與政治活動及其粗魯地退出“五月造反”背后的關鍵性原因之一。正如一個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所指出的那樣,對《太凱爾》派來說,革命與其說與大街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有關,倒不如說與意指實踐的發展有關。③參見Ffrench,Time of Theory,p.119:“《太凱爾》在1968年的事件中發揮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該雜志在這個階段的革命是理論的、文本的,而不是發生在大街上。”(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沈潔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紐約城市大學教授,著有《東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革命和1960年代的遺產》(2010年)、《存在的政治》(1990年)、《文化批評的觀念》(1992年)、《迷宮》(1995年)、《非理性的誘惑》(2004年)、《海德格爾爭論集》(1992年)等著作。本文選自《東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革命與1960年代的遺產》第6章。
**董樹寶,男,黑龍江尚志人。北方工業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歐美左翼文論中的中國問題”( 15AZW0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