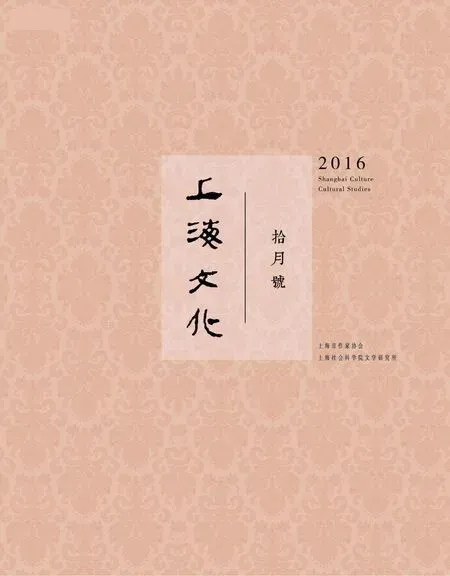美學的三種終結方式及其當代復興
宋 偉
美學的三種終結方式及其當代復興
宋 偉*
美學是一個多次被宣告終結又幾度復興的學科。從美學史上看,美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始終面臨著學科合法化的危機,在不同歷史階段被哲學、藝術和“理論”宣告終結,隨后又再度復興。搖擺于終結與復興之間,美學有時“向外轉”以依助相關學科獲得認同;有時“向內轉”以守住自律自足的理論體系。從現代性視閾看,美學是現代性建構的產物,因而,對當代美學復興來說,無論是強調政治的美學意義,還是重申美學的政治意涵,其核心的議題依然是:現代條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
當代美學 美學的終結 美學的復興 審美與政治
關于美學終結的呼聲似乎從未歇止過。與之相關,還有諸如哲學的終結、藝術的終結、文學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現代性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烏托邦的終結以及人的終結等,不一而足,此起彼伏。20世紀幾乎可以被稱為“終結的世紀”,各種各樣宣告終結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縈繞于整個世紀并一直延宕至今。大聲宣告某種事物的終結確是一件讓人非常快意過癮的事情,因為它不僅可以徑直宣判某種東西已經過時甚至死亡,還會制造出某種聳人聽聞的轟動效應以引起世人的廣泛關注。然而,事情也許并沒有那么簡單,其結果往往很難讓“終結宣判者”如愿以償。按海德格爾的理解,終結并不等同于完結,它意味著一種思想方式的斷裂中止,同時也意味著另一種思想方式的聚集與展開,意味著一種新的轉向與開端。這是因為,諸多事物并不會因不斷宣告其終結就會輕而易舉地消亡,某些事物即便看上去似乎已經終結或死亡,但幾經輪轉卻又死而復生,再度復興起來。美學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經常被人宣告終結卻又不斷死而復生的學科。幾經周折,美學在一次次被終結或宣告死亡的聲浪中不斷地調整改造、更新轉換,以死而復生的姿態迎接下一次的復興與新生。
一、美學的終結之一 ——來自哲學的宣判
美學一直面臨著被終結的危機,或者說,美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始終面臨著合法化的危機。1750年,鮑姆加通初創美學時煞費苦心地與邏輯學攀親,試圖將研究感性的美學作為研究理性的邏輯學的妹妹,以期在邏輯學大姐姐的拉扯下躋身于哲學的殿堂。雖然,經鮑姆加通的努力,美學逐漸被人們認可和接受,感性研究也開始得到哲學的注目,不再冷落寂寞,像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大家,十分重視美學并為美學的哲學建構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即便如此,康德和黑格爾在使用美學這個概念時依然充滿疑慮,顯得小心翼翼。
提到終結,我們自然會回想起黑格爾用歷史邏輯所演繹出的關于藝術終結的斷言。在黑格爾眼里,藝術不過是“絕對精神”發展的一個過渡性階段,而且,在“絕對精神”發展的最后階段,藝術成為經由宗教階段向最高階段哲學發展而必遭揚棄或終結的一個低級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宣布藝術終結之前已先行宣布了美學的終結。為此,他對美學表現出了一種耐人尋思的態度。在《美學》的開篇,黑格爾這樣寫道:“我們姑且仍用‘伊斯特惕克’這個名稱,因為名稱本身對我們并無關宏旨,而且這個名稱既已為一般語言所采用,就無妨保留。我們的這門科學的正當的名稱卻是‘藝術哲學’,或則更確切一點,‘美的藝術的哲學’。”①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4頁。黑格爾傾向于把“美學”等同于“藝術哲學”,試圖用“藝術哲學”取代“美學”這個名稱。從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說,在宣判藝術的終結之前,黑格爾已經先行地宣判了美學的終結。
其實,不僅是黑格爾,再往前追溯,康德早于黑格爾表達了對“美學”的微詞。在寫作《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年)時,康德曾表明對美學這一學科的態度:“德國人是唯一普遍地使用‘美學’這一詞語來表示其他人們所謂‘趣味批判’的人群。這一用法可上溯至鮑姆加通這位令人敬佩的分析型的思想者所做的夭折的嘗試——他試圖將對美的評判引入理性原則之下,并將該評判的原則提升至科學的層次。但是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前述的規則或標準,就其主要的來源而言,僅僅是經驗性的,因此絕不能用來決定我們的趣味判斷具有指導意義的先驗性法則。”②彼得·基維:《美學指南》,彭鋒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頁。在康德眼里,作為感性研究學科,美學僅僅屬于經驗性的,如果美學不擺脫經驗性的視域,就無法完成先驗哲學式的趣味批判。康德試圖在先驗哲學的框架內建構其“先驗感性論”(Transzendental Asthetik)——審美趣味批判。
如此說來,美學創立后經常遭遇質疑,使其不斷地陷入尷尬的境地,就連康德、黑格爾——在美學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性意義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表現出對美學的疑慮,尤其是在美學這門學科的命名問題上頗多微詞。
美學為什么會陷入如此尷尬的境地?這門學科為什么會招致像康德和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的質疑?要回答這些問題,或許應該從“美學”這個名稱入手。當年鮑姆加通將“aisthesis”(意為“感性”)改造為“aesthetica”(意為“感性學”),創立了一門研究感性認識的學問——“感性學”(中譯為“美學”)。這意味著,要將感性的東西納入理性認識的知識譜系之中,也就是說,一定要將感性的東西置入理性認識的邏輯系統中加以分析批判,才可能建立起一門關于感性或美的學問。但是,感性與理性,兩個不相容的東西纏繞在一起,這種分離和對立勢必會造成相互糾葛的尷尬局面。而這種狀況主要源自感性與理性的分離與對立,正是基于此,作為形而上學哲學家的康德和黑格爾都對美學這門學科提出了質疑。
無論是康德,還是黑格爾,之所以對“美學”這個學科命名充滿疑慮,其根本緣由來自“美學”的“感性”。也就是說,在堅固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知識譜系中,作為感性研究之學問的美學卻試圖躋身于理性形而上學的殿堂并建立一套能夠言說自身的話語體系,這不能不讓理性主義哲學家們感到不舒服。然而,伴隨人的覺醒,在高揚理性精神的時代,人的感性訴求日益凸顯,哲學家們已經無法忽視人的感性存在,面對欲望、情感、趣味、審美等諸多問題,不得不以理性的目光加以審視。他們以理性的目光審視感性,以理性的態度對待經驗,將感性納入理性所規定的框架內加以界定研究,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悖論的疑難問題。美學因此將自身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之中。
對于康德來說,這個難題就是如何以“先驗的”態度與方法研究“經驗的”問題。康德的意義在于,通過劃分科學認知、道德功用與審美趣味這三大領域,使美學終于擁有了一個可以分立于科學、道德的獨有領域,以至于人們將康德視為現代美學自律性體系的建構者。不可否認,康德對確立現代美學自律性理論體系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應該看到的是,康德所致力于的理論建構是將美學哲學化,或是將美學先驗哲學化,即形而上學化。正如黑格爾理論工作的重點是將美學哲學化——先使其成為藝術哲學,進而將藝術審美問題歸入“絕對精神”辯證邏輯運行的一個階段,最后宣告藝術走向終結。應該意識到的是,這一美學哲學化的過程,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對藝術、審美、感性的驅離或逃逸。驅離感性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等于驅離了感性具體的藝術本身,美學的哲學化日益顯露出它的傳統形而上學性。也就是說,感性經驗的驅離或逃逸后,美成為思想的對象,而非經驗的對象,美學則成為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站在今天的立場看,或許可以說,美學的哲學化或美學的形而上學化可以被理解為美學自律性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一個必須的選擇。換言之,美學自律性理論體系建構只能依附于哲學化的過程,但美學的哲學化同時也必然意味著一種他律化的過程。這樣,作為他律化的美學哲學化與作為自律化的美學理論化過程便充滿矛盾和悖論地結合為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此這般的矛盾悖論為下一輪美學的終結和藝術學的轉向預留了足夠的空間。
二、美學的終結之二 ——來自藝術的宣判
如果說美學曾經被哲學所終結或改造,那么,到20世紀,美學則可以說是被藝術學所終結或改造,具體來說,是“一般藝術學運動”——廣義的藝術學運動再度宣告了美學的終結。
19世紀末20世紀初,“藝術哲學”或“一般藝術理論”的興起,使“美學”這門學科面臨極大的挑戰。黑格爾所肇始的“美學”與“藝術哲學”差異,為在德國興起的“一般藝術學運動”提供了某些理論的征兆。十分明顯,藝術學獨立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擺脫哲學美學的束縛和制約。通常,我們一般不會太在意“美學”和“藝術哲學”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但這些看似無須經意的差異到后來卻逐漸發展成為“美學”與“藝術理論”這兩種不同學科之間的糾葛和分離,使之成為“扯不斷、理還亂”的學科爭執。
在藝術學學術史上,作為藝術學的創立者,康拉德·費德勒被后人譽為“藝術學之父”。費德勒最大的貢獻是敢于向處于居高臨下地位的美學傳統發起挑戰,并以其令人信服的推論,為藝術學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的合法性支撐。西方哲學和美學的傳統非常堅固,尤其是在具有強烈哲學思辨傳統的德國,實現突破就顯得更加艱難。費德勒曾明確闡明:“美學的根本問題與藝術哲學的根本問題有諸多不同”,因而必須改變藝術研究領域僅僅限制在美學研究領域的局面。費德勒強調藝術活動的真正本源與意義在于創造,這種創造來自人類本性所具有的純粹性、自律性和創造性,進而區分了美的普遍法則與藝術的普遍法則之間所存在的不同。①參見竹內敏雄主編:《美學事典·藝術學》(日文版),弘文堂株式會社,1961年,第77頁;掛下榮一郎:《美學要說·美學與藝術學》(日文版),前野書店,1980年,第103頁。1906年,現代藝術學作為一門學科得以正式獨立和誕生,其標志性事件是:德索出版了《美學與一般藝術學》(中譯本為《美學和藝術理論》)一書,并創辦了《美學與一般藝術學評論》雜志。②在德索的組織領導下,《美學與一般藝術學評論》在國際范圍產生廣泛影響。1913年,由德索組織發起了第一屆國際美學大會,該刊一度成為國際美學會的機關刊物,后因納粹禁止,于1943年停刊,1951年在斯圖加特復刊,更名為《美學與一般藝術學年刊》。藝術學獨立的理論訴求是要從哲學美學的襁褓中掙脫出來,并與之分庭抗禮,德索無疑也堅守這一信念。但是,他認識到,如果完全摒棄美學的哲學方式,藝術學就會變得零亂不堪,難以成為“科學”的學科。對此,站在美學與藝術之間,德索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既要劃清界限,又要互相合作。當然,劃清界限是前提,否則就喪失了平等合作的基礎。美學追問本質,因而抽象概括,容易遠離藝術;藝術現象紛呈,因而具體多樣,難以規約整合。如何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有效的聯系,“一般藝術學”或“藝術理論”就承擔起了中介的作用。他繼承并發揚了費德勒的藝術學思想,提出建立一門與傳統美學并立的藝術學科,并將其命名為“一般藝術學”。德索強調,“一般藝術學”依然屬于理論知識,而非實踐能力,它的任務是對藝術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問題進行理論化的反思,它既不同于美學,始終以藝術為直接的關注對象;又不同于藝術實踐,追求的是理論知識的科學概括性。
“一般藝術學運動”試圖擺脫傳統形而上學美學的束縛,以滿足于建構獨立自律的藝術理論的訴求。這樣的運動是與現代西方追求藝術自律精神互動相生的。簡單地說,美學終結,藝術復興;理性終結,感性復興;他律終結,自律復興。隨著各式各樣的藝術審美思潮,各種藝術流派紛紛以自律自足為堅守的陣地,形式主義、文本主義、唯美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等純藝術觀念大行其道。藝術家們以其高蹈的藝術精神構筑起一個理想純凈的審美烏托邦王國,不僅實現了從傳統形而上學美學藩籬中逃逸出離,也更進一步地從社會歷史語境和當下政治現實中逃逸出離了。
“藝術自律”是確保現代藝術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所必須堅守的基本理念,去歷史化、去政治化、去現實化等藝術自律主張為藝術家們所尊崇。本著“藝術自律”的精英主義原則,“一般藝術學運動”始終致力于劃清自身的研究邊界,并且為了標舉藝術的獨特性,藝術理論家往往希望將藝術置于“遺世獨立”的至高無上地位,以凸顯藝術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卓爾不群。但是,“全面的美學自治意味著美學主體——藝術完全地獨立在了它的宗教、科學和社會政治經濟功用——例如藝術市場之外。自治思想給予美學自治一個范圍,它當然是自治的,但是也是局限于自我的、封閉的、與其他人類活動隔離的、與日常生活隔絕的”。①馬克·西門尼斯:《當代美學》,王洪一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第16頁。在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精英主義原則指導下,藝術學理論為自己劃定了嚴格的研究邊界,越來越陷入自身的圈限和“畫地為牢”的局限。逃離了傳統美學的束縛,藝術史、藝術家和藝術品研究也越來越從宏觀向微觀轉型,對藝術文本的闡釋、藝術形式的關照、藝術符號的專注、藝術史料的實證,逐漸成為一般藝術學理論或藝術史論所熱衷研究的議題,而藝術的人文精神內涵、藝術的社會歷史意義、藝術的文化價值取向等重要的問題,則逐漸地被忽視。
在“藝術自律”或“藝術自治”精英主義原則指導下,藝術學研究必然出現“向內轉”的理論取向,其研究視野也越來越向自身內部收縮,逐漸分割切斷了藝術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內部研究”的局限性也逐漸暴露出來。藝術學取代美學的理論后果是,人們對宏觀的歷史的以及社會的等相關問題不再感興趣,而是潛心于具體技藝層面來研究藝術。
三、美學的終結之三 ——來自“理論”的宣判
如果說,藝術學是以一種向內轉的方式,拒斥美學的形而上學哲學化,以解決美學脫離具體藝術經驗的弊端;那么,理論則是以一種向外轉的方式,凸顯鮮明的“反美學”姿態,改變了藝術自律設定的自我封閉局面,使美學消融在無限擴大的批評理論邊界之中。
眾所周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學理論、美學理論都經歷了一場理論話語建構或擴張的過程,以至于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理論話語——“理論”或“批評理論”,形成了所謂的“理論的帝國”時代。我們擁有了一種叫“理論”的寫作方式,它廣涉哲學、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文學、美學、政治學、倫理學,但又很難歸于某一種學科話語,正如詹姆遜所概括的那樣,“我們日漸擁有一種簡單地稱為‘理論’的寫作,它同時既是上述所有話語,又絕非上述任何一種話語”。②程朝翔:《理論之后,哲學登場——西方文學理論發展新趨勢》,《外國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這種綜合性強、涵蓋性廣、跨學科多的新的理論話語或批評理論,幾乎消滅了所有學科之間的界限,成為統攝所有人文學科的思想方式、話語方式和研究方式。這一理論帝國的建構以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語言學、符號學、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話語敘事、身體理論、新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理論話語建構為特征,突破了傳統文學和美學的研究邊界,無限擴張、延異、播撒。
進入21世紀,理論由鼎盛時期走向衰落,理論帝國大廈開始搖動甚至崩塌,“理論的終結”、“理論之后”、“后理論時代”等呼聲日漸增多。2003年,美國著名理論雜志《批評探索》推出了一系列文章探討“理論的危機”,主編米切爾向編委會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其中關涉到美學等問題:“理論輝煌的時期是否已成為過去;理論是否喪失了其革命的意義,正經歷著向關注倫理、美學和關心自我的轉向。”①王曉群主編:《理論的帝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中甚至不無幸災樂禍地描述了“理論之后”的衰敗癥候。無論如何評價這一“理論帝國”時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理論話語的建構導致了傳統學科邊界的消失。“20世紀80年代中期理論熱衷對‘理論’(主要是哲學、心理分析、女性主義、文化理論,而不是文學理論)的依賴,在一些人看來似乎起了一個更闊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這正是產生問題的核心所在,因為強制人們參閱理論經典或‘最新的事物’可能讓人感到是對文學研究正業的一種偏離,一種令人畏懼的、受到挫折的偏離,或者是一種時髦的偏離。”②塞爾登等:《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劉象愚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27頁。宏闊的理論話語消除了不同學科之間的話語障礙,同時也消除了不同學科所具有的各自特色,原來意義上不同學科的中心研究議題被“理論”的無限擴張性所擠壓以至驅逐。
在理論時代,“美學有個壞名聲,幾乎每年都有新書宣布美學已經過時,或者宣布美學的壞影響無法消除”。③程朝翔:《理論之后,哲學登場——西方文學理論發展新趨勢》,《外國文學評論》 2014年第4期。在“理論”稱霸的“理論帝國時代”,美學同樣被無限擴張的“理論”所擠壓或驅逐,有人曾基于“理論帝國時代”的來臨而提出“反美學”的主張。④福斯特:《反美學:后現代論集》,呂健忠譯,臺北:立緒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或許是對這種現象的反撥,在“理論之后”的“后理論時代”,人們開始提出“美學的回歸”,甚至有些學者提出了“美學的復仇”。新世紀之初,一本名為《美學的復仇》的論文集出版,而所謂美學的復仇可以被理解為對理論帝國統治的復仇。⑤Michael P. Clark, Revenge of the Aesthetic: the Place of Literature in Theory Today, Berkeley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正是這種美學回歸或美學復仇的情勢構成了當代美學復興的基本學術語境。
眾所周知,作為西方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美學的基本問題始終難以擺脫形而上學的困擾,成為傳統形而上學命題在美學方面的解答,如建基于西方本體論哲學基礎之上,美學的基本問題長久以來被規定為美的本體或美的本質的追問。也就是說,在傳統形而上學的哲學本體論的規定下,美學的基本問題只能是本體論的或本質論的問題。以至于一直到今天我們依然需要解除傳統美學的形而上學迷霧。解除傳統美學的形而上學迷霧的目的何在?其目的就是為彰顯美學的現代性意義,而美學現代性意義的彰顯無疑也就是美學當代性意義的彰顯。
我們應該從何種層面上來闡釋美學的現代性或當代性的意義?我想,應該從現代境遇中人的發展的角度來反思和闡釋美學的現代性或當代性意義。從西方現代性歷史語境看,美學學科的建立實質上是一個現代性現象。也就是說,美學的興起,實質上是為了回應現代化進程中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其實質也就是理性祛魅之后的現代社會危機和現代人的精神困境。按照韋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理解,現代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的祛魅過程。當現代理性祛除掉宗教的價值信仰之后,整個社會逐步被工具理性精神所浸染,逐漸編織成理性的鐵籠,致使冰冷客觀的工具理性、技術理性、計算理性成為全面組織整合社會的規則。“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人的精神世界、價值信仰、情感家園在這一理性化的過程中趨于格式化、計算化、同一化、荒漠化。面對“上帝之死”的現代性困境,西方世界試圖通過藝術審美來拯救,這就有了所謂的審美救贖。這一點在德國古典美學思想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康德在完成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之后,進行了審美趣味的批判——即判斷力批判,在宗教祛魅之后的分化世界里追問“我能知道什么”、“我應該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而這三個追問最終的指向則是“人是什么?”也就是說,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的美學思想旨在探尋現代分化世界中人的幸福與自由問題。如果說康德的美學還帶有強烈的哲學形而上學色彩,那么,在席勒那里,美學及其審美教育則更為明確地凸顯其審美拯救的社會功能,《審美教育書簡》亦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解決現代政治問題的策略方案,即通過審美向現代人許諾自由解放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美學的回歸并不應被理解為回歸自主性、自律性的傳統美學,因為美學的當代回歸,并不是向內轉向的回歸,并不是向美學自身的回歸,而是以美學為原點向外轉的回歸,這一點是理解“后理論時代”或“理論之后”的美學回歸的關鍵。所有的一切似乎又應和了黑格爾的螺旋式上升的怪圈。這種新的美學回歸表現為美學的倫理學轉向、美學的政治學轉向、美學的政治經濟學轉向等。這里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不能將當代的美學回歸理解為回到傳統意義上的美學自主性的回歸,即此一回歸并非向內轉的回歸,并非是向美學自身的回歸;二是此一向外轉,并不是將倫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觀點外在地強加于美學,而是以美學為原點重新闡釋倫理、政治、經濟和文化。以阿倫特的政治美學為例,在阿倫特晚年著作《康德政治哲學講稿》中,她試圖重新闡釋康德審美共同感的政治學意義,試圖建立一種感性的政治共同體,賦予審美為政治立法的根基。阿倫特徹底顛覆了以往對康德美學的無功利性解讀,在康德美學中發現政治哲學的感性奠基。在阿倫特看來,與政治判斷一樣,審美判斷也在做出決斷,而且,審美判斷的決斷比政治判斷的決斷更具有優先性。因為,這種“藝術和政治的共同要素在于,二者都是公共世界的現象”。“正是共同感覺/常識讓人能夠把自己定位在公共領域之中,也就是定位在一個共有的世界之中。”應該說,阿倫特開辟了一種當代意義上的全新的政治美學,這種政治美學不是靠審美自律后遠離政治來實現的,不是靠審美與政治的分離或對立來實現的,它試圖將重新找尋政治的原初點,而這一原初點不在理性的強制性規范之中,而在感性的審美共通感之內。阿倫特大膽地設想:一個通過感性來立法的現代政治是否可能?感性、審美、自由、解放,這無疑是美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所有這些難道不也是現代政治所應該致力于追求的理想境界嗎?從此意義上看,福柯晚年所倡導的“自我關懷的倫理學”、朗西埃所關注的“感性的分配”的政治學等當代美學的政治倫理議題,都在新的意義上重申了美學與政治、美學與倫理、美學與社會的關系。誠然,無論是政治的美學意義,還是重申美學的政治意涵,所有的一切都在探尋一個重要議題:現代條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
責任編輯:沈潔
*宋偉,男,1957年生,山東長島人。哲學博士,東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學與藝術學理論。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資本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