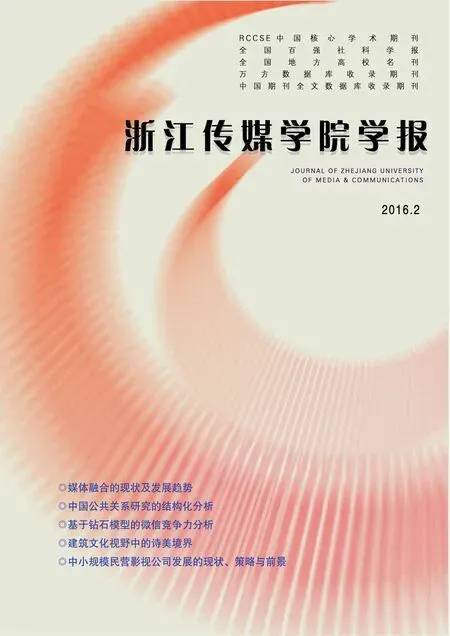3D電影:審美經驗的知覺現象學變革
曾 勝 王娟萍
?
3D電影:審美經驗的知覺現象學變革
曾勝王娟萍
摘要: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強調人的行為環境,主張以身體意向性取代傳統的意識意向性,人通過身體知覺把握世界,從而克服身心之間的二元對立矛盾。知覺現象學與數字美學之間存有一種緊密的對應關系,能夠深入揭示由數字技術引發的審美經驗變革。3D電影最突出的審美經驗就是通過身體進行“審美介入”,受眾的知覺置于理性與經驗兩種秩序的相交處,從而以一種知覺現象學的審美經驗取代傳統的無功利審美,實現電影審美經驗的統一。
關鍵詞:3D電影;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審美經驗
3D電影正在當下世界影壇掀起一場視聽風暴。2009年,20世紀福克斯出品的科幻電影《阿凡達》成為有史以來制作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3D電影。該影片預算超過5億美元,成為電影史上預算最高的電影。3D電影的熱潮推動全球電影產業格局發生巨變。以中國為例,不但一批優秀的影視、動畫工作者紛紛投入到了3D電影的制作,開創了國產3D電影的先河,而且3D電影熱潮還使中國3D銀幕數量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增至兩千余塊,成為緊隨美國之后的全球第二大3D電影市場,占全球1/5的份額。與此同時,3D電影也帶來了一場電影審美經驗的巨大變革,其“沉浸式”的觀影體驗迥然有別于傳統電影的接受模式,日新月異的3D數字技術為電影的“視覺奇觀化”再添濃墨重彩。正如影像媒體研究專家肖恩·庫比特教授在《數字美學》一書中所說:“當代特技電影的成功是敘事時空勝過敘事的成功……對于被加速的消費者來說,有了這樣的敘事時空,意味著可以通過媒介與交互式游戲,更積極地參與敘事的生產。……如果說所有電影都是特技,那么特技電影就是電影中的電影,是一種在震驚時刻把否定變成肯定的電影。”[1]
3D電影實際上就是立體電影(anaglyph),主要利用人雙眼的視角差和會聚功能制作而產生立體效果,因此,3D電影主要是在知覺領域帶來了一場電影審美經驗的變革。法國著名哲學家梅洛-龐蒂創立的知覺現象學,在知覺、身心融合、人與自然以及當代藝術(包括電影)的意義與語言等問題上極具創見,其知覺現象學不但與西方現代藝術遙相呼應,而且在數字化技術方興未艾的今天,也同樣具有巨大的理論價值。本文擬運用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從知覺、身體和環境三個角度對3D電影所引發的審美經驗變革作出深入闡述。
一、“電影不被思考,它被感知”:3D電影的知覺現象場
現象學以“回到事物本身”為宗旨。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扭轉了科學理性對于實際經驗和生活世界的忽視,確立了知覺在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讓純粹意識化、超然客觀的科學自然回歸到人所寓居的生活世界中來。梅洛-龐蒂認為是知覺經驗維持了我們與世界的某種原始關系,并彰顯出生命的真正意義。這種強調身心一體、人與人、人與自然共鳴交織的知覺經驗是西方現代藝術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梅洛-龐蒂在其理論巨著《知覺現象學》中廣泛引用巴爾扎克、普魯斯特、瓦萊里、蘭坡、波德萊爾、塞尚等現代藝術大師的作品,以此證明人是作為中介或紐帶的某一具體處境中的人,我們周圍的整個生活世界就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現象場,是一個主客交融、物我一體的世界。在梅洛-龐蒂看來,知覺是與生命活動聯系在一起的行為,所謂“現象學還原”就是要回到生活世界的現象場,回到知覺活動與知覺對象的相互作用場。物期待著我的介入,我因物而不再無根地漂浮。我們通過我們自己不同的感官綜合地感知這個世界,我們所有的知覺形成一種統一的聯覺,并最終獲得一種知覺經驗。“知覺首先不是作為人們可以用因果關系范疇來解釋的世界中的一個事件,而是作為每時每刻世界的一種再創造和一種再構成。……我們有一個當前的和現實的知覺場,一個與世界或永遠扎根在世界的接觸面,是因為這個知覺場不斷地糾纏著和圍繞著主體性,就像海浪圍繞著在海灘上擱淺船只的殘骸。一切知識都通過知覺處在開放的界域中。”[2]
梅洛-龐蒂對電影關注有加,《電影與新心理學》*梅洛-龐蒂于1945年5月13日在巴黎法國高等電影學院發表題為《電影與新心理學》的演講,后此文收入其1948年出版的文集《意義與無意義》中。該文目前尚無中文譯本,國內相關研究可參見楊大春.感性的詩學: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另外還可參考張穎.一種視覺格式塔:論梅洛-龐蒂的電影美學[J].法國研究,2010(2)2中的相關論述。就是他的一篇運用知覺現象學分析電影藝術的重要論文。梅洛-龐蒂的電影美學理論主張人們拋棄認知心理學和行為主義心理學這兩種傳統心理學在身心二分方面的成見,轉而從新起的格式塔心理學中吸取靈感,因為格式塔心理學在身心統一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人的諸心理能力在任何時候都是作為一個整體活動著,一切知覺中都包含著思維,一切推理中都包含著知覺,一切觀測中都包含著創造。”[3]梅洛-龐蒂將格式塔心理學與知覺現象學結合起來,創立了自己的“新心理學”。梅洛-龐蒂在這篇論文中引用了電影大師普多夫金著名的“面部表情”試驗和經典歌舞片《雨中曲》等例子,認為電影作為一種視聽藝術,并非簡單地將視覺藝術和聽覺藝術相加,而是作為一種格式塔式的結構性整體,其每個部分的意義必須依據它與整體的關系才能得到理解。電影作為一種時空性的感性表達方式,其視聽語言并不服務于電影要表達的觀念(意義),而是通過構成各個層面的有節奏的知覺格式塔,將某種觀念蘊含于自身,因此,電影是與它的節奏合為一體的。梅洛-龐蒂的這種新的意義理論顯然凸顯了視聽主體(觀眾)在知覺現象學上的作用。正如梅洛-龐蒂在文中所說:“現象學哲學或者存在哲學的一個漂亮部分就在于:驚奇于自我的這種內在于世界,自我內在于他人,驚奇于向我們描述這種悖謬和混亂,驚奇于使主體與世界、主體與他人的聯系被看到,而不是像古典派所做的那樣,通過訴諸于絕對精神來解釋之。于是,電影尤其易于使精神與身體、精神與世界的統一顯現出來,并使一個表現在另一個之中。這就是批評家針對電影可以援引哲學而不足為怪的原因了。”*梅洛-龐蒂.意義與無意義[M],法文版,1996:74。中文譯文轉引楊大春.感性的詩學: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3。梅洛-龐蒂的電影理論集中體現了他的現象學美學的核心思想,并在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的代表性人物讓-呂克-戈達爾那里得到積極的回應。
3D電影是由從類似人兩眼的不同視角攝制的具有水平視角差的兩幅畫面組成,放映時兩幅畫面重疊在銀幕上而呈現雙影,通過特制眼鏡或幕前輻射狀半錐形透鏡光柵,觀眾左眼看到的是從左視角拍攝的畫面、右眼看到的是從右視角拍攝的畫面,由于人的雙眼具有會聚功能,所以最后合成為立體視覺影像。于是,觀眾看到的影像好像有的在幕后深處,有的脫框而出,仿佛伸手可攀,給人以身臨其境的逼真感。在電影《阿凡達》中,3D技術使觀眾產生了一種類似真實環境的存在感,人們麻木已久的知覺被喚醒,視覺奇觀激發了觀眾無窮的好奇心,他們和3D影像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審美知覺現象場。
二、肉身化主體:3D電影的身體意向性
“身體是我們擁有一個世界的一般方式”,[2](194)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實際上可以概括為身體現象學。梅洛-龐蒂認為身體具有某種主客一體、心物交融的特征,是某種介于物化和靈化之間的東西,一切意向最終都歸于身體的意向,“必須表明:身體沒有意識是無法想像的,因為存在著一種身體意向性,意識沒有身體是無法想像的,因為現在是有形的。”*梅洛-龐蒂.意義與無意義[M],法文版,1996:74。中文譯文轉引楊大春.感性的詩學: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7。梅洛-龐蒂的身體意向性實際上是強調一種“肉身化主體”,主體的一切都建立在身體行為、身體經驗或知覺經驗基礎之上。梅洛-龐蒂用身體意向取代了自笛卡兒以來一直受到強調的意識意向性,用身體主體取代了意識主體,有力地克服了自笛卡兒以來占據西方主流思想的心“尊”身“卑”的身心二元論。
身體意向性代表的是一種全面意向性,它是由意向活動的主體(身體)、意向活動(運動機能和投身活動的展開)和意向對象(被知覺世界:客體和自然世界,他人和文化世界)共同構成的一個系統。梅洛-龐蒂借用心理學家常用的身體圖式概念來說明人的身體所具有的一種格式塔式的空間圖式功能,從而確保了身體意向性的統一結構,而被知覺世界則是諸種意向性獲得實現的“場所”。梅洛-龐蒂以人們熟知的傳統精神病學中的“幻肢”現象,以及雙眼的“復視”和雙手、雙耳的協調活動為例,說明人的身體是一種“現象身體”,它具有身體圖式結構的整體性功能。因此,身體意向性決定了身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身體不是各自占有空間的或被拼湊在一起的器官總和,而是寓居于某一空間中,具有一種整體性結構和協調功能。身體總是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中參與某種關于存在的籌劃,我們對世界的綜合感知不是由知性來完成,而是被賦予身體。“靠著身體圖式的概念,身體的統一性不僅能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描述,而且感官的統一性和物體的統一性也能通過身體圖式的概念來描述。我的身體是表達現象的場所,更確切地說,是表達現象的現實性本身。……我的身體是所有物體的共通結構,至少對被感知的世界而言,我的身體是我‘理解力’的一般工具。”[2](300)
身體意向性表明人的生存與其生存處境密切相關,我們始終根據情境的變化并通過我們的身體調整我們的在世存在方式,我們身體的或姿勢的圖式每時每刻都在為我們提供關于我們的身體與事物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們對這些事物的一種全面的、實際的和暗含的觀念。因此,身體遠非一件用具或手段,它是我們在世界中的表達,是我們意向的可見形式。真正的身體圖式與處境的空間性相關,也就是說,空間就是我們的生存領域和生存視閾。我們并非僅僅依靠客觀空間生存,相反,客觀空間只是我們生存的前提條件,必須融入身體意向性才能構成我們完整的存在現象場。由于意向與身體運動相結合,正常人的身體具有建構(投射)能力,能夠主動積極地應對新的情境。通過投射或建構能力,正常人在知覺與被知覺世界之間建立起一種意義關系。“在知覺中,我們不思考對象,我們不認為自己是有思維能力的人,我們屬于對象,我們與身體融合在一起,而這個身體對世界、對動機和人們得以對世界進行綜合的手段的了解超過了我們。”[2](304)梅洛-龐蒂的身體意向性理論,實際上是知覺現象學對一種新的空間類型的呼喚:世界成為身體的作用場,甚至是身體的延伸。身體意向性彰顯了現象場或行為環境的概念,突出了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
身體意向性表現在3D電影中就是其突出的“沉浸式”觀影體驗。“銀幕身軀和形象的力量驅動著敘事、表述系統、話語、需求、欲望、影片的情感和觀眾。”[4]3D電影將知覺置于心靈和身體兩種秩序的相交處,強調了受眾行為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這種身體的“介入意識”作為一種新的知覺經驗引發了一場電影的感性學革命,超越了傳統的刺激-反應電影知覺模式。3D電影的受眾以一種參與的姿態介入藝術對象或環境,推動了現代審美觀念由無利害的靜觀模式向欲望的介入模式進行變革。較之其他藝術,3D電影幾乎是完全知覺性的,能夠更直接地對經驗的諸純粹層面進行協調運作,從而創造一個屬于它自己的令人信服、引人入勝的現實世界。3D技術使二維的電影圖像轉化為三維的知覺經驗場,并通過身體進行多感官的、肌肉運動的知覺綜合(聯合),使3D電影的受眾進入一種徹底的審美介入狀態,“電影并不創造現實的影像,它并不產生幻覺,因為電影實質上完全控制了經驗的條件,它能夠創造完整的知覺事實。這鼓勵了一種徹底而深刻的參與,觀眾可能很容易接受電影的世界,完全進入他的它的領地。”[5]3D電影《阿凡達》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3D的視覺盛宴,無論是漂浮于空中的哈里路亞山,還是在翱翔于天地間的飛龍,抑或像水母一樣蕩漾的樹精靈,無不是通過我們的身體向3D影像投入,從而與被知覺世界共同構成的一個審美知覺系統。
三、“野性世界”:3D電影的行為環境
受笛卡兒理性主義影響,西方哲學長期存在科學理性世界與知覺感性世界之間的二元對立矛盾,甚至盲目抬高知性世界而貶低感性世界。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卻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知性的世界,只存在著感性的世界,神秘的自然才是我們生存的真正根基,而非我們認識的對象。他用“野性存在”和“野性精神”來概括自然,其哲學目標就是要為我們建構一種拷問世界之為世界,探討人類文化本質的“感性存在論”。在梅洛-龐蒂看來,世界意味著在科學理性后面尚未被馴服的野性自然,它是一種前科學的、前理論的和前客觀的世界。為了回到這種野性的自然,就必須對理智主義、科學客觀主義進行深入的清理,就必須借助于身體意向性來超越純粹意識意向性,從而進一步恢復感性知覺的地位。這樣,介于靈與肉之間的現象學身體就能夠幫助我們向事物開放,幫助我們揭示出世界的原初秩序。總之,自然最終應該在知覺主體與被知覺對象的原始關系中涌現出來,“存在一個自然界,但不是科學的自然界,而是知覺向我們揭示的自然界。”[2](541)這個前客觀的野性世界,通過身體知覺(肉身化主體或肉身化心靈)而被體驗到,世界就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的一個存在“現象場”。
梅洛-龐蒂為此提出了“行為環境”這一概念,認為不管人還是動物,其行為都與一定的環境相關,這種環境并非指單純的地理環境,同時還包含有意識,是知覺者和知覺對象的相互作用域,是進行知覺者與他的身體、與它的世界的一種活的關系。“行為環境”概念的提出,是對理智主義的客觀世界和經驗主義的自在世界的雙重否定,它取消了刺激—反應模式和理想的建構—判斷模式的對立,強化了人或動物與自己周圍世界的生存關系。梅洛-龐蒂以足球場為例,認為足球場雖是一個地理環境,但對活動的球員而言,足球場卻又并非一個客觀的外在“對象”,因為足球場遍布各種可見與不可見的、與比賽規則密切相關的“線”,它們既制約著球員的身體意向也實現了球員的行為價值,球員與球場是融為一體的,球員的每一個動作都瞬間改變了球場上的所有存在關系,并隨即形成一種新的現象場,所以,球場是一個球員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現象場。梅洛-龐蒂的“行為環境”是一種具有濃郁結構主義特征的存在論觀點,他以此強調環境的整體性、混雜性和綜合性,強調主客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世界不是分裂的、支離破碎的,而是具有某種原初的統一性,梅洛-龐蒂所追求的“重返事物本身”,實際上就是重返這個神秘的前客觀、前科學和前理論的知覺世界。
梅洛-龐蒂的“行為環境”強調空間是一種身體綜合能力,是超越經驗主義和理智主義的“第三空間”。梅洛-龐蒂還以“深度”這種常見的視覺現象為例,說明被知覺世界與感性身體之間的緊密關系。他認為深度不能通過經驗的或知性的方法進行分析而得到,相反,深度與身體的整體性結構相關,深度不是出于精神審視,而是源于身體經驗,“深度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先驗的主體的思維,而是被理解為一個置身于世界的主體的可能性”[2](339)。一個活的身體與一個活的世界相呼應,世界與知覺經驗而非知性判斷相關,世界因此恢復了她的神秘。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是一種蠻荒原始的存在,是海德格爾所謂“天、地、神、人”的交織。梅洛-龐蒂以一種含混的姿態超越了意識—客體的二分,讓世界恢復了神秘和復雜性,讓人充滿了活力,這種“新感性論”的最終目標當然是為了克服科學理性所導致的存在焦慮和哲學危機。
梅洛-龐蒂的“行為環境”理論在美學家杜威那里得到共鳴。杜威也主張從經驗自然主義的視覺來看待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他批判了二元論哲學將世界與精神、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人與動物一樣,只是一個“活的生物”(live creature)而已,動物沒有主客體意識,它們與自身的生存環境是結合在一起的。人是環境的一部分,環境也是人的一部分,人與環境相互依存。杜威認為美學不應該從公認的藝術作品出發,而是要繞道而行,從“活的生物”出發,因為在動物的活動中,“行動融入感覺、而感覺融入行動”,[6]所以在動物身上可以找到一種經驗的直接性和整體性,只有這樣才能把握審美經驗的源泉。杜威所說的“審美經驗”超越了二元論,這種審美經驗既包括環境作用于活的生物的“受”(undergo),也包括活的生物作用于環境所產生的“做”(do);經驗并不只有被動的一面,也有主動的一面,經驗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杜威認為人具有獲得完整經驗的內在需求,只要具有自身的整一性,只要經驗獲得完滿發展,就有可能獲得一個具有一定審美性質的經驗。杜威在其《藝術即經驗》一書中批評了康德美學的無功利態度,認為“審美的敵人既不是實踐,也不是理智。它們是單調;目的不明而導致的懈怠;屈從于實踐和理智行為中的慣例。”[6](40)
方興未艾的3D電影作為一種“行為環境”,極大地打破了傳統電影的審美慣性,為我們創造了一個“野性世界”,它是一個恢復了人的生存活力的“第三空間”。當觀眾面對《阿凡達》影像中虛擬的潘多拉星球、智能生物納威人、半植物半動物的生命體、與人通過觸須相連而交換信息的異獸時,他們身上無不洋溢著壓抑已久的生命活力。此時此刻,他們感性飛揚,身處一種“野性世界”。3D電影的受眾正是在全方位的感官介入中,重構了自我與世界的關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認知與體驗,并借此與真實世界溝通與互動,最終享受到一種類似于高峰體驗的快感。
四、結論:3D電影的“審美介入”
巴贊認為電影發展的原動力往往并非科學發現或工業技術的進步,而是人們對“完整電影”神話的不懈追求。3D電影無疑代表了迄今為止“完整電影”的最高水準,但是,3D電影帶來的絕非只有虛擬技術和商品生產的新邏輯,3D電影強烈的即時性感官體驗,還使其具有了知覺現象學或曰身體現象學的諸多審美特征,引發了電影審美經驗的一場巨大變革。3D電影一改康德無功利的靜觀式審美范式,轉換為消解審美距離、解除情感控制、完全沉浸到欲望影像之中的審美新范式。3D電影(以及呼之欲出的4D電影)對身體知覺以及聯覺的要求,表明電影正在日益彰顯一種感性的力量,身體感知在審美經驗中的關鍵作用日益突出。3D電影實際上也是對麥克盧漢的至理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最好闡釋,在這個不斷由新媒介技術所重構的世界里,我們必須對作為首要媒介的身體進行重新評估,對其產生的身體美學進行新的認識。
3D電影最突出的審美經驗就是通過身體進行“審美介入”(aesthetic engagement),“梅洛-龐蒂在關于知覺作為一個綜合體的討論中,對審美投入作了進一步的論述,這種綜合體在我們對對象的感覺把握中達到了一致和統一。這樣一種綜合體包含了‘作為知覺和行動領地的身體’,但超越了直接感知到的東西,而達到一個整體,即最終作為世界本身的一種完整性。在關于‘看’的描述中,梅洛-龐蒂將這種身體介入的觀點延伸到藝術。”[5](30)3D電影的受眾以參與者的姿態介入藝術對象與環境,人與3D影像共同構成一個連續的、整體的和互動的審美知覺現象場。3D電影為我們帶來了一場知覺現象學的電影審美變革,它直接挑戰了孤立、靜觀的傳統審美無利害學說,走向一種審美經驗的統一。3D電影豐富了我們的審美生活,代表了電影審美理論的新方向,是科學技術發展、社會文化變革和人的知覺能力拓展這三者共同建構的新的審美情境。
參考文獻:
[1][新西蘭]肖恩·庫比特.數字美學[M].趙文書,王玉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25.
[2][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66.
[3][美]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引言5.
[4][英]帕特里克·富爾賴.電影理論新發展[M].李二仕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83.
[5][美]阿諾德·貝林特.藝術與介入[M].李媛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55.
[6][美]杜威.藝術即經驗[M].高建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8.
〔責任編輯:華曉紅〕
中圖分類號:J9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552(2016)02-0098-05
作者簡介:曾勝,男,副教授,文學博士。(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王娟萍,女,副教授,文學碩士。(浙江金融職業學院國際商務系,浙江杭州 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