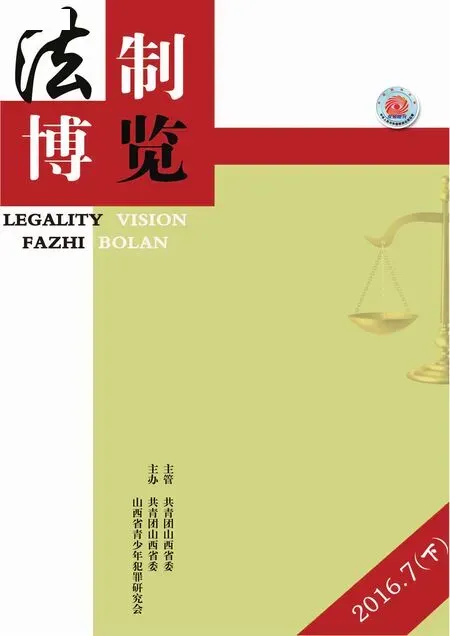對代言廣告名稱的再認識
崔鳳琴
貴州師范大學,貴州 貴陽 550001
?
對代言廣告名稱的再認識
崔鳳琴
貴州師范大學,貴州貴陽550001
新《廣告法》已于2015年4月應運而生,該法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有些地方的規定仍然有待考量,比如利用代言人為商品或服務做廣告的行為,在學術上名稱繁多且雜亂。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將介紹代言廣告的特征、本質、功能,并以此為基礎分析我國代言廣告名稱的現狀及問題,并提出相關完善建議。
代言廣告;名稱規范;建議
一、代言廣告概述
(一)代言廣告的概念及特征
雖然我國《廣告法》并沒有對代言廣告的概念進行規定,但是該法在第2條第5款中對廣告代言人作了規定:本法所稱廣告代言人,是指廣告主以外的,在廣告中以自己的名義或者形象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通過上述對廣告代言人的規定,那么什么是代言廣告也就一目了然。
代言廣告具有廣告的一般特征之外,還具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一般特征如下:(1)有償性。(2)廣告具有傳播效應,是信息得以傳播的一種方式。(3)廣告媒介的多樣性。不僅包括傳統的媒介形式,還包括新型的媒介形式:微信、QQ等社交平臺。(4)廣告的目的性、計劃性。(5)受眾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代言廣告的特殊之處在于在廣告中加入了代言人,利用代言人的名人效應或者代言人的表演來凸顯廣告的效果。
(二)代言廣告的本質
筆者粗淺的認為,廣告的本質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代言廣告的本質亦包括在內。從表面來看,廣告是一種宣傳手段,是信息傳播的方式。根據廣告的傳播效應可知,廣告的傳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絕大多數廣告都需要一個過程才能看到效果,在傳播的過程中,廣告也就具有了“自我凈化”的功效——垃圾廣告、虛假廣告因經不起考驗而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直至逐漸失效、淡化、消失。因此從應然來看,虛假廣告等垃圾廣告并無生存空間。
從更深層次來看,廣告的實質是一種工具——廣告是廣告主為達到預期目標的工具。廣告主在投入廣告費時,總是會有理性的投入—產出分析,并且預期上產出的價值總是大于投入的價值。為實現廣告的工具作用,廣告主會對廣告進行設計,并期待廣告行為能誘導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并促使消費者實施有傾向性的消費行為,這也是成功廣告的內在屬性和要求。
代言人在代言廣告中的作用就是一種效果更為顯著的宣傳手段,同時基于代言人的名人效應,消費者會將對代言人的喜愛、信賴等轉嫁到對商品服務的喜愛、信賴上。[1]對于實現廣告主的預期目標而言,代言人是一種效果更佳的“工具”。因此代言廣告的本質仍然是一種宣傳手段,是實現廣告主目標的工具。
(三)代言廣告的功能
代言廣告本身是個中性詞,并無褒貶之分。因此筆者認為代言廣告的功效是正面的亦或是負面的完全取決于代言廣告前面的定語,即修飾詞。只是基于代言人的加入,代言廣告會使廣告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更加明顯,甚至會加劇這兩種效果的兩極分化的格局。
代言廣告的正面功能筆者在此不再贅述。主要是其負面效果不容忽視:對企業而言會形成惡性競爭,嚴重者甚至會觸及法律構成不正當競爭或壟斷;對消費者而言,會誤導消費者的消費決策,缺陷產品或服務甚至會帶來人身安全隱患;被虛假廣告所錯誤指引購買了預期之外的商品或服務,在經濟學上這本身就是一種浪費。對整個社會而言,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影響價值規律的正常發揮。
(四)代言廣告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目前關系代言廣告的研究還不是很成熟,尤其是代言人代言廣告這一行為的名稱問題,用法繁多且混亂,尚未形成一致的認識,且名稱和相對應的行為并不統一,筆者在下文中將就這一問題進行淺顯的論述。
二、關于我國代言廣告名稱的規范問題
(一)我國關于代言廣告用語的學術爭論及辨析
關于代言人代言廣告行為的學術名稱,我國臺灣地區一般稱之為“鑒證廣告”,該行為的名稱在我國大陸使用混亂,名稱各異。主要有以下幾種用法:“代言廣告”、“推薦廣告”、“證明廣告”、“證言廣告”、“薦證廣告”等,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
“推薦廣告”存在明顯的不足,其不能概括此類廣告的全部內涵,其范圍太過狹窄。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代言人在廣告中并沒有自己獨立的“話語權”和“意思表示”,其廣告詞由廣告主預先設定好,是廣告主的意思表示。因此代言人并不是基于自己真誠的推薦而獲利,也就不存在代言人“推薦”一說。
“證明廣告”、“證言廣告”亦不合適。證明、證言一般意味著代言人所陳述的即為該商品或服務的真實情況。即使新《廣告法》第38條中對代言人的審查義務規定為:“使用商品”或“接收服務”,但是這樣的“使用商品”或“接收服務”無論如何也不能與“證實商品或服務的功效”劃等號。此外代言人是否具有證明的能力或資格還有待考量。
“薦證廣告”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薦證廣告反映了立法者對代言人“擔保”和“推薦”的立法初衷。如果不考慮我國的本土資源,貿然使用“薦證廣告”的用語,其結果只能是水土不服。就目前而言,與其說代言廣告在靠產品的質量說話倒不如說是靠代言人的影響力說話。因此,“薦證”二字與我國的實際情況背道而馳。
筆者認為“代言廣告”比較符合我國的本土情況。理由如下:(1)《現代漢語詞典》將“代言人”的定義為:為一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社會組織的利益說話的人。[2]在利益的驅使下,許多代言人已經淪為虛假代言的工具。[3](2)代言人要想順利獲取代言費,或多或少的要期盼廣告有良好的效果并為廣告主創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言人和廣告主利益訴求是一致的。(3)有“代言”很容易想到“代理”,在某些地方二者也有共通之處。鑒于廣告主與代言人的勞務關系,同代理一樣代言人行為的后果也應由廣告主承擔。(4)“代言”在我國廣告實踐中有深厚的使用基礎和用語習慣。“我為某某產品代言”的廣告詞已耳熟能詳,在商品的包裝上也常常看到“代言人:某某某”。
(二)我國《廣告法》中對代言廣告規定的矛盾
根據《廣告法》第2條第5款對廣告代言人的定義可知,我國對于規范代言人代言廣告的行為所采用的名稱是代言廣告。這也是筆者贊同的觀點,但是條文卻規定了代言人的行為是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這種冠以“代言廣告”之名,卻有“薦證廣告”之實的做法,有張冠李戴、表里不一之嫌。
三、完善我國代言廣告用語規范的建議
關于完善代言人代言廣告行為的用語規范問題,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三點:
(一)立足本國國情,關注本土資源
正如蘇力教授所言當下中國的法治建設的真正立足點是當今的社會生活,主張關注現實,主張在社會背景下全面考慮法治建設。因此在規范用語時,一定要考慮我國的本土情況和現實背景。除此之外良法要想獲得廣泛的遵守,就必須考慮到公民對法律的認同感,對本民族用語習慣和使用頻率的考察無疑會增加公民對法律的認同感,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律才更為科學,也更貼近生活。
(二)名稱與行為的統一
無論是薦證廣告還是代言廣告并無優劣之分,名稱雖不同但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卻是一樣的: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持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因此既然我國使用“代言廣告”的用語,那么只要這一用語的名稱和名稱所要求的行為是相對應的,就同樣可以向立法者的立法目的無限靠近。
(三)完善代言廣告的相關制度,為代言廣告的實施提供制度支撐
為廣告主的產品或服務代言本無可厚非,但是不加區分、不分真假的虛假代言就有問題。美國的真實原則對代言人的代言資格做出了規定,對代言人的代言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法理上堵住了不符合身份資格的主體進行虛假代言的“漏洞”。基于期待可能性和人的趨利性,這種防范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為了代言廣告的正常實施,對代言主體的資格做更為科學的規定就顯得更為合理。
[1]宋亞輝.廣告薦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司法認定——針對<廣告法(修訂征求意見稿)>第60條的研究[J].現代法學,2009(05):68-77.
[2]于林洋.廣告薦證的法律規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1.
[3]崔恒.政治民主與政府效能的沖突與平衡[D].武漢大學,2010.
F273.2
A
2095-4379-(2016)21-0185-02
崔鳳琴(1988-),女,河南安陽人,貴州師范大學,2014級經濟法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