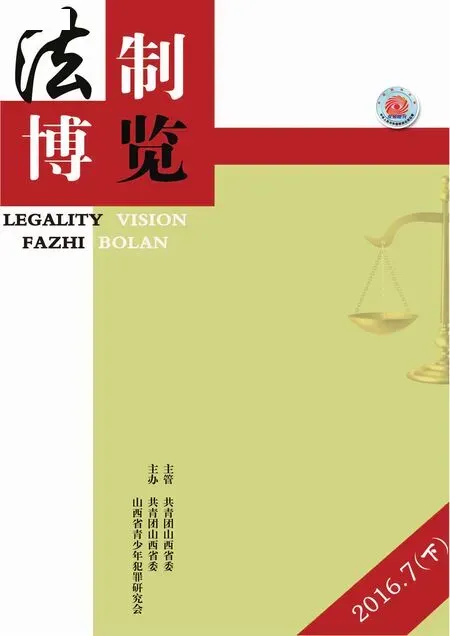淺析中國古代法制的理性特征
——兼評《中華帝國的法律》
汪思薇
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
淺析中國古代法制的理性特征
——兼評《中華帝國的法律》
汪思薇
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中國古代法律經過千年的發展歷程,不僅包含著深厚的文化思想內涵,同時在制度構建上也是獨樹一幟。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得原本嚴峻的刑法體現了人文的關懷,同時嚴密的制度設計也體現了國家對于生命的尊重。所以布迪等人評價中國古代的法律具有理性主義的色彩。
理性;禮法;制度
《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由美國著名漢學家德克·布迪與法律學者莫里斯所著,根據其1960年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開設的“中國法律史”課程材料的加工整理而成。布迪并非專事研究中國法律史,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開設的中國法律史課程是研究古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系列和門類,也因此才有了與專事法律的莫里斯的此項合作。美國高校的法學教育以案例教育為特色,因此本書以很大篇幅在第二部分重點講解分析了從清代《刑案匯攬》中抽取的190篇案例,以加深對傳統中國社會和中國法律的認識。
本書在國外有著巨大的反響,是向國外介紹古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作品。作者以客觀的態度介紹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未摻雜以西方視角可能貶抑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并對清代司法制度如死刑制度予以高度贊揚。這是不可多得的客觀評價傳統中國法律的學術著作。
一、“理性的”法律思想
言及中國古代的法律,“禮源于祭祀,刑源于兵”,是較公認的解釋禮、法源起的說法。之后,禮作為調整人們生活的行為規范,為政治統治者所用,以規范民眾的行為,實現國家的安穩治理。禮是儒家極力倡行的規范,注重個人的內部道德教養,力圖實現人人皆可為圣的大同盛世。“出禮則入刑”,禮在中國古代比法的外延要大得多,可大致將其解釋為一整套的秩序、規范,包括道德教養,規訓懲罰。法在中國古代則主要指刑罰;禮是“禁與將然之前”,法是“禁與已然之后”;禮包含著法律規則,法則是專司懲罰功能的刑事懲罰規則。倫理綱常因為附有懲罰性規則而轉變為法律。自漢代,“儒術”享獨尊,并結合了陰陽、法家、道家等,發展為一個折衷的思想體系,為統治者實現政治統治的長久穩定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禮法連用,援禮入法,“春秋決獄”,以儒家經典解釋法律條文,以經義斷案。到唐代《唐律疏議》的“一準乎禮”,中國古代法律發展到頂峰,儒家思想法律化定型。雖漢以后儒法合流,但從此后主導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法律制度來看,禮、法之間主次分明,禮為治國之重器。
先秦的“儒”、“法”之爭主要是“禮”與“法”、“德”與“刑”之爭。而在布迪看來,雖然儒家所倡導的禮的精神、禮的規范被直接寫入法典,與法高度融為一體。因此中國的法律在其產生之初,即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并且以刑事制裁為中心任務。法律純粹是世俗統治者強制指定并以刑罰要求臣民遵守的規則,其主要目的是維護并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儒家學說提倡禮的等差性、社會身份的巨大鴻溝。法在于修復被犯罪行為所破壞的自然秩序,以回歸自然狀態的和諧。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幾千年,卻是法家取得了隱蔽的勝利——法律的目的在于通過威懾的方式,強迫人民保持良好的行為習慣,實現皇帝的統治意圖,而非恢復被破壞的宇宙和諧。作者認為,從理論上說,帝國時代的儒家學說推崇這樣一種管理良好的社會——一個由等級森嚴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所組成、由賢明睿智的皇帝所領導、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官系統自上而下加以控制的社會。
筆者拙見,作者為西方法律思想直接影響并傳承其精髓的學者,秉承西式思維,對于傳統中國法律的內在精神——“情”、“理”、“法”無法深切體會。“天理”、“人情”、“國法”是古代中國法律思想的核心要素,也是穩定社會秩序的理想模式。“國法”應當是受“天理”與“人情”的引導。三者共同作用于古代中國法律思想及司法實踐,孕育著有別于西方的人道關懷。身兼行政、司法職能的古代社會的中國官員在辦理案件時處理靈活且體現禮法的要求,斷案注重社會普遍的倫理準則。即使造成嚴重后果,但是當事人處于善心,可免予處罰;即便為有損害,當事人出于己惡,應予懲罰。即“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
傳統中國社會以家庭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以血緣為重要的關系紐帶。中國傳統社會又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普通鄉民與土地關系密切,安土重遷,這便型塑了長久延續著的“熟人社會”,法律在民約民俗面前顯得刻板生分。這也突顯“禮”的重要作用,禮使得法律更具有人文關懷。
二、理性的制度
前帝國時期,“五刑”專指五種刑罰:“墨、劓、腓、宮、辟”,其后的各個朝代,五刑逐漸減輕。唐代《開皇律》所確定的五刑為后世沿用,且少有變化,即“笞、杖、徒、流、死”,死刑又分為絞形與斬刑。作為附加刑的刑種有:枷號,刺字,鞭,梟示,拷訊。
中國古代的案件經過嚴格的分級處理的方式,按照案情的嚴重程度予以分別處理。如清代對于案件所判處刑罰的不同而處理機關不同。被處以笞、杖刑的輕微案件,由縣州衙門做出終審判決并執行刑罰。對于被判處笞、杖刑以上刑罰的案件,縣州衙門主持對案件的調查,案件上報至省,由省一級專門執掌司法的按察使受理,按察使對案件的處理意見,須經總督或巡撫的批準。徒刑案在省一級經過處理,案件即告終結,省都督、巡撫將這些案件處理意見匯集后,上報刑部備案。對于流刑案即涉及殺人的徒刑案,總督、巡撫上報至刑部等待判決。而對于死刑案件,訴訟程序則更加繁雜。由州縣主持偵查,將案件調查清楚后經由府上報至省一級,按察使做出處理意見后經總督、巡撫批準并上報刑部復審,由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共同審理死刑案件,即“三司會審”,“三法司”最終將案件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批準,該死刑判決才正式生效。
清代的死刑案件經層層上報至皇帝做批準時,也會有“監候”與“立決”兩種處理方式。“立決”并非立即執行,而是此一決定一經皇帝做出,在此后已無更改的可能。而當案件確定為“監候”時,又會經過“秋審”“朝審”的法定程序。復審的官員為“九卿”,各類監候死刑案件經過秋審或朝審,做出以下四種處理:“緩決”、“可矜”、“存留承祀”,“情實”。
可見,古代中國的法律制度通過嚴密的分級處理,使得關乎生命的案件能夠得到最為審慎的處理,一方面體現了制度設計的理性色彩,同時也是對生命尊重的重要體現。作者對此亦給予高度贊揚:中華帝國具有高度理性主義色彩的死刑案件審判程序,是人類智慧的杰出成果,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創建了有別于西方世界的“正當程序”,可見評價極高。但他也提出了質疑:中華帝國具有高度理性主義色彩的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在經過漫長而審慎的前期判決而進入最終判決階段之時,完全依賴于皇帝本人對事物的認識能力和分析能力,這就導致了權力一體化,不實行分權制、沒有私人的法律職業、因循兩千年以前舊的法律制度、等級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等等弊端。這無疑是中肯而客觀的評價。
誠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中的理性的光輝并不能被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所掩蓋。正如對中國傳統社會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社會的討論一樣,高度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的皇帝也非可以隨意專斷,而即使沒有諸如現代法律一樣精密完整的邏輯,相當一部分皇帝依舊需依規范和制度治理國家。單純說古代社會是“人治”社會未免有失全面。
三、結語
當今中國社會是傳統文化逐漸消散的社會,面對著無孔不入的西方文化的大肆侵略,傳統所留守的陣地日漸縮小。在法律文化領域,自清末以來,中華法系喪失了其存在的土壤,現代的法律制度、法律觀念都是從西方傳入的舶來品。但古代中國在唐代達到其發展的頂峰,成為東南亞國家包括日本所爭先模仿的對象。近代西方科技發展,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并被列強侵略,傳統文化在外力之強迫下被迫改換方向,做出犧牲,救國于危難,潮流之不可抵擋非人力之所能為。曾經之落后于世界,不代表從無輝煌之時。因此,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應當理性客觀,繼承光大其中的優秀精華為現世所用,不應一概予以摒棄。對待西方文化也應冷靜,否則大勢之前,會空有文明古國之名,早已失傳統精華之根,甚為遺憾。
[1]梁治平.法辨[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D929
A
2095-4379-(2016)21-0191-02
汪思薇(1991-),女,湖北隨州人,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