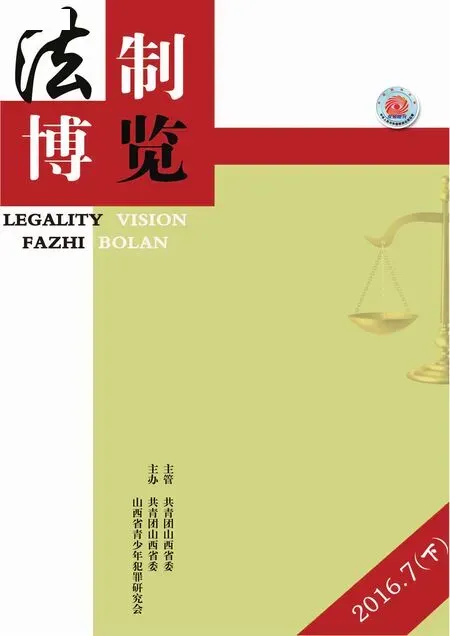芻議臺灣刑事協商程序
王 帶
廣州大學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
芻議臺灣刑事協商程序
王帶
廣州大學法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綱要中均提到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并未規定認罪協商程序,在此通過對臺灣刑事協商程序的探析,以期對我國刑事協商程序的構建有所裨益。
臺灣;刑事訴訟;協商程序
一、刑事協商程序的立法緣由
刑事協商程序發端于美國,體現為辯訴交易制度,它與職權主義的訴訟構造在一定程序上是相沖突的,但目前仍為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所接受。臺灣的刑事訴訟法一直以來傾向于大陸法系傳統,以職權主義為基準,但現在已經開始逐漸朝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靠攏,而我國具有職權主義特征的刑事訴訟法在改革中亦有此趨勢。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是刑事協商制度的典型體現,并為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所借鑒。刑事協商程序的目的在于,通過司法機關對被告的刑事處罰作出一定程度的退讓,以換取被告人自愿認罪受罰的結果,從而大大地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臺灣早在1999年即進行了司法改革,針對減輕法院案件負擔形成了三項協議,即“增設簡易程序中采用略式判決”、“擴大刑事簡易程序”、“酌采認罪協商制度”,但認罪協商制度并未正式寫入刑事訴訟法。2004年,臺灣修訂刑事訴訟法,主要借鑒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以及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認罪協商制度,在眾多爭議聲中增訂了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第455條之2——第455條之11)。2014年,臺灣又對協商程序部分條文(第455條之2)進行了修正。臺灣“立法院”認為增訂該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因為臺灣社會多元化發展后,刑事案件負荷日益嚴重,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為了能夠使得刑事案件審理得以有效進行,對進入刑事程序的案件進行層級分流,允許被告認罪的非重罪案件適用協商程序,以期案件能夠得以迅速審結,也讓法官能夠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處理其他重大、復雜的案件。
二、刑事協商程序的啟動條件
一是何種案件可以適用協商程序?臺灣刑事訴訟法所增訂的“協商程序”并非是全盤接受美國當事人主義模式下的不區分重罪與輕罪的辯訴交易制度,而是配合其改良當事人主義模式下的有限度的認罪協商,僅限于非重罪案件。具體來說,除犯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案件外,均可適用協商程序。由此可見,臺灣的刑事協商程序依然受職權主義的影響對案件的適用范圍有嚴格的限制。
二是何人可啟動協商程序?臺灣的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規定,僅檢察官有權向法院申請進行協商程序,而被告人或自訴人并無此項申請權。當然檢察官申請前應征詢被害人的意見。然,訴訟程序以何種方式進行屬于法院職權,因此該申請仍需得到法院同意,但法院原則上不得拒絕該申請。另外,協商程序之開啟須以被告人認罪為前提,即被告對檢察官起訴的罪名以及適用的法律無異議。由此可見,協商程序并非為某一主體單一開啟,而是由檢察官、被告人以及法院共同啟動,但是檢察官在整個啟動過程當中起著溝通法院與被告的橋梁作用。
三是協商程序于何時開啟?為保障法院審判的公正性,確保被害人的權益,臺灣的刑事訴訟協商程序只能在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者申請簡易判決處刑后,于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才可開啟協商程序。由此可見,即使是在刑事普通程序中,只要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無論是否轉為簡易程序,均可以適用協商程序,但是自訴案件并不適用。
三、刑事協商內容的具體范圍
為確保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保障被告在協商中的自由意志,因此,臺灣的刑事訴訟協商程序是在審判外進行的,法官并不參與其中。檢察官向法院申請進行協商程序得到同意后,審判即暫時停止30日,讓檢察官與被告進行協商,其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事項:
一是被告愿意接受檢察官提出的科刑范圍或者是愿意接受宣告緩刑。因為臺灣的協商程序所作的判決是不經過言詞辯論程序的,被告的權利較普通程序而言亦受到較多的限制。因此,為確保正當程序,科刑范圍應有所限。臺灣的刑事協商程序對被告的科刑以宣告緩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否則法院判決將不受協商程序之拘束。
二是被告向被害人道歉。刑事訴訟是針對特定人的特定犯罪,為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的程序,它較為注重修復被傷害的社會關系,而往往忽略具體個人所受到的傷害。因此,道歉這一形式不僅能夠體現被告的悔罪態度,亦能夠使得被告對被害人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一定的修復。
三是被告應當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的賠償金。被告因犯罪行為而給被害人造成傷害,這種傷害不僅僅需要以道歉的形式在精神上得到修復,更為重要的是能夠讓被害人的傷害在物質上得到實際的修補,雖然金錢無法徹底替代傷害,但金錢賠償無疑是填補傷害較為合理的方式。
四是被告人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并由該管檢察署依照規定提撥一定比例輔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該提撥比例、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由臺灣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規定。被告向國家支付金錢,并用于公益事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為被告對所傷害的社會關系的一種修復形式。
四、刑事協商合意的法律效果
一是協商合意達成的效果。法院對于檢察官與被告的協商合意,經過審查后并無法定駁回之情形,則必須在協商合意范圍內判決。而為減輕法官制作判決書的負擔,可由書記官僅將主文、犯罪事實要旨以及處罰條文記載于宣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并送達當事人、辯護人等。但宣示判決之日起10日內,當事人仍可要求法院制作判決書。
二是協商合意未達的效果。被告可在法院訊問及告知相關權利程序終結前,可以隨時要求撤銷協商合意,但檢察官不可隨意撤回協商程序申請,僅能在被告違反協商合意時,在法院訊問及告知被告相關權利程序終結前可撤回協商程序申請。被告與檢察官協商合意未達時,理當由法院恢復原審理程序,或為普通程序或為簡易程序。
三是協商合意駁回的效果。協商程序中若出現以下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申請,即協商合意未達、被告意思非出于自由意志、協商合意顯失公平、協商罪名為重罪、法院認定事實與協商合意的事實不符、被告有其他較重的犯罪事實、被告可免刑或免訴或屬法院不受理的情形。此駁回裁定是程序上的裁定,在臺灣刑事訴訟法上亦不可以提起抗告。
四協商判決的救濟。協商判決的上訴是受到限制的,原則上不得上訴,但是若出現下列情形之一均可上訴,即協商合意未達、被告意思非出于自由意志、協商罪名為重罪、被告有其他較重的犯罪事實、被告可免刑或免訴或屬法院不受理的情形。第二審法院若發現上述情形,則應撤銷原判,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的程序重新審理。
五、刑事協商程序與其他相關規則
一是協商程序與告知義務。臺灣的刑事協商程序為審判外協商,因此法官并不能介入協商程序,但是為了保障程序的正當性,確保被告放棄相關訴訟權利的自愿性,法院則負有告知義務,即法院應在接受檢察官協商程序申請10日內,訊問被告并告知其所認罪名、法定刑以及所喪失的權利,如受公開審判的權利、保持沉默的權利等等。
二是協商程序與辯護權。在協商程序中,雙方當事人為被告與檢察官,相較于熟知法律的檢察官而言,被告處于弱勢地位,若無辯護人的幫助,則其意志自由可能受到不當的束縛,而被告的自白任意是協商的前提。因此,在被告表示愿受科刑逾有期徒刑6個月,且未受緩刑宣告,亦未選任辯護人的,法院應為其指定辯護人,但辯護人在協商程序中所述意見不得與被告明示的協商意思相反。
三是協商程序與證據規則。協商程序之進行是以被告認罪為前提,因此被告會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陳述,如若雙方協商合意并未最終達成,而允許檢察官在指控中以被告在協商程序中的陳述作為對其不利或對其他共犯不利的證據,將使得被告未敢于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合意。因此,被告于協商過程的陳述不具有證據能力。
[1]張麗卿.驗證刑事訴訟改革脈動[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2]龍宗智.徘徊于傳統與現代之間——論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J].政法論壇,2004(5):80-92.
[3]王小光,李琴.臺灣地區認罪協商程序的引進和運作情況分析[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2):111-118.
[4]李婷.我國臺灣地區刑事協商程序初探[J].公民與法,2010(2):61-64.
D925.2
A
2095-4379-(2016)21-0197-02
王帶(1991-),男,漢族,湖南衡陽人,廣州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訴訟法學。